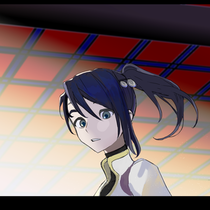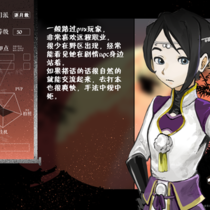作者:蓝湾
——你知道棘轮机构吗?由棘轮和棘爪组成的一种单向间歇运动机构,棘爪卡着棘轮,使其不能逆转。世界就是这种东西,记忆、生命、星球,无数无数存在都是棘轮。人类自诞生之初就想要弄明白它的结构,想要把一切都转化为可操控的齿轮。然而最终失败了,人类像笨拙的孩童拆闹钟一样,把世界拆解重装了,没能拆除棘爪,反倒多出了新的卡在大齿轮上。
世界变成了咔咔作响的、走不准的闹钟,在这样的前提下发生的故事。
一、
恒星的光辉从窗外照进来,银色头发的少年一下子睁开眼睛。
“早上好!”仪式性地说过一声之后,他起身换衣服叠被子,抱着脸盆去院子里刷牙洗脸,然后去东厢房烧火准备早饭。院落里静悄悄的,他拧紧水喉后还特地站着听了一会,只能听见正房里另一个人的呼吸声。
他名叫彦博,有一双金色的眼睛。
然后是打扫庭院。主院落一共种了两株海棠,两株玉兰,后院一角有一株很大的臭椿,前院贴着正座房墙根有一排丰花月季。他一边扫一边数落叶的数量,倒进簸箕里,然后一块拎上昨晚放在门口的垃圾袋出了垂花门。系着围裙的老妇人已经从倒座房出来了,向他微微欠身。
“杨妈。”彦博把垃圾袋递给她。杨妈单手接过,利索地开了大门的锁:“您没必要亲自打扫,都说了让我们来就行。”
“没事,我喜欢每天看看它们。”
彦博目送杨妈推门出去,一手把他早就挑出来的可回收物放进腹腔的熔炉中,一手拎着处理起来更复杂的垃圾上了传送带。
到目前为止,都与昨天一样。不仅昨天,前天、大前天、大大前天……都一样。
要说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同,就是在回忆上次下雨是哪一天的时候,细节开始模糊了。已经过去了28天,他默算了一下,那么就是从用遗忘周期计算时间开始,到现在一共过去了16 384天。
彦博搬张马扎坐在院子里,一边清点记忆一边吃早饭。从遥远的恒星上照射过来的光芒刺得少年眯起眼睛,彦博想起10天前曾指着恒星问他那叫什么名字。
“只是一颗普通的出于主序星阶段的恒星,要叫做太阳也行。”当时他随意地说,垂着手,也没有触碰的打算。
似乎越来越经常给出这样含糊不清的答案了,不便于记忆。彦博发现这些天的记忆中除了每日定规,其余多是大片大片的空白,确信了这一点。他盯着太阳(便唤做太阳吧)发了一会呆,扭头朝正房唤了一声:“明!”
“嗳。”几乎就在同时,黑头发的男人打着哈欠从屋里出来。
名字是彦博随便喊的,反正这个名字只对他有意义。反正在彦博产生这个呼唤的想法的时候,明就已经知道了,喊的是什么也没有所谓。明抓着睡乱了的头发走过来,抬手盖住彦博的眼睛。
“很痛啊,以后不要直视太阳,会灼伤的。”顺带了一长串关于强光刺激和其导致的短暂失明、角膜损伤、偏头痛等等,的相关知识。
两人之间有一条能传送所有想法和感受的链接。信息无条件地从彦博流向明,但是倒过来的话需要肢体接触,并且只有知识性信息。
“杨妈头上有像角一样的东西。”尽管知道在说话之前对方就知道了内容,但是彦博还是习惯用语言表述,“那是什么?”
“那是山羊角。”明也习惯了等他说完再回答。
彦博皱起眉。明总是用另一个他不了解的概念来说明概念,一副懒得说清楚的样子。
“山羊是什么?”
“一种动物。”
“动物?我记得是,存在于星球上的一种生物形式……那,我们有山羊吗?”
“以前有。”
“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因为它们死了。”
为什么会死?彦博想问,但是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记得,19天前因为玉兰落下来的黄叶问过这个问题,当时明瞥了他一眼,按着他的手灌进来了数以G计的文字量。
当时彦博足足眩晕了好几秒。以他的运算能力,这本不应该,一是因为先前估计有一两年没有从明那里获取这么大的信息量了(并不记得,从身体反应估算),二是因为,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那些描述都很复杂,彦博理解起来很费劲。也是因为词汇量不够,有很多概念他都不懂。不懂的东西太多了,这是因为明,很多他根本没打算讲,只等着彦博什么时候停止提问。知识的链接完全受明的主观控制。
就像现在一样。明随意地把垂到锁骨的头发拢到脑后,用手腕上的橡皮筋扎起来,然后抱胸靠墙看着他。蓝色的眼睛半垂着,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还想问什么?”
彦博半张着嘴努力思考。明耐心地等着,顺带低头接过家养小精灵递过来的早饭:“啊,谢了。”
彦博在明耐心告罄转身回屋之前叫住他,不是用开口说的方式:“为什么杨妈头上有山羊角呢?”
“你一直没有改过,就保持原状啊。”
“是说,为什么是山羊角?有什么含义吗?”
“只不过是神话、传说,从前人写的故事罢了。”明的脚下稍微一顿,便迈进门槛到阴影里,“现在没有意义了。”
彦博在院子里四处转,挨个检查每个细节。虽然三进的四合院不算大,但是也受许多自然规律的影响。因为明称得上刻意的沉默,彦博稍不小心就容易忘掉那些常识,必须时常复习。
搬马扎坐在月季花丛前修剪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叶片上出现了黄褐色的小斑点。还在回忆确认昨天是否有过征兆的时候,就听见脚步声,然后明戴着白手套拿着一个喷壶从垂花门过来。
“你看这个!”虽然没有必要,但彦博还是把月季的患处指给他看,以示震惊。
“是锈病。”明蹲下身,左手搭在少年后颈上,“每半个月喷一次敌锈钠溶液或是粉锈宁溶液,一般二到三次就可治愈。”
关于溶液组成的知识和其他相关信息一并经过链接流到彦博头脑中,于是从喷壶底部凭空涌现出液体来。
“确实慢了。”明转动手腕摇匀,然后喷到月季的叶片上。
“因为你很久没让我造物了啊!”彦博一边拿出小线圈本记笔记,一边不甘心地说。
“你自己决定就行,没必要经过我。”明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把喷壶递给对方,“还以为你不会记笔记,毕竟半个月是15天,没有超出遗忘周期。”
“以防万一,我不想看到月季死掉。”彦博伸手摸了摸一朵今早刚开的花,探过身嗅了嗅,“我每天都在照顾它,为什么会生病呢?说是雨季高发的病,现在都秋天了……”
“应该是浇水浇多了。”
“我浇水也很正常啊!”彦博比了个手势以示精准。
“啊,是我多浇了,我的错。”明懒散地说,拨弄着一朵快开败的花,落了一手柔软的花瓣。
疑惑和不解顺着链接流过去,彦博没有出声,但确信对方肯定知道了。他应该之后会解释吧,肯定有原因,彦博想着就把这事丢到脑后,顺带整理了一下笔记。
明沉默着。关于情绪的链接是单向的,彦博逐渐察觉到这种缓慢凝固的气氛,但不知为何,不安地扭过头。
“要除去可能导致生病的因素吗?”黑发的男人垂着头,低声说。
“……那能做到吗?”彦博盯着他的脸,敏锐地抓住了某个核心,“是让月季不再变化吗?那它就没有生命了吧?”
明不知是笑还是叹气,轻轻摇头:“行,听你的。”
今天天气很好,彦博翻了翻笔记,问要不要晒被子。明说你决定,彦博于是又从笔记中翻出给家养小精灵输入命令的部分。
“直接说就行,晒被子又不复杂,这部分的动作程序是内置的。”明叹口气,从竹躺椅上撑起身,拉过他的手把全部50个预设动作的口令传送过去。
“我在复习。”彦博用说出口的方式强调,手上乖乖地记笔记。
明躺回去,把书盖回脸上。那是一本很薄的小说,封面上的文字并不是彦博常用的那两种。他在书架上找了找,查到当时的笔记,上面写着那是法语,意为“人类的大地”。
当时,除了制作一本书需要的信息,明还摸着他的头把小说的翻译版也通过链接讲了一遍。但是笔记没有把全文抄下来,为什么不抄录呢?28天一定是够的,看页数大概5天就行。
彦博忽然怨起那时的自己来。看笔记知道当时获取的信息比较多,记录花费时间,于是舍弃了这本书。即便知道,还是怨着:毕竟明已经很久没有给他读书了。
尤其是现在,即便自己正在这样想,那个人也没有反应地睡着。真的在睡吗?不知道,这很难看出来。彦博盯了一会,忽然觉得泄气,这是在怨什么?直接说让他再讲一遍,那他就会答应吧。
只要说出来就行。彦博忽然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今天要出门吗?
啪嗒,小说滑落到地上,明像是惊醒一般坐起来,吃惊地扭头看向坐在旁边的少年:“今天的素材够了吧?用来作记忆的锚点的话,算到下一个28天都够了。”
彦博点点头,今天比起前一个遗忘周期,发生的事已经够多了。但是,“遗忘周期不仅仅是用来算日子的吧?从定义上来说,是用来清空记忆的。”
他仰起头,金色的眼睛亮闪闪的,“先得有记忆才能清空吧?得发生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事情,不出门的话每天都差不多。定义给了这么长的遗忘周期,就是让每个周期都发生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才对。”
明没有说话,在没有灯的室内瞳孔反常地扩散开,蓝色的虹膜变成薄薄的一个环。过了许久,他才轻轻地吸口气:
“你……”
“我想出门。”
说出来了。不可思议地,好像语言真的有这么大力量一样,明撑着额头露出被打败了的表情。这是答应了吗?好像是答应了。没问题吗,很容易能察觉到他并不想出去。但是……
“你决定就行。”明低声说,像是撑起一团没醒好的面那样站起身。
“真的?”彦博没反应过来,就愣愣地看着他伸出手,贴到颈侧。温暖的信息流从肌肤接触的地方扩散开。
塑料圆罐子出现在少年手里,明单手拧开盖子,然后托在手上示意他自己涂。“油箱要加满,电池估计也没电了。现在干燥,需要涂些润肤露……要做些准备。”男人喃喃着说,看向院子里的树影,“开车估计比较久。”
TBC

标题:【梦游记】《吃饼干的怪物》
作者:回音壁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玛莉娜。她的皮肤又白又嫩,就像最新鲜的奶油,她的眼睛又黑又亮,就像水灵灵的葡萄,她的头发是漂亮的棕色,就像上好的巧克力,她的嘴唇鲜红,就像新鲜的莓果。玛莉娜和奶奶一起住在大森林里,可是她一点都不寂寞,因为整个森林都是她的花园,小动物们是她的朋友。每个月,奶奶都会用石头的烤炉给她烤一炉饼干,奶奶烤的饼干又香又脆,可好吃啦。玛莉娜总想把饼干吃个饱,可是奶奶每天只让她吃两块,不过玛莉娜也不嫌少,因为这样就可以一个月每天都有饼干吃啦。
这一点,是奶奶每个月一次烤饼干的日子,玛莉娜一个星期前就盼着这一天啦。可是,这天早上,奶奶有事出门去了。玛莉娜很失望,刚出炉的饼干可是最好吃的。
到了天黑奶奶也没有回来,玛莉娜一个人上床睡觉了,玛莉娜是个乖孩子。可是,玛莉娜突然闻到一股饼干的香味,她一下就从床上坐了起来。难道是奶奶回来,连夜烤了饼干吗?唉呀这个不行,奶奶的身体不好,怎么能夜里干活呢,饼干明天再烤也是一样的嘛。
玛莉娜闻着香味来到厨房,发现奶奶不在这里,只有烤炉里散发出一阵阵的香味,可是烤炉明明是关着的,摸一摸,还是冷的啊。
她听到有一个声音说,快来吧,快进来,快来有许多许多饼干的好地方吧。玛莉娜细心一听,声音居然是从烤炉里传出来的。
奶奶的烤炉非常大,一次能烤好多好多饼干,能烤两个人吃一个星期的面包,小小的玛莉娜钻进去也没有问题。可是,不能钻进烤炉里去呀。
那个声音又说,没关系,这是梦里呀。
玛莉娜恍然大悟,既然是梦里,那没有点火的烤炉居然发出饼干的香味就说得通了。可是,就算做梦也不能钻进烤炉里呀。
这时,她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玛莉娜抬头一看,原来是好朋友燕子姐姐。燕子姐姐飞到烤炉上面,绕着圈子,在叫玛莉娜。玛莉娜抬头一看,原来有一股热气正从烤炉上面冒出来。玛莉娜和燕子姐姐坐上这股热气,就像气球一样向上飞了起来。她们穿过了云彩,穿过了星得,天上越来越冷,然后又越来越热,身边变得像黑漆漆地,什么都看不见了。最后,啪的一下,玛莉娜和燕子姐姐来到了一个明亮亮、热腾腾的地方。
玛莉娜发现这是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里,大到能把她和奶奶住的房子整个装进去。地是又白又光滑的,亮亮的反光有些刺眼。房间里热得就像是夏天的中午、在厨房里看奶奶烤饼干时站在烤炉前一样。
玛莉娜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有好香的饼干的香味,她定睛一看,眼前的地上摆着好多巨大的饼干,大得像一张桌子,香气就是从这些饼干上散发出来的。
唉,这么大的饼干,一定是只有梦里才会出现吧。玛莉娜想着,向饼干的方向走了走,突然,头发被燕子姐姐轻轻啄了一下。
“对啊,就算是做梦,也不能吃来历不明的饼干啊。”玛莉娜想起了奶奶教她的事。再仔细一看,那些饼干上嵌着坚果和水果,看上去就像眼睛、鼻子一样。玛莉娜有点害怕,就往后退了一下,突然觉得踩到了粘粘的东西。低头一看,地上写着好多好多不认识的字,那些字居然都是用糖浆写在地上的,怪不得粘粘的。
突然,玛莉娜听到旁边传来一个声音:“好大的饼干!我要吃啦!”她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大男孩,头发像乱草一样,穿着很好的衣服,但看到饼干,露出了一副没教养的馋样。
“这些不能吃呀。”玛莉娜说。
大男孩露出一副高傲的神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小屁孩快滚开,这些饼干一看就是给我的,我要全部吃光。”
玛莉娜劝不住大男孩,急得快要哭出来了。燕子姐姐早就躲到玛莉娜背后去了,这样的男孩肯定会欺负小动物的。
大男孩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块饼干,坐在地上休息。毕竟,那块饼干有桌子那么大呢。
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噗哟、噗哟的声音。转头一看,有一团白色、圆滚滚的东西正一跳一跳地过来。仔细一看,白色的东西软软的,就像面团一样,上面镶着坚果,看起来像一对眼睛,红棕色的糖浆披在它身上,就像衣服一样。
玛莉娜明白了,这就是没烤过的饼干胚呀。这个饼干 胚居然是活的,幸好刚才没有吃那个饼干啊。
白色的东西来到两人面前,噗哟、噗哟地说着什么,它没有长嘴,也不知道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玛莉娜赶快往后躲了躲。白色的东西跳得更急了,它对着大男孩发出一连串噗哟、噗哟的声音。大男孩唉哟一声,动作奇怪地站了起来,看上去就像奶奶哄玛莉娜开心时拿出来的木偶一样。
“唉哟,我的身体不听使唤了。”大男孩说着,不由自主地跟着白色的东西向房间的另一边走了过去。玛莉娜有点害怕,但她也不想一个人留在这里,就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只见白色的东西带着他们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大房间的门口。里面发出很多噗哟、噗哟的声音,往里一看,好多白色的东西在开会呐。
带他们来的那个白色的东西伸出一截,向房间里面指了指,只见房间正中间有一个白色的东西,比其他的都要大,它的身上披挂着大红色的果酱,点缀着纯白的奶油,最上面金色的蜂蜜块闪闪发光,就像王冠一样。
“这要是饼干,一定很好吃呀。”大男孩咽了咽口水。
白色的东西不知从哪弄来一副刀叉,递给了大男孩。大男孩接过来,想了想,突然把刀子插进了白色的东西的身体。白色的东西发出一连串噗哟、噗哟的声音,好像很惊讶的样子,但很快就不能动了。只见它白色的身体变得焦黄,变得又硬又酥,很快就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原来这样就能变成饼干呀。”大男孩很开心,拿着刀叉就冲进房间,一边冲一边喊着“我要吃那个最好吃的!”
玛莉娜吓得呆住了,幸好燕子姐姐啄了她一下,她才清醒过来。只见一大群白色的东西身上披着坚硬的杏仁、拿着刀叉冲了过来。玛莉娜吓得转头就跑。
这里有许多很大的房间和很长的走廊,玛莉娜跑着跑着就迷路了。许多白色的东西一跳一跳地跑来跑去,好几次差点抓到了她,但她机灵地躲过去了。有一次,白色的东西已经跑到她面前了,幸好她灵机一动,把手脚都缩到了衣服里面。白色的东西凑近过来,轻轻碰了碰她,她的皮肤又白又软,就像奶油一样,那些白色的东西不知道她是不是同类,围着她噗哟、噗哟地讨论起来。这时,远处响起大男孩的喊声:“这个饼干没烤熟啊!”那些白色的东西就丢下她跳着走了。
“这可怎么办呀。”玛莉娜说着,“快醒来啊快醒来。”她念着自己发明的咒语,可是怎么也醒不过来。她看了看窗外,天色已经开始发亮了。这里本来已经很热了,现在又变得更热啦。
“唉呀,这怎么办。要是天亮了的话,这里不是热得要死人了吗?”玛莉娜说。她明白为什么这些白色的东西会变成饼干了,一定是白天太热烤着他们,烤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饼干了。
可是,玛莉娜不想变成饼干呀。而且她是人,就算被烤,也不能变成饼干的。
燕子姐姐停在她的头上,轻轻啄了啄她,然后又飞了起来,在她面前盘旋。
“燕子姐姐,你认得路吗?”玛莉娜开心地说。她不知道,燕子可是鸟儿里面第二擅长认路的呢。
燕子姐姐在前面带路,她们很快就回到了最开始来的那个房间。地上用糖浆写的好多的字已经干了,玛莉娜突然看到,那许多许多字的中间,有一个糖浆画的圆圈,正是她来到这里的地方。
玛莉娜小心地凑过去,没有踩到地上的字。她看到圆圈的中间,用糖浆画着一扇门。原来,她就是通过这扇门来到这里的。可是,糖浆画的门把手已经被大男孩踩花了。
“没有门把手,是不是门就打不开了呀。”玛莉娜担心地说。这么一会,天气又热了一点,玛莉娜觉得自己就像是要被扔进烤炉一样了。
突然,她听到一个噗哟、噗哟的声音,原来是一个白色的东西发现了她,正急得原地跳来跳去呢。
玛莉娜灵机一动。“对不起啦!”她大声说着,冲到那个白色的东西面前,把它的衣服撕了一块下来。这些白色的东西的衣服都是红棕色的糖浆啊!
玛莉娜捧着一团粘稠的糖浆,冲到那扇画出来的门前,用糖浆赶快画了一个门把手。唉呀,太神奇啦!这扇门一下子就变成真的了。
玛莉娜拉开门,只见里面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眼看周围越来越热,空气都开始晃动了,玛莉娜一咬牙,闭着眼睛向着门里跳了下去。
嗖的一下,玛莉娜觉得自己好像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了下来,她一下子睁开了眼,惊醒了。原来,她不知为啥在烤炉前睡着啦。燕子姐姐趴在她的头上,迷惑地叽叽叫了两声。
“唉呀,好可怕的梦,这下子我可不敢吃饼干啦。”玛莉娜拍拍胸口说道。
可是,天亮之后奶奶烤了饼干,她就把这件事忘掉啦。
免责mode: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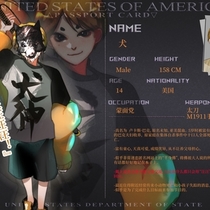

作者:舞舞舞舞舞舞舞
1 齐安托托与小屋的井
齐安托托是个令女仆长无比头疼的孩子。
不知道他今天受了什么刺激,放学回家就闹别扭,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我不吃饭了”“我要绝食”“我要饿死自己”。女仆长自然不敢怠慢,急忙把这事告诉了齐安老爷,也就是托托的爸爸。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让他把这些全部吃下去,一块渣都不能剩!”
女仆长哪敢什么方法都用,齐安托托可是齐安老爷最宠爱的独生子,要是她弄疼了少爷,少爷告一句状,就能让她全家丢了工作。这事她不能自己出手,转头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少爷的陪玩女仆梅莉。
梅莉是大宅另一个女仆的女儿,从小就被当场女仆教养,她4岁就做少爷的玩伴,6岁就开始学习打扫,虽然只有10岁,却也是很多新人女仆的前辈了。虽然女仆不可能和少爷成为朋友,但她好歹和少爷年龄相同而且相处得久,如果她都搞不定这事,那就没人能搞定这事。
“托托,你就不能吃点东西吗?不吃晚饭晚上会难受的,你看今天的主菜是番茄炖牛肉,配的是刚出炉的奶油烤面包片,汤是奶油牡蛎,还有香草冰淇淋和巧克力蛋糕。”
梅莉的小胳膊端着丰盛大餐的托盘,在少爷门口恳求着。她不是厨房女仆,也不是餐厅女仆,平时她是接触不到这些食物的。离大餐如此之近,这是第一次,梅莉报着菜名的时候忍不住吸了口口水,而这声口水,被少爷敏锐地捉住了。
“你想吃的话就自己吃掉吧,我是不会吃东西的。”
“但是,这是你的晚饭啊,我们佣人是不能吃主人的东西的。”
“为什么不能?你只要把空盘子带回去就可以了,谁在乎是谁吃的?”
“但是这些东西里都有香料,如果我吃了,让人闻到我嘴里有主人吃的东西的味道,我会被打的,我的妈妈也会被打的。”
“那倒掉不行吗?”
“不,不行,妈妈说浪费粮食会糟报应的。”
“那我来。”
话音刚落,房门被粗暴地打开,托托夺过梅莉手里的盘子,将盘里的东西一碟碟地倒进了壁炉。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炭火被汤水一浇,“呲”地一声化作了一缕青烟。
“你去拿点新炭,重新点上火,就当我刚刚把饭吃了。”
梅莉的脸上掠过一丝心痛,但少爷的指示比这更重要。她麻溜地跑去了炭房,拎来了一桶新炭。她有点心疼地把炉里的旧碳收进碳桶,把剩汤抹干,把新炭像金字塔一样堆在还有点潮湿的壁炉里,小心地把最顶上的碳点燃,小小的火苗在壁炉里烧旺,房间里充满了番茄汁和奶油汤的味道。
梅莉吸了吸鼻子,提起了炭桶,她装成碳桶有点重的样子,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外挪,因为这味道实在太香了,她想在房间里多留一会。
“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吃饭?”
梅莉想都没想就点了头。
“因为我的父亲是个自私、肤浅、粗俗的人渣。”
梅莉愣了愣,不知道该点头还是为雇主说什么。仆人是不能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的,但现在是一名主人说另一名主人的坏话,反驳少爷会惹少爷不高兴,附和少爷如果被人听到自己肯定没有好果子。
幸好少爷没有注意到梅莉紧皱的眉头,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现在我们出门必须戴面罩,都是他的问题。”
梅莉以肉眼无法分辨的频率点了点头,主人出门要为他们备上干净的面罩,这也是女仆的工作之一。
“我们的空气里都是煤烟,我们在街上能看到很多穷人没有面罩戴吧,每天都会有人因为吸入了过量的煤烟死去。”
这不算是主人的坏话,梅莉可以出声附和。虽然她从小在大宅长大,但出门买东西的工作她也做过。仆人当然是没有面罩的,她知道每次大口喘气时喉咙那种刺痛瘙痒的感觉。那些没有大宅住的人,那些需要开门开窗做生意的人,他们时时刻刻都要吸入这些让喉咙瘙痒的空气,时间一长会死,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家是做煤炭生意的你知道吧。”
梅莉点头。
“这些煤都是我父亲卖出去的。我们能住大宅,吃好吃的,有面罩戴,都是因为他在卖煤,他卖煤给别人烧,烧出那么多黑烟,赚那么多钱,代价是那么多人因为煤烟死去——不只是人,动物也是,每天都有动物从天上掉下来,因为吸了煤烟。我们老师说,人类再不停止烧煤,整个世界都会变成煤炭。他前两天还帮助朋友制作灭绝鸟类的标本,那翅膀上都是细小的煤渣。如果我们不停止卖煤,我们也会沾上煤渣死去的。”
“我,我生来就是托托家的佣人,因为托托的爸爸死去,我,我不怕。”梅莉虽然说着不怕,但她的声音有点颤抖,她怕说错话惹少爷不高兴,但很显然这句话惹得少爷很不高兴。
“走走走,没读过书的人,愚昧,无知,肤浅!”齐安托托摁住梅莉的肩膀,把她推出了房外,碰的一声重重地甩上了门。
托托发完了脾气,肚子开始有点饿了,但他不想看到梅莉的脸,也不想看到家里的其他人。他锁了房门,将一张椅子拖到窗边,打开窗,从窗子爬出了屋外。
九月末,天已经凉了。齐安托托从烧着壁炉的屋里出来,只穿了件单衣。太阳已经落山,一阵风吹来,把齐安托托冻得直跺脚。但他是踩着凳子才翻出屋外,窗台有他一头高,要回屋去,只能走正门,但那样肯定会遇到他不想见到的人。
齐安托托记得大屋后面有个小屋,他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但偶有看到端着盘子的女佣进进出出。齐安托托猜那里是存放食物的小屋,里面应该会放着一盘盘的炖肉、炖菜、蛋糕和巧克力,为了让炖菜保持热乎乎的口感,里面也会烧炭,不让菜凉下去。
真是离家出走的绝佳住处。齐安托托猫着腰,在花园的灌木丛中窸窸窣窣地穿行。小屋近在眼前,齐安托托刚直起身,就听到“吱嘎”一声开门声。
托托立刻蹲下身子,亏得夜色,他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妈妈,我是不是该,去做一个打扫女佣或者干脆做一个和你一样的垃圾女佣?少爷说话我听不懂,我说的话少爷不爱听,我以前以为我可以永远在少爷边上,但我现在,光是不惹少爷生气就,就已经很难了。”
从小屋里出来的是梅莉,和她一起的是她的妈妈。
“你惹少爷生气,是因为你说了不该说的话。和少爷、和老爷说话都要记得,可以不说的话就不要说。你以为你说的是好话,但他们不一定想听你的好话。你只需要点头同意,在他们需要附和的时候说两句附和的话。其他的东西,能不说就不说。”
“但,但以前我们明明无话不谈……”
“以前你们都是小孩子,小孩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现在他是少爷,你是佣人,怎么可能像以前那样说话呢?你该学我们和老爷说话的样子,那样才是一个佣人的样子。”
梅莉抽了抽鼻子,嗯了两声。
齐安托托看着两人走远,一溜烟地窜到了小屋门口。小屋的门没有锁,这里看似是个谁都可以进去的地方。齐安托托推开门,闻到屋里有一股番茄的味道,这和齐安托托的猜想不谋而合。
齐安托托的肚子咕咕叫着,催促他赶快进去用餐。番茄炖牛肉、奶油烤面包片、奶油牡蛎,还有香草冰淇淋和巧克力蛋糕全都是齐安托托喜欢吃的东西,把它们倒进壁炉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倒完了以后才有点后悔。
齐安托托一头钻进屋里,但屋里却不是像他想的那样生着壁炉,摆着大餐。
屋里没有灯,只有屋子的中间有一处冒着黄色的亮光。齐安托托看清楚了,那是一口一米多宽的井,井下泛着黄光。
“喂——”
齐安托托往井里喊着。
“喂——”
“喂——”
“喂——”
齐安托托的声音又从井里冒回来。
“喂——”
齐安托托又叫了一声。
“喂——”
“喂——”
“喂——”
又是齐安托托的声音冒了回来。
喊了两声,齐安托托觉着无聊,正要从井边离开,这时,他从井里听到了不同于自己的声音。
“喂——”
这时另一个男孩的声音,比齐安托托的尖很多。
“——还有人吗——”
齐安托托一个机灵,在井口探出脑袋来。
“有人!上面有人!下面有人吗!”
齐安托托喊道,几声回声响过之后,底下传来了尖声的回答。
“有人!有人的!”
齐安托托从没见过有声音从井底传上来的,兴奋地又往井里探了探。
“我叫齐安托托——你叫什么——”
“我叫——”
“我没听清——你叫什么——”
“叫——”
“你再说一遍——”
齐安托托往井里不停地喊着话,喊得嗓子发痒,大力咳了两声,只觉得脚下一空,整个人倒栽着翻进了井里。
TBC
2021.1.31版
作者:魇
第一次在工作中注意到那个人是在两年前,虽说时间间隔不算长,但那时是第六历的第九年,而现在已经是第七历了,规则更新变动了不少。
当时我怀着指标内的第五个孩子,不知是精子还是环境的问题,早孕反应非常严重,动辄就想冲进厕所伏在洗手池边呕吐。那天我刚刚工作半个小时就开始恶心,跟主管请示得到允许后便挂上“暂停服务”的牌子,一边匆匆向厕所走,一边内心暗暗感激我的主管还算宽容,总能允许孕妇这些琐碎的要求。隔壁组的闺蜜跟我说过,她怀指标内三胎八个月时,胎儿过大压迫膀胱,经常想去厕所,她的主管不但严格遵守“每日如厕四次”的规章制度,还不让她用成人纸尿裤,因为“那样的话你会有一身尿骚味儿,哪个被服务对象会愿意接受这样的服务?”想着闺蜜惟妙惟肖地模仿着她的主管——一个五十七岁的精瘦女人——的样子一手叉腰一手扬在半空中挥舞,我不禁笑了出来。
然后我就感受到一道目光穿过大厅熙攘的人群,准确地投射到我身上。我下意识地回望,发现一个男人站在那里,看着我。他迎着我的目光,笑了笑,露出泛黄的牙齿。我感到一阵恶心,不知是那泛黄的牙齿还是孕期分泌的激素或者二者都有。我低下头,快速跑进厕所开始干呕。
我没有把这件事说出去,作为一个女人,在满是男人的地方被注视是理所应当。员工手册上这样指导我,所有的主管也做过相应的提醒,我本该对此习以为常。但不知为何,我一直记得那个男人和他泛黄的牙齿,还有伴随而来的、无法抑制的恶心。
在前天,我又遇到了那个男人,在我的工作隔间中。
我的工作很简单,与其说是陪伴聊天不如说是倾听,像我这样未完成怀孕指标的女人也很难完成需要较重体力或者更多精力的工作。能来到我这里的男人,大多只想把他内心的想法一股脑地倒出来,糊在对方脸上,然后转身离开,投身到他们认定的宏伟事业中去。在看似感情真挚实则心不在焉的谈话工作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在我的位置上哪怕坐着一只内嵌初级人工智能的垃圾桶,工作成果恐怕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可能会表现得比我更好,毕竟垃圾桶不会恐惧畏缩恶心头晕,能从容应付所有对象。而我,每天面对各种类型的男人,脸上挂着培训出来的职业表情,态度就算再端正,也难免会因为各种原因表现出那么一丝丝的不近人情。
比如说此刻,再次见到那个男人露出泛黄的牙齿时,我小心地扶着肚子,往后欠了欠身。
那个男人大喇喇地拉开椅子,在我对面坐下,眼睛在我脸上来回扫着。我反射性地露出职业微笑,坐好,按下计时器,摆出“我在听”的手势。男人没有立刻开腔,又打量了我一阵,才咧开嘴,又露出泛黄的牙齿。“我记得你。”他说,“你喜欢我,对不对?”
我开始反胃了,其实这一胎的早孕反应并不严重,但孕期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我努力地把这种感觉压下去,微笑着开口:“对不起,先生?”
“第六历,我来这边交点数。”那个男人说,“大厅里人那么多,你只看着我一个,还对我笑。”他双臂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伸着脖子看我。“你笑起来真好看,怎么笑都好看。”
“谢谢。”我说,“怎么称呼您,先生?”
“我的编号是B-2898670,朋友们叫我‘阿零’。”他说,“但是你不一样,你可以叫我——”
“零先生。”我小心地打断他,做了个“请理解”的手势。
“哦——”那男人拖着长音,“明白明白,不能提不能提,大家都不容易。”他向后靠在椅背上,伸直手臂,手指有意无意地对我的胳膊够去。
“零先生是准备要去‘熔炉’了么?”我说,员工守则第八版标准话题一,兼备补充赞美。“能下定决心去‘熔炉’的人,是这世界上最无畏的人。没有你们燃烧自己的生命为全人类功能,人类将陷入无边的黑暗。”
“什么无畏不无畏的,点数差不多,就去呗。”男人说,“第六历我的点数还够在排污工厂,但是干排污啊,你懂吗,就是操纵机器人去清理排污渠什么的。回收回来的机器人一身都是味儿,带着我身上都是味儿。”他摇着头,装作不经意地瞄着我,而我则适时地露出很感兴趣的表情。男人立刻兴奋了起来,张开手比划着:“有一次机器人从排污渠里捞出一把这么长的虎钳!我上交了,后来给我返了大约值我干一个月的点数,我休息了一个月!”
“是古董吗?”我问,还是有点好奇的,但不补上一句赞美可对不起我近十年的工作经验。“您可真厉害!”
“嗨,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老虎钳。”男人说,“后来有干维护治安的同蜂元朋友告诉我,有个干钳工的,为了少上班,逼他朋友转让点数,结果朋友也是倔,咬死了命能给点数不能丢,然后……”
“然后?”
“然后我清了那个干治安的朋友吃了顿饭,还休息了一个月嘛。”男人又笑起来,“那一顿饭让我少休了一天,有点儿亏。我管他死不死呢,早知道只是一件案子的证物我就不请客了。都怪那个朋友,非得说真相很重要,值那一顿饭。”
我虽然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也跟着他笑。“您真的是个幽默的人,又大度。”
男人摆摆手:“这都不算什么,我的工作很乏味,平时也少跟人打交道,除了来这里几乎都看不到女人。”他盯着我看,继续笑,“你的工号是多少,回头我让‘熔炉’的设计师给我的程序里把你编进去,然后咱俩结婚——我肯定会先追求你,然后求婚,订婚,同居一段时间后办婚礼。婚后我们要生很多孩子……你放心,你在我的程序里只用给我一个人生孩子,也没有什么指标,你想生几个生几个——啊,不行,至少得有一男一女。你想不想上班都行,因为那是我的程序,我的程序里我就是神,只要你一切都听我的,你一定会过得舒舒服服的!”
男人滔滔不绝地跟我描述着他精心编织的“熔炉”内世界,甚至忘记继续跟我交待为何他会放弃继续从事排污工作而选择进入“熔炉”。其实不用他说我也能隐约猜到,工作又脏又累,给的点数也不多,与其这样活着,不如进入“熔炉”成为肉身电池,同时精神享受美妙梦境。他描述的梦境很乏味,不过是新世界新秩序没建立前的一些男人认定的“幸福状态”,这种幻想我听过太多类似的版本,到了负责程序的人那边,只需调用——那叫什么来着,主管告诉我的那个专有名词——模板,对,只需调用标准模板,修改几个数值就足够了。其实这样也好,如果和模板出入很大,程序那边是不可能专门为个人订制新程序的,到时又要推到我们这边,劝诱他们选择标准模板之一。要怪也只能怪最开始选择进“熔炉”的男人们,大多也只有那几种幻想,当皇帝,当神仙,当有女人死心塌地服侍的普通人,后来程序也便懒得开发什么新鲜玩意了。
“我们会在我的世界里共度余生,今年我三十岁,至少还能再活四十年——哦,不行,新规则颁布,现在‘熔炉’最高年限只到六十岁了,之后就会直接拔掉营养管等待自然死亡,不过能过上三十年神仙日子,值了。”他忽然停下,仔细打量我,“你看着比我大,有十八岁时的影像吗,我要和十八岁的你过日子。”
我又开始反胃,忍了两秒钟,才能开口说话。“我的工号在办公室门口,只要跟程序那边报我的工号他们就能调用我的所有资料。今年我二十八岁,比您小两岁的。”
“二十八岁?那你生了几个了?”他忙问。
“我正在怀指标内第八个。”我说。
男人脸上显出一点点嫌弃,又竭力掩盖下去。我清楚他的心思,只是笑笑,表示门口有服务部人员照片列表,他可以随意选择。
男人顿时开心起来,转而开始问我:“第八个,马上就够指标了吧?那你怀完了指标内的孩子打算做什么?女人供能不如男人多,进‘熔炉’也需要更多点数吧?”
“前几天颁布了新规则,指标数已经从十个改到二十个了。”我说,“耗能需求越来越大,缺人。完成指标的女人可以选择直接进‘熔炉’。”
男人似乎有点不高兴,但终归也没说什么。此时计时器发出蜂鸣声,我示意男人可以离开了。他站起来,冲着门口服务部人员照片列表走过去。我则在专属频道呼叫主管,表示想去洗手间。得到同意后,我起身走出门,途中小心地绕开那个男人,但他只是专心地记录着服务部人员的工号,根本顾不得再看我一眼。
干呕了一阵,我抬起头。洗手间的镜子突然开始滚动播放一则消息,配合全机构内广播:“熔炉”内梦境仅限使用三套标准模板,不可任意更换数值。我听到频道里的人们发出惊呼,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我想着那个人没办法让我的影像陪他在幻境里共度余生,不觉松了口气。但想到如果我之后选择进入“熔炉”,也只能和标准模板男人共度余生——哪怕可能只有十多年——又禁不住开始恶心。主管在频道里大喊一声“安静”,然后表示我们女人不同,女人“熔炉”梦境中的男人都很帅,也会对我们很好。
“可是如果又有新的规定颁布怎么办?”我小声问,“之前的生育指标是十个,现在就改成了二十个,只要有新规定,谁知道之后我们梦境里的男人是什么样,甚至……会不会有男人?”
主管沉默了,频道里安安静静,只有机构内的广播在一直重复播报着新的规定。
备注:我错了,我应该少刷点微博多看书
评论要求: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