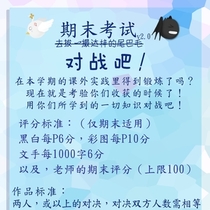目前各元素人物情报(双天赋者和异双天赋者的第二天赋不计入内)
【火】
导师/准进阶导师:25
学员:千加、业火、蜂矢梓、贺茂沙罗、仓山存、马赛克、安德鲁、三桑、六手 瑠夏
【水】
导师:英格玛•怀特
学员:佑马、蓝洛、玛菲特、黑沼石榴、斯瓦莱
【冰】
导师:伊文
学员:系则、艾莉森、赛伦斯、莱斯特、赛芙拉、十六夜石榴
【风】
进阶导师:千纮
导师:凤纹蝶苍羽
学员:乌沙丽塔、宫古奏野、天雫 闪光、Evan
【雷】
导师\准进阶导师:昭一
学员:凉介、夜梵、灾赫斯、浅、诺提、墨恩.斯利维特、雷顿
【地】
导师:卡狄希娅
学员:克罗艾、文森、寺岛茉莉、Bailando、Edmund
【圣光】
进阶导师:阿莉斯泰尔·卡门
导师:羽佐间 锦(保健科)
学员:月白、洛普塔、楼禾、smile mick、夕歌、塞恩、早季 澈、樱庭魅月、叶浅雾、叶浅云、端月、红小花、宫古奏叶、入須徹
【暗黑】
进阶导师:欧利维亚
导师:猫泽
学员:黑星、雅纪、达米洛、西德尼、Daisy、早季 暮、Akira、泷见原堇、千纹海、叶浅生、哈纳·布拉可、球槌、约书亚、佐一、鹤浅川
【意志】
进阶导师:汉德森
导师:奏
学员:塔、次郎、芜铭、佩洛玛、光理、Vic、雷蒙、维卡、Catnip、莫摩·瑞德、千鴞、五十岚 君弥
其他:拜文•耶戈尔(保健科)
【心灵】
进阶导师:鬼山殡
导师:希欧莉亚
学员:澄海、世英俐子、玫芙、沐恩‧希塔努、艾露、无名、索菲娅·艾丽艾尔
【空间】
导师:矢聿遥
学员:雪鸮、奥克塔薇尔、早乙女友人、艾丽斯、Charlie、Azzurra Octavius
【时间】
导师:贺茂丽
学员:小岛优一、菲尔里欧、墨曜染、南瓜 灯里糖、Arrow、弗朗西斯卡·奥丁诺
【混沌】
先
【其他】
芝士(偶像、普通人,心灵气息)
命(冰、心灵异双天赋者,已亡)
ps.
·时空组饱和
·雷系只收男孩子了(喂!)老师是个变态请绕道走,报名建议元素值不要太高
·地系老师欧派很大人很蠢特别好
·水系老师特别懒,风气不正但还是 求学员!!(有学霸,不要怕,学霸和你么么大)
·冰系老师特寂寞
·火系老师不太正常请绕道走
·风系已经变成掀群狂魔组了,不关进阶导师的事
·请尽力保持暗光平衡……
·报名信息好多大家的职称里记得写上年级啊【。
----------------------------------------------------------------------
各小组分布情况
【风纪组】
组长:贺茂沙罗
成员:乌沙丽塔、小岛优一、蓝洛、艾莉森、墨曜染、菲尔里欧、月白
【暗部组】
组长:昭一
成员:猫泽、Vic、西德尼、灾赫斯
【保健科】
老师:拜文•耶戈尔、羽佐间 锦、希欧莉亚
学员助理:玫芙、楼禾、沐恩‧希塔努
【研究组】(无组长)
成员:奏
实习生:塔
PS.
·风纪组人数饱和不建议报名
·教师级别可申请暗部组,非教师的野生天赋者也可申请;学员申请暗部组有人数限制,切元素值要求B以上;申请书由组长审核。
(暗部组由于主线的影响,可能会涉及反派因素,洗白机会较少,而且保有机密,要求比较高还请慎重考虑。)
PSPS.暗部组的申请目前暂时搁置,因为所需人数较少责任重大所以将在企划进行时进行收纳,请见谅!
·保健科目前人数比较充足
·研究组和暗部组均为涉及机密的组织,但平时研究关于元素的课题,招收少量实习生。
如有修改或遗漏请联系企划猪
本公告停止更新,仅作初步参考。一切以已投人设为准。










因为炼金作业实在写不了什么所以改写黑历史...
阅读顺序应该...可以看出来吧?
Twins出没注意(x
1180字
“骗子!”
很痛诶。
石子很硬砸人很痛的。
“叶伊是个骗子!”
中国?我为什么会在中国?
啊对了,我十岁的时候在中国住过半年嘛...
“我不是骗子!我没有骗人!”
咦?
“哥哥...你要走了吗?”
他总是口硬心软的呢。
“小伊在家乖一点,不要惹外婆生气。”
啊...这么严肃的人这么说话真是很让人觉得奇怪呢。
“知道啦哥哥,小伊很乖嗒。”
等等...他是谁?
“...激发他的血统总是有危险的,要不就...”
谁?
“不行!这样下去他会死的!”
他们...在说谁?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死?!我只是...算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试试...就试试吧。”
试什么?
我怎么都听不懂?
“我没有骗你们!你们不信的话自己去吧!”
我干嘛说这个?
我又不骗人。
“骗子!我们就去!你有本事就来阻止我们啊!多管闲事!”
...好幼稚。
“这件事就不要告诉小伊了...”
什么事啊?
“也是挺奇怪的,好好一个人,就这么消失了...”
谁消失了?
烦。
“...明天我就把父亲找来。”
干嘛?
找谁的父亲?
“能快一点是一点吧,到时候行动都困难就糟糕了。”
谁?
怎么都没人告诉我答案?
“知道吗,今天下午三个孩子居然受伤了,就在公园里玩着玩着就被人打了,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谁叫他们说我骗子的!
“据说他们说是叶伊干的...我觉得也不像啊,那么瘦小一个孩子,好像还先天身体虚弱来着,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啊。“
就是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记得有过?
“那孩子...还是没有找到。”
那个...说话很温柔其实很严肃的哥哥吗?
“也苦了他父母了,本来就有一个孩子夭折了,再加上...哎...”
哥哥原来有过兄弟啊...
“然后最近他朋友,就是那个中国人,也不见了。”
什么?另外...一个哥哥的朋友?
“这世道啊...”
“小伊乖,把这药喝下去啊。”
给我的药?
“好的。”
药?什么药?
“啊啊啊——”
怎么...怎么回事?!
“坚持住啊小伊...坚持住就好了...啊...”
到底...怎么了?
“...学弟?Elias学弟?你醒了吗?”
好听的女声。
Elias莫名的困倦,流连在古怪的梦中不愿意醒来。
仿佛梦呓。
“...谁?”眼皮间仿佛被浆糊粘住了,钝钝地张开不了。
“...学弟?”
温柔的不刺目的光。
这是,还在海底啊。
还有同样温柔的少女。
“这位学姐,你是...?”呆呆地张开嘴,Elias询问了一个在玛丽苏小说中被视为最煞风景的问题。
“你就叫我Shallow吧。抱歉翻了你的作业,但是我看你好像被梦魇住了,所以才...”
Shallow躲躲闪闪地不看Elias的眼睛。
“谢谢你了...Shallow,我很抱歉。”
Elias疲惫地揉了揉已经睡得变成一头杂毛的长发,脸上还留着红红的印子。
棕发少女瞬间低下头,Elias可以看到她泛红的耳廓:“不...不用谢!要我...帮你完成...炼金作业吗?”
“如果可以帮忙那就太感谢了。”Elias意识到自己不够礼貌,从大石上翻下来鞠了个躬,“我的魔法阵好像有点小问题...”
“就是这样了!”Shallow长吁了一口气,“你试试看注入魔力。”
“好的。”Elias轻握着清末,前端的绿色树叶形宝石对准了魔法阵和里面的木片、泥土和水。
清亮的绿光在宝石周围闪烁。
Elias深吸一口气。
“自然之神,吾给予汝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