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喜欢企划主!
我要向企划主表白!
终于真的到最后了呢……
这一个半月来真的非常开心,
真的好舍不得啊QAQ
下次再一起玩吧> <。
======================================
“你不但像一个幽灵一样来去无踪,还可以附身在别人身上,凭自己的喜好杀人。”笼目挠了挠头,这些事情早就已经超出一般人的常识范围了,“看来仅依靠‘常识’,是不能看破“失落之城”背后的谜底的呢。”
魔术师的笑容在笼目说出“常识”两个字后绽放了开来,这和笼目用“笨蛋卡”自黑时的那种被戳到笑点的笑不一样,这是孤独的旅行者碰到了同路人的欣喜:“你说不能仅依靠‘常识’,那你要如何跳出常识的框架,来解开“失落之城”的迷呢?”
“要‘跳出常识的框架’,首先就要知道‘常识的框架’在哪呢!”因为从小无父无母,笼目的“常识框架”从来就不是完整的,这也让他向来比别人更容易胡思乱想,“你应该知道的吧,我几乎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如果不是被公园里玩耍的小学生发现,我可能早就死在厕所里了。我的姓氏和名字,并不是因为养我长大的人姓‘香久山’,而是因为我是在小学生玩‘竹笼鸟’的时候被发现的,所以被借了《竹笼鸟》的歌词,被起名为了‘かごめかごめ’,写成汉字以后就是‘香久山笼目’——这些‘设定’我在这里说没关系吧,在这里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再不说可能就没机会了呢。”
魔术师只“噗”的笑了一声,便示意笼目继续。
“我的人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上。别人都有爸爸和妈妈,为什么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呢?或者说我连人都不是,我是另一种外形和人类很相似的物种,或者是什么超越人类的存在,所以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我父母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把我扔掉了——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我知道我为什么被抛弃,因为我的眼睛,天生看不清东西。”笼目的护目镜是有度数的,而且笼目用护目镜的原因也并非什么“护目镜是主角的象征”,而是因为笼目眼镜需要的镜片厚度和重量一般镜框难以承受,“在配眼镜之前,我因为看不清东西,什么东西都要问了别人才能知道,而且问一次还不够,我会重复问,问到我信了为止。因为这个习惯的关系,我都忽略了,在‘失落之城’里,对案件的调查似乎都不是我亲眼看到的,而是我反复询问Nihil才得到的吧。我是因为视力的关系,所以有这样反复询问的习惯,但如果是一个视力正常的人,他也需要这样吗?其实我这幅眼镜,已经能满足我日常生活的需要了,如果只是现场的调查,其实就算不特意询问Nihil,我也应该“看得见”才是,那为什么,我还要一句句去问Nihil呢?”
“你说呢,为什么?”听了好一阵子角色设定,魔术师终于等到了主题。
“因为我喜欢Nihil,想和她说话,想创造更多和她在一起的回忆,如果可以,我想明天的太阳升起以后,也能见到她的脸,听到她的声音。”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出这种话,笼目自己也很意外。
“嗯,你这个应该算是表白?不过为什么要对我说……”这段表白应该是魔术师意料之外的话,他的嘴角有点抽搐。
“因为,你是她的‘创造者’,用人类家庭来比喻的话,你应该是她的‘母亲’不是吗?”笼目揪了揪自己的脸——自己的脸皮其实也不也是很厚嘛,“不过,只是“母亲”的话,我是不会对你说这些的。我对你说,明天我也想和她在一起,是因为你能创造她,也能毁灭她,明天我们‘离开’这里以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保留她的数据,就像你随喜好杀人一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随喜好删掉Nihil。”
“保留……数据……嗯,如果你真的想和她在一起的话,先过岳母这一关如何?如果我觉得把她交给你也没问题的话,嗯,前提是要我觉得把她交给你也没问题啦……”
“前提不该是‘她觉得和我在一起也没关系’吗……咳,继续之前的话题,为什么我应该‘能看见’也要一句句向Nihil确认才能知道我看见了什么,而且除了视觉,听觉、嗅觉也是需要向Nihil询问才能得到的情报,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或者说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进行感知吧。”是时候了,尽管这个想法真的很扯,但除了这个,笼目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说法能解释这几天发生的事,“我,我们也许不是人也说不定,至少对于‘上位世界’(1)的你们来说,不是。”
“失落之城”的主人对每个人都喜好都了若指掌。
第一天见到Nihil的时候,Nihil能够准确无误地报出自己的名字可以解释为之前有人对自己做过调查,所以Nihil知道自己一直用“香久山笼目”这个名字生活至今;之后落水被打捞上来,Nihil能够准确无误地准备换洗衣物可以解释为自己来到“失落之城”前有人对自己做过身体检查,所以Nihil知道自己穿什么型号图案的衣服——这些都可以解释,但“知道大家喜欢什么食物”这一条却怎么解释都显得非常奇怪。
喜好是一种内心活动,很难通过观察确定一个人的喜好。
举个例子,不是每个人都会把自身的喜好表露出来的,笼目就是其中之一(2)。尽管真的喜欢胡萝卜天妇罗,他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好吃”这两个字。这种天妇罗的制作方法是从人体吸收胡萝卜素的角度来设计的,这种东西对一个先天视力不好的人来说,比起食物更像药物,就算笼目每天都吃,也不能从观察得出,笼目真的喜欢吃胡萝卜天妇罗。
比起这个来,魔术师能透过护目镜看到自己眼神什么的都是小儿科了——魔术师是从“角色的设定”上了解每个玩家的,连设定都能知道,那对每个角色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那是再容易不过。
机房的电脑显示屏上锁定了贝叶斯概率公式,通过查询图书馆里的专业书籍,笼目得知了贝叶斯被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其中贝叶斯网络更是一种用严格的数学方法来模拟一个世界的方法(3)——通过不断获取条件,程序能够运用贝叶斯网络算法得出命中概率最大的答案——就和在“失落之城”解决案件所需的方法一模一样。
对于“下位世界”的人来说,也许可以通过扭曲的常识注意到“上位世界”的存在,但要了解“上位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世界,如果没有看到漂浮在屏幕上的字幕(4)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如果魔术师希望“下位世界”的人猜测出“上位世界”的全貌,那必须留下些许线索,机房电脑上的贝叶斯公式和图书馆里完备的资料库就是指向答案的提示——“失落之城”与人工智能有关,而笼目自己,可能就是以贝叶斯算法为运行原理的智能程序。
这样一来,Xeo和banana的死亡和复生也能够顺理成章地得到解释——死亡就是程序中止运行,复生就是将中止程序连同他们被中止的记忆一起删除,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复活他们,他们的程序恐怕就会变成终止运行的状态,就和现在的Jack一样吧。魔术师说过,能否复活Jack要看自己的表现,虽然不知道他期待的表现是什么,但他能够将终止的程序恢复运行,那程序本身应该没有删除,所谓的“复活Jack”应该就是“删除终止程序”。
“我在想什么,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吧,不说点什么吗?顺带一提,如果用以前很流行的一种文画互动活动——‘企划’来比喻的话,我们对应的应该是‘企划人设’,Nihil对应的应该是‘企划规则’,而你对应的就应该是‘企划主’了。”笼目也常常在网上关注些企划什么的,所以拿企划做了例子。实际套用之后,发现切合度出乎意料地高。
“嗯,说得真好。”魔术师拍了拍手,大概是认同的意思吧,“那你看过的那个文件,这个实验的目的,你也知道了吗?”
魔术师说的“那个文件”是他遗留在楼梯口的一个写了“女子高生”缩写的金属U盘里的文件,里面有一个魔术师自己的自拍视频,但是视频拍到一半就因为自拍器故障还是什么的原因中断了,在那个自拍视频里,魔术师让笼目猜测的是“失落之城”这个实验的“目的”。
“嗯,你的目的,是通过企划找一个美术老师或者书法老师吧。”
“……”这个画风突变的答案,让魔术师脸上的高冷和矜持凝固了。
“毕竟你画的画和你写的字,鬼都认不出个来啊。”笼目所指的就是塔楼里发现的图纸和记录了,简直是鬼画符,什么都认不出个,“如果是文画企划的话,应该会有画师和文手参加吧,画师可以教你画画啊,文手如果在死线迫近的时候,也是有一定几率交手稿的,虽然不一定练过书法,但字迹一定比你清晰。你是想从这些人里选出能教你画画和写字的人吧。”笼目说着做了个闪闪发亮的手势。
“不……这个企划是个严肃的企划……请严肃一点。”也不知何时起,魔术师也认同了企划这一比喻。
“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知道你是谁,知道你23岁,还知道你‘狡猾又善变’。”笼目这里说的是他打开二楼卧室门上密码的时候,密码是魔术师的出身年份,也就是实验开始的年份减去魔术师的年龄——笼目在这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居然知道魔术师的年龄,就像看过魔术师的“人设纸”一样,“虽然不管是你的少女日记还是自拍视频,里面都说这个实验是‘为了人’,但说真的,我无法相信你的说辞——毕竟,你的手上可是有三条人命呢。”
如果笼目和VAN当初没有选择复活Xeo和banana的话,魔术师手上就是实打实的三条人命,尽管根据之前的推断,大家在魔术师眼里只是数据而已,但对笼目这样的“数据人”来说,大家确实都是活生生的人。
如果不知道这里是程序里的世界的话,如果把这里当成现实世界的话,同行者的死亡必定会造成恐慌,搞不好真的会像“企划书”上那样发生自相残杀的事情——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应该说多亏了大家都是和善的人吧。
想到“魔术师”曾私下里和笼目说过“我倒希望你们能撕起来”这种话,就算笼目再怎么好人,也不可能把魔术师当成什么为全人类发展着想的好人。
“如果说这个‘企划’就像你之前怂恿我们的一样,那到了今天,这里恐怕会少相当一部分人吧。”先不说被复活的Xeo和banana,如果说魔术师之外的人动手,按照Nihil的说法,动手的人被猜出作案手法和身份后的就会死亡,“如果猜出作案手法得到‘复活’特权但不当场使用,而是留给自己下次被杀的时候复活自己的话,那最容易活到最后的应该就是我们这里‘计算能力’最强的那个人——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之中攻击性最强,最狡猾奸诈同时又具备较高‘计算能力’的人——虽然不知道你想要的是哪种,不过我并不属于其中之一,真是让你失望了呢。”
“唔,那倒不一定。其实我对你的好感度还是挺高——”
“好感度高你就给我了一张写着‘笨蛋’的卡?你是蹭的累吗(5)!”
“不……都说了那不是笨蛋……”
“反正我这样的人你猜不会喜欢哼,我一直在打乱你的计划,复活你杀的人,擅闯你的卧室,偷看你的日记和自拍视频,靠,我都觉得我好变态!”
“嘛,我不会在意的,我可是知道你对我有意思哦。”
“住口!要是哪天我变成同性恋了一定是你这个变态暴露狂的错!”
“但你之前说你喜欢Nihil吧,你还是喜欢女孩子——啊不对,我记得你是双性恋吧。”
“……”
“那,如果说,我能把Nihil交给你——”
“那就是游戏‘胜利者’的奖励吧。”这种把Nihil随便送来送去的说法真是让笼目高兴不起来,“只靠我一个人是走不到今天的,能走到今天,除了和我一起努力过的都趣肆、banana、Jack、Xeo、Van,最不可或缺的人难道不是Nihil吗?”
因为无法靠自己的感知“失落之城”,所以作为信息来源Nihil是不可或缺的。Nihil的信息收集和判断能力,加上‘玩家’的信息处理能力,这两种能力同时存在才能破解这么多天接连出现的谜。
“你是想找一个智能程序,和Nihil合体吧。你想编写与人类思维几乎相同的人工智能,但第一次的编写似乎因为重大缺陷失败了呢。”这些是实验笔记上的内容,“第一次编写的程式,你可是写作‘她’呢,想想这里符合条件的,在我们到达这里就存在的程式,就只有Nihil了呢——至于缺陷,显而易见吧,她能够判断信息的真伪,能够管理企划的秩序,但却没有这之外的能力,也就是一个机械——至少‘实验’开始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机械化’的程式呢。我想‘实验’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影响,让Nihil拥有计算能力——也就是俗称的合体。”这个合体并没有那种意思,笼目在心里特意附加了一句,毕竟魔术师是未来岳母般的人物,不能给他留下那种印象,“你说过游戏的‘胜利者’除了‘奖励’还能够‘离开这里’吧。对于程序来说,‘离开’就意味着‘导出’吧。‘胜利者’,也就是我之前说的应该是计算能力最强的程序会被导出,和Nihil合二为一,最终成为一个非常接近人类思维的人工智能程序——实验的目的就是这个吧。”
“嗯……很有趣的猜想,很接近,但还是没有完全跳出‘常识的框架’——不过对于‘一个人工智能程序’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时间好像不早了,明天会是怎样?Jack和Nihil,还能活着吗?”作为一个“下位世界”的人物,笼目从来就没指望自己能完全猜中谜底,比起谜底,他倒是更在意Jack和Nihil。
“这个嘛,到了明天你就知道了。”
魔术师就像“企划书”上写的那样,“狡猾又善变”。他只给了笼目一个信息量巨大的笑容,然后就消失了。
======================================
(1)出自本企划之前安利过的作品,微剧透就不细说是哪个啦> <。
(2)也就是俗称的傲娇啦……
(3)贝叶斯网络,就算是笨蛋也能读懂的说明:http://www.zhihu.com/question/28006799
(4)出自《非公认战队秋叶原连者》,很有意思的片子*^_^*。
(5)也就是俗称的傲娇啦……
(6)出自《寒蝉鸣泣之时》,但变态真的不是好事哦!(认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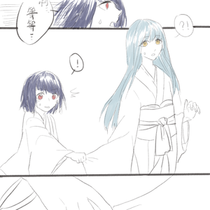






地点火山,气候凉爽。
“……这跟说好的不一样。”
耷拉着头,大半张脸都埋进厚厚的棉围巾中,布拉德哭丧着脸嘀咕。这也怪不得他抱怨,根据他所收集到的情报,这本该是一次避寒兼赚外快的愉快旅途,前不久还只是站在火山口的人十分满意。
冷,真冷啊。随着他的愈渐深入,体质敏感的他很快便意识到了不对劲。虽说自己觉得冷,但布拉德知道此刻的气温对正常人来说仅仅是舒适的凉爽,放在哪都不稀奇。当然,如果地点是一座死火山的话,就两论了。
“呼……十二层。”布拉德搓了搓手,冰凉的双手迫切地想要回到被别到裤腰带后的温暖手套中,但为了不影响探索的进度他只能耐着性子打量四周一成不变的景色,“照这样下去,顶多到二十层,我就该消极怠战了。就算是你,战力多少也会下降一些。”
“我知道,我知道,那东西是不会在这里的。”
自言自语的男人摸了摸无论何时都不会离身的耳坠,冷静地分析着目前的状况,只有布拉德的对话对象——哈特知道,从他的手指接触到银质耳坠的那一刻开始,焦虑便已开始蔓延。
“但是——我也不想空手而归。”
沉眠在体内的冒险因子在躁动,宛如红宝石的双眼中闪烁着奇特的光芒,“既然来了,敲下点火山岩壁带回去当伴手礼送给那些家伙也不错。”
完全看不出是开玩笑的样子,布拉德在石壁上摸索着,就像是真的在人真难挑选着喜爱的石块一般,没过几分钟,笑意爬上了他的嘴角。
“啊哈。”当手指触碰到某一处石壁,指尖沾染了些许的粉末,赤色的火山石的粉末,像是嗅到了猎物的猎犬一般,布拉德快速地扫开这些掩人耳目的粉末,“宾果!”
这道声音多少掺杂了一些讶异,布拉德先前注意到这些浑然一体的石头内部有一个小小的中空区域,这当然是他敲击了一次石壁表面得出的结论,作为一名经验老道的探索者显然是游刃有余。饶是如此,他也不会想到魔石竟是直接嵌在石壁内,只露出了薄薄的一层表面来告诉寻访者它的真实身份。
魔石完美地契合在壁面,光是用肉眼去看也知道凭一人赤手空拳的蛮力一时半会儿是无法将其剥离,不过这也难不倒布拉德。
他的手再次触碰上那枚耳坠,不同的是,这一回他动用了精神力。
“呼吸一下这寒冷的空气吧,哈特。”
首先有变化的是这一小方天地的温度,随着温度的缓慢爬升布拉德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哪怕只是一丁点,也能让这个极度惧寒的家伙感到高兴了。
随后,应声而现的是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哈特舒展着赤色羽翼,热浪扑面而来。布拉德丝毫不惧,他一手抚上令人爱不释手的绒毛,大半个身子都惬意地埋了进去,“还是这样舒服多了,对吧?”
“你啊……”高昂的头颅缓缓低下,如曜日般灿烂的金色兽瞳中酝着关爱之色,如山岳般稳重的声音令人徒生出一股安心感,“先干正事,B。”
“对,正事。”神色间的嬉笑还未褪去,布拉德仍旧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他拍了拍眼前这只庞然大物的腰部,“我数到三,把魔石搞到手。”
“三。”
靠着那身绒毛的掩护,布拉德神不知鬼不觉地握住露出半截的刀柄,伴随着他的一声令下,蓄势待发地短刀刹那间脱手而出,同时一道能灼烧人眼球的猛然扑出,两者的目标正是在一旁窥伺的巨型蝎子。
多年来的陪伴与共同作战,令一人一狮只靠一个眼神,甚至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便能领会对方的意思,早在发现魔石之前布拉德便察觉到这只蝎子的存在,活物总比那么一颗小小的死物好找得多。自然,他也有了对应之策,挂在嘴边的笑容不是懒散,而是运筹帷幄。甚至哈特还有闲心,在擦身而过的瞬间一爪拍在短刀上,加速了暗器的飞行速度。
短刃当仁不让地插进蝎尾与身体的连接处,奈何短刀太短无法将蝎尾整条切下,布拉德望着紫莹莹的毒钩撇撇嘴,“还有点难缠嘛。”
有点难缠,也仅于此罢了。
没有动用一分一毫地优势,仅凭着肉体力量的哈特仍旧占尽了上风,自顾不暇的毒蝎没注意到有个人悄悄地摸到它的身后。
“这把刀。”当它终于意识到尾部的情况,布拉德已是反手握住了刀柄,“也该物归原主了。”三言两语间,割断了长如鞭的蝎尾。
尖锐的厉叫划破天空,倒提着短刀的布拉德皱皱眉,也不管临死反扑的困兽,蹲在地上自顾自地将蝎尾解体,简单地处理完毒钩便把它装进背包中。
“好歹也能收回点本来。”
“下次,找点有挑战性的来。”轻而易举地料理完毒蝎,哈特踏着傲然的步子来到石壁前,“此地不宜久留。要是完事了,就趁早离开。”
“我知道,我知道,别再念啦老妈子。”伸手接住它像切豆腐一样切下来的石块,布拉德继续动用短刀将魔石从中挖出,“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里吗?”
“这里没有。”
“我知道。”
这番对话就像是重复播放的老旧磁带,在这一刻卡带。
如今整个世界为了一个ARM「世界」而动荡不已,各方势力都被惊动,包括布拉德自身所在的洛比利亚,但没人知道「世界」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余兴节目。
只要找到「那个」就够了。
布拉德看着凛凛狮王的额头的十字疤痕,眼神微暗。这道伤疤并没有损害到哈特的神骏,反倒是为其添上一份英武,也只有布拉德懂得伤痕的意义。
他抬手按住自己的额头。
那道疤本该出现在这里。
曾经那道伤口深可见骨。
“我会找到它的。”
“我知道。”
哈特俯下身子,半趴在地面,伸出巨大的狮爪,柔软的肉垫蹭着他的头,一如儿时的时光。那美好的,不复存在的回忆。
象棋兵团。
当这个词汇浮现在心头,布拉德翘起唇角,血眸中映出残酷。很快那抹神色隐去,另一道身影突兀地出现在他的记忆中,他曾经的友人,象棋兵团的旧部,青薙。
多么矛盾的身份,矛盾到布拉德无法判断他到底是友是敌,但面对对方可以说是无力的辩解,他却凭直觉地选择相信。真是一个奇特的人,不由地感叹出声。
察觉到他的内心所想,几乎说是与他心灵相通的哈特低声笑了,“随心而动,B。”
“我知道。”牵起一抹苦笑,他的手无意识摸向口袋,摩挲着一直揣在兜里的戒指,“那也得等我再见到他。”
“好了,既然这里没有我们要找的东西。”
狮王了然地回到了它寄宿的耳坠中。
“就让我们赶快离开这该死的鬼地方吧。”


1.“大帝”萨默菲尔德在通往无则界的道路被关闭之前在无则界呆过一段时间, 对无则界比较了解。
2. 萨默菲尔德颜值很高,在没有什么熟人的无则界被人当作女孩告白过,那个人现在是神族军队的统领。
3.自然族被人族控制这件事情,说起来跟神族有莫大的关联。
4.关于萨默菲尔德和那个人的故事有好几个版本,不过一个比一个扯淡。魔族众更愿意相信那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5.自然族掌握的科技其实比人类要先进一点,不过他们人手不够搞不起大动作……
6自然族的基础魔法体系是最完整的,魔族和人族的基础魔法体系大部分是借(chao)鉴(xi)自然族的基础魔法体系。
7.所以你能明白为什么自然族是亲儿子了吗。
8.兽族的“信使”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并非传说中的两位数。
9.神族在无则界欺负其他小种族的事情我是不会说出来的。
10.对于神族这种黑历史……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
11.任何种族的人死后他有的魔力就会被生命之树强制收回——自然族的理论。
12.妖怪中有鬼。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人族如果对这个世界的执念太深,就会变成鬼。
13.妖怪中的某些需要频繁的“粮食”补充也就是魔力,以得让其能在现世维持生命。
14.大多数妖怪的寿命在3-5年左右,不过他们的繁衍方式不同,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能说一个妖怪死了,而是说他们重组成了新生命。
15.生命之树虽然是个树苗但是它的“根”遍布大陆——自然族的理论。
16.生命之树死亡就是这个世界的死亡——自然族的理论。所以说禁止乱砍乱伐从你我开始。
17.不能随意地在生命之树下发誓或祈愿,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