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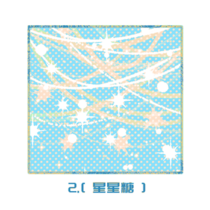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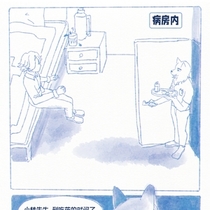
“奚..奚尔..你的头发呢!!”莉特一副惊恐的样子指着爱人的头发,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
“莉特!!莉特!!我秃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奚尔一顿干嚎不落泪惹来了不少护工驻足,这对戏精夫妇自打入院就天天这幅鬼样子,除了耳膜受难之外其他人早已见怪不怪了,不过大清早就如此精神倒是变成了c区的闹铃,颇有把b区也一起叫醒的架势。
莉特一边慎重的捻了捻奚尔的发梢,这参差不齐的发尾看着也不像新剪的,只能无能狂撸一顿小小的爱人,看着对方在自己“一望无际”的胸膛上埋着脑袋干嚎。惹来一个护工实在受不了开口道:“你不是一直都这发型吗!别嚎了!”
莉特抬头看了一眼道:“你个鸡蛋脑袋懂个p!”嚎的更大声了。
最后已两针镇定剂结束了这个早上。
两天后
“这设施好像还怪好的嘞,天天大鱼大肉的。”奚尔坐在莉特腿上戳着盘子里的鱼肉,每一块鱼都变成了鱼肉泥最后进了莉特的嘴里。
“话说回来我这几天拿到了一张不知道开什么门的卡,但看起来跟医生手里拿的卡差不多,回去给你瞅瞅。”莉特一边用嘴处理掉奚尔用叉子撕扯的一片狼藉的食物,一边拿出自己的餐点让他继续奋斗。
“你是说那些长得让人腿软的医生们吗。真想先*后*了。”奚尔说完,莉特感受到周围仿佛看勇士的视线,想起第一天莉特习惯了之后对着各路异形头医生喊了一路“姐姐、姐姐,打针好痛痛,药会吃光光~”就一阵不解为何会有人对此大惊小怪的,没见过xp系统紊乱的病人吗。
不过今天这鱼也奇了怪了,今天不小心看到一眼发现那鱼一个个长得不像日常吃的鱼,幸好文化不高要是看懂了那还了得,莉特只当是什么新奇转基因物种,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有的吃就不错了,味道还不错等出去了去菜市场整两条当下酒菜吃。
又过了几天
看着各路病友发疯的发疯,洗胃的洗胃,昏迷的昏迷,摆烂的摆烂。每一天都上演精彩的大型玄幻奇异惊悚友情爱情亲情百合水仙耽美连续剧,倒是也看出几分惺惺相惜的革命友谊。几十号人活出几千个人的姿态,院长也是有门路的人才,能收集到这么群牛马蛇神也颇有本领,只是一直没见过本尊,倒是总能看见杀鱼的汉子和锻炼的女子,有趣得嘞!
通过这几天的探点和打听,找好了“演戏”的位置和想要搜索的地方。不过比较困难的是怎么用一张卡带两个人上楼。
只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位胸围可观的女子躲避层层眼线和可能有的机关刷开了二楼的门禁,当蹑手蹑脚的到达医生办公室的门后,那位女子的胸“破土而出”。一颗毛茸茸的脑袋从胸口伸了出来。
“哎呦喂憋死我了。”奚尔扯着莉特的领口,仗着医院给的病号服质量不错胡作非为。不过莉特心里只想着要是能挂一辈子就好了,恨不得每天挂着走。
想法刚落就见对方指挥自己走到放置衣服的柜子里找两套合适的服装,分别换上了最大套的医生装和最小套的护士,还找到了没有照片的工牌像模像样的别上,没一会就上演了霸道医生俏护士的场合,毕竟是偷摸上来的没敢搞出太大的声音,等出了门俩人都憋得脸蛋子潮红,俏护士又挂回了霸道医生的领口里。
摸索着进了档案室里,里面琳琅满目的文书看了人眼花缭乱,好在分类做的十分贴心可靠,很快就翻阅到了两人的资料以及几个看起来就与众不同的档案。分别标注了“海盗”“建筑师”以及“羔羊”的信息。翻阅过后两人都有些许沉默,尤其莉特看到自己已经退出业界许久感到一些动摇,但不一会儿就觉得这个病院只是另一个片场而已。记住了所需要的信息便放了回去。莉特表示对自己需要表演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
(先铲了后面再加)


夏季的热天实在让人打不起什么精神,不是谁都能够做到和蝉一样如此勤奋的在树干上“唱歌”。
伊织 白汇有些百无聊赖地坐在座位上,教室里只有一些人在,几乎都是些没有事情可以做所以待在教室里不出去的同学,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她。
实际上她倒是也想过参加一些社团,丰富丰富自己的高中生活,但自她从初中开始的社团活动的累人程度来看,就让她打退堂鼓,但她和植松 美优总是一起行动,就连社团活动她也在,搞得好像她也是那个社团的团员一样。
其实不是,她单纯太闲了,加上只和发小比较玩的熟。高中她也是等着美优社团活动结束后,再两人一起回家。
哦,对啊,既然都这么闲了,今天好像还是社团展示的日子,虽然白汇是个闲人但是她去美优在的文学社凑个热闹蹭杯凉茶应该也可以的吧。
她行动比脑子还要快已经离开座位打开教室门走出去了。
顶着烈阳并一路上走的飞快,很快就在一堆社团里找到了美优所在文学社的位置。她看见美优正背对着她,手上还整理了一些书籍,正认真按照顺序排好。
白汇放静了自己的脚步声悄摸摸的穿过人群来到美优的身后,一脸凝重地抬起了手准备遮住起她的双眼。
“白汇?”
其实看到身上有了阴影的时候美优心里就猜测估计是她来了,加上有股熟悉的洗发水味直接在钻鼻子一样,更让美优笃定人选。
“怎么被发现了,可恶”白汇做出吾命休矣的悲伤表情,但下一秒就凑到美优的座位面前:“能坐吗?”
“嗯,可以的。”
“现在是休息时间还是什么吗?怎么就你在这里。”
“大家去搬书过来了,我在整理书的分类,还有个同学刚刚出去买点冰水,现在还没回来。”
白汇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她的目光下移,被美优压在了书本最下面,只露出了标题的童话故事吸引了过去。
“你正在看这本?”
美优微微一愣,笑了笑从下面将书抽出,从封面来看还是个童话的绘本,好像小时候她们就总一起看这种色彩鲜艳的童话故事。
“内容是什么?”
美优翻开了第一页问白汇要不要念给她听,自然是毫不犹豫的点头。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奇妙的爱情故事,关于爱上了湖中的小花的公主变成了天鹅无法说话,于是公主只能偷偷用各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引起小花的注意,十分的可爱。
和寻常童话故事不同的是,一般童话里好像都有公主和王子的爱情的描写,讲述最后幸福美满的好结局。
但是公主喜欢上的人不是王子殿下,而是一朵漂亮的小花,但白汇或许能理解公主,因为她从美优的描述里听着感觉,那是一朵悄悄绽放很有活力的小花,就算没有公主,王子,其他事物的陪伴,独自一个,也能够绽放自己色彩的花儿。
“你觉得公主能和小花在一起吗?”
“哈哈哈……当小花和公主互相开始欣赏对方,并接纳之后,就能在一起了吧。”
说完后两人相对无言,但是一起笑了出声。
“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