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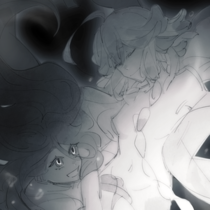



封爵
商溪,开封人士,今少府监丞也。
传其夜梦使者扣门,恭敬有礼地问道,郎君起了吗。
商溪出言相询,门外答道,吾乃祖龙使者,王军已至闽越,奈何敌众,苦战良久。今闻郎君奇技,请君相助。
不待其回答,强请三声,请也。请也。请也。旋即人即已至沙场,始觉胯下骑名驹,手中持长刃,身后阵列万人,虽因逆光故众兵丁面目无法检视,但气势雄浑,默然待其指令,属实为精兵也。又见对阵有一奇伟将军,顶盔掼甲、罩袍束带,日照下银鳞甲胄光彩夺目,身后亦兵多将广,人强马壮。
两军对峙间,使者于场中提声叫道,若成,君可得三公之位矣。
其声高亢,宛如雷霆,亦不知是向哪方言语。此言毕,忽闻杀声震天,人头攒动,瞬息敌将已奔至近前,以长枪与商溪你来我往战过数十回合,而两军将士更是冲入敌对阵中,搏命厮杀。如此交战一夜,众皆感到筋疲力尽,待敌寇尽除,五更鸡鸣,商溪方才从战中脱身,这时手腕抖如筛糠,甚至无力取杯饮茶了。
此后一月中,其夜夜为此东奔西走,征战四方,逐一平定南粤、西瓯,无一晚闲暇,但战斗愈久愈是娴熟,已没有当初的惶恐了。
是夜使者至,激动道,今日终局也,已替郎君请丞相位。郎君请上阵。
商溪淡然起身,逐一净手、洁面、更衣才与使者共赴疆场恶战,并以霹雳手段于阵前斩下首领头颅,遂登殿,提敌首献君受封,闻得头顶有男子之声乐道,吾胜之!
这男音浑厚,震耳欲聋,使商溪陡然梦醒,此时他手中还抓着半粒珍珠棋子,浑圆洁白,自中对半剖开。
后此事传开,世人皆说,是神仙对弈,抽世人神魂做棋,那枚珍珠白棋就是敌方首领。而商溪有功得神仙赏赐才能步步高升呢。
————————————————————————
做官
开封商溪,少府监丞,对奇珍异宝颇有见地,好茶。
有一日冲泡龙园胜雪,汤出白玉壶,八分满,置于茶盏中待凉。饮时,见茶汤中有仙,人首鱼身,银发青尾,大小只一寸有余,将一细物托举出水。
商溪顺意取走托举之物,那物入手后见风即长,是一卷文书。
又见鱼仙搅动鱼尾,掀起细密泡沫,沫上浮现图纹。盏中显一近海溶洞,礁石林立,有一砗磲,壳内满载珍珠,仙卧其上,那些微末珠子惟妙惟肖,又有一人影自壳中搂取珍珠,人影随茶汤晃动,窃珠举动亦栩栩如生。
茶沫消散后鱼仙亦不得见。文书展之,为某地房屋地契。
商溪遂至某地,询之,地契失而复得屋主却并不据实相告。商溪予以百金买其屋,被拒。再加价一倍,仍被拒之门外。后以权谋之,夜居其屋,商溪梦一斗,斗大若室,内中圆珠手插不进,数次取之,缺口仍顷刻补满。
梦醒后,床榻之上满是珠子晃动,莹白圆润,流光溢彩,盈千累万。
甚喜,又于沿海搜寻溶洞,数月后寻至一洞,外观相仿,入内见水中庞大砗磲盛有上等海珠,虽是梦中取走之数甚巨,但仍在壳中余下小半。
洞外又有数条破损海船堆叠,有大有小,乃是近年走失商船,内有残损货物。
商溪凭海珠升官发财,以为奇,与友谈之,友笑道,鱼居于海,卧于贝,珍珠若其丝衾,人至贝中取珠,谓之盗。开封包公断案素有威名,虽包公已逝,但它又能从何处得知呢?你与包公相邻,此鱼状告盗匪至你处,是它误入歧途了。但你将寻得之物据为己有,已开罪于它,依我愚见,余生你切莫近水为好。
——————————————————
来放个之前的链接:
《夜行舟》《石羊》《还债》:http://elfartworld.com/works/9377168/
《复生》:http://elfartworld.com/works/9377199/
《做人》《造梦》:http://elfartworld.com/works/9377233/



关键词/出题人
1 圣诞/浅间
2 离群/夜雨
3 体育/三真
4 关键词/暮夜
截止时间:10月31日晚21:00
作者:山诀文
起因是星期日和妻子打扫房子,从一箱将要扔掉的杂物里,翻出了一对耳环。
耳环是银色的,但大概不是什么贵重的金属,因为经过漫长的黑暗,氧化作用使得它的表面渗出了薄薄的褐色铁锈。
“看起来像你会做的事,在耳环上刻上自己和女朋友的名字。”妻子将它从一堆将要扔掉的杂物中间捡拾起来,放在手里看了看。
我咧嘴一笑,妻子并不是善妒的人,此刻说出这句话大概有些调侃的意味,因为我时常与她吹嘘自己曾在年轻的时候受各路美女喜欢,她最后与我在一起何其幸运。
妻子将耳环放在手里,那是一对被雕成羽毛样式的耳环,小巧轻盈,一只有幸躲过时间的打磨光泽如初,而另一只则有些狼狈,时光的痕迹浸润它灵巧的结构,留下块块的锈迹。
“呀,还刻着字呢。”她故作惊讶地将手指盖住耳环的一部分,流露出夸张的神色,“这只写着什么……L?”
我笑笑,将耳环从她手中拿过来。
“L?你猜猜这个L是我的第几个女朋友?”
“我不猜,反正不是我。”说罢她故作生气地把脸转向一边。
“L是left,这是左耳耳环哈哈哈……”
我噗嗤一声笑出来,随后将那对耳环随手放在了桌上,从她身后紧紧将她抱住。
她很吃这一套,遂在一会儿的缠绵过后,在一声声越来越小声的“放开”和满脸羞红中,也就原谅了我。
傍晚的时候,由于她要上晚班的缘故,匆匆吃了晚饭便出了门,她们这些中学老师就是这样,一年到头的晚上都难有安生的日子,晚自习不仅是对学生的折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教师也是如此。
我正这般胡思乱想着,门铃响了,开门,却不是妻子,而是我的母亲,我大概清楚母亲为何而来,专挑这个时间,想必也是蓄谋已久。
我着领着母亲坐下,自去倒茶,心理盘算着怎么对招。
“你们还没准备好吗?”母亲是个直性子,话开门见山,直达主题。
我苦笑一下,自然知道母亲说的是要孩子的事,这并非我和妻子办事不利,只不过缺了点运气和缘分,一直没能等到一个结果。
“实在不行我去给你们求求神婆,真是怪事。”母亲一面喝茶一面抱怨,而这时我才注意到今天打扫时随手放在茶几上尚未收拾的耳环,便伸手去拿。
“你就是喜欢摆弄这些东西,以前小时候也是,天天戴着,跟个二流子一样。”
“哈哈,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我打着哈哈。
“才不是,你高中的时候就天天戴着这个,你爸当时说了你好几次你就是不肯摘下来。”
我怔了一下,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很多痛苦和压力掺杂在一起,像是泥潭,我每每回忆起,总是会一步跨过去,而非踏入其中。久而久之它变得模糊不堪,难以看清。
母亲的这一提,我自然而然的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一切,即使自主意识并不愿意,但本能还是把我拉了回去。
我记得的,我那时没什么朋友。
那是多方面的原因,正如同一场大的灾难并不是只由一个因素而造成的一样, 我的性格,经历,身体共同促成了这一切的发生,而这样的灾难一旦成型便将难以将其彻底扑灭,于是在我的记忆里,我只有关于那三年的,一段关于我形单影只的记忆,仅此而已。
母亲没有久留,看我心不在焉,抱怨督促了几句便很快离去,只留下我和那对耳环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对视。
我又重新将它们拾起来放在手心端详,左半边耳饰,大写的字母L清晰可见,可右半边的地方已经被锈迹腐蚀,看不到上面究竟是与之对应的R,还是那个我已经忘掉的所谓“女友”,已经无从确认。
但此刻它们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里,已经说明了那必然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情感,不管它怎样绚烂又或者怎样悲壮,现在已经结束,尘埃落地。
于此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一个小小的插曲,记忆就是那样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你不去回想时,它总在你的脑海里若隐若现,仿佛触手可及,可你一旦仔细琢磨,它又变得扑朔迷离,飘忽不定。
后来某一天,我接到了毕业同学的邀请,参加一场聚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几个大男人便失了谨慎和口中的遮拦,大咧咧地谈论起自己求学时的岁月。
诸如当年谁追过谁,谁和谁闹过什么矛盾,这些事通过酒精的作用和饭桌上醉醺醺的气氛,磕磕绊绊地从记忆里被抖落出来,我们狼狈地伏在酒桌上,数落着回忆。
话轴子转了一圈,终于转到了我的身上,我当时是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属于班里只知道有我这个学号,却不知有这么个人的存在,于是大伙努着嘴思索了半天,也没数出个所以然来。
“要我说就是闷骚,这家伙高中三年屁不放一个,毕业之后却换了个人。”终于有人憋不住了,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此话一出,多数人拍手叫好,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确大约是这样的人,但这与我现在的状况却又似乎不相符称。
“所以才说是闷骚,现在终于憋不住了。”有人又言,众人哄堂大笑。
我与他们一同笑起来,在记忆中那个形单影只的身影似乎又清晰了一些,他站在将息的夕阳下,戴着那对羽状的耳环,我甚至不愿将他认作是我,或者说他亦不想将我认作是他,有一刹那我确信他正坐在一角,看着我如今的样子冷冷发笑。
回到家的那晚,我在酒精的作用下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短发的女孩,她牵着我的手,在朦胧的迷雾中,我看到她似乎身着我们高中的校服,背着与我一模一样的书包,挂着一对金属羽毛的耳坠。
我在梦里确切地感受到了悲伤,但我却无法恸哭,悲伤像潮水一样漫过我的胸口,死死地将我摁住。
我惊醒,妻子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做噩梦了?”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妻子有些不解,但仍然抱住了我,如同我之前抱住她一样,体温从肌肤透入身体,我感觉好多了。
之后的几日,梦中的情景便一直困扰着我,它使我心神不宁,我像是被一个幽灵缠上了。
于是我在一个夜晚,带着这个问题,找到了母亲。
“短头发的女孩?没有啊,我从来没见过。”
只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自然有些不满,于是装作回忆生活琐事,与母亲谈起我的高中生活。
“你以前有一次掉进水里,你还记不记得?”
我努了努嘴,仔细回忆着。
“以前你有一次大冬天的去上学,不知怎的居然掉进水里了,当时回来把我和你爸吓一跳,连着发了好几天的烧。”
“然后呢?”我追问。
“没有然后啊,然后就是高考了。”
而后我又与母亲闲聊了些许时间,只不过我有些心不在焉,她临走时不忘又嘱托了一句我和妻子的传代问题,方才离去。
次日下班,我开着车特意绕道,来到了城市的另一边,如今这里有些萧条,城市建立了新的城区,这里作为老城区已经没多少新的建筑,陈旧的房屋躺在街道的两旁,像一群垂暮的老人,低低矮矮地立着。
顺着陈旧的街道一直开,尽头有个岔路口,左拐,便是我的母校,母校的旁边临着一条小河,顺着左边的主干道向下走,能到一片乱石滩,河水是黄褐色的,里面飘着几条运沙的货船。
我停好车,走到乱石滩上,水位褪去,露出已然干枯的青苔和褐色的泥浆,我一瘸一拐地走到临水的地方,空中跑动着有些割脸的冷风,我像个石像一般站在那里,闭上眼睛。
水声,呼吸声,风声,它们掺杂在一起,我感觉身体变得很重很重,好似要沉下去,似乎有什么紧紧拉住了我的脚腕,邀我共如水底。
风声渐息,我睁开眼,已是夜幕降临。
不远处,一个女孩正蹲在乱石滩涂上,用指甲一点一点地扣着板结在石块上的泥浆。
我走过去,靠近她,叫了她一声。
“好久不见。”她仰起脸,说。耳垂上的羽毛饰品闪闪发亮。
我有些疑惑。
她的眼睛里装着漫天的星空,还有我的脸。
“原来你已经忘记我了。”她似乎有些失落,垂下手,不再看我,而是远远地看着和面上驶过的夜船。
我的心颤了一下,一同与她蹲下来,看着她的脸。
“这些年还好吗?”她问我。
“还好。”
她撇撇嘴,似乎在考量还好这个词的深意,可最终摆摆头,什么也没说。
“还给我吧。”她摊开一只手,向我索取。
我知道她在问什么,犹豫了一下,取出一只尚未生锈的耳环递给了她。
她握住那耳环,倏忽起身,做了个很标准地投掷的姿势,夜色中一块儿银色的金属打着转,化作一道弧线没入水中。
“再见。”她起身对我说。
“再见。”我对她说。
……
我再醒来的时候,妻子坐在病床的床头,空气中满是消毒水的味道。
我注意到她通红的眼眶,于是轻轻喊了一声她的名字。
“我没事。”我说。
她先是吃了一惊,而后急匆匆地跑出病房,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一大群医生。
他们掏出听诊器,在我身上胡乱摸索了一阵,最终与妻子耳语了几句,便又离开了。
妻子紧紧地抱住我,哭了。
“怎么了?”
“你吓死我了。”
妻子伴着哽咽说,我失踪一夜,电话打不通,她报警找了很久,才在乱石滩上找到昏过去的我。
“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用手擦了一下她的眼泪,思忖了一下。
“去见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一个再也见不到的朋友。”
事后我向母亲求证,我高中时确实郁郁寡欢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与人说话,直到那次落水发烧,我才突然性格大变,成了如今这般样子。
一个猜想在我的脑子里成型,最后慢慢清晰。
“你说以前你精神分裂过?”
我点点头,妻子则一脸的惊讶。
“可你现在看起来好好的。”她用手指轻轻戳了一下我的脑袋。
“所以说只是猜测。”
“那你是你,还是她是你?”妻子指了指我手里那只生了锈的耳环。
我摇头,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那个答案,或许那只是我的一场中二病,或许只是我的一个幻想,又或者真的我就是个精神分裂,前几天又复发了。
“算了,别想这些了。”她突然故作神秘地握住我的手,把什么东西放在了我的手里。
“你怀孕了?!”
“嗯!”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你前几天晕过去的时候。”
“啊啊啊啊啊!什么时候的事情,你怎么才告诉我?”
“这不是怕你承受不住嘛,医生说这几天不能让你太激动。”
我深呼吸了几下,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浮现,我迫不及待地凑到妻子耳边。
“名字你想好了吗?”
“没有。”她摇摇头。
“我想好了。”
“叫什么?”
“吉光,吉光片羽的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