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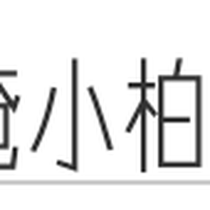

我拿记录本扇着风在金砂镇内随意走动,临海那清爽的风扑打在我的脸上有些酥麻。这片的文化环境与伽勒尔不太一致,人人都满溢干劲做着各自的事,在广告册附送的指南上提到过有关探险与淘金的历史,如果能找到当地的文献也许能作为不错的见闻。于是我挥挥手朝一名看起来同样在散步的路人打了招呼:“您好呀,我是新来这边旅游的,想了解一下当地历史,请问这里有藏书馆吗?”
“书馆?这里没有。不过想了解历史的话倒是有个博物馆。”路人指向大路另一端,给我展示了一下手里的钱包,“我要去商店,没法带路,你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不会错过的。”
我笑着微微鞠躬:“太谢谢叔叔啦!祝您今天愉快。”
金沙博物馆坐落于金砂镇的中央广场前,是新居民与原住民共同的心血结晶,他们携手将这片土地上珍贵的记忆与宝藏汇聚于此。站在正门前,高耸的立柱宛如宝库守卫般保护着时光,诉说柯利奇地区的古老传说。有许多戴着旅行团徽章的游客也在此出入,看来这次空中意外为这个地方带来不少新鲜血液。
随着人流我很快进入了第一个展厅,以砂岩装点,陈列着金砂城周边出土的各类稀有矿石,颜色形状各异,来自于上亿年前的世界。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古宝可梦脚印化石,有的迷你可爱,有的甚至能躺下一个人,在旁边就是研究员们根据发现的脚印和骨头化石等还原出栩栩如生的古宝可梦模型,在现有的宝可梦身上似乎还能看到它们的影子,这会是它们的真实模样吗?我仿佛看到了远古大陆上这些宝可梦们生活竞争的场面,真希望从大学毕业后也能顺利成为探究历史的研究员之一。
继续向里走,是先祖们留下的痕迹——各色航海装置和简易船模。他们或许乘坐着简陋的船只,与风浪搏斗,远渡重洋踏足此处,为后世开创了富有探险精神的金砂城。我凑近展柜观察,十字测角器、星盘之类的工具应有尽有,虽然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然无法正常使用,但鲜少的划痕印证着先祖探险家们的细腻保养。满面的方帆上粗犷地挥洒着两笔鲜红,张扬探险者们一往无前的勇气。更让我惊讶的是,竟有一个带锁的小盒子装着的指南针。在航海新兴的时候,指南针由于科学暂无法解释为何可以“找到”南方,被附上一层神秘色彩,因而一般的航海家都不敢使用。只有胆大的船长才会悄悄携带这种带有锁的盒子指南针。
我在记录本上写写画画,穿过门,展厅一下变得空旷起来,人群围在一座雕像旁讨论。那是一座由嘟嘟利重叠组成的图腾巨作,最顶上的嘟嘟利高昂着头颅眺望远方,像是引领方向的领袖;中层的嘟嘟利三头分别转向不同的方向,也许在谨慎地排除危险,也许在满怀好奇地探寻新鲜事物;最底下的嘟嘟利目视前方大张开双腿作狂奔态,锐利的爪子在地上留下了巨大的脚印,在这片土地上一往无前。我来到一位正在热情讲述的解说员旁边——先祖探险者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原始部落,并在他们的热情邀请下一起生活。原住民们崇拜飞驰的嘟嘟,留下的巨大脚印和时刻警惕周围的双头彰显着嘟嘟的力量与智慧,作为这片土地的守护神与人类共同生活。那些原始的居民们,或许会在祭祀的夜晚,围绕着这样的图腾柱,载歌载舞,祈求嘟嘟的庇佑,感谢嘟嘟与他们共同铸就了这片家园。
我再次仰望起这座图腾,仿佛能穿越时空,看到那位雕塑家专注而虔诚的神情。他的手中握着刻刀,每一次下刀都小心翼翼,却又充满了勇气。他或许是部落中的一员,或许是某个来到此地的探索者,但他对嘟嘟的热爱,让他将这份情感凝固在了这尊图腾柱上。手中飞舞的笔停下,心中所想都抒发到了文字之中,我满意地合上记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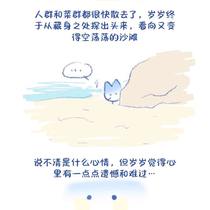








作者:徳蔚
mode:随意
备注:亡夫回忆录,呜呜在想的人物小传,先这样交了吧(捂脸
帘外雨潺潺,水色黯淡。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休息过了,像忘记停止运转的机器,一直步履不停。
高热带来的疲惫把人变成一团面糊,可以拉得很远很远,混沌的意识在沉重的躯体里飘荡,分离的灵肉褪去他背负的枷锁。
当时欲拒还迎地被谢渌带上山,结果着了凉,好像也是这样。
久燃的蜡油在烛台上凝固,一滴新泪方才悠悠转转地从柱面滑落,静静地停在烛柱脚边。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熟悉的脸仿佛近在咫尺。
幽幽的烛火勉强能够到谢渌的脸,然后在清秀的脸上淌下朦胧的光影。疲惫和担忧挂在他的眉间,纵使睡着了也没有完全消散。他就静静地躺卧在那里,胸腹微微地起伏,后颈的肌肤洋溢着朦胧而莹润的光泽。他的口唇在昏暗的光线里吐出热气,鲜活的,好像睁开眼就会同他欢天喜地地把世间风物说尽。
他不由得笑了,因高热而干枯的嘴唇却撕裂出一丝疼痛,宣告此情此景不过是回忆。于是,那帘断梦就这样碎了。
薛旻微微睁开眼,小口小口的呼吸着。空气穿过喉头,像灼烧,像随着檐角坠落的飘雨,由一点燃遍全身。身躯一坠一坠地抽痛,他有些分不清楚,疼痛是不是在心口。
额发被汗水浸湿,丝缕黑发缠绕着贴在颈部,有些发痒。鼻子也因风寒而堵塞,头脑嗡鸣,薛旻感觉自己昏昏沉沉,好像和他一样溺于水底,却又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头脑里倏忽地蒙上层雾,看不清自己在哪里,看不清迷雾里充斥利欲的双眼和背后幽冥的火光。
“是不是放下昔日的怨念与渴慕的权势,就不会此恨绵绵?”他撇了撇嘴,疲惫地阖上双眼,汤药汩汩地在小炉里冒着白气,苦涩的药味混着雨夜的腥气袭来。
腥气,他从来都很熟悉。是骤雨初歇时泥土的腥涩,还是寒风与体温缠斗,鼻腔的毛细血管微微破裂?又或者是在板桥上,眼见他和那些世家同侪拾翠暮忘归,快活自在。柳絮纷纷扬扬地撩着心头,咳嗽和感情在胸腔里作痛,无法掩饰,最后化作午夜里雪花膏般的火焰。
不是的,那比一切都要多几分。它多一点沉痛,添几分潮湿,却又像案板上绵软的鱼尸,泛着粼粼的光,双眼晦暗不明。它丝丝入扣地舔舐着脊骨,冷意永随,纵是狐裘锦衾也稍显单薄。那是石阶上血色的身影,青草池畔的梦魂,随着流水而去。
怎明白咫尺伊人,转以睽隔不得相亲?他看着奔涌的水流,目光已经疲倦。
恍惚间,来人咧着嘴笑,不管不顾地举着酒杯碰向他的那只,说:“薛兄,大事将成,同乐。”他依葫画瓢,勉强咧开嘴,却觉得手重得举不起来。这时忽地感觉一只更加冰冷的手拉着他,轻蔑地劝他杯莫停。
酒水从晃动的杯体里荡漾而出,在深色的木桌上画下点点水痕。水里倒映出模糊的面容,苍白无力,没有眉眼,空洞洞的。像遮蔽的纸张被锐器戳破,顺着破洞往里看,黑漆漆的,浮动着痛苦的青筋。血液从空无里流淌出来,混浊污秽,那是死亡。
再没有这样喜欢山水澄明的青年了,会悄悄约着他看春日悬泉,摇醒他见池边高树,拉着他赏月出五山。和风不会再拂过他的脸,亲吻微微翕动的嘴。
身体里的嫉恨随着死亡而死亡了,薛旻把那柄惯用的折扇和他一起埋了。别人问起,只道,好物不坚牢,丢了便是丢了。
所以之后这里只会剩下一个卑鄙之徒,带着一点爱和无力的肉身自欺欺人,然后被翻覆在沧桑的青史里,不会被原谅。后来有人说,叛国贼子,死得其所。他想,这是应得的。
烈火滚滚,发着焦黑的烟气,药炉碎裂开来。炉里的水已经烧尽,长时间炖煮的草药杂着陶片坠进正旺的火炭里。
声音不小,他当然已经醒了,但还是闭上了眼睛。
他正想到很久之前,他们登山观瀑,谢渌笑脸盈盈,同他说什么岩下云方合,结果踩上青苔一下就掉进水里。裤脚都濡湿了,但他还冲他羞赧地笑着。
薛旻想,若是再来一次,他会扑通一下跳进水潭里,同他一起,而不是手足无措地站着。
他会无所顾虑地,朝着水边跑去,跳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