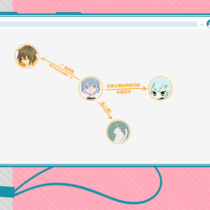“你们要出门?”
雪精灵的通用语有点口音,冰碴子刺着舌头似的总往里卷,像要带出点弹舌。好在他的室友们已习惯这北国来客的话,能理解他的意思,也就作出应答:
“是啊,今晚和小鸽子去酒吧。”
斯特凡诺·达勒将手搭在尼格勒肩上,翼族只稍高一点,人类的动作做起来还算轻松,就是手肘总蹭到对方的羽翼。卡伦特来的船商末子喜欢那些流动的信息,那些趁着风撞在礁石上的浪……他曾将收集起的信息用细线串成束,理成一条完整的信息(充满符合逻辑的推测),又给信息配上惊心动魄的文字并投稿给《镜面报》和《卡伦特河报》(遗憾地未被入选)。传言的追逐者自然会被水流交汇的区域吸引,在苏古塔,这地方就是十年前兴盛起的酒馆“法之理”。去酒馆点上饮料,挑个桌子呆上几个钟头,听听周围的谈话,偶尔还和人聊几句,斯特凡诺很习惯这样。在二月6日这个熏着微风的夜晚,他照例要去法之理消磨时间,室友的加入让他越发愉快,几乎要哼起一段家乡的小调。
“尼格勒还未成年。”阿列克谢说。
面对奇维纳人的指摘,来自联合王国的人类露出一个柔软的笑容:“他可是去做正事的……我也跟着呢!”
“我去找我的老师。”翼族少年补充。
他指的是早春时来到的半精灵。
于是雪精灵不再多做阻拦,他点点头,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站在客厅的两人也并未因室友的冷淡而有异言,近一个月的共同生活已能显出各自的品性,除去生活习惯上的差别,三人相处得不错。
他们是在提供租房信息的地方碰见的。
苏古塔一个月一次的访问限制随着“门”的开启被打破,法师学徒不再是来往人员的唯一构成成分,为了满足自己的日常用度,一群脑子活络的外来商人联系上苏古塔本地的居民,四处搜集房屋出租的信息,再将它们汇集起来,集中展示——这就是“房屋中介”的由来。暗月城似乎也有类似的组织,听说自由度更甚苏古塔,倒也不知是哪里先产生了此种机构。总之,与传统的寄宿家庭相比,有许多不擅长与人打交道或向往无拘束生活的学生都更乐意去中介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阿列克谢就是如此。
那时候他通过书信往来确认了自己通过考试获得入学资格的消息,又恰巧之前留宿的旅店有与之联结的租房中介,奇维纳人就将行李寄存在旅店,准备敲定住址后再前往中介领取:如果利用指定中介,旅店的工作人员就能把编好号的箱子帮忙送至签租借合同的地点。阿列克谢看过两三个地方,很快便作出选择,他依据宣传单找到签订合约的地方,却发现店里坐着一个年轻翼族,像在等人。这人雪精灵认得,他们住在同一个旅馆的不同层,偶尔会碰见,算是点头之交。对方很快察觉向自己投注的视线,他站起来,问道:
“不好意思……这是您的行李箱吗?”
阿列克谢看向他指出的方向,两个相同木箱并列立在墙角。为着方便,他只带上很少的行李,纸、笔等用品都是雪精灵到了苏古塔后在当地购买的,用来收拾整理的方形箱子也是这样。他们可能碰巧买了同一个样式的箱子,而工作人员却在记录编号的时候给弄错了。雪精灵走过去,伸出手指往提手内侧探。
“的确是我的。”阿列克谢说。
“啊,谢谢……”年轻翼族停顿一会儿,“虽然有些突然……但您需要室友吗?”
这正是尼格勒。
在经历过501年春的那场梦境后,翼族法师决心将进修的想法付诸实现,萨米尔在知道这件事后有些惊讶,倒也没阻拦,“哎,现在好歹知道跟家长说一声了”。只一点,他在费用的问题上十分坚持。
“小孩子出什么钱!”德鲁伊说,“你专心学习就好了。”
“我有些积蓄……”
“你不用操心这些问题,有大人在呢。”
“你的年纪只抵人家四分之一。”女诗人夸张地说,还拿手比数字,尽管她活过的年岁也不到翼族的二分之一。
萨米尔反驳:“未成年就是小孩。”
“说的没错,萨米尔叔叔,那么你就出学费吧!”
“那是当然。如果还要什么别的,你奇诺娅阿姨全包。”
尼格勒平静地看着眼前的热闹。他们总是这样,两位半精灵先你来我往讽刺一番,分享似地交换些夹枪带棒的话,当双方都对这应酬满意后,再一齐将矛头对准好脾气的人类,就着他闹上一阵……固定不变的行为变成类似仪式的东西,这小团体就靠它来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冒险者的日子不好过,睁着眼也能一头撞进危险。那些故事、诗歌,哪一个不是流着血与泪?他们幸运地从荆棘中脱身而出,能够用握着兵器的手再度拥抱朋友,用见识死亡与谎言的双眼膜拜太阳,他们需要这样一种仪式,将积攒的细小情绪发泄,将心灵与头脑从生死的悬崖边扯回。
“我也建议先让大人们出一部分,”里德说,“等安定下来了,再自己负担,怎么样?”
话说到这个地步,尼格勒也只能点头。出于少年期特有的感性,他想尽早自立,来自长辈的照顾却也不坏;并且他不在这里后退一步,两个半精灵的言语往来只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就这一会儿,他们的话题就已经跳到了“养老金”“棺材本”。
“哎,你们说什么呢,怎么想也是我先养老啊。”
像是终于注意到人类一样,萨米尔侧过脸:“老大,不用全付,真不用,一半就够了。”
里德听到后,卷起了袖子。
笑闹的焦点转移到两位男士身上,女诗人脸上闪过的动摇就被忽视,那一瞬的怔忪如暗中射出的箭,未明来处,不知去处。银发的半精灵也奇怪自己的变化,方才的热闹像是假的,一切温暖都被剥离,莫名的恐惧攥住她,冷。奇诺娅抬手摸摸自己的脸,又尝试着作出个笑,她思忖:里德说了什么话……他说的什么话?
之后,尼格勒就来到苏古塔,渡过一段时间的备考生活。在经过一次不大不小的误会后,他与新结识的室友一同走在太阳塔区域,回到他们之前都看过的、因为没必要而被排除选项的套房那里,与商业街只隔了一条小巷的楼栋不会被街上的喧嚣打扰,也不过于冷清;整层出租的二楼底下是面包房与餐厅,都包裹着轻盈的烟火气,房间内的设施也较为完善,总体而言是不错的物件。他们在中介人的带领下到了房门口,正好碰上从门内往外迈的斯范特诺,来自卡伦特的人类惊讶地睁圆眼睛,然后快活地问:“要一起住吗?”
事情就是这样定下的。
现在,(自称)撰稿人带着翼族法师前往法之理酒馆,雪精灵则呆在房间里,就着烛光阅读。
奇维纳人的夜晚平静地过去。
“昨晚过得怎么样?”阿列克谢问。
斯特凡诺和尼格勒对视一眼,人类露出“不知怎么说”的困扰表情,翼族则显得很低落。
“嗯……发生了不少意料之外的事。”
听到斯特凡诺的回答,阿列克谢有些讶异地睁大眼,他没有深入追究昨晚发生的事,而是提醒道:“别忘了今天下午的安排。”
“啊——”
雪精灵说的是作业的事。在之前的课上,艾丹·弗宁将教案分发给学生,并布置了一项作业:见证一次神术施展的过程。这项作业完成起来并不难,只要找到一位能施展神术的人就行,无论是德鲁伊、牧师或是卷宗学者,恰巧,阿列克谢正认识这样一个人,于是便将请求同他讲了,对方也欣然应允。他们下午要去见的人是锡里昂·暹罗德,一位来自菲薇艾诺的卷宗学者,同时也是三位室友的同院同学。
锡里昂·暹罗德与阿列克谢·弗拉基米尔·伍比沃克的认识过程充满喜剧色彩。在开学仪式后,苏古塔魔法学部举办了学院内的交流会,方便同学间的交流,锡里昂的动物伙伴也参与其中。当锡里昂介绍伯伦希尔——那只巨大的白狼——的时候,阿列克谢恰好不在;而当雪精灵回到会场、一眼看到那巨狼的时候,锡里昂又恰好转过身,站开了一点儿。奇维纳人立刻朝温顺地趴在地面上的动物走去,他伸出手揉揉白狼的头,又挠挠它的下巴,阿列克谢的身材以雪精灵而言算得上高大,他的手也大,伯伦希尔被他搓得东倒西歪。
“啊,小家伙,谁带你来的?”姓氏与狼颇有渊源的奇维纳人用精灵语小声地说,“真是个乖孩子。”
锡里昂听到带着口音的精灵语回过头,恰好看见阿列克谢搂着狼来了一个过肩摔。据后来的解释,雪精灵,或者说奇维纳的德鲁伊时常这样与自己的动物伙伴(有不少是熊)玩耍。
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下午很快到来,他们约在一处还算僻静的地方,要聚众干坏事似的。在三人的围观下,锡里昂对着地上的目标施放了一个纠缠术。起初,是细小的响动,预示着什么的发生;接着,像烧开的热水一样,那些聚集的土与石块破裂沸腾,藤蔓张牙舞爪地涌出,如同市场上疯狂挥舞触手的章鱼,它们虬结在一起,凶狠地抓住了范围内它能抓住的一切。
“……令人印象深刻。”阿列克谢说。
高等精灵羞涩地笑了一下。
在室友们提出自己的问题时,雪精灵看着天空整理思绪,然后他问道:
“锡里昂,你在随着心意施放神术的时候,能否察觉到生命之流,或者说自然之力的流转?”
“嗯……”年轻人想了一会儿,“德鲁伊——当然我现在是卷宗学者——我们不必借用神祗的力量便使用神术,因此我是直接感受生命流并向其请求帮助。”
“那么你,呃,以前当德鲁伊的时候,是对自然有一定程度上的情感或忠诚心吗?”阿列克谢追问。
对此,锡里昂回答:“我们都是自然的孩子。”
在二人谈话时,尼格勒施展出一个火球术,默默地清理掉这一片过分茂盛的植物。
“那么你呢,尼格勒?”斯特凡诺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施法的时候有感受到与生命流的联系吗?”
“如果说施法的感觉……就像是有什么东西随着法术释放出去了。但那会是生命流吗?我不确定。” 翼族这样回答。
接下来,他们一起去商业街找到个地方吃完饭,说了些学生间常聊的话和过去的有趣经历,再各自分别。
在作业的总结上,奇维纳人写下如下字句:
德鲁伊们依靠自然,感受自然,并向自然请求帮助,这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建立起一种特有的、与牧师和各自神祗们不同的联系……“他们向人们呈现生命之流的原始模样”,这句话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自然之力是未经“加工”过的生命流。“生命之流”本身有随季节循环的特征,此种循环中蕴含的“有生有灭”即是生命流遵循的轨迹;而牧师们使用的神授力量,则是生命之流其中某一个侧面的体现,并且仅就十二位主神的牧师而言,生命之流的体现似乎与牧师们所信仰的神祗的特性有关,如兀烈卡卡牧师们特有的“天炎”与“干雷”。
至于魔法……也许魔法是对生命之流进行了更深一层的加工,且此种加工并非处于物质层面,而要更细微、更深刻。就像洪水经过时总会吞没平静的河道,更为“原始”、单纯的力量将精巧的构造掩盖了,或许这就是神术对奥术具有更强干涉力的原因。
End.
————————————————————————————————
全文4005
大人们就不关联了!
尼格勒:感觉有什么东西随着法术释放出去了
阿列克谢:是肝啊
斯特凡诺:是肝呢
再次感谢锡里昂同学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