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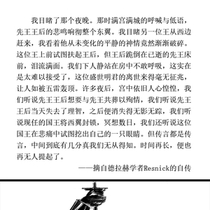









QA提问会持续更新,欢迎在评论区或是私信企划主里提问!
2018/1/18第一次更新,【关于角色】新增四条提问,【关于召唤】新增一条提问,修改一条回答。
2018/1/19第二次更新,【关于秽】新增一条提问,【关于角色】修改一条回答。
2018/1/23第三次更新,【关于角色】新增一条提问,【关于清扫者】新增一条提问。
2018/1/25第四次更新,【关于组队】移动到队伍登陆位置,【关于清扫者】新增一条提问。
2018/1/27第五次更新,【关于组队】重新移动到这里。
-------------------------------------------------------------------------------------
【关于角色】
Q:企划会限制某一种族或是阵营的人数吗?
A:所有角色都不限,就是在某一方比重太大时会限一下。
Q:角色能力有什么限制吗?
A:人类禁止挥手招来千军万马,可以随意动用国家政府资源,妖怪和灵不超过可以随便改变地形,扭曲现实,力拔山河,手撕高达就好。但具体还是在审核中按照情况判定。总之就是不能太夸张啦。
PS:人类也不能手撕高达。
Q:角色外观有什么要求吗?
A:人类要像个人,妖怪和灵随意发挥。
Q:可以开秽妖角色吗?
A:可以。但是场内只有在第一章死线前和清扫者定下契约组队,正在净化中的妖怪这种情况才会允许存在。如果在死线后依然没有达成条件,将强制转为场外角色。
Q:人类可以开那种反社会的角色嘛?杀人狂魔那种的。
A:可以。但是此类极端角色是不允许组队的,死线只能靠自己。
Q:可以允许是有特殊技能或是职业但却不在清扫者阵营的情况吗?
A:允许的,但这种角色在实力上会卡的紧一些。所以要是是有实力却不积极,世外高人这种设定的话还是建议选择清扫者阵营比较好。
Q:请问服装有限制吗?
A:没有哦。但是由于时间线为以现实为基准的现代社会,所以在现世穿古装或是奇装异服还是要考虑下理由啦。
Q:灵是没有实体的吧?
A:是的。灵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存在实体的,人类如果碰到会直接穿过去。不过如果是妖怪或是有妖怪血统的人类就可以普通的碰到它们。
Q:灵说话可以让人类听到吗?
A:关于灵说话……普通人类是不能普通的听到低级灵或骚灵的声音的,所以骚灵一般会借助各种工具(电话,手机)引发骚灵现象来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
不过高等灵就不用在意这些,可以用幻术“让对方认为自己听见了自己在说话”,所以答案是可以。
Q:可以出现海外(外国人,西方妖怪等)人设吗?
A:可以出现海外人设啊。
顺便说一句,关于里侧基本上是不存在所谓“国家”的,当然类似于总统之类的人物也不会存在。但在各个会有妖怪聚集的区域都会由本地的土地神或是实力强劲的大妖怪进行管辖,这些管理者通常很少会在现世或是里侧众妖面前现身,只有当自己的管辖地出现威胁到两界平衡的危机时,他们才会亲自现身解决问题。
Q:如果是那种传说中物品和动物变成的妖怪,是诞生时就是会在里侧出现已经存在的对应种类的妖怪......还是现世的东西直接变成妖怪?
A:让我先理理……
首先……本身新的妖怪就会诞生在现世而不是里侧,这一类的妖怪则要看种类。
如果是物品类就会是在相应的事物上产生像是灵一样的附身妖怪,等到时机成熟时就会真的变成那种妖怪,如果是动物类就是本身化为了相对应种类的妖怪这样吧。
物品类的情况是会和本体分开诞生一个本体出现的一切变化都会共享的“分身”,如果本体出现了什么情况就会反应到“分身”上,反之亦然。
这种的妖怪一般都是“只要曾有人认为它是妖怪”就会有变成相对应妖怪的可能性。
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壶,曾经买了这个的人不知咋的就挂了,然后转手卖了后,很不幸新买的人又因为什么挂了……一旦有人把原因归在壶上,那这个壶就会有变成真的会像传言那样咒杀人的妖怪的可能。
顺带,在物品类妖怪在初诞生时是可以按照除灵的手法根除存在的。
动物类更简单,只要人类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类似“这狐狸这么聪明怕不是成精了”的话……
像这样的语言是具有魔力的。只要动物本身确实有着足以化为潜质……比如比其他同类更高的智慧或是远超其他同类的寿命……就会有变成妖怪的可能。
类如僵尸、吸血鬼等妖怪也是以这种原理产生的。
Q:妖怪和灵到底有什么区别?
A:简单概括,灵=生物具体的残留记忆,妖怪=从幻想中诞生的生物。
Q:既然有半妖,那能有半灵吗?
A:有的。但并不是指祖先是灵,而是说曾经被某个灵长期附身导致自身体质也开始接近灵,因为在濒死间吸收了灵的力量而活下来所以有脱离人类的地方这类的情况。比如容易被妖怪和灵错认啦,影子比较淡啦,容易被附身等等。基本上没啥酷炫的技能,体质接近灵也是说“像灵一样脆弱”,动不动就大病小病,不擅长运动,有能看到各种灵的阴阳眼之类的。和有妖怪血统的人有回归里侧的可能性不同,这种人类就是死后留下灵的可能性稍微大点而已。
顺便说一句,无论是半妖还是半灵,都还是属于人类种族的。
Q:像狐妖猫妖这种动物类的妖怪,或者神仙类型的妖怪,这两种和人类生育后代可以理解,那么请问像A:是树妖花妖或者由器物化成的妖怪可以和人类产生后代吗?
可以。只要化为人形就可以。
Q:灵在什么情况下能被看见啊?
A:基本上中级的灵是努力一些就能让指定的普通人看见,高级灵完全是看心情。如果说低级的灵,除了心灵还很纯洁的人(小孩子)或是动物,就只能依靠清扫者的手段了。
而妖怪只要集中注意就能看见灵,有妖怪血统的人类也同样能办到。
【关于死线】
Q:会有剧情杀吗!
A:不会有啦。要说唯一的剧情杀就是死线。
在剧情里的表现大概就是……被里侧吞噬,或是离开小镇从事件脱身这样。如果种族是妖怪,也有可能是“被秽染后成为了清扫者的目标就地讨伐”这种结局,而灵则有完成执念后消失的可能吧。
【关于两界】
Q:里界和现世的镜像关系 是这俩地方叠在一起还是完完全全是两个世界只是有通道可以连接?
A:叠在一起的感觉吧。但是要从一边到另一边必须有“通道”来打破空间壁(?)才行。
Q:妖怪们是怎么样看到现实这边的?可以是通过镜子啊,水面啥的看吗?
A:可以的。基本上都是从一些离通道接近,或是有成为通道潜力的地方看的。
Q:通道的话,可以是一件物品吗?比如,触碰并吟诵咒文就能到达里侧之类的。
A:不可以。但可以设定是信物或是钥匙之类的,到达某个地方就能找到或打开通道入口之类的。
【关于秽】
Q:秽染与秽妖究竟是什么关系?
A:简单来说,只要是被秽染的妖怪就是秽妖。
Q:秽是如果好多人都有一点(不是很极端)就会根据人数积累成强大的秽让妖怪秽染吗?
A:不会积累,但是这就根除了你周围人都在感冒一样……一不小心就……
但如果是已经秽染的妖怪,就有持续吸引周围的秽到自己身上,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危险的可能了。
Q:有个小小的问题。有里侧血统或是不完全是人类的角色...沾染秽会发狂吗....?
A:不会。只要是人类的部分就不会发生什么。或者说只要还是人类的部分占主导地位就不会。
【关于召唤】
Q:话说存不存在将妖怪召唤入现世的设定啊?
A:存在的。不过只限一些性质特别强烈的妖怪,一般召唤到的是与期望召唤的妖怪性质相近的灵的情况会比较多。
也就是说妖怪性质越接近灵越有可能召唤出来。而关于接近灵的妖怪,所谓都市怪谈和恶魔妖精统统可以归为此类。
Q:那,可以召唤指定召唤的英灵(划掉)对象吗?
A:可以指定卡池……不,是大方向。比如说想召唤恶魔系就是骨头啊祭品啊魔法阵啊这种的……东方系就要跳大神还有摆八仙桌啥的吧。如果是都市怪谈类,则是与怪谈内容相符合的行动这样。
Q:那召唤出的对象是除了大方向外完全随机的吗?
A:基本上是。
Q:有没有只是感觉差不多的东方系妖怪结果被指定西方类型的召唤仪式错误召唤的情况?
A:只要指定性质相近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想召唤“暴食”类别的恶魔结果出现饕餮也是可能的……
就像从限定PU池里歪出来的常驻五星……
Q:召唤来的灵或者妖怪还能回到里侧吗?过程可以自定义还是有特定方法?
A:可以的。一般是利用附近或是召唤产生的通道回到那边。企划也接受过程自定义的方法。
Q:普通人也能召唤妖怪和灵或是和他们签订契约吗?
A:可以。只要掌握方法,无论是谁都可以召唤,契约也是如此。但是......因为召唤的代价或是方法搞错弄错召唤对象,以及由于缺乏关于契约的知识导致做出的契约存在漏洞,结果被钻了空子的妖怪反杀......等等原因造成的各种悲剧,基本上可以得出普通人乱召唤or乱写契约=离死不远的定律——
当然也有一些因为契约条件对妖怪来说完全没问题,并且妖怪方也乐意付出,最后可以顺利的活到寿终正寝的草根召唤人......不过这些人的后代通常都会为从祖辈那里继承来的契约所苦,而被召唤出的妖怪到最后不是变成了秽妖,就是被现世同化。
无论如何,这些鲁莽的打破两界墙壁还完全不会考虑后果的人对里侧和现世都是灾难。所以有一定实力的妖怪都会下意识的回避召唤,而清扫者们也会在发现后第一时间前去解决。
【关于玩法】
Q:企划的每月打卡有什么硬性要求吗?
A:有的。每月打卡主线首先要求至少有涉及当月主线的地方,哪怕一句话一个画面也可以。
完成度方面图禁止火柴人或简笔画,文禁止千字以下创作。用支线打卡的情况下要求要有完整叙事,如果是实在不能在本月内完成的情况,需要事先和企划主说明情况,可以酌情延期。
Q:每章支线数目,以及支线之间是有联系的还是无关?
A:每章只有四个,但有时候会开放一些特殊的支线,比如节日支线什么的。但是就算支线被拿完了也可以创作主线来打卡啦。至于有无关联,有一些支线是只有前一个被解决后才会继续开放的,所以是有的。
Q:任务结束后的奖励要怎么发放?
A:只要记得打上任务的标签提醒企划主任务完成就会按照任务的说明在评论栏发放相应道具。奖励多半会是钱或是娱乐向的小道具吧。
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很OP的东西啦。
Q:角色与角色间可以对战吗?
A:可以。但由于企划不是战斗为主,胜负奖惩还请自己决定。
【关于组队】
Q:可以随便换队伍吗?
A:队伍一旦结成不建议解散重组。因为登录队伍会变得麻烦(。
顺便,小队之间是可以相互合作解决任务的。也就是允许同一个支线可以用来打最多两队(或者按照支线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卡。
Q:组队的人要怎么创作啊?一起合作画漫画?接力?还是说讨论好事件四个人分别不同视角来一遍?
A:这个就是组內自己讨论了,就结果而言只要一个队伍每个月能完成一篇记入主线/指定支线相关的创作就能免除死线。
Q:跨阵营可以组队吗?
A:当然可以呀。毕竟不是对抗企划嘛。阵营代表的也只是“你的看法”而已。
Q:因为还没找到契约对象所以先暂定其他阵营可以吗?
A:不行,企划不能转换阵营。不过也并不是其他阵营与清扫者签约就不能打架,保持阵营与清扫者签订契约,等企划结束后在场外转换阵营也可以哦。
Q:序章结束后还能组队吗?
A:可以啊。
Q:可以给队伍起名吗?
A:可以。
【关于清扫者】
Q:除去签订契约的情况,契约清扫者是只限人类选择吗?
A:是的。顺便一提半妖或是半灵也是算在人类里可以进行选择的。
Q:清扫者的净化有什么代价吗?
A:没,就是麻烦还风险大。一定要说有什么代价那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在入封印素材这里花钱绝不能手软……以及祛秽也是一样烧钱的。
一般来讲只有制作与妖怪或是灵的契约书或是实行比较凶险的召唤才需要见血的。
Q:妖怪有可能在被清扫者收服后外形发生变化吗?
A: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被强制封印了部分能力后因为力量缩减而外形也随之改变,一种是清扫者为了在现世掩人耳目所以在契约中写明了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
Q:如果式神的主人死去,后人可以继承契约吗?
A: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效果极强的契约,而且对方不是被祛秽过的妖或是无害的灵,自身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契约的话,是有被撕毁契约然后GG的可能的。
Q:清扫者最多能和多少妖怪或灵签订契约?
A:按自身能力而定。企划场内的最高限制以队伍上限为限,最大契约对象为3人。
聖誕快樂
“冬至快樂。”
讓本大人看看這個包裹,本大人是說,天底下不可能有比這個還糟糕的包裹了。
“啊,怎麼了,這個盒子怎麼這麼大……你究竟送了什麼禮物啊?”
本大人聽到一個男聲這麼說著。本大人覺得他肯定會失望,畢竟這包裹實在是很糟糕,這個包裹底下軟綿綿的,上面卻很硬,而且這個盒子黑乎乎的,讓本大人摸起來覺得難受。本大人覺得送給女孩子、男孩子、還有無性的、雙性的所有的禮物都應該是完美而美麗的,如果他是軟的,那就應該全部是軟的,如果他是硬的,他就應該全部是硬的,這樣一半軟一半硬,實在是不像話。
本大人就是這麼覺得的。
“拆開看看吧!”女聲說。
“停一停,首先,今天不是聖誕節嘛?和冬至有什麼關係嗎?”男聲說。
“冬天的節日總是有那麼些相似之處,不,我覺得他們就是一回事兒。”女聲又說道。
本大人聽到本大人的頭頂傳來了一聲撕裂聲,本大人尋著聲音望去,一個紅頭髮的男人看著本大人的臉。
大笑。
“天吶……!這是一隻……”
本大人呆愣愣地看著男人。
“是個機器狗的頭,我從警察那裡卸下來的。”女聲煞有介事地說道,“開齋節——還是什麼快樂!希望你能喜歡它!我想我們可以用他拍點東西不是嗎。”
天吶。真煩。
本大人只好面對那女人和那男人,擺出來難過的笑臉。
生日快樂
“我很感謝你誕生的事實。”
金燕梓吻了水野純,這是他們開始慶祝的第一步,吹蠟燭和切蛋糕的步驟在雪城的夜裡被省略了,他們交纏在一起,隨後金燕梓咬了水野純的舌頭——那是個綿軟的攻擊。水野純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
他們依偎在雪夜的火堆旁。
“你聽到了嗎,火焰爆裂的聲音。他們在跳舞。”金燕梓說道,“這團火會無限地跌落再升騰,隨後一個個小世界在裡面滅亡又誕生,滅亡再誕生,知道火焰熄滅了,事情都會結束的。”
“都會結束的。”水野純疲勞地重複著這句話,“到以後。”
“是的,我現在希望這團火也能祝你生日快樂。”金燕梓俯下身來,向那火堆吹了口氣,隨後她從她的口袋裡拿出那把匕首,并割掉了一綹頭髮。她將那段烏黑的綢緞丟進火中去,火迅速地吞噬了那點祭品,隨後燒得更汪。“我希望你能幸福,我親愛的旅伴,水野純先生。哪怕這個火焰不能祝福你,其他的火也會這樣。”
他們的手疊在一起,這比火焰更灼烈。
“如果我不能呢?”
“那我也不會幸福,我希望你能活得……隨心些。我會愛你,無論如何我都愛你。”她又吻了他,這個吻被賦予了保護的意義。水野純想起奧茲國遊記中的女巫也是如此。
這個吻是有魔法的。
“我很感謝我能遇到你,謝謝隨便什麼玩意讓你在今天誕生。”半晌,金燕梓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