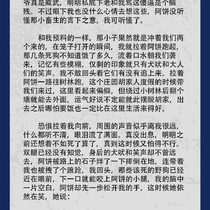作者:格子
评论:笑语/求知
1881年10月31日的清晨,爱丁堡旧城区的石板路被冷雨洗刷得发亮。加布里埃尔·格伦戴尔夹着一摞记录本,从乔治四世桥下的出租公寓一路小跑,穿过雾气缭绕的皇家英里大道,钻进一条名为"断掌巷"的鹅卵石小道。小道尽头是皇家学会的地窖实验室——原本是18世纪走私犯藏匿白兰地的酒窖,如今被改造成电磁学研究中心。门口的黄铜铭牌刻着“麦克唐纳教授·以太与电磁谐振实验室”
加布里埃尔把兜帽往后一撩,掏出钥匙。钥匙齿痕被磨得发亮——教授亲手把它递给她时,只告诉她:"别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真正的实验在午夜后才开始。"
她当时以为那是句夸张的玩笑,直到今晚,她才明白"午夜"并非修辞,而是精确到秒的物理条件。
实验室里的空气混杂着松节油、凡士林与铜绿的味道。天花板低矮,上面煤气管像黑色藤蔓一般蜿蜒。最中央的工作台上摆着那台"以太共振器"——两个直径半米的铜球被紫铜线圈缠绕,线圈之间用从伦敦皇家学会借来的水银开关连接,整套装置被固定在一口苏格兰花岗岩凿成的槽里,槽内注满蒸馏水,用以"冷却以太涡流产生的热"。
加布里埃尔先检查水银开关,再查看鲁姆科夫线圈的绝缘胶木。确认无误后,她在记录本上写下:
"10月31日,14:00,环境温度11℃,湿度87%,装置状态A级。"
刚写完,背后传来咳嗽声。麦克唐纳教授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他身材高瘦,灰发垂到领结,眼睛却像少年般亮。
"格伦戴尔小姐,"他向她展示手里的文件夹,从里面拿出一封信来,"我从大学图书馆借到了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1879年未刊行的信函。他提到'以太密度在季节性民俗节日期间可能出现可测量波动'。我想,再没有比今晚更合适的民俗节日。"
加布里埃尔心头一跳。她早听说过麦克斯韦死前曾私下研究电磁场与民俗学交叉的"边缘课题",但学界普遍认为那是大师晚年被病痛折磨的呓语。
"所以,"教授压低声音,"我们今晚不只要验证以太,还要验证'记忆以太'——一种能储存人类情感与死亡回响的介质。"
教授的话顿了顿,目光穿过煤气灯的光晕,落在加布里埃尔胸前那块不起眼的灰色燧石吊坠上。
"我注意到你常戴着它。这是,高地燧石?"
"是的,先生。小时候我父亲在因弗内斯附近捡给我的。"
"好,"教授若有所思,"燧石含硅量高,压电效应明显,也许能充当'记忆以太'的天线。"
他转身从书架抽出一本发黄的《凯尔特考古学》,翻到折角的一页,指着19世纪学者手绘的"萨温篝火"图继续说道:"凯尔特人相信,10月31日夜,生者与亡者的世界像两张对折的纸,边缘重叠。如果以太真能保存记忆,那么重叠之时,电磁谐振或许能把那些记忆'播放'出来,就像留声机播放蜡筒一样。"加布里埃尔望向那幅插图:黑夜中,火焰像橙红的舌头舔舐天空,人群围绕跳舞,影子被拉得极长,像试图爬出画框。
17:30,实验室天窗已被夜色涂黑。加布里埃尔点燃第二盏煤气灯,开始调试照相底片。她使用的是最新款的明胶干板,感光度足够捕捉瞬间电火花。为了延长曝光,她在镜头前加了两层深红滤光片,希望记录到以太涡流可能发出的"极化幽光"。
19:00,雨停了。城市上空的云层却愈发低沉,像一块被反复折叠的锡箔。加布里埃尔端着茶缸,却一口也喝不下。她想起故乡流传的"幽火"故事:萨温之夜,高地沼泽会浮现蓝白火光,那是亡者举着火把寻找替身。人们称之为"鬼火",科学家则解释为沼气自燃。想到这里,她忽然对今晚的实验生出一种近乎宗教的敬畏——如果科学仪器真能"显影"记忆,那它就不再只是探索外界的锤子和尺子,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人类自己堆积如山的亡魂。
21:00,麦克唐纳教授换上黑色长礼服,郑重地像要去出席葬礼。他递给加布里埃尔一张手写时间表,上面精确到秒地记录了操作的步骤。
"记住,"教授强调,"零点是关键。爱丁堡城内七座教堂的钟声会在同一瞬间产生频率约0.3赫兹的次声波,足以让'记忆以太'发生相长干涉。"
加布里埃尔点头称是,却注意到时间表下方还有一行被涂得潦草的小字,隐约能辨认出"……人形……影……切勿……对话……"的字样。
她抬头想问,却见教授已转身去检查接地铜棒,不知为何,她从对方的背影里读出一种刻意的回避,让她一时失语,将疑问咽回肚子里。
22:30,实验室只剩下了加布里埃尔一个人。教授突然接到皇家学会紧急通知,去处理另一件"与电磁屏蔽有关的突发事件"。临走前,他把实验室钥匙塞进加布里埃尔手里:"格伦戴尔小姐,我相信你能独立完成这次实验。"语调郑重到有些诡异的凝重。
然后他匆匆关门离去,锁舌咔哒一声,像给接下来的夜晚上膛。
加布里埃尔深吸一口气,戴上橡胶手套,把燧石吊坠取下,放在铜球中间的花岗岩槽里。她告诉自己:如果实验成功,她将成为史上第一个在万圣节拍到"以太记忆"的人;如果失败,也不过是浪费几块干板。
22:45,她合上刀闸。线圈发出低沉嗡鸣,像远处风笛的C大调。水银开关内的液态金属颤起波纹,反射出她略有些扭曲的脸。
23:00,电压升到一万伏。铜球之间爆出靛蓝电须,空气被电离出刺鼻的臭味。加布里埃尔把干板插入暗盒,开始计时一小时。
23:05,第一声怪响出现——像有人在实验室深处撕布。她猛地回头,只见一排玻璃烧杯自己在架子上旋转,却没有掉落。
23:10,温度骤降。挂在墙上的酒精温度计从11℃跌到6℃,水银柱缩成一颗银豆。她哈出一口白雾,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
23:15,照相镜头里出现一道灰白雾带,缓缓聚拢成人形。没有五官,头部却随她的移动而转动。加布里埃尔强迫自己看向电压表——指针稳在9800伏,没有波动。也就是说,眼前景象不是电气故障。
她想起教授被划掉的那句警告和临走时信任的嘱托,咬紧牙关继续记录:
"23:15,出现无面人形,高约1.75米,轮廓边缘呈高频抖动,疑似电磁驻波。"
写到最后一字,笔尖突然自己滑动,在纸上拖出一道古怪的曲线,像歪歪扭扭的一个骷髅。
23:30,无面人形开始"说话",这并不严谨,因为它没有发出人声,而是某种鼓点敲击一般的震颤,吵得她心头发紧。
她看向花岗岩槽,燧石的表面竟开始裂出密密麻麻的细纹,里面透出的暗红好像被篝火重新点燃。
23:40,实验室墙壁被灰白雾气笼罩,无数陌生面孔从里面显现,凝聚,若隐若现:戴熊皮帽的苏格兰士兵、穿维多利亚褶裙的女仆、脸颊溃烂的水手……他们同时张嘴,却发出同一种声音——
"SAMHAIN——SAMHAIN——"
那是古盖尔语"萨温"。
加布里埃尔双腿发软,却死死握住记录本。她告诉自己:这是"集体记忆"在以太中回放,他们不是鬼,而是历史留在电磁场里的回声。
00:00,大本钟的声波穿透石墙,与铜球共振。整个实验室像被巨人提起,剧烈颤抖。雾气形成的人形和面孔突然分裂成两条雾带,一条扑向照相干板,另一条卷住加布里埃尔的燧石吊坠。
瞬间,她眼前闪过无数画面:她看见苏格兰士兵在1745年卡洛登战役中被炮弹削去半边脸,腰上挂着燧石样的装饰;她看见女仆在爱丁堡鼠疫期间用燧石模样的刀具把死去的主人牙齿撬掉,卖给牙医做假牙;她看见带着燧石火枪的水手在北海风暴中把同伴尸体绑在桅杆上,只为多撑两天……
所有画面被压缩成一道白光,投进她瞳孔深处,然后又解压成无限延展。她感觉自己的意识与他们在一起,也向着无限涌动延展……
00:05,共振戛然而止。实验室陷入死寂。加布里埃尔跪坐在地,发现燧石已碎成粉末,落在她掌心,像冰冷却仍在发光的灰烬。她踉跄爬起,取下照相暗盒。里面干板表面覆盖着一层奇异结晶,像被极寒瞬间冻结的浪花。
00:30,她把底片浸入显影液。图像一点点浮现:没有铜球,没有线圈,只有她自己——五岁的她站在高地篝火旁,父亲的大手覆在她肩上,手中还拿着那颗燧石。背景的夜空被拉长成一道布满繁星的幽暗走廊,无数模糊人影踏着星辰向她走来,像要借她的童年重返人间,又像要带她的意识一同离去……
早上六点,终于解决了皇家学会那麻烦的突发事件的麦克唐纳教授兴致勃勃赶回实验室,期待看到这一夜的重大突破,却被推门而入的景象震惊到失言。一片狼藉的实验室好像被台风过境,他精心挑选的女助手晕倒在实验室中央,不省人事。
事后经过盘点,并没有任何贵重器材和实验数据丢失,但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格伦戴尔小姐那一晚的记忆。
三个月后,皇家学会发布简短公告:"以太共振实验终止。麦克唐纳教授转而研究高频变压器方向,取得重大进展。"
……
1901年,一位名叫马可尼的年轻工程师在纽芬兰接收跨大西洋无线电信号时,意外记录到一段杂波,解码后竟是一串古盖尔语:
"SAMHAIN——"
同年,爱丁堡皇家学会旧址翻新,工人在地窖墙缝里发现一张泛黄照片:
加布里埃尔·格伦戴尔身着黑色长大衣,站在两台铜球之间,手里握着一块正在裂开的燧石。
照片被封存进学会的档案,自那之后,每当10月31日,档案管理员就会听到走廊传来极轻的脚步声,像有人穿着橡胶底鞋,一路走向地窖——那个早已被封存的以太实验室。
可当他们打开灯,只看见空气中悬浮着细小尘埃,在煤气灯光里缓缓旋转,拼出同一个单词:
"SAMHAIN"

作者:蜂銀
评论:随意
编辑盯着我的稿子,拿食指不断敲着桌面。
我在舒适的接客沙发上坐得笔直,旁边墙上挂着的钟正走着,滴答滴答。
“为什么不写回童话呢。”
“我没法再写童话了。”我尽量诚恳地注视编辑,说,“我只能写这个。”
“科幻呢?黄金时代的那些,宇宙航行?机器人?再新一些的那种…赛博格的那些?”
“我只能写这个。”
滴答滴答。
编辑抓着头发,长叹一口气。
“当真再没办法?”
“我们什么都没剩下。”我看着编辑在上衣口袋里摸索,掏出自己的烟递给他。
我跟编辑走到吸烟室,他用火机把两人的烟点上。
“我也不是不能完全理解…你这样的我见过太多了,你不比他们特殊。”
“是。”
有别的编辑叼着烟走进来,应当是见过几面,我帮他把烟点上。
“谢谢…在聊什么?”那人吐着烟圈,在我俩脸上瞧来瞧去,接着反悔一般讲:“算了。”
我说:“在聊怎么拒稿的事。”
那人瞪大眼睛看过来,“拒了不就完了。”他讲完,上下再扫了一下我的脸,突然和记忆握上手来——“哦,是您…”
编辑的香烟已经燃到过滤嘴前半公分的位置,沉默着。
“怎么拒还是很重要的。”我圆场。
那人应和地点头,把半根烟摁灭在烟灰缸里出去了。
“你再想想吧,这个肯定没法收。”编辑开口讲。
我把烟捏灭,“我只有这个能写了,又不能不写。”
“事到如今又饿不死了。”他半开玩笑地讲。
“是不会饿死。”我说,“但已经死了很多很多人——”
编辑眉毛倒竖:“又关你什么事?”
他吼完,又安静下来,重新点了一根烟。
“我总要写的。”
编辑嗤笑,我只好又强调一遍,“我总要写的。”
他不再讲话了。
“我总要写的。”我重复。
“有鬼在追我。”女人说。
我敲打着从女人胸腔里掏出的心脏——有一个喷洒阀门漏了,机油没法在腔室里爆燃。
女人正在低耗能待机,嘴巴都没动,只有发声器在工作,话语被闷在口中。
“鬼吗?灵魂吗?”我说。
“是我,我在追我。”女人说。
“这种情况得重启了。”我转过头去对等候的客人说。
客人在空中颇为遗憾地顺时针旋转了两圈,处理器闪烁了几下,把密钥传到我的服务器里。我滑着椅子过去把刻好的十六个软盘从软驱里挨个取出来,又挨个塞进连接着女人的读取器里。
女人一下子死去,等她活过来,她的编号会从41变成42。
我接着敲打那个阀门。
一阵音乐传来,女人的脸一下扭曲成可怖的样子,我把供电闸的电压调高一些,那些肌肉慢慢滑回该在的位置,女人笑着用发声器说:“主人好,很高兴能为您服务,我是安德洛公司产深坑探索用机器人二代,编号EL-42。”
我把软盘收回来,倒序放回软驱,回收的Ghost-40会在那里被一张张读取到局域网运行的脚本里扮演爬虫去,毕竟做这行总得赚点外快。
阀门总算敲回正常状态,我满意地瞧着,把心脏塞回去。
咚咚,心脏跳动,女人从椅子上坐起身来,抓住客人塞回胃里——
“为什么是胃?”猫问。
“当然是胃,啊,永动的熔炉,万物的归都将被您化为力。”蜥蜴说。
猫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这爬行类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她问。
“别问我。”我说。
“你不生气吗?我一直都好生气,但不知道为什么。”猫说。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愤怒。”我解释。
“对我是后怕。”蜥蜴说。
“谁—问—你—了—!”猫每说一个字就拿爪子刨一下蜥蜴的头。
我又看了看自己的稿子,写得一团乱麻,我的表达也像鬼魂在那个陈旧的躯体里不断迷路。
“死了好多人。”蜥蜴说。
“每天都在死人,那个编辑说得好,关你什么事?”猫说。
“我怕吃不到大份起司汉堡,怕不能舒舒服服地睡觉,怕没有爱做没有后代——”蜥蜴还没说完,被猫狠狠地照脑袋来了一下:“原来是你,你一直害我生气。”
“我们生气的原因太多。”我帮着解释说,“目前其实主要是因为写不出东西。”
猫瞪着我。
“好吧,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迷路。”我承认。
猫又恢复那股趾高气扬的模样,她优雅地盘着蓬松的尾巴坐下,说:“我们既生气又悲伤。”
我回想我的一切文字,回想它们真正从我的子宫娩出的那些夜晚。
“我正怀抱我的使命和我的孩子迷路。”我说,言语争抢着从我的喉舌中蹦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混乱着,“我们的疫病——那是我们的世界大战、我们的双子塔,我们的大地震——我们却不去记忆它。”
怪兽就在那里,环绕无数的鬼魂,追逐我。
我的二十岁,我不断呕吐的文字与醒觉。
懵懂的温室外,我的脚步深深浅浅,愤怒而哀伤。
作者:【十一招】宅斯特
评论:随意
“抱歉,所以你的意思是,因为主张‘怪谈是不存在的’,所以加入了怪谈社?”吴炆露出一个疑惑的表情,看着眼前申请入社的少女。
“是的。因为怪谈……”翟芊芊歪着头,面无表情地思考了一阵。
思考了一阵。
“……是不存在的。”翟芊芊收回目光,看着吴炆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坐在社团活动室一旁玩手机的女孩忽然笑了出来。
“呃……那,这个‘不存在’该怎么理解呢?啊,欢迎加入怪谈社。”吴炆把报名表收进抽屉。“社费20元,扫桌上那个码就行,谢谢。”
“社费一般是用来作为车旅费,去调查存在怪谈传闻的地点。”坐在一旁的少女收起手机。“我叫白叶,是副社长,你好哦!”白叶笑着对翟芊芊打了个招呼,她有着浓艳的妆容和挑染的紫色刘海,一眼看上去很难让人把这位精神小妹和985、211高校联系在一起。
“嗯,社长好。副社长好。”翟芊芊向二人点头问好,依旧面无表情。
社团活动室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怪谈社和围棋社共用一间活动室,但是围棋社的人几乎不会在活动室露面,他们更多地选择在自习室或者中心花园中进行活动。
“如果把怪谈分为概念和现象的话,那从概念角度来说,怪谈可以从神怪故……”翟芊芊忽然停了下来。“社长要听长的还是短的。”
“叫我吴炆就行。长的会很长吗?”
“会很长。”
“那短的吧。”
“好。”翟芊芊点了点头。“怪谈是不存在的。”
房间静止了8秒左右。
“没了?”
“嗯。”
“哈哈哈哈哈……”白叶在一旁捂着肚子笑成一团。
“呃……”吴炆挠了挠头。“我们倒也没什么坚持或者主张,只是大家讲讲鬼故事出去探访一下出现怪谈的地点,和春游差不多……”
翟芊芊的面无表情让吴炆搞不懂她是在认真听讲还是不置可否。
“社费不退了哟。不过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白叶笑眯眯地看着这位新社员,一副饶有兴趣的表情。
翟芊芊歪着头思考了一下,说:“谢谢。这样就好,我没有退出的念头。”
吴炆笑了笑,说:“这周六有社团活动,我们去博阳路46号那边,最近红小书上在传一个伪人的怪谈……”
“啊,不去也没问题。我们社团很自由的。”白叶随意地摆了摆手。
“我会去的。”翟芊芊微微点了点头。
周六14点。博阳路地铁站。
吴炆和翟芊芊差不多同时到,等了十分钟左右,白叶也到了。
“整理一下情报……”白叶划着手机屏幕,一边往前走一边向两人进行解说,新做的指甲在阳光下色彩斑斓。“这次的怪谈和一般网上的怪谈故事相比,有两个不太一样的特征。其一是发布源并非灵异领域的博主,而是本地city walk博主,在偶然向路人搭话的时候聊起的事件;其二有复数个被随机采访的路人都提到了这件事……啊,买个奶茶吧,芊芊喝什么?我请你。”
“柠檬水,全糖。谢谢。”翟芊芊的面无表情不受时空环境影响地维持着。
“我要青梅绿茶。等下微信转你钱。”吴炆看了看奶茶店里等着取单的人,在门口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要我说,应该是节目效果吧。博主为了话题性所以加进去一点小小的灵异元素之类的……”白叶熟练地扫码下单,然后在门外的吸烟处点了一支烟。
“去逛一圈完了吃个咖喱吧。那附近好像有个还不错的咖喱猪排饭……”吴炆悠然地靠在椅背上,刷着大从点评。
翟芊芊站在一边一言不发,在看上去耐心等待和看上去显得拘谨之间选择了看上去琢磨不透。
博阳路46号是一个写字楼,因为沿街而且地段好,里面充满了私家厨房、美发沙龙、律师事务所、桌游吧、烘焙坊等各类企业和商铺。
三人上了电梯,按下了9楼的按钮。
“传言是说在9层楼梯间,有概率见到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但是跟对方说话也不会有反应,只是会站在那里看着你。但是当你再一转头,对方就不见了,像是凭空消失一般。”白叶吸了口手里的噗噗脏脏芋圆珍珠奶茶。
“像是从那种‘遇见了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的元故事来的……”吴炆掏出手机简单搜索了一下。
“芊芊害不害怕?”白叶看了眼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的翟芊芊。
翟芊芊叼着吸管摇了摇头,说:“不害怕。”
9层的电梯间写着各室的标牌,这里有一家传媒公司,一家健身房,一家观影咖啡厅,一家陶艺工坊,一家外卖寿司店,以及一些没在电梯间挂名牌的房间。
“怎么有四个楼梯间……”吴炆看着楼层结构图。“这应该远超出消防安全标准了吧……”
“应该是风水方面的考虑吧……啊,网上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白叶盯着楼层结构图看着。
“我去问问这里的人。”翟芊芊向正对着楼梯间的观影咖啡厅走去。
“那我去上个卫生间……”吴炆走向远处的一侧。
吴炆在走进卫生间前回头看了看,见二人都没有跟上,于是转头钻进了旁边的楼梯间。他看见一个身穿偶像团体T恤和休闲短裤的男性站在楼梯间看着他。
“哟,你这T恤……你也是AAOO的粉丝啊,这都能遇到同好!”吴炆笑着向那个人搭话。
“对啊对啊,我也是AAOO的粉丝,这也太巧了。”那个人笑着向吴炆点了点头。
“你是从哪场的时候开始追的啊?”吴炆靠在了楼梯扶手上,攀谈了起来。
“我是……哪场的时候开始追的来着……”那个人歪着头开始思考。
“确实,时间久了也容易记不清。你推的是谁呀,还是团推?”吴炆从口袋里摸出一粒润喉糖,放进嘴中。
“我……我没有推,没有人掉下去……”那个人也在摸索着口袋。
“大罗天罡,弗弗阴阳,玄火焚煞……急急如律令!”吴炆念出拗口的咒文,面前的空气中忽然爆出一团火焰。火焰沿着空中不可见的轨迹向吴炆对面的男人迅速爬行,静默却猛烈地点燃了此人的全身,猛烈吞噬着他和他周围的空间事相。
被点燃的人没有叫喊,只是仍摆着摸索口袋的姿势被火焰吞噬着。四秒左右后,火焰和被其包裹着的一切凭空消失,只有空气中的一点余温证明着刚才它们存在过。
“还好来得早,都会学人说话了。”吴炆自言自语着。“我的这个秘密,可不能让别人发现了……”
白叶看着吴炆和翟芊芊走开,转身推开防火门,进了电梯间深处的楼梯间。她看见一个挑染着紫色刘海,挎着蓝色痛包的女性站在楼梯间看着她。
白叶盯着这个人,从挎包里摸出一个化妆镜,打开后确是一个风水罗盘。
亥坤午……酉丙乙癸巽……白叶熟练地拨弄着罗盘上的各层转轮,一个白绿色的虚影像幻灯片一样投影在她的身后墙上。而对面的人也跟白叶学样拨弄着手中的化妆镜,却什么都没发生。
虚影渐渐清晰,那是一只白色的四蹄兽,有着晶莹透绿的毛冠和弯曲成美妙弧形的双角,但是嘴巴上交叉贴了两张写着“封”字的符纸。
“白泽,上。”白叶紧盯着眼前的人,刷了睫毛膏的眼睑一眨不眨。
白泽的投影从墙面上放射而出,冲向对面。投影映射在对面的人身上和后面的墙壁上,形成了两个层次,就好像放电影时有人在大荧幕前走动一般。说时迟那时快,那人身上的投影边界开始消失,平滑地与墙壁上的投影合二为一,再看那个人,已经从原地消失不见。
“回来吧。”白叶点了点头,收起了手中的罗盘,对面墙上白泽的投影也一起失去了痕迹。
“又解决一个怪谈。”白叶吸了口奶茶,看了看紧闭着的楼梯间防火门。“我的事要让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
翟芊芊在店铺门口站着,两人很快赶来回合。
“怎么样,店员说什么没。”吴炆双手插着兜走来。
翟芊芊说:“店员说,他听店长提起过,但是她没亲眼见过。我们应该更多收集信息吗?”
“啊,我刚才去那边的楼梯间看了一下。”白叶指了指电梯间的安全出口。“那个楼梯间什么都没有,而且好脏……”
“嗯。”吴炆挠了挠头。“我就说什么都没有吧。我觉得也不用打听,一起去看看,没事就闪人去吃咖喱了……”吴炆的语气中透露着轻松,像是内心中知道问题已经被解决了,有着根本就不怕被人检查的余裕。
“确实哦,还是去看看最直接。”白叶把喝完了的奶茶丢进垃圾桶,拍了拍手,像是刚刚解决一件难题,有着已经完全没关系了的自在。
“好。”翟芊芊点了点头,像是面无表情是她唯一的表情一般地面无表情。
三人来到电梯间的安全出口楼梯间,打开了门,空无一人。
三人来到了卫生间旁的楼梯间,空无一人。
三人来到了楼层另一侧的楼梯间,防火门闭着。
“肯定没问题。”吴炆说。
“啊?难道会有什么问题吗。”白叶笑了笑。
翟芊芊打开门,空无一人。
三人来到了最后一处楼梯间,它在大楼远端的深处。也许是因为刚好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也许是因为久未打扫,又也许是因为这里有个中央空调的出风口,总之这个楼梯间的入口前散布着一股更为幽森的气息。如果说其他几个楼梯间周围的环境都像是通往温室的花园小路,那面前的这个楼梯间附近的气场就像站在什么魂类游戏BOSS的雾墙前。
“最后一个,赶紧看完走了走了……”吴炆不经意地轻轻皱起了眉头。
“这里怎么有点冷……”白叶下意识地挑起了一边眉毛。
翟芊芊打开门,走了进去。门的弹簧很重,啪的一声迅速弹回关上。
吴炆和白叶几乎同时冲上前去,再一次打开了厚重的防火门——
只有翟芊芊一个人站在那里,依旧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二人。
“怪谈是不存在的。”翟芊芊面无表情地说着。
三人去吃了咖喱猪排饭,坐地铁回家。
白叶在地铁上一边用手机P图,一边和翟芊芊交谈着:“看不出来芊芊还挺外向的,主动会去跟陌生人了解情况。”
翟芊芊歪了歪头,思考了一下,说:“一般的人类,都是会这么做的吧。”
吴炆抓着地铁拉环,看着张芊芊白皙的脸庞,说:“芊芊是因为不害怕,所以会主张怪谈不存在,还是因为认为怪谈不存在,所以不会害怕这些?”
翟芊芊歪着头思考了一阵,说:“不是后者,因为有的东西会因为其‘存在’而害怕,也有的东西会因为其‘不存在’而害怕。也不是前者,因为我害怕不害怕,和怪谈存在不存在,没有必然联系。”她把头回正,看着吴炆说。“总之,怪谈是不存在的。”
“如果怪谈存在的话,会发生什么吗?”白叶抬头看了翟芊芊一眼。
翟芊芊摇了摇头说:“如果怪谈存在,常理的膜就会被感染,会变成存在怪谈的世界。”
“就是说,兹要一点儿怪谈都不存在,都不会有一点儿怪谈存在是吧。”吴炆笑了笑,但心里暗暗对翟芊芊在意了起来,因为她说中了这个世界正在被怪谈入侵的现状。
“可是如果大家都承认的话,就算你一个人自己不承认,也没有用呀……好,发送!”白叶把终于P好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怪谈是不存在的。不管是谁,不管相不相信怪谈,都不应该相信怪谈的存在。我会否定怪谈。”翟芊芊依旧是面无表情,但白叶似乎读出来了一点执拗的味道。
“对了,我问你们个问题……”吴炆露出一个微微难堪的表情。“我的眼睛是很小吗?我觉得还行吧?没有那么小吧……”
翟芊芊回到家时太阳刚刚落山。在她进门正准备开灯时,手机忽然响了。是白叶发来的消息,她说:芊芊,你身边有没有什么遇到那种怪谈的人,或者你自己有遇到过吗?
翟芊芊很快地回了消息:没有。怪谈是不存在的。
回完消息后,她收起手机,打开灯,和房间内另外23个自己一起平躺在地板上,等待第二天的到来。
同人,纸房子,xmm
想了想还是没写成限制级(也不会写((#`O′)
免责:随意
徐敏敏看人的时候总像在笑,就像她对所有人的态度一样,轻飘飘的,说不上是善意或者是温和,但也不带什么贬损。而这一点是赵颖最感到痛苦的,这也许是赵杰在她身上留下的伤疤,她最无法接受的就是这样空洞而不带痕迹的目光,喜欢或是讨厌都没有关系,可为什么这样什么都没有?
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徐敏敏的名字,但她总想起她,这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她每一个丢脸狼狈的现场,不用多说一句话,就让她轻而易举地选择跳进海妖的领域之中。
陈水是个小县城,但也不乏那些出格的铁t来彰显自己和其他人不同的样子,她的宿舍里就有一个,赵颖并不评判他们什么,她本来就不记得人脸,泛泛人潮里何必有那么多能让人记住的东西呢?
但徐敏敏不一样,徐敏敏就像是她幻想出来的东西一样,书里不是说什么青春期小孩的幻想朋友吗?徐敏敏就是了。
“我可不是你幻想出来的。”徐敏敏看了一眼厨房里还掂着条草鱼的赵颖,突然说道,声音被烟雾绕住,让人听不真切。
简直像读心一样,赵颖在心里回答她,她能感受到徐敏敏的视线落在她身上,平静的、不留下任何痕迹,却轻而易举地让她的疤痕开始发烫。赵颖讨厌这种感受,她更讨厌徐敏敏,如果有新的幻想朋友的话,总要第一个丢掉这个家伙。
但她没有回答徐敏敏莫名其妙说的话,只是专心致志地处理那条草鱼,在菜场买的时候鱼贩已经给这条鱼掏了膛,她则把鱼腹里的黑膜撕干净,鱼还算新鲜,黑膜撕的时候也就不会很困难。她手上沾着鱼腔内残余的血,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徐敏敏的手,徐敏敏的手算不上好看,但足够苍白,所以沾上其他的颜色就会很突出,她突然想看徐敏敏手指被折断的血腥景象,又知道这种一瞬闪过的想法算不上可以展示出去的健康产品,徐敏敏做饭又实在是让人难以下手,连个低劣的代餐场景都无法设计出来。她忍不住笑出声来,为自己这莫名其妙的想法。
徐敏敏在抽油烟机底下吐出最后一口烟,其实她之前从来不考虑在哪里抽烟的,但看着赵颖做菜很有意思,赵颖看起来不像是厨艺很好的样子,她发色浅,又老是臭着一张脸,像所有人都欠她一包烟一样,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在厨房里会乖乖地按照流程做菜,甚至口味还相当不错。不过也不算奇怪,就像赵颖这个人一样。
徐敏敏觉得自己算不上很喜欢赵颖,她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她和很多人上过床,男的女的都有,但和未成年上床的机会不算多,赵颖算是自己跳进来的,她也就懒得拒绝。有的时候她会觉得赵颖想把她杀了,尤其是在床上的时候,赵颖下手没轻没重的,偶尔她看着赵颖的眼神落在她前胸,再往上看,停在她的脖子那,然后久久地没挪走。赵颖太有趣了,如果是她的话,早就掐上去了,她这么想过。
不过也可能也不会吧,她靠着厨房的门换了个姿势,悠然地想。都无所谓的事情,到时候自然有自己的答案就是了。
她丢掉已经灭了的烟头,贴到赵颖身上去,头搭在赵颖的肩膀上,兴致勃勃地看着赵颖继续处理这条鱼,赵颖在用刀刮鱼鳞,刮得整条鱼惨不忍睹,鱼鳞一部分拖在刀上,一部分顽固地留在鱼皮上,剩下的四散天涯。她一时兴起地从赵颖腰边划过去,手落在鱼皮上,赵颖没反应过来,刀就蹭到她的手指,划出一道明显的伤口。
这下倒真是有些血腥和残暴了。赵颖愣了一下,拉住徐敏敏就去冲水,破碎的鱼鳞和新鲜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在苍白的手里展现出诡异的生机,徐敏敏还在笑,赵颖倒是有点急,语气不算太好:“你在干嘛?没看到我在用刀啊,就这么凑上来?”
徐敏敏还是一副不当回事的样子:“觉得好玩就试一下了,嘶……你轻点,有点痛。”
“你怕痛?”
“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怕痛吗?”
赵颖有时候真会觉得对徐敏敏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她动作粗鲁地拉着徐敏敏到了客厅,拿出碘伏和棉签,真碰到她的伤口的时候又还是收了力。徐敏敏还是那么淡淡地笑,赵颖听不出来她想说什么,也懒得再思考这空空如也的容器到底想传达些什么,她只是想亲她,于是她说:“我想亲你。”
赵颖闭着眼睛亲她,她已经习惯和徐敏敏的亲吻了,徐敏敏看着赵颖,轻松地回应着她的亲吻,用另一只手牵引着赵颖的手,虚虚地来到自己的脖子上。赵颖绕着她的脖子环绕一圈,像掐住她,也像是抱住她的头颅,更用力地亲了下去。
徐敏敏,你真的是幻想朋友也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