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魔法道具:
- 为了控制学生持有【魔法道具】的总数,经讨论后每个月企划组仅会通过【2个魔法道具】的审核。
- 学生在设定魔法道具时需要意识到并非【就算道具很强】但是【有足够副作用】就会让企划组批准。企划组反而会觉得副作用太大会导致这个【魔法道具】危害性较高且曝光可能性很大——不论哪个就算过了也会被校长请去喝茶然后【没收】,所以在设定上请注意这点。
- *持有魔法道具的情况下如果造成了不良范围影响将也会被校长【没收】该道具。
关于自创魔咒:
- 自创魔咒本身从念法到效果都需要非常严谨的设定。
- 自创魔咒需要向企划组汇报,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地可能会造成范围影响的事件】
- 低年级一般不能自创魔咒。
关于守护神:
- 守护神没有在人设纸上表明的,默认不会。
- 现已停止招收开始就会守护神的人设。
- 六至七年级可以通过上课(魔咒/黑魔法防御术)学会守护神。
关于阿尼玛格斯:
- 现已停止招收阿尼玛格斯(*注册/非注册都已停止)
- 为了企划平衡,目前学生不能通过学习成为阿尼玛格斯。
- 易容玛格斯也是一样的,并不招收。
关于外籍人设:
- 现已停止招收亚洲籍人设。
- 现除了欧洲籍人设外皆有限制。



O抱歉过了这么久才写了这么一点儿可以发的东西。
O被剧情憋成一只咸鱼,不会说话没有逻辑只会啊啊啊和吐泡泡(躺)。
O擅自互动。如有不妥,一定修改。
O概要:这个处处散发着“另请高明”气味的老师,看上去很像一个骗子。
——
曾几何时张觉得学好这些本事,讨得师傅欢心,每天的日子就会像太阳一样东升西落,永远这么过下去。每天都是好时候。从没想过这一身本事到底有何意义,这书上的道理到底有何深意。以他的见解:每日待在山上钻研,好过山下万千红尘。要做到常清常净,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人。
他没有什么济世救人,开天辟地的心志。那些匡扶大义,指点江山的术士高人他也不曾仰慕憧憬。道,与他而言就是有一日算一日,做好每一日于他而言就是活着最好的方式。尽管这看上去优秀得浑浑噩噩。但也平凡到一帆风顺。
这原是张蕴心的道。
在那段单纯无邪的日子里,他在书房里磨墨熨纸,在田野里浇水扑蝶,在广场上扫叶舞剑,在早课上打坐温书。他跟着他的师兄弟一齐在道馆里翻书,附和着师傅的声音一起念搭配: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由于某一位老师有罚人抄书的习惯,他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抄写书目。最上面一本就是《师说》。张蕴心再看到这本书时,心中不免泛起涟漪。
阴错阳差,最为浑浑噩噩的他到如今成了现代人口中的一座灯塔,一根蜡烛,一个灵魂工程师。设身处地,才知道要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哪里有那么容易?传道受业解惑,下笔仅仅六字,真要做到周全妥当受之无愧,非神即仙。
原以为上蜀山是桩闲差,没料想实是苦活。张蕴心自认没有当好一个老师的功力。
“老张,你怎么也看起《师说》了?你们哪个娃娃不听话?也要抄这个?”
扈安走进办公室时,手上还拎着一副烤箱用手套。多年老同事叫老张知道,这位电子设备白痴许是需要人帮他摆弄一下新世纪高科技灶炉——也叫烤箱。张蕴心将插头插上,点亮黑色立方体前面的触控面板:“没有没有,我随便翻翻。对了,你今儿要做什么?”
“布丁。”
“那我预定一个试吃位,这玩意儿要烤几分钟?”
“要先把烤箱预热10分钟的……”
老扈这股不耐烦完全是因为他已经说了不下五遍烤箱要预热的事,但老张每次听完就像第一次听见似的:“还有这种讲究?”
一边的老扈放着自动打蛋器不用,一手抱着打发碗另一只手拿着打蛋器高速运转,整个人都想通电了一样干劲满满势不服输:
“老张你可长点心吧。”
不止同事这么说过,他的学生也这么觉得。这位符宗老师上课迟到已是常态。其中原因说出来丢人,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跟这群娃娃打交道,而是因为他在蜀山呆了几个春秋依然没记住哪个教室在哪里。有时侥幸被他蒙对了地点,他也会因为没带教案在走廊上草丛间翻东翻西,把自己变成一个真园丁。如果有人统计班上谁没带课本的次数最多,结果一定是张蕴心(老师)。
他不是不想做好,他也想脚步生风昂首挺胸手上端茶徐徐盈盈,身后桃李满天下。但是人这个字只有一瞥和一捺,万事总有做不到,要求不能太高。硬要做成一个王,只会从人变成八。他只能做到把要用的试卷放到正门口,好让自己一出门就能记起它。他只能把银行卡密码贴在银行卡背面,好叫自己不会因为试太多次被吞卡。
用他的话说,活了一百多年了,脑子不好使也是很正常的事。
就这样的人,要做老师这样一个精细活,不是强人所难嘛?况且,学生自有老师传道受业,那老师又由谁来解惑呢?曾经的老张以为自己活得明白,不过是因为日子过得简单。现在的老张生得糊涂,是因为他自己个儿也找不到答案。难到生存还是毁灭,简单到有学生陷入困苦时,你帮还是不帮?
老张从没觉得自己选对过。
如果帮,那么——
“你这个老师真他妈烦!”段语在三年级的时候对着老张这样说。
这是个清澈的孩子,上课十分认真,作业也按时完成。如果没有那句发聋振聩的直白话,老张几乎就要确认他是自己上辈子修来的好福分,难得碰上的好学生。
这个孩子最讨人喜欢的一点,是记性好。
就是几天前讲得知识点,他都能倒着背给你听。哪怕是你无心的一句玩笑话,他也能记在心上。老张有一次听见他劝其他同学不要把雷符往手机上贴,原因是“你他妈是傻逼吧?要给手机充电也要在符上写上变压公式啊!直接贴雷符不炸就有鬼了。”除去话语中浅显的道理,内核显露出来:要给手机充电需要在雷符上写上变压公式——这是老张随口胡吹的一句昏话,符上哪里可以写什么变压公式?但这孩子相信了,不但相信了还记在了心里。
老张曾盘算过把这孩子骗进符宗,但最终没有这么做。一是这孩子确实有更适合去的宗门,二是他有身而为人跨越不过的限制——他的手使不上力气。
明明是一位丽人,手上却总缠着绷带。明明抱着十二万分的努力,可画起符来还是有些吃劲。老张注意过这个埋头描贴的孩子,看他一横一竖尚且笔直工整,一点一瞥就已经缺了力道。符小些倒也不打紧,但是符大了,这少点劲道,那却点势头,先辈前人道尊神佛误认他这好小孩心不诚,不顺他的意随他的心。神仙一任性,符没了效用是小事。损了他的自信才是真事。
为此老张专门跑去医宗问了问,问他这手到底是怎么伤才能变成这副模样,也问了有没有什么法子治。结果辛夷没把答案给他。(反倒把好苗子给拐跑了。当然这是后话。)
“他这是筋骨折损之症,只能以草药外敷调养。无药可医。”
老张没了声音。
一来是心疼他小小年纪就经此大劫,二来是心疼他经此大劫却依旧是赤子一个。而他最喜欢这孩子的原因,变成了他最心疼这孩子的原因。换作别人倒还好说,但老张心里清楚,记着以前的事情是什么滋味。那些搅扰心绪的东西天天扎在脑袋里头叫嚣着迟早要完。叫人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要是能忘掉反倒是一件幸事。
在某节课上,因为有同学提问符宗到底能干啥?感觉既不能打也不能扛。
“上天入地段段不行,打架杀人也是够呛。”老张没有生气,倒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随便画了三两笔。第一笔止住了第一排同学不停歇的咳嗽,第二笔修好了教室里那个已经不转的风扇,第三笔画成,只见四个大字:骗钱诓人。
他以为只是开个玩笑,没想到段语这小子真的把老张随手画上黑板的鬼东西拓了下来。那治病的符箓这本不是三年级该学的东西,对他这双手来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东西。
可这傻小子就是犟,下课了还是在画。老张一直没走,最后实在看不下去,把他叫到了教室外的走廊里。
“段同学……有时候,其实你没必要把有些事记牢。”
“我记我的,关你什么事?”
“记住了却什么也改变不了,还不如忘掉。”
“你这个老师真他妈烦!”段语没听进去不说,还恼了。“神特么就算你是老师也别把自己的观点套在我身上啊,你跟我又不是同个人!。”
老张眨巴眼睛,十分想回答:被和自己有三位数年龄差的人训斥自己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自己记着,我自己开心。我至少这样活过!”
“您别瞎操那闲心了行不?”他扭头就进了教室阻止别人把那张符擦掉,继续他的描写工作。留老张一个人回味那句我这样活过。
他的努力和认真都是因为要以更好的姿态活着。他将好记性认作是他引以为豪的特色,他用这天赐的能力拾起岁月中的贝壳。小心珍藏,好好保养。才不管贝壳本身是黑是白,有好有坏。
毕竟,说到底,贝壳就是贝壳。
那一百多来岁,原来都是虚长的。老张思索半晌,只觉得自己白白老了,不如年轻时敞亮通透。可想到头去,还是想不明白。即使能掐会算,到头来还是活成了这副模样。若是不掐不算,倒地是过得更糟还是反倒活出本样。
罢了罢了,只希望段语其人,不忘始终。老张看着孩子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
如果不帮,那么——
自段语那件事后,老张不再多管学生的闲事。直到他犯了一个大错误。
老张是眼看着如圭脚下一滑,整个人落到沟里去的。摔倒后小姑娘甚至没有发出叫喊。
你可能遇上过很多帮你看相的瞎子,似乎瞎了双眼睛就代表他们泄露天机受了天谴,是看卦准度的凭据。但事实上,这些瞎子都不是真瞎,他们骗完你的钱就会睁开他的眼睛。而真要是窥探天机,要赔上的东西绝不止一双眼睛。这件事老张也领教过故而对谁盲谁瞎看得很淡。全校可能就他一个老师记不住相宗的凤如圭是双目全盲。也可能就他一个老师会看到这孩子在路边晃悠时,还神经大条地以为她只是像普通女孩那样在伤春怀秋。
把那孩子拉上来之后,老张看到了她的眼睛才发觉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他放任学生去做危险的事情不说,还不出手帮忙。自己这副模样还算什么老师?而这女娃娃,她正慌忙整理自己的衣衫。她明明把自己打理好了依然还在摸自己的头饰,疑虑它是不是歪了。确认一切规整完毕后,她郑重向老张道谢。
小女孩朝着刚才见死不救的老东西深鞠一躬。但是很明显朝向了反方向。这不怪小姑娘,毕竟是老张羞得想悄悄溜走故意没发出声响。
“谢谢你拉我上来。额……请问你的名字是?”这句把老张嘲地脸都红了。他只好轻手轻脚挪回去,接下小姑娘的谢意,然后装出自己是普通学生,故意捏尖嗓音:“啊?我,我是隔壁符宗的,我一会儿还有课,同学,你自己小心些。”
姑娘连连点头,继续握紧她的盲杖,敲打前行。
“……”老张看着姑娘越走越往左边偏,下一步又要滑到沟里去。还是忍不住开了口:“那个……同学。”
“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如圭看不见世界,但却知道如何对人展现一个笑容。
“我要去西边的教学楼可我不知道怎么走,你能带我去么?”老张面对如圭的善意,一时间满心酸涩,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也不能说出来。
她明明是个需要别人帮助的姑娘,但却乐于给予别人她力所能及的帮助。反观刚才不管闲事的自己,到底哪一个才是老师?
老张的确又忘了自己接下来要去哪一间教室上课,但这是他所有话里唯一是真事的东西。他不会向如圭问路,因为如圭自己也需要帮助。他只是单方面觉得,让这个迷茫的姑娘知道有一个同样迷茫的同伴陪伴着她,能让她觉着好受一些。自己也可以用同伴这个身份帮她一程,而不至于损害到她的自尊。
如果如圭看得见的话,她会发现张骗子说这话时满眼都是对于她的歉疚。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老张合上《师说》,那烤箱正好发出“叮——”的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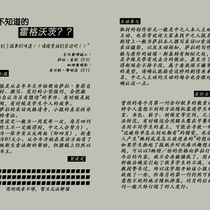




企划挺有趣的,本次又是试验,试试我自己看的那些鬼故事咋写的,文风和我说再见系列……但是很好玩!
强行带百琅出场假装有互动,接下来交给io了!
为了避免被404让我打码一下(?)
————————————————————————————————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
这支军队被鬼缠上了。
李懂醒的时候天还没大亮,但看时间又不是,天一直雾蒙蒙,似乎总也亮不彻底。
周围很湿,他拧了一把衣摆,挤出水来。
冷极了。
湿冷最难熬,骨子都冻得打颤,他撑着洗了把脸,在营地里头张望了一番。前些天人还多些,他们进了村,抢了粮食,杀了老人,抢了女人,征用男人——也有不愿意走的,要么杀了,要么自己在那儿饿死。更多人是被带着走了,一开始也不愿意,谁愿意打家劫舍?过半月都愿意了,因还想活,也因所有人都跟着做。事情做得多了,就去了恶字。
人本该越来越多的,开始是这样。
李懂坐下来,觉得自个快疯了,这支乌合之众凑出来的军队愈来愈安静,几乎嗅不到生气。
人怎么愈来愈少了?
领军的姓赵,六指,现在落草都得有个名号,不然不合适,就叫赵六指——他自然是叫赵将军。
赵将军和他住在同一个城里,涝灾出现前都是常人。
雨下的太久了。
饿时间长了整个人都肿胀起来,他是起先意识到没东西吃的人,逃也逃不掉,水淹了太多地方,哪里不是炼狱?饿的厉害了,人就要吃人,这种事并不少见,都是迫不得已的法子。
但人也不是立刻就生长出来,再不走自己也要被吃了。
赵将军于是带着一帮饿鬼离开了那个几乎死绝的镇子。
要去哪里?不知道。该反了,但又不知道反谁,好像双目可眺之地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境遇,都是死人,都是水,都是乱象。只好边打听边走,边走边杀,好歹李懂混到了赵将军侍卫的位置,少不了一口吃的。同城的不代表关系好,见过彼此食人的勾当,笑着招呼后都是更戒备。
被裹挟后,流民也成了武器,打仗他们先上,没死的一批批淘汰,留下的都是狠辣麻木的兵油子。
李懂的活儿较为轻松,只要守夜和站岗即可,但现在比之前辛苦,因为和他轮班的那个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
但他问周围的人,又没人说奇怪,好像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消失的人们依旧在。
怎么只有他看不着?李懂陷入惶惑,不知是周围人疯了,还是自己疯了。
军队似乎被融化了,融化的死者和生者,死者依旧在窃窃私语。夜里又冷又安静,睡着耳朵里也是水声,密密麻麻的,醒了却又没落雨,只是潮。
李懂回到营帐前,跺了跺脚,哈了口气暖手。
赵将军恐怕也疯了。
他眼见着赵将军一个人在屋里自言自语,像是在对谁说话——可没有一个人。他站在门口侧耳听,意识到对方是在和一个女人说话,带着焦虑和恐惧,以及暴戾狂乱的情绪,有的时候还在那对着空气拳打脚踢,有时候又对着那个不存在的女人跪下哭泣,有时候则是自个弓着腰耸动,自顾自的和没有形体的女人交合射精。
李懂很确定赵将军从未让他带着哪个女人一块儿走。
赵将军走出来,李懂恭敬的朝对方弯了弯腰。
赵将军很高,高而壮,在一个人吃人的年代,这种体格本身就是一种实力。他的脸上有疤,右手六指,左臂则是缺了一块儿——之前战斗时被削了块肉下来,勇武不减,烧了村子后杀了好些人泻火,尸体手脚都砍了堆一块儿。
能吃口饭的时代,这显得很荒谬。
但现在谁又没疯呢?
想要清清白白,就活不下去。
赵将军喉咙里咕隆一阵,朝地上呸了口浓痰:咱们往南走。
他站过去:往南。
赵将军像是和他说话,又像自言自语:南边好,有吃的,有稻米,也有肉,还有女人,以及屋子。我们就往南去。
皇帝也在南边吗?他问。
没,要往北一点儿。赵将军哼了声:哪里没有死人,皇帝那儿也要死人——谁让他在北边?
喔,李懂点点头,那就往南走。
赵将军和他并肩站了一会儿,像是想说点什么,但终究还是沉默了,又走回帐子里去。李懂实则和对方也不熟悉,但比起这支已然陌生的队伍,算是有个老乡的关系……这又有什么意义?他忽而感到又累、又饿、又疲倦,明明才醒来,又累的一根手指也不能动弹,跌跌撞撞找个地方,蜷缩着睡了。
我是不是也被鬼怪缠上了?他迷迷糊糊的想,不然怎么如此没有精力,呼吸都难。
睡了一会儿,或许时间实则很短,他就惊醒过来。
空气中飘来血的味道,极浓,带着腥臭。
他立即警惕的弓下身,往外看,这一看把他吓了一跳:不晓得什么时候,外头打起来了!
但他又看了一会儿,却没有发现敌人是谁。
他们的士兵仓惶的拿着刀砍,似乎砍中什么,但从刀刃接触的地方开始,立即也同虚无连成一片儿。但凡交战,便要被那个看不见的敌军吞没。甚至连惨叫的声响,都被消失所吞噬。
人越打越少。
大战时声音却寂静,莫非是阴兵?
他的心跳的剧烈,腿都软了,但还是想起自己的职责,哆嗦着爬去大帐。
赵将军果然还站着,脸上的肉绷地死紧,像是一块块凸出的岩石,他在城里是出了名的准头好,架着把大弩,对着战场射击。
李懂猛然扑过去:将军,我们走吧!
大势已去,走,尚能东山再起,不走是死路一条。
与人斗算是擅长,谁知道怎么和鬼怪纠缠?
赵将军只是暴怒,却不是没有脑子,衡量一下,也知道得失,放下了弩箭。李懂站在那儿,看他急匆匆的奔去帐中,抱着什么出来——是那个‘女人’?可定睛一看,的确是什么都没有。
李懂冷汗流了一身,现在也不好说,免得被自己将军宰了,岂不是更冤。
他们飞快的离开这个营地,往南边奔去,马也骑了一会儿,得亏人都不见得差不多,不然李懂哪来的福分骑马?到底不熟练,落后一些,更害怕起来:那支军队追上来了,尽管看不见,但他能清晰的感受那阴冷从后方弥漫而来。
行至断崖边,赵将军果断的弃马,而后招呼李懂也躲起来。将匕首往马臀上一插,那马惨叫起来,更飞速的向前奔去。
别出声,赵将军比划道,而后自己也缩了起来。
李懂藏在怪石后头,只能求天求地,不要叫那些鬼怪找着他:他的头又疼起来,浑身乏力,像是忘了许多事,又像是本身就不记得什么。这种发热感笼罩着他,有种大病的前兆。
冷极了。
那种湿冷感轻而寂静的降临,蔓延在这片无人的战场上。
李懂昏昏沉沉,也顾不得什么了。
时间不晓得过去多久,忽然他听到一声杂乱的滚动声,而后是低沉剧烈的低喘,以及咒骂。赵将军从藏身的地方滚了出来,脖子呈一种怪异的角度扭曲着,双脚在地上乱蹬,青筋暴起,手指死死扣住空中看不见的什么。
李懂吓醒几分,瞪大眼看,只见赵将军的脖子那处出现了撕裂,血从那儿不断涌出来。
有个什么东西,正在死死咬住对方的脖子撕扯,尽管赵将军用力抵挡,但那东西似乎有着更强的意志。
你,赵将军发出嗬嗬的粗喘声,话语像是破了的风鼓:我……哈咕……我没杀你……
他一下一下用匕首捅着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像是要拉它陪葬。
去死,去死,去死。
刀刃每下都带红出来:李懂意识到,那东西是个活物。
滚开!滚开!滚开!
这样的响动持续了又一会儿,李懂几乎觉得那群阴兵要被引过来。
但赵将军终究是瘫软下来,不再动弹了。
李懂警惕的握住手中的长刀,慢慢走过去,想要看个究竟。其实不该如此大胆,可不看,他只觉得会死的更快:赵将军算是死有全尸,他应当更进一步,死的明白。
赵将军的尸体僵在那儿,面孔扭曲。
一道风声袭来。
李懂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只是本能的挥刀,接着便手一沉,意识到斩到了什么。他猛然爆发出一股力气,沿着那阻滞斩下去,只听咕咚一声,那东西被他割了下来。
他浑身发软,瘫坐在地上。
那东西咕噜咕噜滚了一圈,他大口喘气,而后才看清那是什么,只一眼,就让他浑身发冷。
那是一个女人。
说人,已经不太准确,因为她的四肢都被斩断,怪不得从不需他带着。现在头也被李懂砍了下来,阴冷的盯着这边,还缺了一只眼,只剩一湾空洞漆黑的眼窝。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至少她死了,李懂安慰自己,不杀,死的就是自己。
他已经明白过来:这女人是在没有四肢的境况下,死死咬着赵将军的喉咙,活生生将他给咬死了。
他忽然头疼的厉害,身体里有什么在凄厉的惨叫。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秋至今未复。」
就在这当儿,他看见从那女尸头颅的眼窝中,有什么东西探了出来。那东西一开始只是很小一截,而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在那小洞里牵扯出来,飘飘荡荡的浮在空中,展开成一袭极洁白的绸缎。接着它其中又生出手脚,露出一张苍白的面孔来。
我舒展了手脚,踩在地上,虽则黏着血肉,但是比之过往还是好上不上。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李懂像是吓得厉害,往后直退,我叹了口气,对他说:这次也失败了呢,看来还是得我出去,你不适合。
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但我也不是说给他听。
我自诞生出已千年有余,但实际在外时间很少,因为比起其他九十九,我过于庞大了。我并非为某事、某人、某物而生出,而是为千万人生出,自然也要承受千万人的拉扯。由于这拉扯还与日俱增,为了避免自身的崩溃,我只好待在意识的深处做个平衡杠杆,维系体内庞然情绪的微妙持平。
说到待人接物,那真是半点经验也没有,毕竟我没人说话,和我说话的也不是人。
在前不久,大概百多年前吧,或许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住,我的部分从这深渊底部逃了出来,来到了意识的表面。因此从面上看,我忽然很像个人了……当然九十九肯定不是人,我这么说也不是对九十九有意见,但由于我的性质,我看它们,一眼看的是根源愿望,比起人形,更早一步看到的是物形,因而很难说真把九十九当人看了。
我对此没什么意见,大体来讲我和他没什么区别,谁上去不一样?
但今天这事实在叫我头疼,以致于我开始考虑要不要杀死他,自己上去呆着了,毕竟我的性质之一便是强烈的求生欲,是不可违背的,而他因为不是完全的我,自我意识薄弱就罢了,竟然连求生欲都不强,再这么下去,岂不是要闹笑话——不过是个白玉葫芦,这也着道,实在是好笑。
不过这葫芦也有个好处,因而我做了个局,轻松便将他困住了。
问答不难,只是他看不见提问的人,尽管已经更换许多附着的人物,他还是看不见。
李懂凄厉的瞪着眼看我,显然是承受不住躯体内庞大灵魂的冲击了。
行了,我说,暂时还是我上去,等你有朝一日看见了,自然也就是我了,那也没差。
李懂的身体里传来一个声音,影影绰绰,像是许多声音叠在一块儿:为何我看不见。
因为你不想看见,我说,你受不了。
你说谎。
我骗自己干嘛?我只觉得脑壳疼,你只是叫人自燃,只是想看光,理所应当是瞧不见落下的灰烬呀。
我知晓丑恶。
是的,我说,但你只用余光看,真正要看的,你又假装看不见了。当然这也是为了自保,因为不完全的我只有白日,若是白日见鬼,那自然很糟糕。
我是听从人们的呼唤而降临。
是的。
我只是给予祝福,但我也走过所有死地。
是的。
可我还是看不见,我仍旧无法见到我的过去向我发问,我找不到。
是的。
那声音叹息道:我究竟缺少什么,我究竟遗失什么,我是谁?
我是谁这问题问得好,属于不能细思的问题,我有时候也思考,但基本无疾而终。他会什么,我自然也会,与我们交谈,便不自觉吐露心声,不自觉被引导,被点燃,冲动同振奋一同到来,几乎分不清是什么致死。但他只是白日的光,他祝福的人我也都知晓:我们出现在人类前的条件十分苛刻,只有了悟死之恐惧,并非一时冲动的拼命,而是敢于奉献崇高牺牲的反抗者,我们才会降临——有趣的是,接下来我们就要将这考虑化为冲动本身了。
但看英雄变作人,又从人变作野兽,却是让他无法接受的:他过于执着的探寻光,当然看不见那女人。
鼓吹行动而从不行动,我叹息道,不行动便是罪,薄弱也是罪,你还是太苍白。
那个漆黑的洞从他身下浮出,这片原野的景象渐渐清晰起来,风一吹,薄雾便散尽。
可这一切是有意义的,那声音伤心道,不要否认它。
或许有,我答,但并不该是我们来判断这意义,为了好的制度而杀尽阻滞,为了美妙的明日而屠戮今日,为了喜悦而生下苦痛,谁又做这个判断?谁都不行。倘若只承认行动有其意义,那被卷入轮下的人呢?不行动亦有其意义。
成千上万的尸骨在四周累积,并不都是战死。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矮贼。生灵歼于此矣。」
听好了!我高声道:我是知晓残酷而带来残酷之人,是哀叹战争而点燃战争之人,是渴求温饱而狂乱之人,是希翼休眠而行动之人,是奔腾的血液,也是寂静的河流,是为漆黑之夜点燃火烛之人——
那洞中数以千计的肢体瞬时就把李懂拉了下去。
——亦是为不被允许有梦者做梦之人。
寂静重新到来。
我站起身来,正打算离开,忽而感觉脚腕被拉住,低头一看,原来是那女人的头颅咬住了我的脚腕。但我双手双脚本身就伤痕累累,倒也不怕再添一个。
我蹲下身看着它,叹气起来:那白玉葫芦居然这当儿还想阻拦我出去,实在是有些好笑,论起幻境,我的能力要比它强上太多。
只不过借它做个陷阱,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那头颅呜呜的咬着,仅剩的一只眼恶狠狠的看我,周围无数阴兵也围绕过来——原本倒不是阴兵,只是变作牺牲品,他就看不见,所以才觉得愈来愈少,现在人都死完了,叫阴兵也无甚不妥。
这女人我也知道,姓卢,是个靠织布维生,不知什么时候被掳来,还有个两岁大的孩子。
这孩子被赵静石一伙儿给烹了。
它的眼窝中流出泪来,因为咬着我,含糊不清,听不出说的是什么。
你恐怕搞错了什么,我对它——对此时悄悄听着的白玉葫芦道:我比那位要更完整,但这并不意味我比他多愁善感,事实正相反,我比他看的更多,也感受更多。我为残酷自圆其说。
随后我把手放在那头颅上,不紧不慢的往里握,感受到皮肤同黏液在手掌下挤压变形的滋味儿。
那头颅的声音听了好一会儿,总算叫我分辨出来,它是在说:我也是人。
来自滚滚车轮下不值一提的尘埃。
啊,我温柔的对她说,我知道。
随即它在我手中不可思议的粉碎坍陷,连同皮肉骨骼一起毁去了。
人要成为英雄太难了,可要成为野兽却十分简单。
我闭上眼,一脚踏出,破开这幻境。
那葫芦恐惧的看了我一眼,逃了,我也不追,毕竟还需要时间适应修整。
远远传来铃铛声,我往那儿瞥一眼,原来是九十九。
对方相貌看着很年轻,但九十九也没有老去这概念,毁了才是死,他看着我,很有些犹豫的模样,像是不晓得要不要搭话,大约是看我模样十分不妙,又是那位的熟人。
最好不要,我想,倘若只是和我对视,快速逃开倒也无视,人类受我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人类的念头是复杂多变的,但九十九这种靠念成形的生物,与我而言太容易被破坏。
而但凡受到提问,我也没法不回答。
这也是我的性质之一,是我的局限性,我毕竟不是人类,有自身的狭窄。
因此我只好盯着这风铃在心里叹气,希求他赶紧走人,最好不要和我讲一句。我是潜藏于人心中的怪物,但凡并非摈弃一切杂念之人,或多或少都要受到我的影响,好在对视不算严重,只要不和我说话,就可当无事发生,因而在我看来,最好赶紧移开视线,别再思考。
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风铃。
我说的是你。
正看着这儿的你,请务必移开视线。
就现在。
END?
赵静石醒的很早。
天不亮他就开始去院子里锻炼,之前爱玩长枪,最近又喜欢上弩箭,没事总窜到林子里去猎兔子,他虽然天生六指,有缺陷,但为人义气,也热心,这条街的街坊都很喜欢这年轻小伙儿。大汗淋漓后他打算去挑水,还想着给在私塾念书的弟弟带点糖人,最近小孩子老是闹着要,若是考试成绩不错,奖给他也不坏。他心里轻松,脚步也轻快,日出时的风还有些冷,但也不碍事。
这座城镇还未苏醒,静悄悄的,没有什么特别,但赵静石爱着这土地。
私塾的夫子怎么和弟弟讲的?他低头想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就叫好日子。
前些年他还买不起糖人,也是凭着一双手勤劳能干攒出来的。
想着想着,忽然顿住步子——前头城墙底下,立着个白色的影子。
赵静石吓一跳,但仔细一看,明明是个人嘛,暗骂自己胆子不行。
你怎么站那儿,风口凉得很啊!他喊道。
那个影子慢慢转过身来,露出一张好相貌,一半面孔隐藏在袍子下头,也挡不住他的好看。这个人看着赵静石,露出悲伤的神情来,叫他也心里难受起来,而他无法理解这是从何而来,又是为了什么。
那个影子轻声道:为什么你……明明……
赵静石迷惑的问:什么?
那影子又不说话了。
他又眨眨眼,发现眼前空无一物,这下是真怀疑自己撞鬼,要去庙里拜拜了。
他又走了几步,忽然感到面孔一凉,接着又是冰凉的触感,砸的生疼。
赵静石仰头一看,城镇的上方已经笼罩上阴云,他只好跑着找地方躲避。
暴雨轰然坠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