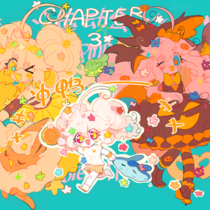“喜形于色”这样的形容是与阿伯拉德完全无缘的,至少在遇见泽万并确认搭档关系之前确实如此,然而现在的阿伯拉德任谁看到都会被认为满面春光,说得再夸张点,甚至可以看到他周身有小花在飘。
白光在宿舍门口与提着大包小包的阿伯拉德走了个迎面,他当然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对方的异样,如果不是非常了解自己的舍友,他都快要怀疑从对方那颗毛茸茸的脑袋上长出了一副狗耳朵。
“阿伯特。”避开是不可能的了,虽然讨厌麻烦的事,但阿伯拉德已经被白光划为“伙伴”的那一栏,即便没心情分享对方开心的事,但好歹招呼是要打的。
阿伯拉德站定,规规矩矩地问好:“下午好,白光。”
“要出去?”目光滑过对方提着的东西,心里想的却是其实你不用告诉我,我也没兴趣。
“是啊,我今晚不回来了。”
白光终于把目光定格在高大舍友的脸上,他停顿了一两秒才重复了一遍:“不回来了。”
点着头,阿伯拉德说:“我要住在我搭档那里,他说我可以留宿。”
一时间白光竟然不知道说什么。阿伯拉德是少有的完全不在意他身高的哨兵,他以人品、能力和言行评判一个人,而不是受困于那些先天因素,同时他也无数次地证明自己不仅真的不会以貌取人,并且是忠厚诚实的朋友,白光对于这位憨厚的舍友兼同期生还是有一定程度好感的。
“注意别睡太晚,明天还有体能测试。”白光想这样也好,即便自己也许真的一个人可以,但哨兵需要向导。
阿伯拉德明显没有第一时间理解白光的话,他偏着头,显得有些疑惑:“11点之前我会睡觉的。”
白光点点头,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况且这也不是他有权利担心的事情。他摆了摆手,准备离去。
“等等,白光,等一等,”阿伯拉德将手里的袋子换了一只手,突然问,“我第一次固定组队,有什么是应该注意的?”
沉默了片刻的白光看着阿伯拉德,恍惚间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他有些迟疑,他不喜欢因为任何事情对自己的过去开展回忆。
“……保护好你认为重要的。”
“我会的。”
“人也好、事也好,物品也罢,只要是你认为是重要的,就一定要保护好。”
白光说罢竟头也不回地走了,阿伯拉德看着空洞洞的宿舍楼,想着下一次有机会请白光吃些好吃的吧,他看上去像是难过得快要死掉了。
“喝茶。”
泽万轻巧地端着茶杯放在阿伯拉德面前的茶几上,此刻阿伯拉德正临危正坐,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他第一次来别人的宿舍,作为青春期的大男孩,他也曾幻想过伴侣的家住起居,但当他真的坐在对方的客厅里的时候,反倒僵硬地像是吞下了条木棍。
“好、好,我喝。”急匆匆地端起茶杯,生怕动作慢一点就被泽万嫌弃,慌慌张张地凑到嘴边后果不其然地被烫了下。阿伯拉德一时间拿着茶杯也不是,放下也不是,只是半张着嘴吸着冷气。
泽万突然想,自己究竟是怎么看上这只蠢熊的?
“东西都带来了?”不得已,泽万开始找话题,指望阿伯拉德看上去是不可能了,他的僵硬令泽万感到可笑的同时竟然也觉得有趣。
阿伯拉德忙不迭地点头:“带了、都带了。睡衣、枕头、牙刷、牙膏……”
“停——”泽万比了个手势,心满意足地看到阿伯拉德立刻禁声,他站起身走到对方面前,然后坐在阿伯拉德的身侧。这个傻大个儿立刻就为了腾出位置向旁边挪,但很快后悔了就又悄咪咪地移了回来。
泽万开始翻看阿伯拉德的包裹,发现对方虽然带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但好在没有太过超出自己的想象。能为这么空旷的房子增添些人气也是好的,想到这里泽万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就默认对方会一直住在这里。
“睡的地方为你准备好了,但你要是打鼾就睡客厅吧。”
眨了眨眼,阿伯拉德茫然地点着头。泽万叹了口气,他知道对方肯定没有听懂。
“我希望你不会认床,晚上失眠的话我可不陪你。”
“不会的!”阿伯拉德高兴起来,“睡哪里都是睡,只要和你在一起!”
好吧,这个傻子终于开窍了,泽万随便靠在阿伯拉德的肩膀上,感到对方确实是犹豫了下后,终于有勇气揽住了自己,他也就放松地完全靠在对方怀里。说实话,阿伯拉德的怀抱虽然有些硬,但却是足够温暖和宽敞的。
“在我的老家,有这么一个传统,”将手指卷在泽万的长发上,阿伯拉德忍不住低头吻在他的发间,“结了婚的……人都会把头发编起来。”
临时改口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阿伯拉德讪讪地看着泽万,对方并没有多余的表示。但泽万怎么可能没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他的小心思,原本这只笨狗熊想说的是“女人”吧。
“别想了,我可不会把头发盘起来,你要是愿意留长,我倒是很乐意看到你挽成发髻。”
“不盘不挽!”阿伯拉德有些着急,体现在行动上就是将泽万紧紧搂在怀里,“就是编一缕辫子……”
“免谈,我可没那闲工夫大清早起来编头发。”
“那我来!我可以早起一点,给你做好饭后叫你起床,然后你吃饭的时候我帮你编。”
这次换泽万沉默了,饶是他也没想到阿伯拉德会做到这个程度。就在这个空档阿伯拉德已经用另一只手环抱住了他,见他没有排斥就开始真的尝试编辫子。
“在我的民族里,即便是最勇敢的人也绝对不会碰编着辫子、有家室的人,否则的话——”
“否则?”泽万抬起头,恰巧看到阿伯拉德向下望着他,他看到对方眼睛里亮闪闪的,就知道不好了。
“——他会永劫不复。”
阿伯拉德低下头,吻在泽万的唇上,他很快就松开了他,同时放开了搂在他胸前的手。泽万低头,看到自己的一缕左侧头发被胡乱地扎了一个小辫子。
“那你可要起来得再早点,这种乱七八糟的发型我是不会接受的。”
FIN.
=============================================
时间轴在zz和熊第一次肉体与精神结合后,两个人悄悄开始的同居生活,也说明了下zz发型的原因www
感谢好舍友白光友情出镜,你真温柔又不会多问,虽然熊这个人没什么羞耻心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啦(你倒是要点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