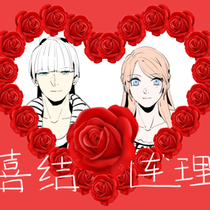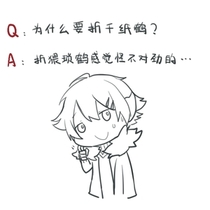




总是会看到七濑在微笑
可其实是个挺容易生气的人
但就算在生气的时候也会保持微笑
虽然会拼命忍着不表露出怒气
可还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挺会照顾人的类型
因为受朋友委托照顾朋友亲戚家的孩子
吐槽只会在心里进行
虽然看上去挺正经
但也仅限于看上去而已(。
看到猫的时候会整个人都被治愈了一样ヽ(●´∀`●)ノ(///´艸`///)
看到狗的时候大概会是这样→ (here is a dog)Σヽ(°Д °; )ノ?!!
这样→(here is a dog)(゚Д゚≡゚Д゚)
或者这样→(here is a dog)ε=ε=ε=┏(゜Д゜;)┛
其实有时候是个挺蠢的人(。
【【有时间的话再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