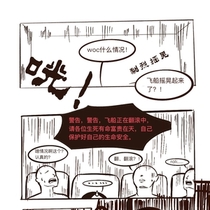


作者:乘零
评论:随意
从我听说尸体复生者——赫伯特·韦斯特的名号时爱丽丝已经下葬了半个月。
我的爱人,捧在心上的小女孩爱丽丝,她躺在漆黑的棺椁中,唇是鲜红如花园中的蔷薇,苍白的面容比之她穿着的白裙更加柔软。她安静地笑,她在梦中呼唤我名,她在面前转着圈,让裙摆划过我的手背,邀我入舞池。
“哥哥,爱丽丝今天好看吗?”她卷着颊边的金发,俯下身问我。问题的答案是无须言明的,我再次牵过她的手,包裹着蕾丝手套、只有我半掌大的小手,虔诚地落下一吻,一如最后一吻那般。
爱丽丝。我在梦中呼唤她名。
父亲早年间挣扎在家族遗传的头疾,痛苦不堪的他决定将家族交托到我手中,并将自己的生命终结于睡梦中。我在床幔遮挡出的影影绰绰里双手紧握住他的,许诺绝不辱没家族,发誓定会照顾好他的小女儿。
姑母三日前启程离开了这里,希望依靠城市的喧嚣洗涮掉心沉积在中的伤痛,临行前她神色凄怆,与爱丽丝同样的金发枯燥而凌乱地盘在珍珠发夹里,劝我莫要被死亡困囿。
那些深绿色、黑棕色的苔藓爬在灰岩砖壁上,根系侵入到了千万年形成的石块里。如今的庄园依旧浸在经久的粘稠雨雾中,仅是少了一位少女的欢声笑语,周身便都笼罩在阴郁里,与我同悲。
当我在一家疗养院找到那位一直跟随韦斯特的助手时,此人已然癫狂,我只得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
韦斯特早就死去,他消失了!复活的埃里克少校将韦斯特撕成了碎片!那个无头人带走了他!
那位特殊的医生神秘失踪时,现场只有他与助手,作为第一嫌疑人,警探们曾将人仔细盘问过。我难道是为了追寻真相吗,不如说正是这些怪诞不经的传闻将我吸引而来。
“……不要妄图窥探死亡……不要惊扰亡灵……他们来了、他们悄无声息、他们就该永远扭曲地眠于墓穴!永远!”
那人形容枯槁,无法言说的恐惧如附骨之疽,把他折磨成了一个精神病。他喃喃说着疯言疯语,突然抓着自己的头发抬头,眼窝中凹陷的瞳仁闪烁着绝望的惊惶,那爆发的大叫将我吓了一跳。
得到消息我便立即来到了这里,连着两日未眠让我看起来不比这个疯子好多少。他的身躯瘦削,肩骨就像那早该畸形死去的的树枝,我咬着牙关,面目都因这狰狞起来,钳制着他逼问那禁忌的死者复生的法术。
“我不在乎!塔纳托斯休想从我身边夺走她!我只要她回来,告诉我!”
最后我在疯子手中拿到了医生多年的手稿和残存的药剂,得知复活死者的“成功”案例皆为刚死去不久的人。
我明白不该就此绝望下去,但还是在爱丽丝墓前痛哭了一场。我那可怜的小女孩提着裙子,蹲下身来抹去我眼角汹涌而出的泪水,她托着腮,多么天真,多么可爱!
她说:“不要哭呀,爱丽丝会一直都乖乖的。”
我是那样地希望能拥她入怀,却只能哽咽着承诺:“等我、等我带你回家……”或者共你畅游冥府,我去触碰她放在我脸上的手,笑着调侃:“我不在身边,爱丽丝不要在冥王家里迷路了……”
“哥哥真坏!”她皱皱鼻子,轻轻地“哼”出一声,甩开我跑开了,徒留我一人在原地。
爱丽丝的金发微微卷曲,被红色的丝带束在脑后,她越跑越远,像在阳光下融化似得模糊了面容。我只接到她遗落的发带,刺目的鲜红死去般垂在手心,宝石点缀其上,像凝落的泪。
直到她回头呼唤我,抱怨:“你怎么不过来追上我呀?”我拼命眨着眼睛,方才用视线捕捉到她娇嗔的模样。
当初医生为了合适的实验素材,日日向教堂打听近期死去的居民,如同秃鹫般守候在新增的坟冢前,鬼魅般行踪。
我的家世足以令我不惊动任何人即可得到合适的、新鲜的尸体便于利用,纵然此举过后家族的名声受损,人们将这座庄园视作蛇蝎,谈及都是嫌恶。
我只是在犹豫,我的目的并不是替医生完成那一项伟大的壮举。我仅是、仅想要,唤回我的爱丽丝。
爱丽丝,何时你口中才会呼唤出我的名姓?
如何能容忍她的一生就此停止在石碑上的破折线后,那样短暂地、如同惊飞的白鸟那般从我的生命里掠过,令我再无法深切地凝视着此生挚爱。
那颗在阳光下闪耀着辉光的宝石吸引到了冥府使者,鸦羽泛着金属的靛色,锋利得如同淬火过后的死神之刃,叼走了爱丽丝留给我的发带,连同我的怒火一齐点燃。
它嗤笑着,用它嘶哑丑恶的嗓音嘲弄我的痴心妄想,眼珠如黑曜石般把来自死亡的问候带到。这只面容英俊而行为绝对肮脏的鸟类!啄食着我的心脏,欲要将我毁灭。
我挥舞手杖,打在虬枝盘曲的枯树干上,多想当场将它宰杀。
似乎感受到我的意念,它歪着脑袋,与我的无力一并讥讽过。而后向昏沉的天际飞往,扑闪着羽翼落在教堂塔尖上的十字,留下层云遮蔽的阴影。
药剂的颜色是深浅不一的绿,纯粹得令人迷醉,恍惚能将之窥成生命树上流淌着的汁液。
镇上医院给我送来了一个意外死去的人,血液已经僵冷,想来是魂灵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再次睁开眼睛。我小心翼翼地将生命注进了这具青灰的躯体,期待他醒来后诉说出关于亡间的故事,若是能得到爱丽丝的音信就更好了。
这间简陋的实验室位于庄园角落,地下阴冷,潮湿的灰尘似乎附着上了鼻腔。我难耐地走了两步,听见自己紧张的呼吸,每一口皆带着陈腐的气息,来自冥府开合的大门。
空气中的缄默直至我悲哀地贴在尸体毫无起伏的胸前,试图找到任何他即将苏醒过来的迹象,“没用、没用……”
之后我又进行了几次实验,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在这期间了还发生了一件事,那个掘人坟墓的罪人葬身在疗养院突发的无名大火,死前将他的哀嚎直直传到我的梦中。他浑身焚满了地狱的业火,伸着焦黑扭曲的肢体向我招手,身后隐约有着一个奇怪的高大人影——没有脑袋。
即使早有先例,死而复生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很快说服了自己,庆幸没有轻率地进入爱丽丝的睡梦中打扰。
她可是个娇气的小女孩,经常是要哄着才肯起床,睡眼朦胧地把脚蹬到我心口,闹着再睡一会儿。冬日里若是晴朗,我和她在蔷薇园午憩,爱丽丝蜷缩在我的怀抱里,像一只猫。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她的嗜睡代表着什么,这些记忆里日常的小事却成了如今我为数不多的幸福。我想我该痛恨死亡的无情。
可怜的爱丽丝曾蹲在这棵树下安葬她的小宠物,我还能想起抚过她面孔的触感,温软而稚嫩,乖巧地仰着脸,上面的血迹像沾着的蔷薇花汁被我擦出一道道红痕。
现在她也跟在身旁陪我埋下那只乌鸦,填好土壤后只略微拱起了些,它和周围的几具尸体为伴,根本看不出是一座小小的坟丘。
它羽毛零乱,尖利的喙歪斜,眼睛里再藏不下恶意。
它曾经丑陋又恶毒,但在我扭断了它的脖子再注入药剂之后,它无力地动作证实了我的所作所为是有用的。尽管后面它的生命归于沉寂,我很确信那不是臆想,这给我带来了希望。
爱丽丝怜惜地摸着它的爪子,我似乎看见它奋力挣动了一下想要和小女孩握手。让我皱眉,不赞同地搂过她,“……脏,不要碰。”
在墓地我挖出了许是第十具尸体,就躺在面前,我攥紧来自梦中的红丝带,不知该向谁祈祷,将它放至心口才戴上了手套。
结局是失败。这具实验体与爱丽丝年龄相仿,死于一周前,丧礼时他父母的哀伤我仍依稀感到,为何他就不肯醒来。
时间拖得越久希望越小,恐怕再难跟上小女孩贪玩的脚步了,我失魂落魄地蹲下身。但是突然出现的那可怖的嘶吼声如同天籁,正从尸体的口中发出!
我欣喜若狂地去看他浑浊的眼睛,在他耳边喊他的名字,试图唤回他的神智。这或许是有成效的,因为他已经将目光移到了我身上,牙齿张合着,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嚎叫,似要传达些什么。
我用一颗子弹结束了接下去的疯狂,又在焚化炉里将他化作灰烬。这是疗养院里助手再三告诫的——千万别再让那些“生命”遗留在世。
先前我没有在意,直至再次埋下的土壤松动,仆人声称目睹怪物并为之所伤,才知我险些酿出祸患。何况我是多么为他的复生而高兴,但是他只想吃我的肉!
这没有打击到我,我亲吻着红丝带,告诉爱丽丝这个好消息。
“那又怎么样。”她还在为上次的事而生气,看到我时叉着腰,夺过自己的发带束起金发。
我低低地笑,拥住她,念诵她的名字,似乎就能把快乐传达。
第十具不行没关系,第十一、第十二……终有一天会接回我的小女孩。
地下室偶尔传出的恐怖叫声惊动了庄园里的另一个主人,姑母匆匆赶回来,斥责我的疯狂之举。她流着泪,说认识了几位美丽的小姐足以当我的夫人,说只想爱丽丝在主的环抱下安眠,让我不要执迷下去。
却不知道世界上唯有纯然无辜的爱丽丝是我此生的妻子,唯我能拥她入怀。
我时常造访教堂的目的改换,石碑上刻着的墓铭志述说着底下人未尽的余生,他们或许有过多么大的成就,或许多么的良善,籍籍无名地于此地安眠。可惜与我而言,不过任人采撷的荒冢。纵使沐浴在主的光辉下,终究无人来祭。
请原谅我的无礼,与不敢望您名号的怯弱,只我心中永恒响彻着挚爱的姓名,再无其他。
弦月在天穹勾勒出一弯冷色,小女孩在庄园里摘蔷薇,浅淡的金发落在她颈脖,去感觉那细弱的脉搏,她笑靥如花,将点点猩红的花瓣往我身上扔,呼唤我名。
我直起身,垂下放至心口的手,背过身示意手下动作。
一铲铲的土壤被挖掘,正一点点地掏空这座坟墓,“沙沙沙——”,是枯枝被吹着摇曳,是虫蛀着木屑的贪食声,是亡者最为狠厉的诅咒,狂乱的冷风中咒骂着我这个肮脏的食尸鬼。
而我不在乎那无名的坟冢,只心里喃喃着吾爱——爱丽丝。
*背景取自洛夫克拉夫特《赫伯特·韦斯特——尸体复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