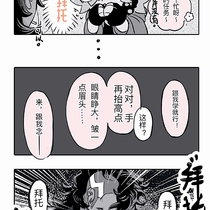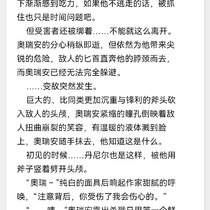





Summary:大家载歌载舞,最终走向墓地,公墓里也是灯烛通明,逝者的相片在墓前熠熠。这是魂灵也将为此欢笑的夜晚。
阅览注意:全文2k+。故事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支持!
贝蒂并不经常回家。她的学业繁忙,论文和考试总在等着她,当然那些随之而来的机会也是,她如今站在繁华城市中最优秀的学府,张开每一根手指想要抓住所有的橄榄枝。二十来岁正是人生的坦途都向你打开的时节,日程表上的每个格子都恨不得填满铺路的砖石,以至于她忽然发现这些砖石一时没跟上她的步子、竟给她空出了整整一周假期时,才惊觉时间过得是那样快,已有近两年没有回去过。
分别时她叫悬铃木记得回家过亡灵节,去年真到了节日将近,她却终究还是没订下机票。好像爽约的人变成她了似的。这段时间她逼迫自己不去摄取有关瓦尔基里的任何消息,新闻也好传言也罢,后来再忙起来也没有心思关心这些了,偶尔就像这个种族从未在地球上存在过一样。去年有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似乎是出了什么大事,她的同学们都挤在屏幕前观看新闻直播时,她走上去扣上了那台笔记本电脑。有时一些莫名其妙的芥蒂就是会长在你心里,让你不愿回头,即使没有人做错什么。
作为瓦尔基里一定很忙,她说不定也没有空回家;寻找自我是一件很难的事,她说不定也还没有找到;穷乡僻壤的地方没什么意思,不想回去也是人之常情。贝蒂如是想。
但她站在月历上那一整行空白前良久,终于还是长长地叹出一口气。
干燥、窄小,这是每一个人客观描述此地时都会使用的词;对如今已成年的贝蒂来说,它已经小得花不上几步就能走完。她挨个敲响每一户的门带去问候和礼物,熟悉的邻居们有的已苍老得不便出门,曾经的同龄玩伴不少定居他乡。老狗布鲁托趴在中心广场的喷泉下眯着眼,只在她伸手时才慢悠悠把脑袋搭上去,松弛的颈项皮软软热热地堆在手心。建筑和街道翻新过,但傍晚亡灵节的彩灯亮起时,她感到这里依旧无比熟悉。
贝蒂并不是抗拒参加派对的内向派,不过来到广场的人群中时,她还是久违地听到自己心脏正砰砰跃动的声音。她穿着的是希拉年轻时的红舞裙,配以传统样式的鲜艳花纹,即使她不怎么会跳舞,稍微转转身子也足以变成一朵张扬醒目的花。被她踩了好几脚的舞伴并不在意,依然伸手邀请她再跳一曲;贝蒂笑着冲他摇摇头,拎起裙摆退步行礼,告诉他自己已有约。
有谁的约呢?她真的会来吗?如此一走神,手上的工具一不小心也歪了,贝蒂的目光重新落回她正制作的墨西哥剪纸上,她从小就喜欢这项需要一点点凿出来的精细艺术,敲出一个个规整的格子令她感到平静。现在,纸上骷髅头的脸歪了,看起来像在滑稽地歪着嘴笑。贝蒂也被它逗乐,笑了一声又觉得没什么好笑的,于是抿了抿嘴。有时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会长在你心里。
她跟在游行的队伍里,手里捧着一小时前雕出来的镂空南瓜灯,脸上化着半小时前画好的骷髅脸妆。削弱五官的线条后大家都长得很像。这是令所有人都十分愉快的夜晚,你能听到哪一家的电视里在放什么节目,奔跑的小孩擦着你的裙边挤过去,我们拍手笑,一些油彩被蹭在衣裙上,一些花被素不相识的人为你别在头顶。大家载歌载舞,最终走向墓地,公墓里也是灯烛通明,逝者的相片在墓前熠熠。这是魂灵也将为此欢笑的夜晚,因为你知道你们彼此爱着,在那看不见的地方,有无数的灵魂踩着烛火、糖果、万寿菊花瓣,走过去、走回家。
大南瓜留在希拉的墓前,里面填满她沿途收到的花与糖。人群散去后,贝蒂才独自走回家,街上安静了,她的脸尚且还发热,因为聚会欢闹而略感头晕。铺满花瓣的大路上分出一条细小的小路,大概是从南瓜镂空的口里漏出来的,通向她们偏僻的小房子。贝蒂有些恍惚,踩着片片橘色花瓣往回走,离开镇上一窗窗的暖黄灯光,当她真正站在漆黑的夜里时,她看见家里的灯竟也亮着,门前的树下有一个影子。
她设想过很多次重逢会是什么样的:也许会很平淡,也许会很尴尬,她可能不想和悬铃木说话,甚至在看见她的那一刻就转身离开假装从没回来。但在以上情景的任何一个成真之前,眼泪先她的思考一步涌了出来。
她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先抬手把泪珠擦掉,它们越擦越多,最后简直变成揉搓着整个脸颊。妆一定抹花了,油彩一定满面都是。她感到被瓦尔基里身上散发出的融融微光笼住,在拥抱与不拥抱之间犹豫的手握在她肩上,熟悉的未曾变化的低沉而平缓的声音在她头上响起:“贝蒂,贝蒂。不要难过……你为什么哭?”
她也不知道。她报复般地抓过瓦尔基里的双手,将满面油彩蹭在干净的掌心上。她听见自己在说话:“手怎么还是那么粗!长那么糙干嘛!”又说:“你怎么变了那么多?怎么这样,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话不经思考地从嘴边流出:“早知道我就真的不看新闻了,也不看那些资料,早知道我就真的不回来了……”最后她实在哽咽得无法说出任何话,于是蹲下来,瓦尔基里也随她一同半跪,用肩膀支撑着她的额头。
“我们约好了每年亡灵节回来……我记得,我用笔记下来了。”悬铃木用要一句句回答过去的语气叙述,“超越改变了很多,但我不会忘记你们。贝蒂,贝蒂……我不知道你今年会来……关于手的事,我会试着用护手霜……”
贝蒂又笑出来,一拳锤在她另一边肩上,声音闷闷地让她别说了。她们安静地互相拥抱着,瓦尔基里小心展开羽翼,让它成为第二层温暖的包裹。有那么一刻贝蒂觉得这羽翼上会腾起火,一把烧尽她们二人让她们融成一颗玻璃球叮当落地,但这只是一瞬的幻想,她们只是这样温暖地互相拥抱着。
“我好像又明白人为什么会在这时候笑或流泪了,”悬铃木的胸腔随着说话嗡嗡着,“但又有点不明白,我有些忘了。你还愿意教给我吗?贝蒂。”
贝蒂并不经常回家,她的学业繁忙,与瓦尔基里相关的法条总是争论不定,研究资料又更新一轮,案例和论文总在等着她阅读,即使她已经读过非常多。
但我不会告诉你这些的,贝蒂想。她以把更多面妆油彩蹭在瓦尔基里胸前作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