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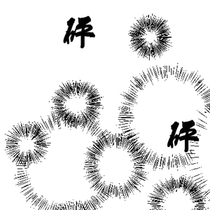





西玛不知道自己为何还要来Ponder,在一个昏黄的午后,夕阳携着自己所不熟悉的寒意。他站在旗塔前,看着远处的云彩后隐着一个圆润的光球,像是一个烧红的铁球落入海水中,溅起的水花四散在云朵上,它们于是被融化,中间裂出几条缝隙来,金光万丈,如同雷暴雨时划破天空的闪电。突然他的脑子里也像是由这光劈出了几道奇思妙想——他想去那栋并不与他完全相容的图书馆,并且他想起不久之前,他匆匆地从医疗部奔下楼,去和他的朋友赴约。观星社的魔法师,总是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前来。他的脑中浮现出对方的剪影来,映在窗口,也深深刻在他的回忆里。
西玛并不指望着能见到艾希礼。最后一丝记忆阀门打开,他推翻了桌子,落荒而逃,却有着强行续约之嫌。他们的交易,本到破开里政府职员身上的遗忘咒为止。
可那些东西又算什么呢?西玛愣了很久,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的生命本就轻飘飘的,对待艾希礼也毫无积蓄可言。他把自己了解到的美好小心翼翼地给艾希礼看,又担心误导这个比他还要年轻的少年。他看到一幅买不起的精美油画,心里艳羡的同时,甚至不敢碰一碰它精雕细琢的相框。——不该,艾希礼会来吗?在这样危急的关头。
他愣了很久,回过神来人却已经在图书馆门口。他的右手手指扣在左手腕上,被什么硬物硌到。那是一枚闪闪发亮的蓝宝石袖扣,温凉的触觉让西玛很喜欢它——而且它很衬艾希礼的眼睛。他摘下这枚随身了许多年的袖扣,塞进了白大褂的口袋,手指碰到两颗巧克力糖,他嘴角咧开一个无奈的苦笑。
可艾希礼在那里。站在那面花窗下。天气冷了,他又一次穿上了那件外套,是西玛最为熟识的模样。第一次相见,艾希礼也是这样的装束,湛蓝的眼睛,翘起的白发有几分不羁,眼中实实在在地沉着观星社给人们带来的固有印象式的敌意,由于西洋剑锃亮的光更有些晃眼。
西玛无话可说。这一段路程实在太远,他的脚下忍不住地快了几步,在跑起来之前又惊觉自己的失态,勉强压住了速度。
艾希礼朝他点了点头。
定了定神,西玛朝他走去。一瞬间的狂喜在方才的压抑中分崩离析,它们的碎片和着沉淀在心底的忧虑一起翻腾上来。他的袍角掠过风,他不得不用手压住它们,以至于张开手心时他感到一阵凉意——他不知何时已满手是汗,悲戚在这样仓促的见面下不可避免,更何况他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所谓失控。
西玛知道自己有多平庸。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宣言,什么波澜壮阔的抉择。他的悲剧很简单,即使是出场也只有八拍的单调配乐,循环往复地响着。他能感受到自己在痛苦中沉沦,被亲朋好友的死去击溃。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却不信命,或许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身上微不足道的光。其余的时刻,他们往往在市井中腐烂。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以卵击石,只有黑暗中孳生的毒药,让他无言地死去。
他的叔母说得对,他的确不是什么高贵的人,他没有魔法师的血统,一切都太遥不可及、痴人说梦。可或许,他能暂且抓住一些什么,就在现在,他的身边,尽管他是一朵枝头落下的凋零的花,在行人的头发上暂且停留。
“……艾希礼。”
他的脸上堆出有些勉强的笑意。欢欣是真实的,笑容却是虚假的。他自己能感受到他的肌肉僵硬,嘴角勾得诡异。压抑的快乐和思念,离邪恶和黑暗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对于他所信赖的人,都无法表达。
于是他很快地接上一句:
“对不起。(Pardon me.)”
西玛不清楚自己在道什么歉。或许是他两周前公共场合掀了桌子(那看起来就像是正在约会的小情侣闹脾气),留艾希礼一个收拾烂摊子却没有半句解释,或许是他无法对对方展现真实,因为真实带来的后果他俩都无法承受,或许是……他一直以来的亏欠。
西玛知道自己预想中的该是如何。因为有一瞬,仅仅是那一瞬间,他看着艾希礼穿着那件厚重的大衣,远远地等待着他,他有了一种可怕的冲动——跑过去,抱住他……亲吻他。
恶疾早已在他心中种下,不知不觉中病入膏肓。那是恐怖的鸩毒,掺着甜美的酒,西玛无法拒绝。于是他站在艾希礼面前,道歉,眼底是木质的地板,撒着最后一点黄昏的光。斜切的阳光束中有小小的尘埃,似动非动地游走着,仿佛闪烁着星光的池塘中,漂浮着细小的蜉蝣,可已经现出了颓败的颜色。夜晚马上就要来了。
半晌,温热的纸杯贴在他冰冷的脸颊上。那是多么温暖合适的一种安慰,西玛被它激得抬起了头。
“西玛,”魔法师低语,眼神中是让人心安的平和,“如果你愿意说,我可以暂时当一个中立的听众。”
他怎么还能这么平静呢?西玛有些惊讶,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艾希礼背后的夜色已经悄然袭来,发暗的玻璃上,反射着西玛的表情。那个青年很疲惫,肉眼可见的忧虑,可却习惯性地微微勾着很薄的唇角,露出的是有些恍惚的、难以形容的……。
那是他的母亲看着他的目光。那个即使是疯了的女子,面对他时记忆错乱,神经恍惚,却还难以抹杀的温柔。现在,这个要命的神情,正出现在他的脸上,湿润的棕色眼眸,如同幼兽的天真和脆弱,又带了几分本能的安慰和慈爱。
西玛明白了。一种悲凉从脚底涌来,他禁不住瑟缩了一下。魔法师紧张地把手伸到他身侧,建议他坐下。西玛跌跌撞撞到靠到椅子里,把脸埋进臂肘。他感受不到泪水的湿润——它们早就在父亲死去和西尔莎身亡时流完,就像是啼血的夜莺已经成为一具尸壳。他只感到一种有些疯狂的冲动,像是荆棘一样从他心底窜上来。他想笑。太荒谬了,这太荒谬了。
他怎么可以……他怎么可以……?
“艾希礼。”他颤抖地憋出一句,努力使自己的声音趋向平板,但难以自制的波动还是出现在这短短的一个名字中,“最近不太平,你还来这里?这么信任我,值不当的。……我们今后,还是不要多见面为好,于你于我,都没有好处。你也知道……”
艾希礼蹙了蹙眉,将肩膀倚上靠背,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从不乐意落下风的观星社巫师,当然乐得一切威胁在他面前挑衅。肆意的狂狷让西玛不由得愣了神,而一时间涣散的目光让巫师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艾希礼的世界中从未太平,也懒得与面前这个敌对方的职员断交而对暂时的安稳擦脂抹粉——艾希礼从不屑于这点。
——而实话讲,面前的人瘦弱忧愁,哪里有半点里政府的模样,倒该像个大学里满口莎士比亚和歌德的青年学生。
“信任和不信任有差别吗?反正吃亏的从来不会是我。”他直言道,“对我而言,北风从未停止,现在无非是把窗打开,站到风口去而已。谢谢你担心我,可若你不想气氛变僵的话……”
纸杯散发着恰到好处的热气,轻轻贴上对方苍白的手背。触碰到的时候,他微不可见的躲了一下,为此,艾希礼又不动声色地握住了杯子,蓝色的光如同萤火,微微一亮。
“倒不如换个话题吧——比如我猜到你会冷。”末了,魔法师有些不习惯似的废话了一句,“双倍焦糖,你会喜欢的。”
西玛露出了一个笑容,他欣喜地握住了纸杯,温热的奶香从杯中飘了出来,保持得恰到好处的热气将他的眼镜片熏上一层白雾:“谢谢。”他低下头,白皙的手指被热甜奶蒸出了几分血色,轻轻啜了一口。像是为了向魔法师证明似的,他抬起脸,露出了一个笑容。
艾希礼把目光偏开了。
图书馆的夜色袭来,灯火亮了起来,更衬得外头的寒冷。这一年的秋天推进得格外的快,才刚刚到了季节,寒风就乒乒乓乓地敲打起窗户。西玛抱着甜奶昏昏欲睡,他已经许久没有这么心安过了,在一个阔大的公共场所,人来人往筑出的巢,和身边信赖的魔法师。他几乎要忘了他早就准备好的台词,那些温和的遣词造句排练了多遍,在温暖的甜奶和艾希礼面前简直就是坏气氛的利刃。
舌尖的甜味陡然间炸开,沉淀在杯底的焦糖抓紧最后的机会洗刷他的口腔。他清醒些许,甜奶在冷去之前,他已经将它们通通喝下。他扭转过头,艾希礼仍靠在椅子上,喝着属于他的那杯咖啡,脸上有几分少年鲜有的警惕。
或许是时候了。
“我调去侦查组了。”西玛冷不丁地说,他的语速尽量的快,用词也力求精简,以免艾希礼反应过来,把唇从咖啡纸杯上撤下后,他再也没有勇气说下去,“以后可能要多上前线了。这段时间风头紧,上头和红学联手……我们见面恐怕也要小心些。不过你别担心,等风头过去……”
他没说出最后的结果,只是轻松地笑了笑掩盖心中的苦涩。感谢自己习惯性的表情,那是天衣无缝的温和,没有人能看出坚硬的水晶正在从核心碎裂。很快地,他又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袖扣,递到对方面前:
“喏,这个给你,”他尽量轻松地说,“我叔父留给我的,他既然也是魔法师,这玩意儿应当也不是凡物。我知道你们那最不缺的就是魔法器物,不过蓝宝石却是货真价实的,你留着,好有个念想,我对你也算是放心。”
他的脸上露出些许“长辈”似的关怀。
艾希礼抬手接过袖扣,没说什么,垂下眼,抽出腰间的魔杖——西玛还记得他曾经是惯用剑的,翻找破除遗忘咒的日子里,艾希礼对咒语的练习渐多,虽还是不怎么用魔杖战斗,但还是常带在身边。
咒语里最多的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祝福,魔法师母亲常常赐予孩子或是爱人的庇护,那些至为善良的咒语。
“回礼,左手伸出来。”他拿着魔杖说道。
水蓝色的咒印刻在左臂,艾希礼低声吟哦着晦涩的咒语。而后,他细心地为西玛隐去了那些痕迹。
“小心一点。”他说,没有做任何其他解释。
西玛站起身,答应了一声,然后心血来潮似的,摸了摸艾希礼的白发。
“你也是,艾希礼。”他轻柔得像是在念哄小孩子睡觉的童谣。然后他拎起桌上的纸杯,捏着它的边缘踏入了图书馆外的夜色中。夜晚的黑暗像是粘稠的梦,河水一般的冰凉。左臂上仍带着几分灼热,西玛苦笑了一下。
追踪咒。
可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了然地笑了。反正时日无多……他眷恋地投入了夜色深深的海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