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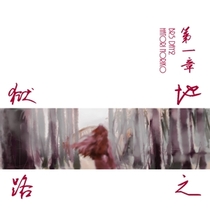

.共1636字.
阿戈斯蒂诺.科斯塔感觉到了来自身后的视线。
她觉得有人在看着这边,但又好像并不是看着自己。那不像小说故事里所谓“灼热的视线”,反而让人有一点点发冷的感觉,第一次察觉到的时候,蒂诺甚至想象过身后有一条巨大的黄金蟒,正用翡翠般的绿眼盯向这边,口中还吐着细丝般的蛇信。
然而她猛地回头的时候,都看到座位后空空如也——并不只是座位后而已,星期天的大早,整个图书馆都空空如也,只有蒂诺一个人呆呆地环顾四周,桌上是摊开着的作业和里头夹着的小人书,纸页在轻风中“哗啦哗啦”响着。
一开始,蒂诺考虑过这是幻觉的可能性,又或者只是自己累过头连感官都不太对劲了。但在这个想法出现的下一秒就遭到了强力的反驳:这不对。她想,我的感觉……从没出过错。
她忆起自己7岁那年,在家门口遇到的那个小男孩。
那个男孩的身体是半透明的,他就那样静静地蹲在门口,垂着眼看地上的花朵。风吹过的时候整个人像是马上就会消失。
蒂诺慢慢地朝他走过去,她觉得心脏快跳出来了,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兴奋。离那个男孩越近,她就越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他身边的那一片地方并不是自己所认识的家门口。但她还是走过去,直走到男孩的面前。对方抬起头用看不出瞳色的双眼注视着她:
“你的眼睛真好看。”那是男孩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声音温暖得像一朵刚盛开的野雏菊。
蒂诺愣住了,她突然想去握他的手,也就真的这么做了。却直直从他手心中穿了过去,感觉像是浸进了一盆冰水里,凉得令人心慌。
“啊哈哈…对不起啊”男孩挠了挠头,对着已经呆住的蒂诺不好意思地笑着,“我是个幽灵。”
7岁的她就那样一只脚踏入了魔法的世界,自己却浑然不知。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话题广无边际,更多的时候是蒂诺手舞足蹈的讲,对方静静的听,偶尔报以温柔的微笑。他是蒂诺遇到过的最好的听众,从不会对质疑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当然,也许他本身就是想象的一部分也说不定。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父母。“反正一定也没人会相信吧。”女孩这样想着。
也正因如此,那天看到母亲和男孩谈话的时候,她才会那么震惊。
匆匆跑去的蒂诺被母亲一把抱住,母亲把头靠在她肩上,开口说话时嗓子带着一丝哭过般地沙哑:
“阿戈斯……我的好女儿…我早该想到……”
蒂诺呆呆地站着,碧蓝的瞳中写满了不解。她的目光越过母亲的肩放到了男孩的身上,对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带着如同初见时那样平静的笑容,朝她摇了摇手。
下一秒,男孩消失在空气中。仿佛一开始就不曾存在。
那之后她们再也没有见面。蒂诺退了学,被关在家里,直到12岁生日那天早上冲进卧房的白脸猫头鹰带来了霍格沃兹的录取通知。
蒂诺合上书,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那时候她每天聊完天回家,男孩就在身后望着她进家门…和如今的感觉,一模一样。
没有温度,却不会令人惧怕的视线。虽然图书馆里的这位对自己也许没什么兴趣,他在意的是自己手中的书——书合上不久,那感觉就消失了。
蒂诺盯着书封,厚重的魔法史课本上有一圈圈漂亮的金色纹路,而夹在里头的儿童绘本则是色彩斑斓的封面。她想象着那个未曾谋面的幽灵,眼睛里闪烁着明亮雀跃的光芒。
是男还是女?是老人还是少年,抑或是刚刚好的大人模样?有着怎样的声音和怎样的容貌?为什么会在这里?喜欢怎样的书?
…………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好想知道,好想了解,好在意。
蒂诺把书抱在怀里,低下头‘吃吃’地笑了起来。偌大的图书馆里,只有这细小的笑声飘散在空气中。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热情也好、好奇也好,内心深处莫名的颤动也好…这一切都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她在脑中勾画着一个方案,虽然只要是正常人听了都会觉得可笑,但蒂诺觉得说不定可行。一字未动的魔法史作业已经被忘在旁边,她走向书架,在一行行让人头晕眼花的书目中翻找着自己想要的。
“今天就先试试这本好了……”
她拿起一本可以说是画集的书,掸掉上面的灰,封面油画中的羔羊歪过头来好奇地望着少女。蒂诺把画集顶在头上,迈着轻快的步伐回到座位上。
“总之,这段时间都请多多关照啦。”
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嘟哝了一句,蒂诺合掌祈祷后,翻开了第一页。
fin
前面大概都是Rano的焦虑心理活动x正文大概是接着Hilda的文之后的部分...
--------------我是分割线--------------------
脏乱、潮湿便是形容Rano踏进男厕所的第一想法。与大大咧咧遍踹开了男厕门的妹妹Hilda不同,Rano起先可也是矜持了一下的。略微在这对女子高中生的禁区门口踌躇了两下,却又想起Cielver的难题,便也不得不为了搜寻线索而进去。鉴于之前的探索完全没掌握一点线索为今次的谜题打下奠基,那去这种其他伙伴除了生理需要并不十分愿意踏入的地方,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吧。稍微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Rano便尾随已在男厕打量起的Hilda之后也进入了男厕。
乍看之下并没有什么显得可疑的地方,与仔细研究地上裂纹的Hilda不同,Rano选择先随意地检查水池底下。弯下腰往布满苔藓的水池底部略微地一瞥,除了附着于上面的几只臭虫以外并没有什么发现也是情理之中。然而此情此景已经足够刺激到有轻度洁癖的Rano了。不得已地洗了把手,便走到正在调查墙上痕迹的Hilda身边的抽纸盒旁擦手。想着顺势也调查下抽纸盒吧,拍了几下出来的除了纸巾还是纸巾。觉得有些尴尬的Rano便朝调查中的Hilda发话:「有什么发现么?」「嗯?啊..似乎是关于男厕所堵塞了的通知,被撕了些部分看不太清了。」一向有焦虑症状会不自主瞎想的Rano略微愣了一下:『男厕所?男厕所也能堵啊真是。又不是女厕所会被某些女性用品堵塞住马桶…谁拉大条吗。还是说堵住的是什么别的东西…不不别瞎想,你又没来过男厕所哪来的经验啊。』便又转移注意力到水池边上的电箱上。
打开了电箱完全没有线索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真是的来这种地方究竟能有些什么发现啊…』心中烦躁之感混杂着些不安又欲上前,Rano只得将这种负面的想法强压下去。『不过不这样干兴许就不能解出Cielver的谜题了,那现在这么干自然也是值得的了。总是觉得被这个学院的一种违和感压迫着,这个学校究竟发生些过什么,又会不会威胁到我们呢。如果能趁这次机会一举发现这个学校的秘密那也就了了我的心结了。但是在这之后,我又该怎么办呢…』又要陷入焦虑漩涡的Rano强逼着自己打起精神:『不不现在可不是顾虑这些个事情的时候啊,要做的事情可还摆在眼前呢。大家也都在为解开谜题尽力搜寻线索,我又怎么能只是想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呢。』给自己定了定心神的Rano决定鼓起勇气查找最后一片禁区——男厕的四个隔间。
从面对两人的最右锁着的隔间开始,Rano因为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人,为了避免尴尬便先礼貌地敲了敲门。没有预期中的回应,『奇怪…这是有人还是没有人啊?』没有得办法只好透过门缝看。『这可真是有点失礼了…!』通过底下可以看到有一双脚,是坐在马桶上的样子。好像是察觉到来着脚底下的视线,坐在里面的人咒骂了起来:「喂你这小子看什么呢有人啊!神经病!变态!」『什么啊有人的话就早说嘛。得趁这人出来察觉到我们前快溜。』Rano叹了口气转向下一个隔间。空荡荡的隔间敞着门,没有任何线索可言。第三个隔间也是一样的状况,不得已便走到了最后一间隔间。『这可是最后一间隔间了拜托了给点啥线索吧…!』这样想着的Rano敲响了这一间隔间的门。跟最初的情况一样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诶不会又是个上厕所上到忘我境界的人吧…?!』又不耐烦地加重了手上敲门的动作,还是得不到任何回应。从门缝往里望也没有任何人的脚,但是地上似乎有什么跟其他隔间不一样的地方。『这间不会就是那间被堵住的隔间吧,那可务必要看看了。』从来都是以谨慎作为原则的Rano回头叫了正无所事事的Hilda:「喂,Hilda,你来看看,这间隔间似乎有点不一样啊。怎么敲都没有人应,估计是堵了的那间隔间,而且地上似乎有些什么东西,」Rano迟疑了一下,道:「你有办法搞清楚里面是什么东西吗。」
听闻总算觉得该轮到自己出场了的Hilda有些小孩子气得意地道:「办法自然是要多少有多少的。」说罢,她观察了一下那间隔间便也试图从门缝下得到些什么线索。与Rano不同的是她直接很自然地趴在了地上想要看清地上的异常。「呀,看不太清呢,没办法,厕所的门缝着实不大啊。不过…」她的眼神坚定了一下,「看不到里面有人的脚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她又将视线放回隔间的门上:「你让一下,稍微站远点好了。」便抬起脚做出要踹的姿势。「喂等等啊你…!!这是要踹吗!!先不说会破坏公物单是会破坏现场这点就…!!」然而一向谨慎为重的Rano也劝不住自己的妹妹,说时迟那时快少女已经踹了好几脚。「嘭!!」「嘭!!!」然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呀…这可真是没办法啊。事到如今也只有那样了!」看着自己的妹妹没有丝毫动摇依旧是很有动力Rano也顿觉拿她没办法。「只有上到隔间马桶上窥视这一个办法了呢,以我比姐你高一厘米的优势!」「啊啊…你这丫头…」然而Hilda已经站上了马桶盖,正极力趴上门板。「啊,Hilda,看到什么了么?」Rano抬头问她,却正好看到她表情惊恐且看似痛苦地扶着头。「喂Hilda!!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吗?!」Rano不无担忧地呼唤着Hilda。再睁开眼的Hilda看似已经恢复了正常,喃喃道:「唔嗯,我没事,肯定都是错觉…」她又继而定了定睛,搞清了那边隔间的状况。「…老姐,我不太相信我看到的东西,为了确认,我要翻进去看看,为了确认一些东西。」「你到底看见了什么啊,快告诉我,还有,不要那么莽撞。」Rano有些心急地发问。
「我,看到了很多的血...」她神情紧张地告诉Rano,依稀都能看到太阳穴上的青筋。「你说什么?!!!」Rano完全是一副受惊的样子,不等她说完便叫了出来。「嘘...姐啊小声点。」Hilda指了指那边的隔间。「啊…对不…」「所以我必须得翻进去看看。」这下纵然是谨慎派也着实无计可施,只得同意:「那你要及时汇报,小心点。」见Hilda点了点头便一个反身翻了进去。此时的Rano的好似是被砖砸了一般脑中感觉要炸眼冒金星。学校里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状况如何?」Hilda的声音隔着门板闷闷地传过来:「啊…血液看上去还是新鲜的。不过没有任何人啊。这么多血是从哪来的...难不成人被冲下马桶了吗。」Rano虽没身在此情此景却也没心情开玩笑。既然没有人那有这么多血迹也不一定表明是有谁被杀了吧?!还是说是死后被带走了??不…但是门是锁着的...那这到底是?!!过多的刺激已经让Rano无法好好地思考了。「总之,」Hilda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好歹让她有些安慰感,「我先拍了照我们出去再说吧。」


----------------3129字------------------
他们看见了“神”。
那位名为“第五季”的神祗将他们——来自各个世界的探险者们集中起来并且给与信物,为了拯救世界。
阿伦德尔收集的诗歌里,这类题材的作品很多。从平民到贵族,不论哪个阶层的人都爱这种拯救世界的英雄故事,在阿伦德尔还在唱诗谋生的时候也多次唱过这种诗歌。少年时期,阿伦德尔也向往成为这种诗歌的主角,但当这种命运真的降临的时候,他的心颤抖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未知的旅程,一方面是因为“神”。
阿伦德尔是有信仰的,他和养母一样信仰瑞图宁,但在这之前他从未见过真正的神,信仰对他而言像是一种习惯。后来他到了遗都,在一次拜访的回程中触碰那张神秘的纸,被传送到这里,他就折服于“神”的能力下。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自己能用各种各样的华丽词句繁复修辞来赞美眼前这位神祗,用上“萤火虫”“启明星”来作为喻体,拿圆润清脆的精灵语作为基调,再由自己作曲自己吟唱。他再也不腹诽那些前辈诗人的“溢美之词”了,因为见到这位神祗的瞬间,心脏就被某种可以称之为感动的感情填满:这或许是伟大时代的开始;这是绝妙的诗歌题材;如果完成了神给的任务会怎样,瑞图宁会显现吗……?他脑子混混沌沌地想着这些问题,握紧了自己的那片弦月。
这片弦月是“神”给与的通讯用信物,由完整的一块原料制成,有着古朴的外形和优雅弧度。阿伦德尔不是鉴赏家,但他觉得这比那些贵族女子的珠宝首饰美丽的多。同样的弦月在他的队员手上,像是在昭示着什么。半精灵和侏儒就算了,竟然还有一位高等精灵作为队员。阿伦德尔不由得苦笑,然后在心里默念队其他人——尤其是队长——的名字,希望不会发生叫错名字的尴尬情形。毕竟他是个半精灵,以前并不常与人组成这样的队伍,甚至不常体会到被不含恶意的眼神看着的感觉,这一切都让他觉得又紧张又兴奋。但是又有一些心虚,因为其他队伍大多以战士暮刃巡林客甚至法师为主,但自己所属的队伍却由吟游诗人和牧师组成,到后来才招募到一位高等精灵暮刃,万一碰到混战场面,估计会十分辛苦。
思绪跑远了,又被身边的队员招呼回来。少女们与队长在说着什么,引得队长大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阿伦德尔脑子里关于其他人名字的碎片又一次散落一地。他干脆把弦月交给队长,让队长做一个帽饰给他,顺便让他多一点时间再把名字的碎片拼齐凑好。
二
尽管做了被传送到怪异世界里的心理准备,也一再深呼吸擦拭自己动摇颤抖的心,但在身体被白光笼罩的瞬间,阿伦德尔还是不由紧张的握住了那个弦月。他不是身经百战的战士,而是以一个普通半精灵吟游诗人的身份,与不知道底细不了解个性的队友们——侏儒、半精灵和骄傲的高等精灵,他有时候还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一起加入拯救世界的旅程。他的手指已经因为害怕而轻微的发着抖了,但愿女神保佑。
传送没有让阿伦德尔紧张太久,白光在呼吸间减淡。他们落脚,吐气,未稳定身形,震耳的嘶吼声就包围过来,撞击鼓膜,震动心脏。随后是地面不详的颤抖、血腥味、金铁交鸣、呻吟痛呼、肢体剥落。
——是战场。
传送带来的不真实感消散,他们才看清了自己的处境。这个小队被传送到一个陌生世界的战场,降落在两军之间,霎时间烟尘弥漫,重骑兵发出可怕的声响,没有掩蔽物的他们,被撞入两军冲锋。
那些带着可怕表情的士兵,不论是哪一方,都挥舞着沉重的冷兵器,敲击、撞碎、刺穿、撕裂。不远处一个头颅飞起来,动脉血溅在阿伦德尔脚前。而远处传来士兵被扯出肠子的要命尖叫声。一个跛脚人拿着自己的断臂走过空地,然后毫无征兆地被铁锤砸的脑浆迸裂,此时眼前的场景和梦魇重合了。
跑、快跑、找地方躲起来——
颅内尖锐的鸣声响起,但阿伦德尔的关节锈住了一样无法动弹,他的灵活身手消失无踪,手指的颤抖反而停下了。身旁Iris一声轻呼给了他发条,这名独来独往的半精灵吟游诗人脚下轻挪闪过刺来的长枪,随后凭借腰的力量,转眼间腾出三丈有余。他知道自己可以逃跑了,只要朝一个方向跑,只要战线不被拉的太长,只要……身体动起来之后,大脑也动起来,低级神经中枢促成逃跑的反应,但大脑告诉阿伦德尔他需要回去,他意识到自己还有几位同伴。他不想人被抛弃,所以他也不能抛弃他们。
与此同时,同样全神贯注心情紧张肾上腺素超额分泌,笼罩在Suzette身边的,是全然不同的感情。那位高贵的高等精灵放任自己沉浸在初上战场的偏向喜悦的兴奋中,她手中的武器一次次挥动,带出简洁有劲的银光收割首级,给旁边的半精灵Iris创造了一个完全安全的地带。但只有两个人撑不了太久。阿伦德尔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与低落感,他应该回去,作为这个小队的队员而战。
逆着人流,比溯流而上更艰难地回到小队的范围,之前阿伦德尔身上让他不能呼吸的战斗压力骤然降低,有了小队队员帮他抵挡他身后的攻击。在背靠背的战斗中,他定睛仔细观察了两军的标识和旗帜。一方是狮鹫,这些狮鹫花色的士兵已经几次试图攻击他们;另一方,即最开始把这个小队卷入的,是飞龙。
“队长,怎么办?”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声音迅速淹没在空气里。
这个小队缺少战力,留在原地作战的结局就是消耗体力而死,脱离战场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队长奥列格却好像没听到一样继续战斗,足下产生了一束束痛苦扭动的火焰,这是侏儒的天赋幻术,即使没有实际攻击效果但还是有力的牵制了敌人。阿伦德尔在闪过一把来自狮鹫的刀并顺势拗断握刀的手,把刀刃插入敌人胸膛的间隙里,毫无恶意地揣测队长或许同样过度紧张,陷入了他之前的窘迫情境。
虽然还有趁着闲暇腹诽,但巨大的体力消耗也不是开玩笑的:担任主要攻击的Suzette挥动刀剑的速度降低了,身边防线有了缺口。伊利亚斯不动声色地向缺口踏了一步,尽管是个诗人并不擅长白刃战,但她还是拿着任何可以用来做武器的东西攻击那些士兵。旁边Iris的治疗速度也下降了,牧师的治疗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而同样的,阿伦德尔跳来跳去的脚步已经不那么灵便,奥列格吟唱时也口齿含糊。这五个人带着盲目乐观和清楚上映的绝望并肩战斗着,缺口逐渐扩大了。
他们身边的士兵密度也增加了,看来被当成硬钉子了。阿伦德尔听到粗重的呼吸声,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反正都一样疲乏,崩溃或许就在下一秒。一柄枪刺来,阿伦德尔几乎要跳不起来,他的身体已经判定自己躲不过去了,于是任命地闭上眼睛。
但是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没有被撞飞也没有被刺碎胸骨。一队身上有飞龙花纹的士兵挡住了这些攻击并漂亮的反击。他们经受过团体战斗的训练,效率比这个临时凑起来的小队高不少,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起来没有攻击这个小队的意思。
看来这个小队没法成为混战中莫名其妙战死的冤魂,倒是有可能变成某一方的俘虏了。把周边的狮鹫士兵粗略打扫干净后,那队看起来友好的飞龙士兵传达了的长官想把这个小队带回军营的意思。
但愿选择跟他们回去比留在战场上要好,虽然不信任但这群人还是跟着飞龙花色的士兵离开战场。回头的时候,阿伦德尔久违的听到队长忘情的高呼“冲啊!!!”随后是伊利亚斯和Iris制止的声音,阿伦德尔忍不住敲了敲小队长的头。
气氛突然变得轻松了一些。这群人——瓦尔哈拉小队被两位士兵护送着向飞龙花色的军营而去。
脱离战场后,大家都变得放松。脱离了直面死亡的威胁,他们甚至开始跟那两个士兵搭话。即使险些被撞破异世界人的身份,但聊天还是保持一个轻松融洽的旋律。话题甚至跑向了弦月,阿伦德尔发誓他听到了那两个淳朴士兵对他们队伍感情的赞美。
瑞图宁啊,他们哪有什么两肋插刀的战友情谊。
然而看着旁边奥列格揉着头上被砸到的地方,还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阿伦德尔忍俊不禁。他抬头环视身边的这群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刚刚的战斗中替他挡下攻击,而在养母死后就独来独往的他也在替他们战斗。这些稍微有点熟悉的脸让阿伦德尔在这个陌生世界里感到安心。对他来说,这个小队在此时才算是结成了,他认定了自己是小队瓦尔哈拉的一个成员,也是这场旅途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场旅程,大概会被写成诗歌传颂下去吧。
-------------------------------------------------
考虑着阿伦的改变来写着。
第一点是,他对小队的称呼从“这个小队”“这群人”到“瓦尔哈拉”,说明他从游离变成了参与。
第二点是,在“一”里的心理活动比较多,对话和与其他人的互动几乎没有描写(尽管正常的和人交往,但这对阿伦来说是不重要的)但后来开始注意别人的活动,互动也增加了描写。
这样是想塑造一个看起来很友好和大家玩,但心里有所疏离的人,下篇会继续描写他的变化并增加好玩的互动w可能会着重写写Su因为阿伦对高等精灵有点微妙的感情(并不。
以及,因为奥列格……不,队长已经详尽描述了全过程,所以我打算只把战场这段认真写一下(说起来,为什么战场部分你写的那么轻松我写的那么痛苦啊队长;A;)。因此在“离开战场”部分结束,可能的话会补上后续作为连接段落(可以的吧?)
2015-7-26 (话唠的)司磷
*正文总字数3149
*我完全是在涨他人志气【
————————
我摸了摸放在口袋里的十字架项链,稍微安心下来,然后抬头看向眼前的高大建筑。
——亚历山大图书馆。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不吉利。有人说托勒密一世时候所建造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曾经是人类文明的太阳,那么这里也许是魔法界的太阳吧。
这座图书馆的外貌确实仿照了古罗马的风格,粗大的筒形拱撑起高大的正门,稍微处理做旧的痕迹使得历史感从每一块砖岩间弥漫出来。
为什么要特意取这个名字做成这样的外貌呢?历史上的那颗太阳就像是真正的太阳一样燃烧着熊熊的战火化作了灰烬,而现在这颗魔法界界的太阳边也燃起了战火。
我推了推有些滑落的眼睛,紧了紧胸口抱着的书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来还书的普通魔法师,快步走进了图书馆的大门。
昨天在旁边的岛上驻扎下来之后,今天一大早就开始了侦察行动。因为我的想法被主教所认同,所以我轻松地找到了陪我一起来搜寻资料的同伴。在这个岛上巨大的丛林里转悠了很久,才终于踏入了魔法界的居住区……恩,中间的过程我们忽略、忽略。
本来一起行动的linus一进来就不知道溜哪去了,本来明明是说好去图书馆的。变装过的有栖和syvia也装作是普通的魔法师溜了进来,我们相互眼神示意之后,就在阅览室里面四散去寻找需要的资料了。
在一排一排的书架里转悠的熟悉感觉让我安心不少,似乎几个月没有这样的经历了吧?不用靠近就有淡淡的墨香味传进鼻腔,在这样木质的丛林中似乎只是稍微晃悠了几圈,光线就慢慢变得昏暗了。然后我才意识到,本来在岛上晃悠就花了半天,再为了绘制魔法界居住区的大概街道图晃悠了一圈之后,时间本身就已经临近黄昏了。如果再在这里无所事事的话,估计就要通宵赶路了。
随手从书架上抽下两本看起来似乎是魔法教科书的东西,我开始观察起周围的环境来。因为夕阳西下这个图书馆里的光线已经黯淡不少,本来为数不少的魔法师也都开始向着外面走去。已经快要到闭馆时间了么?那么得快点了。
我正准备在浩瀚如烟的书海中寻找我的同伴的时候,一个逆向而行的女性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穿着似乎是制服一样的东西,行走的方向与其他人不同本身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她手上棍状物体的异样。原本以为那就是所谓的魔法杖,然而它的顶端暴露在阳光下的瞬间我才注意到似乎有哪里不对——即使是在这昏暗的阳光下,那顶端反射出的危险寒光似乎是刺向我的眼睛一般锐利。
不是魔法杖,是把长枪。而且是把好枪。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点眼熟。这样的念头在脑海中升起的同时,那把枪的持有者的面容也暴露在了阳光之下。
看到那张面孔的同时,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那把枪那么眼熟。
那把枪是之前张炎那家伙偷偷摸摸从教会仓库里摸出来然后又偷偷摸摸带上飞机待会中国送回家的那把,而这个拿枪的人——
张青。
我下意识摸了摸脖子,被链子绞过的疼痛从记忆深处再次升腾起来。那句感情色彩淡薄的“这个倒霉家伙”好像也在我耳边不断地被复诵。虽然早就准备好了会有一战,但是相遇的时机这么早,还是让我不禁欢欣起来。
眼下是个不错的机会。
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放开脚步去寻找有栖和syvia了。
做完准备之后,我一路小跑着来到她的面前,像是一个怕生的家伙一样低着头向她搭话:“那个,保安小姐……”
“什么事。”依旧是那个冷淡的声音,似乎是一瓢冷水倒进去一般,我觉得我心底的有锅滋啦啦的躁动起来。
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才能注意到两人的身高差。加之我稍微低下了头,只能看到对方的腹部。在制服下摆处,皮带的扣环没有被遮住,在昏黄的阳光下,金属扣环上面的一些擦痕显得格外明显,不过上面刻着的字样还是勉强可以辨认出来——“cos”。
欸,cosplay,还是余弦函数?
对了,印象里当时的前半句是“叫余弦的女孩”……原来如此吗。
跟她会是什么关系呢?以及拜托张炎弄回去的枪,好像就是她拿在手上的那一把。
“boku想拜托你——”
一个有趣的主意在心底形成。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能好好地解解气吧——
我把左手伸向腰间。
“去死三次吧!”
用力捏住藏在外套下的刀柄,然后把刀全力甩向对方。
是动作暴露了吗,还是语气忍不住上扬了呢?对方似乎有所察觉了。银色的刀光划破空气,却只是发出“锵”的金属碰撞声。
用白色的枪架住了我的攻击之后,她眯起眼了我很一会,然后才摇摇头,说道:“啊,果然来了吗?”
……果然,我说,这个应该是我的台词吧?张炎,果然透露情报了啊。要申请把她关禁闭吗?
不对不对,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自由之风,化吾利刃。”
快速地念出咒语之后,空气明显地流动起来。虽然能感觉到聚集过来的风少了不少,但是似乎比以前的感觉更加凝练。我握紧了刀刃,把风和刀一起挥出。
“雷霆震怒,诸异退避!”感觉到圣力的鼓动,对方把短枪刺来,刺耳的噪音在两人之间爆发之后,一阵巨力传来,我不由得后退几步才稳住身形,“你看起来很愤怒,但是怒火是个危险的武器。”
像是在指点一样提出意见,并且把左手的长枪也像我刺过来。感受到那把枪尖的危险性,我努力把太刀扯回来,借着圣力才勉勉强强隔开了这一击。
……野蛮的女人!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个评价都绝对没有过当之处。
一旦战斗起来,她之前懒洋洋的那副样子就完全不见了,双手的短枪的每一次刺出都带着呼啸的破空声,我只能连番招架。
狮子搏兔,亦用全力。
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冒出了这个成语,我赶紧把这个念头甩开,以免真的把自己当做兔子,失去战斗的意志。
这里本身就是魔法界的结界之中,我的圣力完全受到压制,战斗力减弱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是“弱者”。
所以我拜托了同伴,并且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我再次退后几步,穿过一条通道来到了另外两排书架中间。
有栖从右边的书架后出现,涌动着厚重的土之圣力的开山刀随着啸声砍向了张青。
也许是感受到杀意,张青下意识把右手的白色短枪向身后一架。开山刀与枪身相接,发出沉重的轰鸣声。
这时候我已经把手中的太刀刺向地面,激活了刚刚简单画下的消音阵。好在临近黄昏,已经没有读者还留着图书馆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其他人到来之前解决问题。
“极寒之冰,”我拔出太刀,“助我杀敌。”
圣力流转,萦绕着淡淡的白色气息的太刀斩向张青。
腹背受敌的张青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用枪接下我和有栖同时发动的攻击之后,借力向着左侧的书架一撞。
随着张青因为撞击皱了皱眉,书架发出沉闷的声音倒下。不过这声音被早就布下的消音阵全数吞下。
我心里滚烫的热开始咕咕的泛泡,不管是多么强壮的狼,都逃不出猎人精心布置的陷阱。
不过这个绳套还需要继续收紧。有栖的开山刀被有了躲避空间的张青避开,斩在地上,地面似乎是被这一斩唤醒了,轰隆作响,一根巨大的石笋几乎是在瞬间冲破地面爆发出来,张青不得不左跨一部避开,在那里等待的却是一把锋利的太刀。
这样的追击持续着,又有两个书架被波及倒下,张青的动作却是明显地迟缓起来,不光是体力的消耗,还有我一直在使用的冰圣力的作用。
原来看着猎物一步步走向死路是如此有趣的事情。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那些反派总是精心布局,甚至常常稍微放松绳套,看着主角挣扎。
的确很有趣呢。不过我可不是那些妄自尊大的蠢货,我是“弱者”。
接下来就是checkmate——
我这么想着的时候,一把萦绕着狂风的短剑从另一个方向刺向张青,迫使准备避开攻击的张青用短枪架向我的太刀。
是syvia,她来了代表有人接近了。
“冬之长河,急速凝结!”我连忙追加咒文,并且把圣力灌注到太刀之内。散发出更强寒气的太刀斩在白色的短枪之上,从接触点开始,无根的冰块开始生长。
意识到不妙的张青匆忙把短枪丢出,没有附加多少力量的短枪自然是无法有所斩获。
最初目的无法达成的话,只好执行这个目标了。
“准备走了,有栖、syvia!”
听到这话,syvia斩出长长的风刃,把张青逼退一步,有栖则是把开山刀刺向地面,一堵土墙骤然升起。
至于我——
躁动的火焰在我的刀刃上燃烧起来。然后我把太刀向着那把被冰封的短枪用力斩去。
将它化作了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