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台向下望去,恰好能見到隔著無數樓群、在遠方化作一線的太平洋。城鎮化的格子就像不停地靠近的俄羅斯方塊,越是靠近鎮子中心便越透不出來氣,給人一種壓迫感。海都要看不見啦!我想向平房吶喊,但在叫出聲來前控制住了。
我在天台上吃著從食堂買來的午餐三明治,火腿和丘比色拉油在夏天時總給人一種奇特又疲軟的口感。但因為只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所以我並沒有對這三明治做過多地要求。
“這就是所謂的笨蛋和煙都喜歡高處吧。”秋元那傢伙曾經那麼評價過我。
“因為高處才能放鬆啊。”我在那時候那麼回擊秋元,“在這種地方才能明白過來自己的渺小,然後進而就會覺得壓力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對於我的話,秋元他只是抱以嘲弄的笑容。他一向喜歡將自己當做高位者看待,我早就習慣他沒來由的自信。
他和我是青梅竹馬,這段孽緣從我們六歲的時候就開始了。
“如果說這樣就是笨蛋的話,宇航員一定笨的突破大氣層了吧?”我將這個論點作為我最後的反駁。
“當然啦。”秋元他從來不會改口,所以在這種時候總會絆自己一下,不過他那種根本就沒有在聊天的態度也很煩人,所以最後啞口無言的還是我。我們兩個就坐在被水塔遮蔽的陰影下看著遠方的海,風很清靜,一下子就能將夏日時產生的汗珠從臉上給刮掉,只是吹得我耳邊有點痛。
“四季啊。”
“嗯?”
“如果從今天開始世界就毀滅掉,你想做些什麼?”
“想從世界中心跳下去。”
“搞什麼啊,這麼抑鬱。”秋元那麼笑著,但那也已經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一年前的夏天,我從學校的籃球隊退部,秋元則從學校退學,理所當然地,和他一起在樓頂一同吃午餐的機會,就像逐漸被漁業碼頭蠶食掉的海岸線那樣消失了。
我們小小的聚會變成了只有我一個人,這樣的落差感帶來的只有寂寞而已。今天,我就像往常那樣坐在學校的樓頂上,一側,是逐漸被城鎮佔據的海,另一側,則是遠遠地能看到一點的巨大鳥居。
葛飾北齋在畫出《神奈川衝浪里》的時候,應該也沒有料想過太平洋會變成如今的模樣吧?我在沒有秋元的情況下,獨自一人開始思考這種問題——當然是一開始就已經有了答案,我對這一點再清楚不過,只是想象著如今看著的海洋在幾百年前或許兇猛又勢不可擋,能對我產生些許慰藉而已。
差不多將三明治吃到只剩下麵包皮時,我放棄了在樓頂進行午餐的權力。太平洋的海風從東面溫柔地吹拂而來,但只要走出水塔的陰影之下,立刻就能感覺到陽光的灼熱,甚至略微能聞到水泥被太陽烤焦的味道。再這樣在樓頂待下去可能會中暑,那就有點麻煩了,不如盡早下樓去體育館乘涼。
當然,今天我也不知道世界中心究竟在哪兒。
快步從樓頂下來,走廊裡,在吃完午飯後走出來的女生們已經三三兩兩聊起來了家常。我回到班裡拿了一下素描本,接著馬上衝著體育館奔去。我所在的天羽學院,在體育方面實際上並不那麼擅長,最出名的實際上是管樂團,但體育館仍然是個好去處。
打開體育館的門,我小心翼翼地在空調旁尋找著我的寶座。啊就是這裡就是這裡,空調剛剛好能吹到,但又不會讓冷風太強,還能觀覽到全場。畫畫也很方便,除了經常被球砸到的情況,基本不會被人撞到。
坐定之後,我才開始觀察起來今天使用籃球館的人。說起來也蠻有趣的,今天在體育館的半場打球的居然是兩男一女的組合。女生大概一米七左右,看起來在同年齡的女孩裡相當高挑,大概長至肩膀的頭髮被胡亂扎起來,雖然有些凌亂,但很清爽;剩下的兩個男生,一個皮膚被太陽曬成古銅色,一個則是一頭捲髮、個子稍稍有點矮的少年。
這個年紀一起在運動場上玩的異性已經蠻少見的,我也很少看女孩子打籃球,畫畫似乎沒什麼損失。我一邊在素描紙上勾勒出透視線,一面聽著那三人在籃球場上喊話時的聲音。
“好球!六十七往這裡傳!把小春打個措手不及吧!”矮個子的男生大開嗓門,極為熟練地從女孩身邊運球,被叫做小春的少女也不甘示弱。而我則被這局面帶來的信息量給衝昏頭腦。
誒,原來是兩個男生對一個女生嗎,就算女孩子的技術再好,也稍稍有點欺負人吧。
——這麼說來,那女孩似乎在哪兒見過。在鉛筆快速地勾勒出那個少女的臉頰時,我突然想起那份違和感。小春、小春……誒,那不是我們學校的女子籃球隊的隊長三千院小春嗎。
雖然對女子籃球並不怎麼熱衷,但我也知道秋元有時候會為了看女球員的大腿去坐女籃隊的板凳,(現在想起來他真的是滿身缺點,不過,我依然期盼著他快點回學校)有一次,他去看了之後悻悻回來,說是被女籃隊“男人一樣”的隊長罵了;加上,雖然我之前參加籃球部很不上心,但偶爾來,女籃隊的人會過來和我們進行聯合訓練,我其實在那時候就見過三千院小春了,只是因為我只是個冷板凳隊員,所以沒能和她說上什麼話。
這不是很糟糕嗎,在被他們發現之前先快點溜掉吧。如果不趁現在,再晚一點就要被發現了。
“啊,這不是籃球部的斉京嗎。”在我準備收拾東西離開前,三千院打破了我完美逃離的幻想。
——嗚呼哉!已經晚啦。還有,就算是籃球部的部長,起碼也要叫我前輩啦!
“哈哈哈……是啊,午休的時候恰好過來看看而已。”事已至此,我除了向三千院打招呼之外別無他法,於是便接受了自己的命運。我合上素描本,在那兩個男生略有些好奇的目光下糾正了三千院,“現在已經退部啦,因為三年級了嘛,學業稍稍有些緊張。”我撒著無傷大雅的謊,在三千院那略帶審視性的目光下說服了自己。
“感覺比在部裡的時候胖了。”
“……三千院君可真是不留情面啊!”
“原來是籃球部的人嗎?剛才是在幹什麼啊?”那個矮個子的男生問道,他凝視著我的素描本。
“在畫畫……”
“在畫我們?可以看看吧!”糟糕,我超級不擅長應付這種情況的。儘管那麼想著,我還是在那個男孩面前打開了素描本(人類的虛榮心真可怕),翻到剛才在畫的那頁。
“這個是小春耶,小春被美化過頭了吧!”就算那麼覺得也別說出來啊,我作為作畫者會被人誤會。我在內心吐槽道。
“不好,六十七被畫得超帥的,但是為什麼我被畫得那麼矮啦!”有嗎?
“那是因為一二三你本來個子就不高。”三千院嘲諷地笑了一聲,但是被矮個子的男生給痛擊了下肩膀。當他翻看完我的素描本時,一二三抬起頭來問道。
“我看前輩你骨骼清奇、曾經打過籃球、還會畫畫,來加入我們的3V3籃球隊吧。撒,別畫了!進來!”
這是什麼少年漫畫開場啦。我在內心腹誹。但更令我吃驚的是,對方似乎是在認真地說這句話。該不會讓對方產生了什麼誤會吧?應該不至於吧,畢竟我也很小心地在尋找措辭了。
“對不起……我的話,打球根本就不行!已經不行了好幾年了。”
“斉京前輩雖然這麼說,但剛進學校的時候可是體育特長生啊,我聽男籃隊的隊長講過呢。”三千院插嘴道。
“現在已經是碌碌無為、毫無成績,籃球部也退出了的三年級生。”說實話,我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在這種情況下被人提到自己曾經是個體育特長生的事,不過,那也是很久以前了,我現在也徹底認清了,“現在的我跑一千米可是會累死在地上的。”
“一千米……”六十七的臉頰微微抖動了一下,似乎是在心裡度量這句話所表達的含義,接著,他馬上就露出來有點傷感的表情。
“那四季能幫我們畫一個招人的海報嗎?”
“……我試試吧……”我抱起來素描本,向對方說道,在自己完全被社交給壓垮之前選擇逃跑。
“那就來看比賽吧!”
3V3籃球嗎……
意外的,我甚至在當天回家的路上也在想著那個叫做一二三的男生的話。我像被設定好的機器人那樣踏上電車、走過車站,接著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對明天或許會有的轉變稍稍產生了一點期待的心情。
進入平時居住的公寓,就像往常一樣,必然會經過門口掛著秋元兩個字的門棟。我在躊躇間,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那扇門。
“秋元……”我向著門裡的人喊道,“對了,今天有人告訴我他們要組建3V3籃球隊,好像是以全國賽為目標哦。他們邀請我去看,然後啊,那個,我會為他們畫個海報什麼的。”
“今天在屋頂上一個人吃了三明治,我突然想起來你很久以前說過的話,你不是曾經說過笨蛋和煙都喜歡高處嗎?”
“來學校吧,求你了。”
“……”
就像往常一樣,門的那頭了無回應,我在等待了一陣子之後,悻悻地放下幾乎就要按上門鈴的手,隨後轉身用鑰匙進入了自己所居住的公寓房間。
“四季啊,你這傢伙搞不好挺脆弱的。太寂寞也不行,會死掉,太吵鬧也不行,會死掉,好好地呵護會死掉,完全不管就那麼放著也會死掉,總之無論如何都會死掉。”秋元曾經這麼說。
“我是兔子嗎?”我反駁。
“不是,是小鳥。”秋元說。
“……被你那麼說感覺真的很惡心,不過鳥比兔子好。”我評價道,“這樣聽起來真的很奇怪啊。”
“兔子也好鳥也好,總之我要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四季,你能明白吧?”秋元合上鋼琴蓋,在那個下午對我大放厥詞,我呢,完全不知道對方到底想幹什麼,老實說我的青梅竹馬又讓人討厭又會說些不明就裡的話,現在也搞不清楚我是怎麼忍受了十二年。
“不明白。”我回答。
“那是因為四季是傻瓜,喂,把頭髮用發卡給夾起來吧,這樣蓋在臉上完全看不到眼睛了。”
“幹嘛啊,又不是混混,戴什麼髮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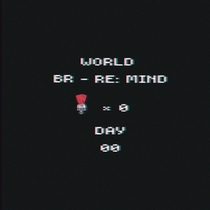



“请午餐至少不要吃太饱,xx日午时2点30分,我在2号试做区等你。”
这个语气不用看落款就知道是谁,根本用不着确认。沈京看着通讯终端里的短讯,乐呵呵地猜测壬亥要约他做什么。
已经毫不在意壬亥完全知道自己当班和其他安排行踪的事了,沈京轻轻抛着终端,完全没有顾忌地释放自己的好心情。
说起试做区,给人的印象就是研发组那些狂人时不时搞爆破,还会经常出现搬砖修墙之类的事情,常常端出的菜品都惨不忍睹——不是糊成一坨就是呈现各种恶心的颜色,不仅没有食欲,就连吃下去是否会引发生命安全问题都没法保证。想想他们还在研究怪物肉的食用方法,就觉得共用那些餐具一阵犯恶心。
壬亥究竟是脑子抽了哪根筋才会想去试做区?要约吃饭的话食堂不是更好的选择?
抱着这个疑问,沈京有些将信将疑地赴约了。
“你真准时,还有51毫秒就到点了。”
壬亥张嘴就是听起来有些欠扁的话——不过这话他只在亲近的人面前说,沈京也就默认了他这是在跟他套近乎——这么想的话这句话还蛮可爱的。
壬亥脸上的神情比平常柔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仅仅和沈京约会还不至于变成这样。
“对了洛仔,你今天不是应该出任务——”
话还没说完,沈京就被面前的场景搞傻眼了。
“等等,这是哪一出,你该不会和哪个人一起玩我吧?”
眼前是一片昏暗的室内,开了灯,但也只有制作区——通俗来说就是厨房——亮着光,试吃区——餐桌——那边隐约能看见台灯的轮廓,反倒是窗外亮一些,能看见一些星星点点的光,窗户还特意贴上了某些材质,导致从里面看上去,天空是静默的蓝色。
这简直就像是。
西餐厅。
沈京没有说话,他只是怀疑地盯着壬亥。
要弄成这样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能办到的。
“我拜托了几个人……算是我欠他们人情,以后会还的。”
冷静地陈述让这间屋子的情调减淡了些。
“那你爹呢?今天他出任务不管你?”
“今天他绝对不会管我的。”
不知是想起了什么,壬亥有些落寞的感觉。他趁着沈京还在怀疑,大步走过去把一侧的椅子拖出来,摆出了一副“您先坐”的表情。
沈京也就沉住气,看他不太想说过程的样子,走过去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盯着人影往厨房那边走去。
隔得不是很远,沈京能清楚看见他在做什么。
壬亥从自己带着的箱子里取出一些调味料,看起来都是平时不舍得用的那种——瓶子很干净,也没有什么使用的迹象,甚至有些看起来没开封过。那些调料一看就比厨房里供用的高级,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
然后沈京看见壬亥从箱子里拿出来一块用保鲜膜包着的,不小的肉块。
“我求了很久研发组和普通组,他们这几天才肯答应我分一点培育的肉,虽说很巧,但是这次欠的人情可就多了。”
趁沈京还没来得及发问,壬亥就像是抢着回答一样把这块肉的来历交代了。
“还很新鲜,是货真价实的肉。”
壬亥有些怀念地摸了摸那个质感,随即手脚麻利地将它刨开,分割成了几个部分。中心的肉质与边角的口感不同的部分分开,感觉像是要做两种不同的料理。
沈京也不是不会做菜,他看着壬亥行云流水的动作,产生了些许好奇。
“你以前做过菜?”
哦,不对。沈京这才发现问错了。他刚刚才想起壬亥经常捧着一些类似饭团的东西——一开始还以为是托食堂阿姨做的,现在想来,那些东西都投射着某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嗯。”
壬亥没有丝毫诧异,很平淡地陈述。
“戊戌真的不会做饭,我不吃快捷食品都是拜他所赐。”
沈京听闻后撑着头发出一些嗤笑。
“什么?这样啊!”
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回想那个其实很颓废的男人,沈京就像掌握了什么一样开始盘算一些事。
肉块过油煎过后翻面,刚刚抹过一些类似蜂蜜的合成品,还不知道壬亥加了什么调味料,从锅那边散发出美味的焦香味。壬亥估摸着时间,拿了另一瓶调味料,往锅里倒去。一时间,那香味里又混合了葡萄酒的香味。
沈京挑挑眉,对出现的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反正是和研发组有关系,这些人一天到晚都在捣鼓什么呢。没有听壬亥的话至少吃到七成饱的肚子在闻到那阵香味之后也不争气地叫唤了起来,让他扭过头看起了那精心伪造过的“夜景”。
这时锅里的葡萄酒正在慢慢熬煮,壬亥打开了另一个电力灶,开始弄起之前处理的另一些肉。那些不规则的肉块被他切成了姣好的形状,锅里抹了一层油,他将他们一块块地放上去。爆发出的香味就像是混合着黑胡椒的香甜气味——还带了点隐隐约约的辣味。
壬亥将他们挨个翻面,等候煎制的过程中,将恰好收汁的肉排盛出,又把刚好煎完的肉块们装盘。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强迫症。
沈京没吱声,他怕接下来还有什么更加令人吃惊的事。
还真有。刚刚把这些肉放下,沈京没注意到的烤箱就发出了清脆的报时声。
“你还烤了什么东西……”
“面包,我想你应该喜欢吃。”
包着手套的壬亥看起来很滑稽,沈京盯着他打算把这场面记下来,以后好打趣他。壬亥将面包们装进大小刚好的瓷盘里,那上面像是刚刚淋上去了一层果酱,应该是酸甜口味的。
——等等,瓷盘?
已经打算不问的沈京还是没沉住气。
“这东西又是哪来的?!”
壬亥转身去冰箱里取了冰好的土豆沙拉和饮料,转身回答。
“找人租借的。”
沈京都没心情看着那些散发诱人食欲的菜品,望着眼前的洛·什么都能找到·仔,对这个人的印象彻底改观。他刚来时帮着各种部门干活有人缘是不假,可人缘好成这样也真是令人惊叹。
就连沈京都觉得自己刚刚的笑容有些凝固。
好在现在壬亥端出来的杯子只是常用材料制成的,只是做成了高脚杯的形状。他往里面倒上了混合着各种水果香气的液体。
“研发组新研制的果汁,还没有量产,但是已经确保没有问题了,可以放心食用。”
没有提他又是怎么将这个拿到手的,他为沈京和自己摆上餐具,甚至考虑到沈京那个性格,除了刀叉就连勺子筷子也一并为他准备了。
壬亥这才坐上椅子,刚刚熄灭了厨房的灯,他悄悄打开了桌上和头上微弱的灯光。
一切都变得朦胧,让沈京有些不真切的错觉。他想到很久之前最不想去的餐厅,吃饭的仪式感让他感到沉闷,甚至菜品的总和不能让他吃饱,只是家里会客时会偶尔去的一家店,让他居然有这么深刻的印象。
他只记得那些餐包挺美味的。
顺手拾起餐盘里的一个小面包,一口咬下去,是有些粗糙的松软口感,还有些烫。那些果酱成了最好的调剂,成功弥补了材料的不足。
壬亥有些专注地切着肉排,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沈京毫不怀疑要是没有末日,壬亥绝对可以拿这模样假装贵族,而且肯定有人上当——前提是壬亥真的想。举手投足都一股子斯文的气质,甚至有些优雅。
“你的肉排不给我吃啊?”
嘴里还嚼着面包的沈京看到壬亥吃着那块最好的肉,心里还是有些惦记。
“我想着你估计吃过了,应该吃不下这么大一块。”
壬亥放下叉子,伸手抹了一下沈京的嘴角,没有拿纸巾擦去,只是放到嘴边轻轻一舔。
“这次味道比上次好一些,应该合你的口味?”
——说好的强迫症呢?
那动作怎么看都像是为了掩饰不自在——沈京立马又抓了一个小面包塞嘴里。是另一个果酱口味的。
还没等他品尝完这个小惊喜,就被壬亥出声打断。
“等等。”
壬亥又抄起刀叉,稳稳地切了一块大小适中的肉块,伸手喂到了沈京的嘴边。
沈京也反应快,十分配合地张了嘴一口咬下去。
火候正好,肉的多汁得到了保留,虽然肉质做不到入口即化,但在辅料的配合下也差不多了。
“哇塞。”
沈京趁着味道还没消散又塞了一口面包。
“你手艺这么好啊?”
看着沈京把嘴塞得鼓鼓囊囊吃得开心的样子,壬亥难得地也摆出了微笑。那笑容很自然,不像是为了迎合沈京摆出来的。
沈京还很少看见壬亥笑——这父子俩都这样。沈京又想起了某件事,登时吃饭的好心情消下去了一点。
“想起什么了?”
笑起来的壬亥比平常好看了十倍,沈京心想。他继续咬住壬亥第二次送来的肉块——是另一个风味的,甜辣黑胡椒。
为了防止油汁低落的另一只手上貌似接住了一些汁水,壬亥本想抽纸擦掉,沈京手快抓住那好看的手掌,把那些汁水舔干净了。
“可不能浪费了。”
沈京笑着看着壬亥,发现那张脸的笑容又笑开了些。
“就这么高兴?”
“……嗯。”
隔了一会儿才恢复了淡淡的笑容,沈京还颇有些失望,壬亥这才开口回答。
接着他们默默消灭了桌上的所有东西,连果汁都没放过,说着一些“说什么都不能放过了研发组那些混蛋”之类的话,在壬亥有些调笑意味的眼神里沈京吃撑了。
看来今天是不用吃晚饭了。打了个嗝,沈京决定不去浪费粮食了。
全程给沈京喂菜的壬亥倒是心情超好,收拾了餐具,将桌面收拾整齐,把沈京送出了门。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我还得洗碗刷锅,处理一下后续。”
看着壬亥的笑脸,沈京又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想说?”
“嗯。”
可是壬亥没有继续说下去。沈京感觉自己等了很久,结果只是壬亥蜻蜓点水般落下一吻。
“谢谢你陪我过生日。”
“……”
刚刚还想假惺惺发一下火的沈京这下愣了。他还真的没想到这茬。末日里感觉也没几个人想过生日,但壬亥应该是不一样的。沈京想了想他和他爸的关系,或许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内情在。
“那祝你生日快乐,不过我不会给你礼物啊。”
厚着脸皮说出这句话,没想到被接下来的话噎住了。
“你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壬亥凑近沈京耳语,还趁机蹭了一下沈京的侧脸,弄得他自己的头发都有些凌乱。
“回见。”
壬亥闭着眼,眼角的弧度好看得让人着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