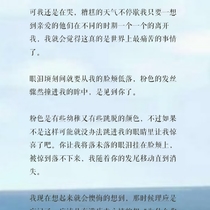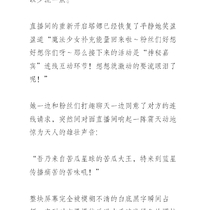小柳介一成轻轻带上门,低头看了眼手中的任务卡。卡片设计得很精致,边缘印着节目组的logo,内容是关于一次杂志拍摄的机会,末尾还特意标注了“有机会竞争封面”的字样。他嘴角微微上扬,这确实是个不错的资源。
他穿过走廊,来到伊拉娜的房间门前,敲了两下。
“请进。”里面传来平静的回应。
他推开门。伊拉娜的房间以蓝白为主色调,收拾得异常整洁,几乎看不到多余的杂物。她正背对着门,坐在靠窗的书桌前,专注地写着什么。窗外午后的光线柔和地洒进来,落在她的笔尖和摊开的笔记本上。
小柳介一成放轻脚步走到她身后,原本想直接说明来意,却先被笔记本上的内容吸引了目光。那上面并不是他预想中的作业或行程笔记,而是一页页密密麻麻的知识点整理和自测题目。
“诶?”他有些意外,“最近学校功课很紧吗?娜娜酱怎么在额外做题?”
伊拉娜闻声抬起头,转过脸来笑了笑:“不是学校的作业,是我自己整理的。感觉最近课外练习做得少了,有点不安,所以抽空补一补。”
小柳介一成点点头,这才想起正事,将任务卡递到她面前:“节目组发布新的任务喽~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机会呢,娜娜酱。”
伊拉娜接过卡片,仔细阅读起来。她的目光在字句间移动,表情逐渐明亮起来:“杂志拍摄……还能竞争封面?这资源真好。”
“娜娜酱对于这个很感兴趣吗?”小柳介一成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期待。
“当然,”伊拉娜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尽力争取的。”
小柳介一成顿时精神焕发,握紧拳头做了个加油的手势:“好!我会全力协助我们最最最可爱的娜娜酱的!”
伊拉娜被他高涨的情绪逗笑了,但随即注意到任务卡底部的一行小字:“等等,这个‘或许贿赂一下’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有点...”
小柳介一成接过卡片重新审视,眯着眼睛读了一遍:“应该是节目组在玩梗吧,制造一点综艺效果。”
“我也觉得,”伊拉娜点头,“感觉像是个故意设置的陷阱,让我们过度解读。”
两人相视一笑,心照不宣地决定忽略这个模棱两可的提示。
“那么,首先得决定拍摄穿什么。”小柳介一成说着,走到伊拉娜的衣柜前,“我来帮娜娜酱搭配吧~”
伊拉娜的衣帽间虽然不算小,但里面的衣服大多偏日常休闲,适合杂志拍摄的服装并不多。小柳介一成仔细翻看每一件衣服,不时拿出一两件在伊拉娜身前比划,然后又摇摇头放回去。
“这件颜色不错,但款式太简单了...”他自言自语道,又抽出另一件,“这件设计感很强,但可能不太适合拍摄主题...”
伊拉娜配合地换了几套衣服,站在镜子前和小柳介一成一起评估效果。
第一套是休闲西装搭配短裙,干练有余却缺乏亮点:“好像太正式了,不够灵动。”伊拉娜评价道。
第二套是蕾丝上衣配长裙,优雅但略显成熟:“这个风格把我显得年纪太大了。”她对着镜子皱眉。
第三套是青春风格的连衣裙,活泼可爱却不够大气:“这个适合日常,但上封面可能压不住场。”小柳介一成摸着下巴分析道。
尝试了十多套搭配后,两人都有些沮丧。无论是风格、颜色还是款式,总是差那么一点感觉。
小柳介一成看了眼时间,突然拍手道:“不如我们把拍摄约到明天吧?今天下午就去买新衣服!”
伊拉娜有些犹豫:“临时去买能找到合适的吗?而且节目组的预算...”
“没关系,这次机会难得,值得投资。”小柳介一成已经拿起外套和钱包,“走吧,我知道几家很不错的设计师店。”
半小时后,他们来到了市中心的一家精品商场。小柳介一成显然对这里很熟悉,径直带着伊拉娜走向几家他常光顾的店铺。
第一家店主打前卫设计,衣服款式大胆创新。伊拉娜试了一件解构主义的连衣裙,镜中的她看起来时尚却有些陌生。
“这个...不太像我。”她犹豫地说。
小柳介一成点头:“确实,风格太强烈了,可能会抢走你本身的气质。”
第二家店偏向职业装,剪裁利落,面料高级。伊拉娜试了一套裤装,干练有余却少了些少女感。
“像是要去参加商务会议。”她评价道,小柳介一成忍不住笑出声。
走了几家店后,两人都有些疲惫,坐在商场休息区的沙发上稍作休息。
“是不是我太挑剔了?”伊拉娜有些自责地问。
小柳介一成摇摇头:“不是娜娜酱的问题哦。娜娜酱只是很认真负责而已。”他伸手轻轻揉了揉人的发顶,“找到既符合拍摄需求又能凸显你个人特色的衣服确实不容易。我们再看看,不要着急。”
休息片刻后,他们继续寻找。在商场转角处一家不太起眼的店里,伊拉娜的目光被一条挂在中岛的连衣裙吸引。那是一条简约的奶白色连衣裙,设计简洁大方,面料有着微妙的光泽,腰部的剪裁尤其精致。
“试试这件?”小柳介一成注意到她的目光,建议道。
伊拉娜取下裙子走进试衣间。当她再次走出来时,小柳介一成的眼睛明显亮了起来。
这条裙子完美地贴合她的身形,既不过于成熟也不显得幼稚。奶白色衬托出她的肤色,简洁的设计凸显了她干净的气质,同时腰线的处理又增添了一丝优雅。
“就是这件了!”小柳介一成赞叹道,“既显气质又不会过于隆重,正好适合杂志拍摄。”
伊拉娜在镜前转了一圈,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真的很舒服,行动也方便。”
决定购买这条裙子后,小柳介一成的购物热情似乎被彻底点燃了。他拿着裙子去结账,然后又拉着伊拉娜继续逛了起来。
“你看这件针织开衫,颜色很衬你!”
“这条半身裙的剪裁很棒,以后上节目可以穿。”
“这双鞋子的设计很特别,搭配刚才那条裤子一定好看。”
小柳介一成仿佛变成了个人造型师,不断为伊拉娜挑选各种服饰。每拿起一件,他都能说出适合的理由和搭配的建议。
伊拉娜起初还试图理性消费,但很快就被小柳介一成的热情感染,也开始享受起购物的乐趣。他们一件件地挑选、试穿、讨论,不知不觉中已经买了许多衣服。
“小柳先生,真的买太多了。”伊拉娜看着手中越来越多的购物袋,有些过意不去。
小柳介一成却毫不在意:“这些都是投资啊!娜娜酱现在正是需要多样化形象的时候。再说了,”他笑着补充道,“每件衣服穿在娜娜酱身上都很好看,我觉得什么都适合娜娜酱。”
这句话让伊拉娜的脸微微发红,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当他们终于结束购物时,夕阳已经西下。两人手中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走出商场大门。
回程的路上,小柳介一成兴致勃勃地讨论着明天的拍摄计划:“明天一早就让化妆师过来,我们可以提前试妆。发型的话,我觉得简约的低马尾会很适合那条裙子...”
伊拉娜听着他的规划,心里充满了安全感。有这样一位既专业又关心自己的保育员是她的幸运。
回到住处后,他们立即开始整理新买的衣服。小柳介一成坚持要帮伊拉娜把每件衣服都妥善挂好,甚至还规划起了第二天的搭配方案。
“这条裙子配那双新买的鞋子,再加上一个小小的项链,就完美了。”他一边挂着衣服一边说。
伊拉娜看着他忙碌的背影,轻声说:“小柳先生,今天真的很谢谢你。不只是因为买了这么多衣服,更是因为你总是这么为我着想。”
小柳介一成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这是我的工作啊,而且看到娜娜酱成功,我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哦。”
他拿起那条奶白色的连衣裙,仔细地挂进衣柜最显眼的位置:“明天,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最棒的娜娜酱。”
伊拉娜坚定地点点头,对明天的拍摄充满了期待。有了合适的服装和小柳先生的支持,她相信自己一定能拿出最好的表现。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但房间里的两人却因为明天的挑战而精神焕发。他们继续讨论着拍摄的细节,为即将到来的重要工作做最后的准备。
(2867字)
清晨五点半,伊拉娜是被窗缝里渗进来的风轻轻吹醒的。
她眨了眨眼,屋里还暗着,窗帘没拉严的地方漏进片青灰色的光,斜斜落在地板上,像谁不小心泼了碗冷水。她侧头看向窗外,西天还挂着几颗星星,细得像缝衣服掉的银线,要凑很近才能看见。
这时候醒实在少见。她最近总熬夜——要么是直播到后半夜,要么是连夜完成任务,早上全靠小柳介一成的闹铃催,有时闹铃都不管用,得等他打电话来,在那头用不成调的歌声把她吵得受不了,她才磨磨蹭蹭爬起来。
大概是昨晚真歇得早。前晚直播到一点,昨天节目组临时调了日程,下午五点就收工了,她回了住处倒头就睡,一觉睡了快十个小时。这会儿醒了,倒不觉得困,脑袋里清清爽爽的,像刚喝了杯凉白开,连平时熬夜后发沉的太阳穴都松快了。
她轻手轻脚坐起来,套上放在床头的运动服——是小柳介一成上次陪她买的,浅灰的,料子软乎乎的吸汗。头发随便抓抓,扎成高马尾,皮筋勒在后颈,有点痒,她抬手拨了拨,踮脚走到门口。
刚要去玄关换鞋,厨房那边传来“滋啦”一声,是油锅响。
伊拉娜愣了下,推开门走过去。厨房门虚掩着,她轻轻推开条缝,看见小柳介一成背对着她站在灶台前,系着条粉乎乎的围裙,围裙上印着个举着魔法棒的卡通女孩——是她某次直播时粉丝送的周边,当时小柳见了直笑,说“哎呀~这是娜娜酱的魔法少女同款吗,我得穿上沾沾元气”,现在倒真常系着。
“小柳先生?”她轻轻敲了敲门框。
小柳介一成猛地回头,手里还握着锅铲,看见她眼睛亮了:“哟,娜娜酱醒啦?早安早安!”他把锅铲往旁边的盘子上一放,转身从橱柜里拿保温杯,“我还琢磨着,今天要不要晚点叫娜娜酱呢,没想到你自己起了,娜娜酱果然超级棒啊!”
他边说边往杯子里丢了两片柠檬,又挖了勺蜂蜜,冲了热水,搅了搅递过来:“娜娜酱这是要去晨跑?那把这个带上吧!不要跑的太累哦”
伊拉娜接过来,杯子温温的,柠檬的清香混着蜂蜜味飘过来,她抿了口,点点头:“嗯,去跑会儿。”
“快去吧,”小柳介一成抬手揉了揉她的头发,指尖蹭过她的马尾辫,“我会给娜娜酱准备好早餐的!煎太阳蛋,再烤两片培根,保证娜娜酱回来就吃上热乎的,怎么样?”
伊拉娜笑了笑:“那我尽快回来。”
换了鞋推开门,晨风呼地吹过来,带着点凉,还混着楼下草地的湿味——大概是晚上下过小雨,草叶上沾着露水珠。这会儿小道没人,只有几只早起的鸟儿在枝头试探地鸣叫,偶尔有辆自行车碾过路面,“叮铃”一声,又远了。
她沿着常走的那条路跑,脚踩在柏油路上,“嗒、嗒”响,在这安静里听得格外清楚。平时总被镜头围着,要么是练习时教练盯着,要么是直播时要想着说什么,难得有这样的时候——不用管表情好不好看,不用算着时间,就只是跑,听自己的呼吸,看路边的树影慢慢晃。
跑了大概四十分钟,手表震动了下,是平时结束的时间,但她没停,反倒加快了点步子。心里有点急,想赶紧回去吃小柳先生做的早餐——他煎的太阳蛋总煎得刚好,蛋白边有点焦脆,蛋黄是流心的,拌着吐司吃,香得很。
到了楼下,她放慢脚步走回去,掏钥匙开门时,就闻见屋里飘着培根的香味。
“我回来了。”她换了鞋,把保温杯放在鞋柜上,解了马尾辫,头发有点潮,贴在脖子上,有点痒。
厨房门“吱呀”开了,小柳介一成探出头,脸上还沾了点面粉:“欢迎回家~娜娜酱快洗手,早餐马上好!”
“我先冲个澡。”伊拉娜往卧室走,刚走两步又回头,“小柳先生,你脸上沾东西了。”
小柳介一成摸了摸脸,没擦掉,反倒蹭得更匀了,他嘿嘿笑:“没事,做完再洗。”
热水冲在身上,把晨跑的薄汗都冲掉了,舒服多了。她换了件棉T恤和宽松的裤子,拿毛巾擦着头发走到餐厅,桌上已经摆好了——盘子里躺着个圆滚滚的太阳蛋,旁边是两片培根,煎得金晃晃的,还有片烤得脆生生的吐司,旁边放着杯温牛奶,冒着点白气。
“看着就好吃。”伊拉娜坐下,拿起叉子,刚要戳开太阳蛋,小柳介一成端着碗沙拉走过来,看见她头发还湿着,皱了皱眉。
“娜娜酱!头发不吹干可是很容易着凉的。”他放下沙拉,转身去拿吹风机,“快坐好,我给你吹一下。”
伊拉娜想站起来:“我自己来就行——”
“坐着吧坐着吧,能为娜娜酱服务可是我的荣幸。”小柳介一成把她按回椅子上,插上吹风机,调了温风,“你吃你的,我给你吹,还不耽误时间呢。”
他解开毛巾,手指轻轻梳开她打结的头发,温风呼啦啦吹着,头皮暖洋洋的。他手很轻,梳到打结的地方会慢慢扯,一点都不疼。
“对了,”他提高声音盖过吹风机的响,“娜娜酱洗澡时节目组来人了,送了个东西。”
伊拉娜愣了下:“节目组?今天不是下午才直播吗?”
“说是临时加的小任务。”小柳介一成腾出一只手,从桌上拿了张卡片递给她,“你看看。”
卡片封面印着节目LOGO,内页是制作人手写的任务说明,字迹清晰有力:
【致天鸽小姐 & 小柳先生】
早安!临时插播一个轻松愉快的合作任务! 本次任务赞助商是备受好评的XX运动相机!该产品以其卓越的防护性能、超高清的4K画质、惊人的240帧慢动作捕捉能力以及极速Wi-Fi传片功能而闻名!无论是日常记录、运动挑战还是高难度动作拍摄,它都是您可靠的伙伴!
【任务要求】 请二位自由发挥创意,拍摄一段不少于3分钟的短视频,充分展示运动相机的上述优点,并于今日下午3点前上传至指定平台。祝拍摄愉快!
——《闪耀希望101》节目组
“运动相机啊……”伊拉娜看着卡片,“下午三点前就得交?”
“时间够呢。”小柳介一成关了吹风机,拿梳子把她头发梳顺,“娜娜酱的头发超级软的诶!吹完娜娜酱就变得更完美了!”他没忍住揉了一把“好了好了,娜娜酱快吃吧,边吃边想怎么拍。”
伊拉娜戳开太阳蛋,流心的蛋黄淌出来,她拌了口吐司,满足地眯眼:“那先吃,吃完再说。”
小柳介一成坐在对面,托着下巴看她吃:“怎么样?我今天特意多放了点黄油煎的哦。”
“好吃。”伊拉娜点头,又叉了块培根,“小柳先生你不吃吗?”
“我早吃过了哦,在给娜娜酱煎蛋前就啃了个面包。”他指了指厨房,“那相机在桌上呢,等娜娜酱吃完咱们看看吧。”
吃完早餐,伊拉娜要收拾盘子,小柳介一成抢着拿去洗:“娜娜酱去看相机吧!我来就行!”
她走到客厅,桌上放着个黑色的小盒子,打开来,里面是个巴掌大的相机,沉甸甸的,摸着手感很扎实。小柳介一成洗完碗出来,擦着手凑过来:“这相机我听说过,挺好用的,防水防抖,拍出来还清楚。”
“任务说要展示它的优点。”伊拉娜拿起相机翻来覆去看,“得拍三分钟以上。”
“那得动起来拍才好看。”小柳介一成拿过相机,研究着怎么开机,“娜娜酱早上不是晨跑了吗?要不就拍晨练相关的?刚好贴合运动相机。”
伊拉娜点头:“可以。开头你用手机拍我假装刚晨跑回来,看到这相机,然后拿起来试,后面就用这相机自己拍?”
“这个好!”小柳介一成眼睛一亮,“然后娜娜酱带着它跑几步,跳几下,试试防抖;再滴点水上去,试试防水;拍个落叶什么的,试试慢动作——最后再传视频,展示传得快,就齐活了!”
说干就干。小柳介一成拿手机站在门口,伊拉娜假装刚跑回来,擦着不存在的汗,走到桌边拿起相机:“这是什么?”
“娜娜酱自然点,再好奇点。”小柳介一成举着手机,“再来一条——对,就这样,拿起来翻看看。”
拍了两条就过了,接着换用运动相机拍。伊拉娜把相机扣在胸前的支架上,在客厅里小跑,小柳介一成跟在旁边看手机上的实时画面:“真稳!一点都不晃!”
她又走到阳台,拿起喷壶往相机上喷了点水,镜头上挂着水珠,画面还是清楚的,小柳凑过来看,啧啧称奇:“这防水可以啊。”
最后试慢动作,她在院子里捡了片银杏叶,往上抛,相机对着拍,回放的时候,叶子慢悠悠往下落,连叶脉上沾的小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
“真厉害。”伊拉娜看着回放,有点惊讶。
“最关键的来了!”小柳介一成打开手机APP,连了相机的Wi-Fi,“试试传视频快不快。”
刚点了传输,手机上就跳出进度条,没几秒就满了——刚才拍的几段高清视频全传过来了。
“这么快?”伊拉娜拿起手机翻,“比我之前用的相机快多了。”
“看来这相机真的很不错啊”小柳介一成晃了晃手中的相机,“娜娜酱快来,咱们剪一下,把最清楚的镜头拼起来。”
两人挤在沙发上,小柳介一成拿着手机剪,伊拉娜在旁边看:“把抛叶子那段放慢点……传视频的时候拍个屏幕,这样能看见有多快……”
小柳介一成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没一会儿就剪好了——开头是手机拍的伊拉娜拿相机,中间是运动相机拍的跑跳、防水、慢动作画面,最后是两人凑在一起看手机传视频,结尾伊拉娜举着相机笑:“用XX运动相机,记录每一个精彩瞬间。”
“好啦!”小柳介一成把视频保存好,“我这就上传。”
看着上传成功的提示,伊拉娜松了口气,活动了下脖子:“比想象中顺利。”
“毕竟有娜娜在嘛。”小柳介一成收起手机,拍了拍手,“娜娜酱中午有什么想吃的吗?庆祝任务完成,我可以给娜娜酱做一顿大餐!”
伊拉娜想了想,窗外的太阳照进来,亮堂堂的:“早上吃了油腻的,中午清淡点吧,日式定食怎么样?”
“ok!保证完成任务!”小柳介一成站起来往厨房走,“我做鲑鱼茶泡饭,再弄个豆腐沙拉,清爽!”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对了,这相机挺好用的,娜娜酱下午要是没事的话,要不要拿着出去拍拍?刚才试慢动作,拍落叶挺好看的,附近公园的枫叶好像红了,要去吗?”
伊拉娜看着桌上的相机,点了点头:“好啊。”
中午的鲑鱼茶泡饭做得真香,鲑鱼烤得焦香,拌着热米饭和茶,一口下去暖乎乎的。吃完歇了会儿,两人拿着相机往公园走。
公园里人不多,有几个老人在散步。靠近湖边有几棵枫树,叶子刚红了一半,绿中带红,风一吹,沙沙响。
“从下往上拍试试。”小柳介一成找了个三脚架架好相机,“仰着拍,叶子落下来的时候,背景是蓝天,肯定好看。”
伊拉娜把相机调好,固定在三脚架上,对着枫树等风。风来了,几片红叶悠悠往下飘,相机“咔嚓咔嚓”拍着,她凑到手机旁边看,画面里红叶转着圈落下来,连风拂过叶子边缘的弧度都拍得清清楚楚。
“真清楚。”她回头喊小柳介一成,“小柳先生,你快来看。”
小柳介一成跑过来,刚站定,脚边有只小麻雀蹦蹦跳跳,他赶紧指给伊拉娜看:“娜娜酱拍它!拍它飞起来的样子!”
伊拉娜调了慢动作,对着小麻雀,等它扑棱棱飞起来,相机跟着拍,回放时,小麻雀的翅膀扇得慢悠悠的,连羽毛的纹路都看得清。
两人在公园里拍了一下午,拍了露珠从草叶上滚下来,拍了蜻蜓停在荷花上,还拍了湖边的芦苇在风里摇。太阳快落山时,才收拾东西往回走。
“今天拍了好多。”伊拉娜翻着相机里的素材,笑着说,“比任务要求的多太多了。”
“多拍点也好,”小柳介一成帮她拿三脚架,“回头剪个短片,就当记录我和娜娜酱的生活了。”
回到家,两人又凑在一起剪视频,把下午拍的好看镜头拼起来,配了首轻快的钢琴曲。剪完时天已经黑了,小柳去厨房做饭,伊拉娜坐在沙发上看成片——画面里红叶飘,麻雀飞,芦苇摇,安安静静的,看着心里就舒服。
“吃饭啦!”小柳介一成端着菜出来,今晚做了寿喜烧,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香味飘满了屋子。
“还点了蜡烛?”伊拉娜看见桌上放着支小蜡烛,亮着暖黄的光。
“庆祝嘛。”小柳挠挠头,“任务完成,还拍了这么多好看的照片,不得庆祝下嘛。”
两人围着桌子吃饭,寿喜烧的牛肉嫩得很,沾着蛋液吃,鲜得很。小柳边吃边说:“下次有机会,拿着这相机去海边拍,拍海浪肯定好看,防水功能正好用上。”
“好啊。”伊拉娜夹了块豆腐,“下次直播如果去户外,也带着它。”
吃完饭,伊拉娜去洗碗,小柳介一成在旁边帮忙擦桌子,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说下次拍什么,说下周的直播内容,屋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水流声和说话声。
临睡前,伊拉娜坐在床边看相机里的照片,翻着翻着,看见张她没拍过的——是她下午蹲在地上看相机屏幕的样子,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嘴角还带着笑,背景是红通通的枫叶。
她回头看了眼隔壁房间,小柳大概已经睡了。她拿起相机,对着窗外的月亮拍了张,月光洒在地上,像铺了层霜。
“今天真开心。”她轻声说,把相机放在床头,躺下盖了被子。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着院子里的树影,轻轻晃着。伊拉娜闭上眼,想起下午拍的红叶,想起小柳介一成帮她吹头发时暖暖的风,嘴角弯了弯。
明天大概又是忙的一天,但今天这些事,记在心里,挺好的。她想着,慢慢睡着了。
(4799字)
“——地地地地狱直通车,鬼怪的追逐者,你们这群怪胎的领路人!频率扭到FM■■.■,准备好了吗,乘上怪电波——”
洲际高速路的这一段恰好能捕捉到被称作“地狱频段”的电台频道,模糊带噪声的夸张声音传来,伴着重金属乐的劲爆低音,轰得整辆车都在发抖。安德烈笑到拧了好几次旋钮才成功把音量调低,让自己不至于必须扯着嗓子说话:“哎哟……我还不知道那个在图书馆一坐一天的学术痴喜欢听这种地下电台,路维特?”
坐在副驾的红发青年吃了安德烈略带揶揄的一肘,有些不太好意思地笑一声,为自己辩解:“是小菲之前爱听,我才跟着听一点,不完全算我的爱好。”
“我看你也挺喜欢嘛,别老拿妹妹当挡箭牌,是吧菲利西亚?”如是打趣着,安德烈透过后视镜望了望后排,“菲利西亚?”
后排座上被称作菲利西亚的女孩皱着眉撑头看向窗外,一脸厌烦地,晾了他们数秒才开口:“你们打乱了我的思考。”
“你刚刚在这么炸耳的摇滚乐里思考?”
“那是朋克金属。好好开你的车去吧安德烈。”她换了一边腿跷着。安德烈低低地懊恼一声,目光移回一成不变的柏油路上;但路维特的关切从不以妹妹的厌烦为转移,他朝后排回头,试图看懂菲利西亚那被撑着下巴的手挡住的表情:“是什么让你如此苦恼?父亲说过我们不用为将来发愁,虽然从前积累的那些灰黑产全都处理掉还需要些时间,但现在你已经毕业,随时可以接管他合法产业中任何你喜欢的部分。帮派的过往不会成为你、我们未来的绊脚石。”
“绊脚石?”饱含不满的嘁声,“他把那些放在那儿就会继续生钱的东西当绊脚石?老头不过是想在死之前洗脱他的罪孽,好干干净净上天堂而已。”
“但这让我们也不必背负他犯下的错。你看,继续留在美国,你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
安德烈意识到空气有些凝固、想说些什么玩笑活跃气氛时已晚了,他再次看向后视镜,从中望见菲利西亚十分认真的表情,锐利的眼神扫过他、钉在路维特身上。风自半开的车窗里呼啸进来,扬起她火焰般飞扬的红色短发,风声丝毫盖不住她的声音一分。
“我要做的就是拿走他妄图抛弃的那部分。”菲利西亚语调冷冷,“你从未认真了解过我的任何一个想法,除了车载电台听什么,不是吗,路维特?我会回去,回墨西哥。”
//Chapter3. 赠礼//
阅览注意:正文约9k字。很大篇幅用于角色个人线补完,主线纯享版请拉到最后。加入了瓦尔基里死后灵装会逐渐失去力量的私设以及各种各样奇怪的特性,如果不方便的话,请当做是仅这一件灵装独有的吧!
登场角色:
老奥利瓦雷兹——他的愿望是建立他的黑色帝国、拥有像他的钞票一样多的子孙,达成前两个愿望后,他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赎完他的罪进入天堂。
希拉——她的愿望是所有自己受过的苦都不能白受,达成这一个愿望后,她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当一个无忧无虑的母亲。
路维特——他的愿望是让罪恶和仇恨的链条断在这里,为达成这个愿望,他会付出自己。
菲利西亚——她的愿望是向折磨她与母亲的那人复仇,达成这一愿望的途中,她的执念混沌地传递下去。
安德烈——他的愿望是朋友们头上的阴霾能够退散,或者,新生者可以得到新生。
悬铃木——她的愿望是找到究竟什么是自己。
这辆车扬起尘土,在高速路上驶远。
现在,若我们沿着它前进的方向拨动时针,你会看到他们的未来。你能看到火红短发的少女头也不回地离开美国、回到她生父在墨西哥创立的帮派;能看到她如何苦于自己势力之弱小,进而想到需要一位瓦尔基里作她的人形兵器;一直到安德烈驾驶的小型飞机如何被狩骨击落,菲利西亚如何手持兄长授权予她的灵装,赐福一般佩在他颈上。之后时光飞逝,直到一位忘却了前世的瓦尔基里握着那枚倒挂的十字、握着不知何处来的复仇执念从黄沙中站起。
倘若我们往它来的方向倒转回去,我们将得以来到这一切的开头。这一年墨西哥北部有一个帮派如日中天,它的首领姓奥利瓦雷兹;这一年得到奥利瓦雷兹先生资助的众多贫民与孤儿中,最小的那个名叫安德烈;这一年奥利瓦雷兹的第二任妻子给她生下的孩子取名菲利西亚,发誓会让这孩子成为刺向这位踩着她发迹的丈夫的尖刀。
十八年后,年事已高的奥利瓦雷兹忽然梦见了天主,醒来后他痛哭流涕,誓要抛弃那些非法行当、只留他投资的合法企业,送他的两个孩子和一众年轻人赴美继续学业或工作,帮派合法化后解散似乎已成定局。四年后,他死于妻子注进他静脉的毒。三个月后,菲利西亚接过他的位置、重操他的旧业。两年后的亡灵节,沙漠边陲的小镇走进一位新生的瓦尔基里。
等在停车场的医生抬起腕表看了又看,先前帮助他的两位瓦尔基里一个也没有来,荆骨还在继续蔓延,积雨云也开始在天边堆积,他不能带着伤员再等下去了。轿车惊险地绕过两个弯避开新的裂隙转上主路,原来待的地方很快被漆黑的尖刺挤满,医生从未如此期待这辆平日时速不超40码的老家伙快一点、再快一点。好在他熟悉出城的道路,一路直行就能最快离开这个地方。两边高楼夹着道路,狩骨在其中咆哮、荆骨自窗口迸出,他丝毫不敢减速,油门踩到底,扬起的烟尘几乎叫他看不清道路。
就在这时,伴着哐当一声与剧烈的震动,有什么跳上了他的车顶。男人几乎要害怕得呼出声,接着看见一条他曾见过的灵装甩开,镀红带刺的铁鞭破空而出,立刻有几只狩骨破碎的躯体掉下来、顺着前引擎盖滑下去。收回铁荆棘时瓦尔基里跳下来,单手拽着车顶行李架把自己挂在驾驶位一侧,半边躯体硬化,替他挡下高处建筑崩落的碎玻璃。
“换条路走!”悬铃木在一片嘈杂中冲他喊着,“前面有狩骨——换条路走!”
汽车转过一个匪夷所思的急弯,跳下主道,沿另一条原本被荆骨封锁的小路奔出去。铁荆棘不断甩出,缠卷在荆骨之上,将它们击碎或连根拔起。就像热尼亚指导她做过的那样,灼热的铁刺深深扎进根部,荆骨发出惨叫一样的滋滋声,很快灰白地萎缩下去。她咬着牙重复开路的工作,呼吸急而重,心跳如重锤咚咚擂在胸口,全速流动的血液滚烫得几欲燃烧。
那柄黄铜十字被攥在手心里,已经失去了能让她冷静下来的凉,取而代之的是要灼伤皮肤的滚烫、抑或刺骨冰寒,此刻她无心区分这两种感受极为相似的疼痛。它微微颤动着,好似正在与什么共鸣。
破开所有拦路的刺,瓦尔基里跳下车,目送人类消失在道路远方,随后她转向另一边,地平线上盘踞着几团黑影,张牙舞爪的轮廓宣告它们狩骨的身份。其中唯有一个纤细的人形显得格格不入,一头火红的短发张扬在空中。
她当然知道那里是什么正在等着。
日光从地平线腾起。一天中最安静的黎明时分,对路维特·奥利瓦雷兹来说依然有几分惊魂未定。这是他——祂经历逾越礼后的第三日,直到今日的朝阳照上皮肤,热度才带来了一些死而复生的实感。
盼了又盼,终于看到菲利西亚张扬的短发远远出现在道路那头,路维特立即冲上去抱住了她。
“小菲,你没事!在这节骨眼上出了这件事,联系不到你们我真担心……啊,抱歉,”祂轻咳两声,展开刚才紧紧拥抱她的胳膊,向她展示这副新生的少女模样身体,“你看。我没想过真的能重新站起来,这太神奇了,但我还是无法对那个教会抱有好感,所想的只有快点回到你们身边来——安德烈呢?他还好吗?”
菲利西亚难得地没有挖苦祂,只是勾起嘴角:“他在操办老头的葬礼。那边真是乱套了,不出所料大家都在等着你回去继承这个首领的位置。边走边说吧。”
二十岁出头的人类女孩带着看起来像与她同龄的瓦尔基里沿公路慢慢前行,后者难掩雀跃地同前者絮叨复生后的感触。路维特的灵装是一把长足半臂的铜质十字架,随祂一挥手又能像蜂群般散开变成几十枚只有拇指长的小型复制品,微微振动着,像在彼此共鸣。
“教会的人协助我测试过,灵装能通过冥想录入一些……指令,接着让它接触狩骨或动物这样没有心智的东西,它们就会听从灵装储存的命令。你看——”
路维特举起其中一枚,凝聚心神,片刻后稍一用力将它插进一旁的树干里,那树一阵簌簌,明明还绿着,竟抖落大片大片的叶子下来。菲利西亚挑起半边眉毛。
“我刚刚让它落下它一半的叶子。对植物也能生效,很神奇吧?它对人和瓦尔基里也有效,但条件很苛刻,他们都说把它当一个自己的护身符或首饰佩着时才被它攥取了心神,要摆脱也很简单,觉得这东西邪门把它丢开、认为它不‘属于’自己时就不受控制了。虽然越多个体合在一起效力就会越大,但似乎还是很容易挣脱,只要有心……研究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唠叨?”
“没有。”走在前面的菲利西亚踢着石子,“我还想知道你是怎么遭人绑到这的。”
“听说父亲走得突然,我本想带些人回来,没想到司机被买通迷晕了我们,醒来就到了教堂。临出发前我让安德烈去拿落下的行李,司机不愿等,现在想来真是幸运,他不在这辆车上。”
“嗯嗯。”她漫不经心地点头,“我原以为会是他带着你们那帮手下赶回来,这么看来真是意外之喜嘛。”
“是啊,要不然——”
本来应着她的话,路维特忽然站住了。轻快的表情冷却下来,与嘴角还未来得及褪去的微笑混合成不可置信,祂感到喉咙有些干涩:“——我们的‘意外之喜’是一个意思吗,小菲?”
菲利西亚感到想笑。她刚刚不合时宜地想到,若这是一部电影,此时应有一团风滚草刚好爬过他们二人之间。既然想笑,她便真的发笑了,转过身对路维特大大地笑着:“大概不是吧?”
就像风滚草真的在她身上滚、挠着她的痒痒那样,菲利西亚几乎要笑出声来。她对祂摊开双手:“我原本想带一位瓦尔基里回去就够了,谁知道这位天选之人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继承了老奥利瓦雷兹先生观念的、他最出色的长子?若是别人通过了逾越礼,我还能劝他做我的辅手;可惜这人是你。路维特,我恨你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样子,如果我没有生在这个家庭,或许还能和你与安德烈成为真正的好友。”
分明是仲夏晴天,路维特却感到浑身发冷。祂听见破空声,一支灵装箭自后向前贯穿左肩。杀手丝毫没有停顿,第二箭让祂咳出血,第三箭将祂的膝盖钉于地上,这具新生的身体即刻又要死去了。最终,祂看见菲利西亚朝那隐藏的杀手点了点头,终于不再有新的箭支飞来。
菲利西亚半跪下来,怜悯地掺住祂摇摇欲坠的身体。然而,她感到瓦尔基里颤抖着的手臂环过来、抚上她的后背,竟给了她一个拥抱。被推开时路维特对她露出笑,将黄铜十字放在她手上:“……我刚才许了一个愿,猜猜是什么?”
“怪人。你要用它让我放弃吗?”
“不,”摇头的动作也显得极为负担,“我对它说,‘帮助菲利西亚,完成她真正的愿望’。它们相互交融,这条指令会传达给每一份构成它的个体。我——咳——为父亲对希拉做过的事、对我的偏爱向你道歉,如果这能成为微薄的补偿——”
“我最讨厌你们自以为为我好的时候。”菲利西亚的表情沉下来,她握住十字架调转半圈,让长端整个没入瓦尔基里的胸腔。
她重新站起来时,手中的大十字架自行分裂成一颗颗小的,无法被再拼合成一体,但依然能正常使用。她感到有些恶心,为她将要使用她刚才还看不起的这份遗赠,但就如她同样要使用老奥利瓦雷兹曾用过的敛财手段那样,她不会因感到恶心就放弃的。
“——这就是你当年错过的部分,解答你的疑问了吗,安德烈?”
三十四岁的菲利西亚·奥利瓦雷兹如此讲述。仿佛想象中的风滚草依然在对峙场面的中间路过,她毫不掩饰地弯着嘴角,身边形貌可怖的狩骨对她低眉顺眼,她正安然坐在其中一只的掌上。离近了方才能看到,她的面容过早显现出衰老痕迹,红发中混着几缕银丝,这些是作为凡人被灵装长久侵蚀的后果,她把它们掩盖得很好。
“我说过了,我有自己的名字。”悬铃木紧握灵装,铁刺扎穿她的掌心,颗颗血珠砸在地上,它们与铁荆棘一般鲜红。菲利西亚轻蔑地摇头:“好吧……好吧。也许是他死了太久,这灵装的力量也在一天天减弱了,才让你的——安德烈的——记忆得以松脱。但你竟然如此恨我吗,明明以前我们还是一同度过成年礼、一同完成学业的好友?”
“我追着那份念头走了这么远,它一定有一个原因,只有你能告诉我。”瓦尔基里的目光紧追着人类,“然后我会杀了你。”
菲利西亚从鼻子里发出一声轻笑,略带失望地俯视着她:“真坚持。那么,你知道大仇得报后是什么感觉吗?”
她们站在一处高地上,得以俯视不远处的城区,红河城那彻夜不眠的霓虹已被裂隙的紫光覆盖,各式花哨繁复的建筑倾倒成一片不分彼此的废墟,荆骨疯长、狩骨横行,“将军”拖着它巨大的身躯,仍执着地向橡林镇行军。你若经历过在赌场里不分昼夜玩到赢,就能尝到这种复仇的快意,机器哗哗吐出的筹码奖券淹没你的双足、迷花你的双眼,那是今宵一死也值得的极乐;但当你仰天大笑过后,目光从灯光炫目的穹顶移回地上,失去目标的空虚感会撑满你的胸腔,这口浊气无论如何也吐不出来。或许你抱着满盆金银回家, 想着要是当时下注再大胆一点会怎样,遗憾地此生再也不碰赌桌。或许你会用它们继续更大的赌局,你用得到的财富钱生钱、利滚利,但再也感受不到快乐;你赢下更多奖励,依然无法开心起来;你甚至开设自己的赌场,铺起一座城或者更多,然而还是找不到满足,总有一个深深的伤痕横亘在肺脏之上填也填不满。
“走私、放贷、倒卖军火,这些已经像过家家一样让我厌烦。我开始思考究竟有什么比钱权更强大,最终发现是更完美的生命形式。瓦尔基里与死棘都还算不上,于是我再次回到这里——发现真是令我惊喜啊,裂隙吐出了比这二者都更进一步的生命。”
菲利西亚张开双臂,她乘坐的狩骨身后是卡里略巨大的影子,尽管已经濒死,那力量仍不容忽视。
“我曾建议安德烈做一个不要有太多问题的副手,然而他不愿接受;我曾祝愿他的来生能够无忧无虑,然而你不愿接受。现在我邀请你放下那些过往和我一起拥抱更强大的未来,若你的答案还是否定,我当然不会做自愿被你杀死的那种人。”
大地在颤动。悬铃木弓起步作备战姿态,像双脚被钉在地上那样纹丝不动地立着,解开铁荆棘:“我拒绝。”
“听……滋滋滋……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能和我共用同一双眼睛就好了!我不知道如何跟你们形…容(哐当)裂隙吞吃暴雨的画面,这场雨来得太——是——时滋滋滋候——啦!是的,如果本频段出现了一些音质(哐当哐当)问题或者——呃!什么杂音,那是因为我们正在接近风暴的中心。莎拉,让我们把麦克风交给随处可见的一位狩骨朋友……(哇嗷嗷嗷!)”
积雨云此时是绀紫,沉沉压在红河一带,城内外一片泥泞,而逃命者、亡命徒们并不会看见,靠近东南出城口的一片高地反常地干燥。铁荆棘抽碎一簇雨幕,雨珠立即被高温蒸发,只留下刺啦一声的白汽;它落到狩骨身上,发出更为难听的滋滋烤焦声,怪物一声惨号,一用力又挣脱开束缚。悬铃木抽回灵装,回身将它末端的铁球掷向身后那一只,击中的闷响与偷袭的破空声同时响起,她立刻借惯性闪身回避,却还是被利爪刻下两道伤。好像已经感觉不到遍身的伤口,它们变成和灼烧感相同的那种浅而大面积的痛觉。仅凭单打独斗几乎不可能突破狩骨的包围圈,然而她还在战斗着。
黄铜十字没有在她的颈上,在手心和铁棘之间握着。她本没打算取下它,与热尼亚和她的朋友们告别后也计划着重返正面战场,一转身却看见熟悉的影子靠在走廊墙边。他或许来自过去某段记忆的碎片,正和不存在的朋友说笑着,窗外的光线透过他投在地板上。她走过去问他,你到底为什么一直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死棘、因为裂隙还是什么?他们大约正在聊瓦尔基里的话题,开玩笑地说不会吧,你知道她们一共才多少人吗,机会怎么会轮到我一个无名小卒头上?她又问,以前发生的事,为什么你们不肯让我知道?他朝走廊那头招手,哎,菲利西亚,这儿!你觉得我们中间出个瓦尔基里的概率有多少?
好吧,悬铃木盯着他的脸,我会自己找她问清楚。
安德烈表情变得有些失落,或许是又被挖苦了两句,他辩解道,我没有想做什么……只是在想多活一辈子虽然挺有意思的,但肯定也蛮累的吧。
我不觉得累。她说,你确实成为瓦尔基里了,你对此到底怎么想?
我啊,我觉得……他思考着,复活也就相当于开启新人生了吧,要是真轮到我,希望她能有新的生活吧——哎、哎你要走了吗?等等我菲利西亚……
他追着好友跑出去,消失在一片舞动在光中的灰尘里。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最后低头摘下十字挂坠,仍然拿在手里,大口呼吸着接受那影子淡去、却在回忆里如潮水般涌来。
“你明明已经知道如何挣脱这件灵装对你记忆的束缚了不是吗?可你还没有丢掉它。”菲利西亚好整以暇地看着她在狩骨群中挣扎,“我知道你很喜欢你的新生活,享受没有过去带给你的安宁感,你想要的只是切断这些不属于新生的你的牵绊。趁早放弃吧,它们不会陪你玩太久,我可以当你从没来过。”
赤红的影子不断闪过,铁鞭有时劈开一道破口朝菲利西亚袭来,又被守卫在她身边的仆从击回。一只狩骨身躯破碎倒下,它体内的黄铜十字掉在地上,立刻有新的一只补上空缺,一群死棘想压垮一位独行的瓦尔基里很容易,即使她杀死它们的速度越来越快,菲利西亚也随时可以将掉落的十字嵌入新一只体内,红河城周围的狩骨无穷无尽,无穷无尽都是她的后备援军。
悬铃木能听到安德烈的声音,提醒她注意身侧身后的危险,混杂着过去的闪回。他在老奥利瓦雷兹灵前整晚守着,等回了菲利西亚却没等回路维特,友情崩塌的声音在他胸腔中闷闷回响,他逃走了,逃兵自然要被处决。她能听到他意识消散前火焰在耳边的噼啪声,他手中握着那枚倒置的十字,心想着要是能早点和菲利西亚聊聊就好了。再过一会儿就能得到安眠,再过一会儿,或许就会有新生的瓦尔基里从这具躯壳里站起来,忘掉过往开启新的人生。
“不,告诉我……”瓦尔基里的声音从包围圈的缝隙中传出,“我要知道……”
灵装缠住一只体型庞大的狩骨,收紧、加温,砰!那怪物在哀嚎中爆燃,很快被暴雨浇灭,只留下一团齑粉与其中的黄铜十字。其余狩骨被震慑住,在它们没有动作的空隙里,她抹去脸上的血迹,直视着菲利西亚,铁荆棘绕在她的双臂上燃烧。
“菲利西亚……告诉我,菲利西亚,”雨从她的颊侧滑落,“为什么……你的恨来自哪里?”
“小宝宝还没听够故事吗?”红发女人发出并无笑意的笑声,“如果在上辈子你们就如此关心我该有多好? 你——安德烈、路维特,还有其他我身边的人,对你们来说奥利瓦雷兹先生是父亲、是救世主,资助你们的家庭,给你们上学和工作的机会;他对我的轻视被描述成宠爱,他们相信路维特会成为他的继承人,甚至相信会是那个据说陪他白手起家的跟他差不多老的二把手,有谁相信我才是更好的领导者?”
她一步步走近,走近她狩骨军团的包围圈中,挥手指挥它们向瓦尔基里施以一击、又一击,肉眼可见她的白发愈来愈多,她死死盯着已近力竭的瓦尔基里:“他所谓的皈依悔改让想报复他的人都成了笑话,连与我最亲密的好友都无法理解,我只能夺取他曾拥有的一切,这让我感到恶心,一天更比一天恶心!我清理他的残党,意识到杀了他们也无法改变他们对他的看法,甚至你们还有转世复活的机会,拥有这种我连靠近都会感到头痛的武器,那么我呢?他才不是白手起家,奥利瓦雷兹是个用着女人的钱和人脉发财的懦夫,我不会忘记希拉每晚每晚都教给我,如果没有他她本应过着怎样好的生活,我本该拥有一个多么幸福的家……”
霹雳一声惊雷从天边响起。悬铃木睁大了眼睛,扛着狩骨的爪击,几乎竭尽全力地想要插话:“等——等等!希拉,希拉·伽萨?她是、她是你母亲?”
“我不记得和你介绍过她。”
“我、我见过她的,”瓦尔基里的声音急切,“她住在…奇瓦瓦,沙漠旁边,她养了一个女儿还有许多猫狗和盆栽……”
“是吗,我该谢谢你告诉我?”菲利西亚挑眉,挥手叫停了狩骨的攻击,”九年还是十年以前,我去清理奇瓦瓦的老麦考伊时该见她一面的。她过得如何?”
悬铃木咳嗽着,越来越多的雨珠从她的脸上落到地上。她花了好一会儿才喘匀呼吸、整理好语言:“她在那里很开心……她死了。”
在内心深处,菲利西亚有时会恨母亲。这个曾出身官员家庭的女人被年轻的奥利瓦雷兹骗走了感情、金钱和人脉,她在第无数次帮他脱罪后,终于发现她不过是他的婚外情妇之一。她趁他妻子病逝时再度接近他,不久后结了婚、生下孩子、帮他管理大小事务,她做了很多来一步步拿回本该属于她的东西——不止于此,她认为自己值得更多。菲利西亚有时会恨她把一部分恨意投射到自己身上、督促自己成为与她一样的复仇者,但更多时候,菲利西亚觉得她们确实值得。
希拉结交的众多关系中有一位认得圣逾会的领袖,她告诉菲利西亚如何联络对方、自己毒杀老奥利瓦雷兹后,她们就再也没有见过。有时菲利西亚会想她或许还在天涯海角逃命、或许已经被逮捕,不管如何,她有时会为远离母亲松口气。菲利西亚想起,二把手麦考伊藏匿的镇上确实有许多流浪动物,她摸了摸它们光洁的皮毛,随后让狩骨们翻遍整个镇子把他找出来。
她愣在原地,五秒后才注意到瓦尔基里向她走来,她本能地想后退、想逃走,但那两只胳膊的力气比她大得多。解开铁荆棘的双臂粗糙而温热,遍布大小伤痕与灼痕,没有扭断她的脖子,而是给了她一个拥抱。暴雨浇湿她们的头发与脸颊,她听到对方未定的喘息像雷鸣般沉重,或许是与灵装共处真的让她的灵魂损耗太多,她的四肢此时都像生了锈,不能再指挥狩骨。
“我想明白为什么我忘掉那些、唯独记得复仇了,”悬铃木的声音混在哗哗雨声中,“复仇的想法从来没有离开你,就算那个人已经死了。你拿着黄铜十字冥想时,它们同样听到你的执念你的欲望。”
“我找到我的路来自哪里了,它来自你,菲利西亚,它来自你。我们走在一样的路上。”
——只想知道自己的心来自哪里。
“滋滋滋滋……莎拉,快醒醒!我们得把这里的……喂,喂!你们听得到吗?我的天,这里根本不是地狱啊!只是……另一面,你们懂吗?现实的翻版,只不过没有人!全都是——”
大地在震动。拥抱的力度不大,菲利西亚挣扎几下便从中挣脱,她向后退着,退到高地的边缘,她知道下方已打开了一条裂隙,紫光照亮她的脸。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她湿透的脸上带着丝毫没有快乐的大笑,“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祝贺你,幸运儿,可我已经在抛弃一切的路上走太久了!你看好吧,我会找到裂隙下面有什么的,我会找到你们这些怪物诞生的秘密,然后我将——”
悬铃木没有拉住她,她向后倒去,落入张着大口的裂隙里,所有声音都在此刻消失。控制着狩骨们的力量彻底消失了,它们循着本能扑向面前的瓦尔基里,一层层地压上来,接着它们中间燃起爆焰,一双燃火的翅膀撕裂包围,十数只怪物瞬间化为飞灰。瓦尔基里如一颗火流星,扫平附近参差的荆骨、点燃游荡的狩骨,直到这片区域的死棘都消灭殆尽。
她回到高地上,熄灭火焰、收敛双翼,望着下方深不见底的裂隙。也许经由自己选择的才是真正的新生。安德烈如影随形的声音在雨声中渐渐淡去,她想,他终于也得到如愿的安息。
她并不感到多畅快,但是,过去最后的影子也消散,它们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而她得以开启他们没能拥有的未来。朝阳挂在地平线上,有一瞬间,它像要落进裂隙里的夕日,不过最后,裂隙逐渐合拢,而太阳又升高一分。
“再见,”她对裂隙喃喃,“再见。”
凌晨五点四十一分,下了一整夜的暴雨逐渐平息,悬铃木将脸埋到手心里掩面而泣,此时,干涸十一年的沙漠才终于得以落下一场雨。她拾起散落在附近的黄铜十字,重新将它们合为一体,闭上眼感受它已变得十分微弱的能量,重塑其中的混杂的意念。它弱到只足以执行最后一份指令、弱到只要想就能挣脱,但她想,它也许还有一件能做到的事情。
橡林镇与红河城的交界如同炼狱,卡里略与希尔维娅的交战摧毁了大部分建筑,将军的身躯数次破碎又再生,灵体心脏闪烁不定,死亡已在前方等候。瓦尔基里们将大部分战力转向对抗希尔维娅,然而始终不敌,即使是部分力量得以重塑的也抵抗得十分艰难。
六点二十七分,卡里略的再生已十分缓慢,庞大的半截身躯仍试图扑向希尔维娅,扑向那把军刀。六点二十八分,一团火流星冲入战场,凭烈焰硬生生挡开希尔维娅即将处决卡里略的一击,在双方反应过来之前,将一枚小臂长的黄铜质地十字架嵌入将军灵体身躯的中心。
在复仇的火烧尽你之前,至少,清醒地与朋友们告个别吧。
排版已编辑,广播内容用斜体呈现。
相关链接:
前篇,关于她如何想起过去:works/9729799
前篇,与热尼亚医生于医院:works/9729792
感谢希弗对电台的详细设计,擅自引用了一些(介意的话请告诉我!):works/9731739
悬铃木的人设已更新:works/9599273(主人设卡)、works/9732389(前世补完)、works/9732688(超越形态)
与主线相关的省流:悬铃木选择了【超越】。在将军濒死之际,她利用黄铜十字(灵装)向将军传达了“指令”,意在让其恢复清醒的神智(不再是只想向希尔维娅复仇)来面对最后一刻。黄铜十字的力量十分微弱,只要将军不愿意,这条指令将失效。无论生效与否,黄铜十字将失去力量,变成普通的铜制品。
【超越】后新增的能力:她可以主动使身上燃起火焰,亦能主动令其熄灭。一般的方法如水、灭火器无法灭火。
黄铜十字原理解析:可以通过冥想往其中注入指令(在文中也称为过愿望/命令),令目标强制听从。当无心智之物(动植物、死棘,灵装也在这个范畴)接触黄铜十字,指令即生效,取消接触则失效;有心智的生物(人类、瓦尔基里等等)在产生“自身持有/佩戴黄铜十字”的念头时则被指令控制,反之则失效,也可以通过强大的意志挣脱。黄铜十字可分散成数十个小个体,每一个都可以单独录入指令,当任何单位合在一起时指令会叠加而非覆盖。
指令不会控制灵装的主人,在这个故事中,“主人”一开始是路维特,接着被他利用指令定义成菲利西亚,在他们二人离开之后,捡到它的悬铃木成为“主人”。
菲利西亚给安德烈的一最小单位黄铜十字中录入的指令是“忘掉此生的一切”,然而在她冥想中混入了她的复仇心(按理说她使用过的所有黄铜十字都会被录进复仇念头,但狩骨没有意识无仇可复,因此对它们它们没有影响)。安德烈在死前接受了它。
(因为在文章结束后黄铜十字就杀青了,所以没有详细设定剧情体现不到的细节,在此为它可能有点扯的设定滑跪,希望没有做很超模的事……)
后记:
感谢你看完这篇文章。我很感慨所以有一大堆free talk要写。
我纠结了很久,纠结的时间甚至大于写作的时间,从本章节一开始就在纠结,在想要不要细说前世的故事,在想我设计得有点扯不知道能不能讲好,在想四种重塑都有点合适又有点不合适。中间一度想过不写了摆了,但是一看她上春晚了,太感动了决定还是写完。
很纠结的时候和朋友讨论了这个角色和前世的故事,她说子世代是相似而延续的,菲利西亚是被塑造的复仇者,悬铃木的复仇执念同样是她的欲念塑造的,她们在这方面很相似;路维特的牺牲像锁链将所有人链接起来,在这之后是安德烈。这位朋友说她感到悬铃木的“复仇”也是更好地理解菲利西亚的过程,我说天哪那我突然明白了,其实她(悬铃木)追求的也不是非得要复仇,她自己执念的本质是想理解过去到底是什么、她自己又是什么,其实是自我探寻。写作时又想到这么说菲利西亚也许像她的导师,因此还是写了“反派话多”的情节,笔力有限如此表达了,希望观感没有太差。
在此感谢这位朋友。也在此感谢和悬铃木互动过的赫尔维尔和热尼亚及创作她们的老师,有一些东西还是我和你们讨论过才自己有了灵感的,比如这篇用了两次的拥抱,还有悬铃木正在形成的死生观啥的。我不是很会在正文里回应所以在这里说了,大感谢!
路维特和菲利西亚的故事原型是我很久以前设计的,纠结了要不要详细写,怕观感太拖沓,最后决定还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希望写好了!跟安德烈滑跪一下,因为设计他是一个被大人物推动的无名小卒那样的角色,也许显得他有点苍白,不好意思以及祝你安息。
这篇的标题“赠礼”也源于和那位朋友的讨论,我们聊到悬铃木像他们三人所失去的未来。我想“赠礼”也确实贯穿这个故事吧,路维特将黄铜十字送给菲利西亚,菲利西亚将它赠予安德烈,安德烈收下它也是希望新生的瓦尔基里可以真的新生。
我骰了很多次骰子都不能确定重塑的方式,最后下定决心不反悔的那次出目指向超越,仔细一看之前的结果也是超越偏多。还挺意外的,因为我定的点数范围里是锚定最大,不过我想也许是角色自己真的很希望走超越这条路吧,这种角色跳出作者掌控的感觉!因此很努力地推测了到底怎样超越,我觉得这个方式意味着舍弃过去,就像剥皮一样(比划),对她来说这种割离一定是一个没有那么正面的悲剧,但同时也是她真的能把赠礼内化开启新生的体现吧?尽力想表达了这样的一点点悲剧感,和她完成自我课题的感觉。未来还有很多要学的。说起来一开始我的设想还是那种日本王道漫画味故事,笑。
然后想说希拉这个角色。写完序章我就耿耿于怀,觉得写了一个很扁平的白月光牺牲者式母亲,我想让她也有自己的生活。后来在补过去设定时将她设计了进去,决定让她也有她的反面,虽然觉得因为我的设计力现在还是有点扁,但总之也是了却一个心结。
还是有遗憾的,笔力所限没能写得更好,许多小设计也塞不进去。不过这一整个发生在前世的故事就此完结了!谢谢所有支持我和悬铃木的!从此以后就是她自己的人生啦!
最后贴一首歌,是刚开始写那会儿偶然刷到的,几乎是因为这歌的氛围写了这样的开头。中间换过几首歌听,最后还是听着它写完了结尾。
——From your embrace, our hearts have untwined.
【Blues with you】
https://music.163.com/song?id=2045421486&uct2;=U2FsdGVkX1/jze1vhNC81t9x6gohIwCm6Imcdi7CdHY=
祝这个故事里的所有人还有读到这里的你找到自己的道路。


前情提要↓
欢迎点击好医生的作品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729792/
及租狗人女士的作品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729809/
二位的故事都是完美的和特别好的!
————————正文————————
朝日反射在埃布罗河上,水面无波无纹,涓流于踝下半指处。
维诺在亮闪闪的铁皮前思索良久,终于想出办法,把本月水电缴费单塞进爆满的1204号公寓信箱。
她退后一步,志得意满地欣赏,并掏出手机,对准满满当当铁皮纸砖般的信箱调整焦圈。
伴随着震动全城的一声巨响,死棘刺破地砖,尖头敲在铁皮信箱底部。
快门声。
死棘先头军横冲直撞,接连突破四层信箱,从白铁皮顶部扎出头来,身上横七竖八串了一叠缴费单。
地面震抖,穿老式邮递员制服的瓦尔基里向后小跳半步,大量死棘便在此时穿透地下车库,顶破公寓楼板,把房间串成空心烤肉块,欢欣鼓舞纵情向上生长。维诺抬眼皮观望了下高度,手指一滑直接把缴费单肉串发进Whatsapp群组。
商业纠纷调解:出事了!
她沿着一层室外台阶往下跑,飞快地打字。
商业纠纷调解:大家伙儿那边怎么样啊?
还没有人回答,在她和信箱搏斗的时间里,雨水已从积云中泼下,维诺离开最后一步台阶往停自行车的方向走。路边好几辆哈雷摩托把邮差自行车夹在中间,几名壮汉正倚着摩托喝罐装咖啡,任由雨点打在墨镜上,不动如山地谈论刚刚的震动,以及红河城究竟是否处于地震带。
“嘿!邮差!”花臂、蓄须、穿皮夹克搭粗项链的骑手们呼喝,更南方的口音,“这是你的车?”
“是的,先生们。”维诺以两根手指轻碰帽檐。
“我奶奶都不骑这种车。”男人们隆隆作响,善意地笑道,“小姐,你的监护人呢?”
邮递员回以笑容,在她随口扯出什么理由来应付差事之前,首先预感到后颈皮发凉,这种凉意与雨不同,于是她往边上趔了趔身子,几块人体组织碎块伴随着雨滴从天而降砸烂在她脚边。
她听见谁大骂了一声脏话,骑手们纷纷直起身子向上看,死棘从窗玻璃和通风管道中伸出枝桠,看来被这场雨给浇活了,纵向穿透公寓,挑着人类的胳膊腿、宠物皮毛和家电开始往横里生长。当棘刺分支爆出楼栋本体有一定距离时,肉块松脱,于是血沫残渣混着机械零件叮铃咣啷往下掉,公寓逐渐解体,空气中一时全是粉尘和此起彼伏的脏话。
维诺抖落了几下小腿,试图甩掉飞溅到制服上的组织物血点,可惜徒劳无功,只好低头继续看手机。
AAA租狗人:你醒了?
AAA租狗人:红河城炸啦!
商业纠纷调解:什么玩意?
阿德利企鹅:[文件]通古斯爆炸.pdf [文件]警情通报.pdf
商业纠纷调解:这紧要关头老爷您怎么还发pdf啊?
商业纠纷调解:三句话总结?
AAA租狗人:我告诉你啊老兄。
卡罗尔一句话让维诺等了长达五秒钟,她之所以没有继续等下去,是因为公寓第二十三层里的真皮沙发比解释更先一步抵达脑袋顶。她满心愤懑跳起身给出一记飞踢,把沙发组踹到马路中间,砸碎了红绿灯并引起尖叫一串。
邮递员挑剔地认为在天降胳膊腿的情况下,实在没什么好为一只沙发尖叫的,还好现在有其他事分散她的注意力。
商业纠纷调解:您请说话?
AAA租狗人:赌场地裂了,死棘到处长,红河城被劈成两半。
AAA租狗人:四层楼高的卡里略将军正在大搞破坏。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我操,这是能卖关子的事吗卡罗尔?
AAA租狗人:你就说三句内解释清楚了没有吧。
群组内两个俄罗斯人没有任何动静,邮递员抿住嘴唇,盘算起是否应该把自行车丢在这里,徒步去拿基金会配发的灵装。
她从上衣口袋掏出怀表,默念着艾米丽的名字按开,指针金属线组成A字花,指向十一点方向。而季米扬诺娃医生的面孔刚在脑子里闪现,指针便无声无息滑向五点钟。
医生和她竟然不在一起?
米拉老妈本来只想在红河城稍作歇息,没想到赶上个大场面。
她扫开面前烟尘,耳坠上塑料材质的几何亮片噼啪作响。车队里的小伙子们四散跑开,试图安抚尖叫不止的路人,并把他们带离危楼范围。
米拉老妈只是个老太太,因此恰好找理由抄手闲着,把墨镜往额头上一推,观察面前这位瓦尔基里。发现邮差蓝眼珠在手机屏幕和怀表表面上两边打转,忙得很。左手摇晃一番老怀表后打开,接着眉毛拧起,右手大拇指飞速摁几个单词发送信息,嘴里咕哝着合上怀表,用力在车把上铛铛磕几次。
“嘿,那老家伙不经碰。”米拉老妈搭讪,“你是个瓦尔基里,没错吧?”
和怀表这种东西一样老掉牙的邮差停止忙碌,对她抬了抬帽檐,露出服务业标准笑容。
“我刚巧认识一位瓦尔基里,二十多年前环美摩托越野赛,差点儿冠军就是我的,可惜参赛者里头有她。”
“太遗憾了,夫人。”邮递员热情洋溢,“当时还不限制瓦尔基里和人类运动员同台竞技,是有点不公平。”
米拉老妈向外努了努嘴唇:“没那么坏,她开起车来真够劲,仔细看长得跟你也有点像。不过那家伙是棕色皮肤,长卷发,脸上身上到处都是大块白斑,像条鬣狗,还不爱说话。”
“很高兴您能这样评价对手,患皮肤病是个显眼特征,可惜我并没见过这位同胞。”八颗白牙,符合老派宣传画刻板印象。
在瓦尔基里邮递员背后,三十五层高的公寓大楼从内部被死棘撑爆,楼身四分五裂仅留下框架柱。死棘兀自围绕承重结构攀援,四部电梯卡在中段,上下颤抖,像颗喉结。尖叫与警报声此起彼伏,棘柱往四面八方延申,意图染指周围楼栋。透过建筑物被蛀的褴褛空隙间,米拉老妈看见阴云遥远处升起几股黑烟:“发生你们才能解决的麻烦事了?”
邮递员回头看了一眼:“是的,夫人。”
“不去救救幸存者?”
“救不了,夫人。”邮递员把怀表揣进口袋,踢开自行车脚撑,“死棘感染不可逆,里面的人即使救下来也活不过半天,您也尽快离开较好——劳烦让让路,我得去确保医生安全。”
“什么医生?很重要?”
“非常重要。”
“哇哦。”米拉老妈咂了下舌头,“宝贝儿,那你肯定不能骑自行车去干这份差事。”
邮递员当真沉默了几秒钟,最后不得不承认:“您说得在理。”
一把钥匙落进维诺手心里,米拉老妈冲她眨眼,鱼尾纹挤做暧昧的一堆:“借你。”
“噢太感谢了,但我不能保证物归原主。”邮递员嘴上还在客套,眼睛已经黏在那辆火红色摩托身上,随即臀部挨了老太太一巴掌,被拍得向前趔趄。
“嗨。”米拉老妈食指一拨,墨镜从额头滑脱,稳当地架在鼻梁上,“哪来那么多废话,给我乖乖把小屁股放到车座上去!”
邮递员的职业性笑容裂开条缝,米拉老妈打个响指,叫来一位彪形大汉,这就上了他涂着绿色鬼火的摩托后座。塑料耳坠哗啦啦作响,雨滴造成的水波纹反光全落到邮递员脸上,映得瓦尔基里面孔五光十色。接着她两腿一夹,像跨着匹大马,扶着司机肩膀在车后座上站起身,扯起嗓门喊:“——小伙子们!换地方嗨咯!”
七八辆大排量摩托齐齐轰鸣,先后顺路绝尘而去。
维诺回身跨上那辆火红色哈雷,边发动引擎上路,边飞快把消息列表往下滑。
AAA租狗人:嗨,有条狗看见医生在医院,有没有人趁手能接过来,赌场急需医生。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我去。
AAA租狗人:打手也缺,将军大杀四方,目标移动中。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再具体点呢?往哪儿动?
AAA租狗人:你到了就知道了,将军有四层楼高好认得很。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我比较好奇你怎么在操心调度,被骑士团捏着脖子干活了?
AAA租狗人:瞧你这话说的,掐我脖子的是地主,人正和企鹅钟表匠一起扛线呢。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哪个钟表匠?
AAA租狗人:企鹅他老相好的。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噢!
AAA租狗人:速来。
维诺放下手机,调转车把,停在一只自动饮料售货机前。
按动数字盘,投币口弹开,露出一只深孔。邮递员扯下手套,把半个手臂探入其中,掌纹扫描完成,探针取血,售货机验证身份结束,从中间裂开,露出一只狭长琴盒。
邮递员伸手捞起,将它挎在背上。
卡罗尔放下手机,猛灌加冰苏打水,莉莉安娜忙里偷闲瞅她一眼,问:“怎么啦?”
租狗人咧嘴,苏打水里的丰沛气泡赶巧在她张口时往上涌,于是所有战斗人员的耳麦中传来清晰打嗝声。
莉莉安娜咯咯直笑。
“从雪莱公寓到医院路况如何?有人去接医生了——瓦尔基里的医生。”
“哇噢~也就是说季米扬诺娃要过来?好消息。”
“通常来说下句是——”
“坏消息,医院附近是死棘重灾区,从那儿到市中心的路完全被截断了。”
冰块融化的速度不算快,此时刚好裂开,于是在句与句的短暂间隙中插入喀琅一声脆响,卡罗尔不置可否地抬了下眉毛。这点动静当然不能刺激她的神经,也没有被中控室内两人察觉,莉莉安娜紧盯屏幕,卡罗尔忙着满脑袋回荡的怒吼中分辨出亲疏远近,再压缩思考速度,挤出一根微不足道的分线来对此情此景发下评语。兴许是算力不足,当她做出选秀节目中嘉宾之常见神态,预备发表一番淋漓尽致的刻薄言论时,却只成功撂下一句:“那只好希望医生等到的不是辆破自行车了。”
然而当事人季米扬诺娃医生跨上后座时,却宁愿维诺是蹬自行车来的。
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不含安全头盔的摩托车原本并不算太可怕,只能说隐患较大。热尼亚在湄公河流域工作时坐过不少,当地驾驶者们喜欢超载、违规操作、不戴头盔的案例比比皆是。
但按年代计算,总归不会有人左手开车,右手狂敲手机。
即使瓦尔基里能够做到将摩托开成公园摇摇车,也还没能进化出变色龙视觉,可以左右两只眼睛各看各的。当火色摩托又一次唐突地大幅倾斜,于行驶中擦着路边消防栓过去时。医生双臂紧紧扣在邮递员腰上,及时把腿一缩,避开障碍物的同时顺势踩了一脚驾驶员脚后跟。
——维诺半点反应也没有,看来还是太温柔了。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路上呢。
AAA租狗人:好,现在全力踩自行车脚蹬,踩出火花——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脚蹬?哈哈!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你还不知道吧卡罗尔!我搞到一匹好马!
AAA租狗人:偷的?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借的!
摩托避开水泄不通的车行道,跳过路障驶上人行道,逆行于主方向,接着便遭了报应,被疏于检修的井盖绊了一下,车前轮咣当颠起。维诺因惯性弹起身体,后脑勺咚一下撞在医生鼻梁上。
好的,这下双方都知道疼了。
邮递员支出腿把车停下,扭头,看见季米扬诺娃医生捂着鼻梁,正面无表情地盯着她,手掌底下瓮声闷气:“您还是更适合骑自行车。”
“不不,好医生,您听我解释呀。公寓解体的时候它把手让砸歪啦,我倒是能给掰回来,不过刹车一时半会儿没法修。”
就车速和瓦尔基里的体质两方面而言,没有刹车的自行车不碍大事。
季米扬诺娃医生不赞同的眼神戳在维诺脸上。
好漂亮的绿眼睛。
在米切尔宅时邮递员还没仔细注意过,现在突然挨得那么近,那眼神扎得她皮肤发麻,血直往耳垂上涌。维诺理直气壮的架势泄掉一半,微妙理解了艾米丽为什么愿意低头听命。季米扬诺娃医生检视谎言如剪除病灶,维诺在战争年代学到的重要信条之一是不要试图和医生作对。
她摇摇手机:“我和卡罗尔打个招呼。”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接到医生了,什么情况?
AAA租狗人:卡里略将军吵着要找“塞拉斯·维萨留斯”,并且到处殴打瓦尔基里。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塞拉斯是谁?
AAA租狗人:邪教头子。
季米扬诺娃医生没说话,只是把右手掌心摊平伸到邮递员面前。
打字,速度快了一倍:“马上就好!”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把医生送到我就撤。
AAA租狗人:?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拜托!我看起来像能打将军的人?
AAA租狗人:将军逮谁打谁,是个人就行。
商业纠纷调解专员:填线啊。
AAA租狗人:嗯啊。
AAA租狗人:顺便一说,迪布瓦快死了。
埃布罗河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开始涨水。
河水漫过轮胎和胳膊肘灌进西班牙人耳孔中,使他呼吸困难,浑身打起冷战。
埃布罗河又在涨水了,泥泞浑浊,血浆翻滚,水下炮声隆隆。
手机拍到医生掌心,屏幕还亮着。红头发扭回身,花花舌头打直成一根铁棍:“给你了,医生,请帮忙对接卡罗尔,接下来我得专心开车。”
铁棍舌头踹一脚启动杆,发动机轰鸣。
季米扬诺娃依言扣住对方的腰,摩托一骑绝尘,提速到最高时产生的劲风差点将她刮飞,恰巧在几乎睁不开眼的车速下,邮递员压在桶形帽下的头发被吹得乱飞,露出平时被遮蔽的发根处半指长的一块棕色皮肤,像溅在红发间的咖啡渍。
此时——就在热尼亚眼皮子底下,咖啡渍肉眼可见地又缩小了一些。
“——邮递员接到医生了,她骑车时不方便接电话,现在应该正从医院出发,我看看地图……25号路、17号路和19号路都被封死了,死棘把路面破坏得一干二净,要顺利过来她得绕到64号路去,穿过柳树街,避开老城区,再从铁轨后面过来,多花一刻钟才能到铄金赌场。”无线电频道里卡罗尔的声音响起,及时向参战人员汇报情况。
“邮差肯定不会这么走,卡罗尔。”
“什么?你知道她要走哪边?”
“不知道,但换了是我就不会按你的方案走。”巴尔苏克随口总结,“太慢了。”
“太慢了,我们从上面过去。”红头发驾驶员扫了眼后座乘客伸到面前的导航截图,做出如下评价,“等绕路磨蹭到地方,迪布瓦老爷早变成迪布瓦酱了。”
语毕,火色摩托调头便从台阶上了人行天桥,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季米扬诺娃医生发出疑问鼻音,这声质疑本该被安全帽阻隔下,但由于二人未做任何头部保护,于是医生的声音顺利传进骑手耳中。
卡罗尔发送在WhatsApp群组里的截图显示,医院周边已完全被死棘挤占满当,原本三条支路一条主路均可通往铄金赌场,但现在游荡的狩骨化市民和纵横荆棘遍布其上,卡罗尔提供的导航截图用桃粉色荧光笔在这些地段上画着巨大的叉。
租狗人女士作为调度中心推荐的路线是先调头返回,绕开老城区,再从那里兜上半圈到达铄金赌场主战场。
平心而论,医生认为这套方案十分稳健,执行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掌握车把的西班牙人却直接将它从头到尾否定,未经任何沟通便直接在三条车行道之间选了拿车轮爬人行天桥。
医生对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极度不赞同:“这套方案可能已和所有人敲定过,你擅自更改路线会产生问题。”
“在到达铄金赌场前咱们走哪条道都没关系,只要够快。”台阶已爬到头,摩托顺着桥面狂飙,桥下死棘丛生,似乎是感应到了有瓦尔基里正从上通行,这些半结晶体沿着桥墩往上蔓延,很快攀上桥面,而正对摩托车头部的是一扇自动式四开商场感应门。维诺对此视而不见,只提醒医生伏低脑袋:“坐稳!抄近道咯!”
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季米扬诺娃医生不认为靠摩托的速度及冲击力可以撞碎面前的阻挡物,现在又不是60年代。再说,进去了以后又能怎么办呢?她们还是得回到大路上去呀。
她和她就像马匹与驴子,永远也搞不清楚对方脑袋里转动着什么离谱念头——活动金属门框并扛不住冲击,整块玻璃门被她顶飞出去,甩在购物车中间。邮递员就这样大剌剌地拖着茂密丛生的死棘,长驱直入,越过摆满杯碟碗盘和家居用品的货架,笔直攮向商场对面的安全玻璃,在即将发生碰撞时拧转车头向侧面一趔,把成排收纳柜像多米诺骨牌般撞倒。死棘冲势不减,替她将整片玻璃幕墙击碎,维诺趁乱调车从商品陈列厅蹿出,后轮着地落在临近商铺屋顶上。
在医院和铄金赌场之间分布着大量红河城老式房屋,这批建筑仍然是淘金时代的产物,总体并不很高,且多为带阁楼的斜坡屋顶或铁皮平顶。老城区地面路网复杂,充满了各种违建加建和没有标在导航地图上的死胡同。按照直线距离看,穿过老城区这片房屋是到达铄金赌场的最短路线,卡罗尔在规划时还是直接略过这一区域——毕竟车是要在地上跑的呀!
当摩托在屋顶间跳跃时,医生才察觉那句“从上面过去”并非虚指,而是陈述事实。
她回头望了一眼,死棘像爬藤科植物,在有接触物的情况下转移速度很快。老城区复杂的空间关系使它们失去目标开始胡乱生长,在每个建筑物空隙处试探,短短几息间便被甩到身后看不见了。
又一次剧烈颠簸,医生差点被从后座上甩下去,她把头扭回前方,看见雨幕中铄金赌场原本所在位置已化作废墟,卡里略将军庞大的虚影凸显在雾气中。不断从各个方向攻击它的瓦尔基里们与之对比和松鼠或鸟雀差不多大。
离将军越近,建筑物毁坏程度越高,老城将至尽头,附近重新开始出现高楼大厦,摩托颠簸地更厉害了。被将军在战斗中毁去的建筑物参差板块和外露钢筋间互相堆叠,热尼亚眨眼,抹掉脸上的雨水,看见骸骨巨人咆哮着将楼体从当中斩断,击飞几名眼熟的瓦尔基里——等等,那里面是有雅克·迪布瓦吗?
没等医生脑袋转过弯来,倒霉大楼发出可怖闷响断裂了,像只巨树将躲避不及的雀鸟与松鼠砸在混凝土底下。
这些孩子身形的瓦尔基里有些不幸负伤,因此被废料穿透,在瓦砾堆中挣扎时让骨刺给追上了。发狂的骸骨巨人摁死她们如拧断家鼠脖颈那样轻松,人体当场化作飞灰,只留灵装做墓碑——摩托跳上混凝土巨树,骑手擦过最近那只新坟,抄起墓碑船锚,把铁链在手臂上绕了几圈,拖着那根东西扎向将军。
“——小心车胎!”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季米扬诺娃喊道,大风倒灌进喉咙,尘烟未散,砖块稀里哗啦往地面崩塌,雨里全是水泥呛鼻的气味。
然而骑手充耳不闻,只是加速,加速,提速到最高,一臂扶车把,一臂将船锚悠荡地越来越快——摩托冲至尽头,起跳,楼体嘎吱吱向地面滚动,她甩出船锚,灵装击中卡里略将军后脑,在颅骨上穿了个洞,锚体从右眼穿出去钩住眼眶。
维诺拉紧船锚铁链,趁将军因受击惯性低头时,摩托车后轮砸在她后脑勺上——很可惜,没造成一丁点伤害,船锚创口处立刻愈合,灵装被卡在头骨内无法拔出。
邮递员尝试将自己固定在将军头颅上,但是创口处骨刺大量增生,将军一甩头,把拽着锁链的骑手连带医生摔向地面。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季米扬诺娃措手不及,啪一声把维诺的手机给捏裂成了块废铁。被当作摆锤悠向地面的过程中,两人一摩托于半空中暂时分离,幸而船锚还插在将军眼眶里,且因愈合而卡的十足牢固。船锚锁链的另一端系在邮递员胳臂上,给事态提供了一定挽回机会,然而人工放链跟不上被抛出的速度,于是在手臂脱臼的咯吱脆响和肌肉撕裂的剧痛中,邮递员硬撑着哪怕皮肉丝丝断裂也没有放开锁链,用完好的那只胳膊扣住季米扬诺娃医生,并出于不知什么诡异心理,她下一步选择是用腿夹住摩托,把医生按回座位上。
可能这就是拿人手短的具体表现,早知如此就不该借别人的车,也不该载别人奶奶。
她们以锐角状态让摩托后轮砸在另一栋大楼理石贴面上,在报废了挡泥板,后车支架,几乎磨平轮胎橡胶垫后,一路刮着火星从大楼墙壁上开了下来。车身快坠毁时,维诺丢下锁链,踹了一脚群墙,溜肩把身上的琴盒灵装斜着杵进沥青路面,接着又补上自己的一条腿做缓冲,摩托嘶哑悲鸣,在连续打滑中险之又险地留下歪七扭八的黑痕和两道深沟,终于咣当一声停住了。
维诺呼出一口粗气,垂在身侧的右胳膊肘处一截粉白骨头露在外面,腕和手指像团肉皮,耷拉在整个手臂最末端。撕裂的肌肉已在弥合,她来不及处理骨头上的问题,眼神在战场内逡巡,很快锁定方位,冲不远处浑身湿透的“钟表匠”方向喊道:“他还喘气吗?!”
“喘着呢!”不知对方怎么样福至心灵地理解了她的意思,勒梅尔把滴水的马尾甩到背后,从瓦砾中重新站起身来,碎石窸窣滚落,那柄军刀被雨水洗得光洁如新,反射出卡里略将军扭曲的骸骨身躯。水珠从对方鼻端刀尖落下,维诺看见她身躯呈蓄势待发的弓形线,连番战斗后虽满面疲惫,脊背依旧笔挺,提刀之手似乎较为松弛,刀锋冲下,一个可以随时可以应付各方向敌袭的准备姿态。
“钟表匠”是位可敬的老练战士,西班牙人理解自己不需要对她多嘴问东问西。
邮递员扭回头,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季米扬诺娃医生抹了把脸上的泥水,比她更快摸上那只脱臼胳膊,没打招呼便咯吱一声将小半截粉色骨头推回肉里,一捞一掐把反向弯折着耷拉在身侧的胳膊嘎巴回正道,应急升起的肾上腺素刚巧褪去,俄罗斯人这两步操作疼得红头发眼前发黑,哼都哼不出来。
在她故作镇定实则动弹不得时,勒梅尔从陷进地里的迪布瓦身上扯下一截东西,丢给新加入战场的两位人士,季米扬诺娃医生替骑手接了,发现那是带一只耳机的喉麦:“迪布瓦暂时用不上,拿去吧。”
勒梅尔拿空闲的手在耳朵边比划了一下,医生看见里面塞着同款通讯设备:“——来自慷慨好客的弗农领主,你们可能需要这份赞助。”
热尼亚对勒梅尔点了下头,转手将喉麦挂在了邮递员脖颈上,向后一拉扯紧,跟拽狗似得。
接进无线电通讯频道的一瞬间,骨爪对着双人摩托迎头踩下,驾驶者不得不紧急避让,从侧面围着将军打转,试图寻找合适的时机出手。在确认雅克·迪布瓦先生还会喘气以后,维诺那根铁棒舌头迅速软化成血肉,观察战场的档口嘴巴也没闲着:“我的天哪!她是把所有会动的都当作那个什么‘塞拉斯·维萨留斯’吗!”
卡罗尔的声音在耳机里骤然放大三倍,震得邮递员直眨眼:“对,就是塞拉斯·维萨留斯!既然它嚎了大半个晚上想要干掉那个家伙,我们就带它去!”
“哈哈,我喜欢这个提议……老爷,弗农老爷?”
“我在听,继续说。”
“把你那辆运可乐的卡车借我,我们领这个迷路的客人回家。”
“……天啊,巴尔苏克,你可真贵,”摩托打横漂移,避开一串突出地面的骨刺。维诺兴致盎然地听着通讯频道里的声音,挨个点数里面都有哪些老熟人,原本巴尔苏克出现便已经让她略有些惊讶,劳蕾塔·弗农接下来的话更使她吃了一惊,“结果到头来还让牛仔说到点子上了,让格伦把车开到城南的铁架桥和你接应,我们来吸引那个卡里略去橡林镇见她的老相好。”
老天,这趟真没白来。
邮递员支起耳朵正听得津津有味,卡罗尔紧跟在后头幽幽接了句:“听见了吗商务纠纷处理专员,咱们得把将军领到橡林镇去。”
“听到了啊。”
“听到了还摸?现场机动性最高的就是你,快上。”
“……人是活的摩托是死的,这车可以换人开!”
“少废话,邮差。”弗农领主笑意吟吟的声音插进来,嗓音甜蜜,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格伦在巴尔苏克的卡车上备了医疗用品,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得给我把医生送去,伤员全指望她了。”
“那将军呢?”
“拉上。”
沉默,维诺看了眼正无差别攻击在场所有人的卡里略将军,盘算了几秒钟,回头问后座上的医生:“听说您曾辗转近代各大战场,那么您一定也知道怎么开摩托吧?”
“想不想驾驶这匹铁马试试?很简单的,握住车把让它跑就行。”西班牙人双眼闪闪发亮,极力推销:“现在我只能指望您啦!好医生。”
饶是在战场见够了各式各样的突发情况,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季米扬诺娃也还是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当骑手珍而重之地把她的手放在车把上,医生紧急回忆当年在湄公河沿岸工作时,那些骑摩托的越南人都是怎么驾驶的,这份工作太紧迫了,导致她连激烈的俄语支持都没来得及说出口。俄国人过于用力地攥着把手,语言系统先操作模式完成跨时代接驳,越南语的“三句话教您开摩托”飞快滚过几回合,先踩油门还是先踩刹车终究没想起来。维诺在她肩膀上一撑,从驾驶位翻到后座。西班牙人撒手的一瞬间,火红色摩托便失去平衡,大幅度向外侧倾斜,热尼亚试图掰回车头,然而忙中出错撞到地上的瓦砾,咣当一颠,车子差点翻倒。
蹲踞在后座上的老兄爆发出大笑,狭长琴盒滑到右肩外侧,蹲身曲腿压低重心踩住后座脚踏,扶着琴盒灵装在地上一杵,摩托便被推回正轨。
一长串夹着越南话的俄语机关枪般叽里咕噜溅射出来,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季米扬诺娃作为说明书的忠实信徒,此时连胯下机车的型号都不知道。它燃油量多少?时速多少?应该什么时候踩刹车?又什么时候需要用腿辅助保持平衡?种种信息一团雾水,当头危机悬而未决,俄国人觉得这一天未免太不顺利,手心满是薄汗,眼前走马灯乱转,紧张地像第一次握手术刀。
背后传来机括弹响,西班牙人玩杂耍一样在歪七扭八行进的摩托后座站起身,将一直挎在肩背上的狭长琴盒开启。
一排六只带倒钩的黢黑投枪被束带勾连,呈半扇形喀琅展开,枪头处安装着闪动红点的可疑设备,细看似乎打着希帕提亚基金会LOGO:“嘿卡罗尔,你觉得将军看过斗牛吗?”
“老兄,它现在的理性可能还不如牛。”
“这算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你想和它谈判,坏事。”
“好在我们首先排除了这一选项。”
“是的,对的,他妈的你有完没完?”
“哎。”红头发西班牙人反手抽出一只投枪,在手里掂了掂。即使面前所有突发情况都急着挑战她固有的生活习惯以及戳刺短板,但季米扬诺娃医生毕竟久经沙场,依然以堪称刚强的态度将所有问题承受下来。维诺本打算尽可能多和卡罗尔说点废话拖延时间,好等待医生适应驾驶模式,如今却陡然间发现自己才是忧虑过重的那一方,于是突兀切换话题,“既然它的智能还不如牛,请其他瓦尔基里帮忙把它往城郊方向引,我在短时间内集中输出把它打疼,让仇恨顺位移到最高,接着拉着这家伙上公路去和巴尔苏克接头,你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噪点杂音:“哇哦,你是说要来场西班牙斗牛表演?”
“真不错,但你确定那细条条的玩具能撼动卡里略将军?”
劳蕾塔·弗农被畸形怪物攥在巨大骨爪中,狠狠砸进建筑废墟里。血注的疯狗手脚并用跳上巨人肩膀,闪电般顺着胳臂撞向巨爪,将三根短钉和一根长钉顺次打出嵌入巨人手骨,想尽办法阻挠对方,意图抢到弗农领主面前去,四肢着地冲那个怪物咆哮:“——你这狗屎给我松开!”
她面庞肢体上全是裂开的伤口和鲜血,所途经处均是带血抓痕,整个人像一只被过度使用以至于开始逐渐解离的瓷器,但瓦尔基里非凡的自愈能力又挽救了这点,使伊克斯表层釉面被内部血肉以反直觉的方式粘连在一起,碎块向内拉扯,维系住形体不会溃散。
“我可没说要一个人干?”邮递员到达骸骨巨人侧肋,投出第一枪,细条条一根的投枪扎在卡里略将军骸骨化的腹腔边缘,枪头处那可疑设备高速闪动,接着嗙一声发生爆炸:“斗牛是一门需要团体紧密协作的艺术,需要花镖手、骑马斗牛士、副斗牛手及若干工作人员严丝合缝地配合才能处理一头公牛。”
“哇。”卡罗尔干巴巴地应声,掐断科普话题。
爆炸产生的冲击力使骸骨巨人打了个趔趄,没有追加攻击劳蕾塔·弗农和拦在面前的恶犬,巨大的头颅连带肩膀旋转半圈,直接拧向投枪飞来处。
“我们的将军卡里略——了不起的英雄卡里略——”西语从移动铁马上传来。
维诺确认自己映在对方眼球中,并已将卡里略将军从弗农身前引走后,瞄准它脖颈处投出第二枪:“您好!有您的送命邮件到!伊丽莎白!想不想加入这场表演!”
爆炸使骨头碎屑四处飞散,骸骨巨人半张脸烂掉,又以肉眼无法跟上的速度疯狂再生。
“再叫我伊丽莎白试试?撕烂你的嘴!”呵呵吐气伴着喉音咕噜噜滚在邮递员耳边,维诺听声音判断这位瓦尔基里的肺应当正忙着把碎肉和血沫往外挤,她可能有一会儿没法呼吸也不能说话。西班牙人抽出第三根枪,卡里略将军从失衡中恢复,向高速移动的骑兵处甩出带骨刺的尾巴,却在即将抽中目标时于半道上被长钉拦截,理应既不能说话也无法呼吸的伊克斯身形摇晃,手持长钉从天而降,口鼻还在不断向外涌血。谁也想不到在这样的状态下她还能够做出有效反应,更别提如此迅猛的攻击——然而邮递员对自己邀请的对象怀着种莫名其妙的笃信。
和公牛角从不讲情面一样,斗牛士也不轻易交托信任。
维诺邀请,因为伊克斯绝对可以做到。
血注的疯狗将卡里略将军的骨头长尾楔在地上,摇摇欲坠的身躯如烟灰般轻易就可以被抹去,她咳出的血和肉块溅在长钉周边,拧转长钉,将附近骨质全部粉碎,生生斩断那只尾巴,使该被撕烂嘴的邮递员顺利投出第三枪——正中胸腔部分。
不知道可疑基金会私底下做了什么研究,比之前更盛大的爆炸蔓延到整个灵质身躯上,骸骨巨人仰天痛呼,接着不管不顾地带着满身未熄灭的火焰俯身冲向枪骑兵。
“过来了。”西班牙人汇报,医生已不需要多关照,虽然仍没搞清楚怎么刹车才能不侧翻,但她已完全掌握使车辆横冲直撞的方法——这就够用了。因此维诺逆着行驶方向踏在后座翘起的尾部,似乎此时终于觉得邮差帽风阻太大,影响平衡,于是解开系带让它自由去了,差帽呼啦一声飞向火焰中心时,她投出第四枪。
巴尔苏克打开车门便跳上驾驶座,看也没看一眼车厢里的货。
弗农领主的手下——格伦·卡罗特顺势从驾驶位挪到副驾驶座,他没有瓦尔基里那种底气,可以在将停未停的行驶状态中上下车。在等巴尔苏克完全接手方向盘过程里,此人多问了一句货怎么处理。
哥萨克换挂挡倒是娴熟,但格伦还是有点担心她能否够得着刹车和油门,好在交通工具驾驶座的尺寸看起来刚刚好:“余货还有多少?”
“我们只来得及卸一点,把武器和设备补给放上去,里面还剩四分之一车厢可乐。”
信使分给他一点余光,格伦耸耸肩:“领主很喜欢这种饮料,庄园对此有需求。”
司机意不在这种细节,专业精神使他只关心有用的和将要有用的部分:“安全锁销开着吗?”
“没有。”格伦缩回开车门的手,扭头确认对方是否在开玩笑,并尽力劝阻对方做出什么疯狂行径:“您要在行驶过程中启动自卸货吗?这不太恰当。”
信使为此发出大笑,红白两色涂装座驾适时咆哮,新出厂未达八个月的重型卡车饮饱柴油,发动机隆隆作响,蓄势待发,整车震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巴尔苏克自己的那辆老东西有些年头了,驾驶室脚垫磨损挺严重,一上路就颠簸抖动,晃得像老式洗衣机筒。车还是自己的好,尤其是面临紧急任务时,磨合并驾驭机器本身就要花多余精力,然而,要是让他把老东西开来做现在这档子差事,巴尔苏克还多少有点舍不得。
马永远是自家的好,四蹄打颤也知道得把喝昏头的主人驼回家。
哥萨克过去常喝到天旋地转,晃悠悠把胃压在鞍袋上,闻着后蹄上的干草和马粪味,喉咙里一个劲反酸想吐。一双醉鬼眼睛望见大太阳底下,老母马鞍具缝里磨得全是雪白汗沫,都快不记得自己叫什么了,还知道心疼心疼马。
妲莎,宝贝儿,载我回家去,妲莎,我的漂亮宝贝儿……哥萨克伸手想摸母马脖颈,一巴掌拍在了可乐卡车方向盘上,鸣笛声比马嘶更长且洪亮。
这里是红河城,没有皮毛斑驳的老马。卡里略将军从裂开的地缝钻到外面,咆哮声一直传出三四个街区。哥萨克咂嘴,满心想抽它一鞭子试试咸淡,然而手里既无马鞭也没有马。副驾弗农领主的人还没走,识相地等待信使与新车联络感情,顺便确保对方没有意图让这挂卡车翻在公路上。
“老弟,别瞎操心,我不会在半道开自卸。”巴尔苏克顿了顿才捞起对话末尾继续,“油泵会烧死,犯不着这样,四分之三个货舱还不够她们用吗。”
她用衣袖擦着卡车仪表盘,赶苍蝇似得打发格伦道:“下去,别碍着我干活。”
格伦跳下车,倒退着跑了几步,庄园的雇佣兵小伙子们全副武装地等在大切诺基边上。他眯起眼睛,望着印有可乐广告标语的卡车嗤嗤呼气,调头逆着车流开上通往橡林镇的公路。
今天一直在下雨,轮胎上的泥都被刷了个干净,闪闪发亮,像要去好莱坞拍电影似得。
格伦按住喉麦:“报告,卡车出发了。”
哥萨克打开车载电台,旋动音量钮,卡罗尔的声音及作为背景音的乡村乐队立刻充斥驾驶室:“巴尔苏克,好消息,我给你找了个护航的。”
“我不需要护航。”
“噢,别见外,大家都认识这么久了,他还带了礼物来呢。”
“礼物?”
“同城快递季米扬诺娃医生,无奖竞猜,巴尔苏克——”
“你找来的护航是邮差。”
“好的——是的,跟你猜迷真没意思。”
雨大了些,水雾使车前窗上色块糊成一团,哥萨克把雨刷速度调得更快了些,模糊色块清晰化为红河城路警及新设路障——前方道路维修,车辆止步。
巴尔苏克低头,车载导航上城市道路系统一片通红。
“卡罗尔,路断了吗?”
“没有,骑士团和血注分别联系了警方及市政系统,现在正合作清退普通人。”
“好。”
穿带反光条雨衣,手持警示灯棒的工作人员拼命挥手示意,然而可乐卡车速度不减,他们只得眼睁睁看着车头莽过路卡撞翻障碍物,呜一声冲了过去,劲风刮带着三角锥向前滚上好长一段距离,沙袋与塑料障碍则直接被截断压烂,卡车屁股连歪都没歪。
民谣正唱到乡村小教堂与马,卡罗尔的声音插进来:“巴尔苏克,你见到路卡了?”
“见过了,邮差什么时候到?”冲过路卡后,前方空旷,没有任何车辆或人烟,两旁偶有经过的房屋里一盏灯也没有点,略微抬高于地面的公路和两侧路沟不断向前延申,“我到橡林镇不用多久,是否需要调整行车速度?”
“稍等,邮差正忙着表演‘西班牙国粹’,暂时腾不出嘴说话。”杂音,伊克斯不知怎么误触了按键,烈风伴着高声大笑猛灌进来,卡罗尔的声音被彻底掩盖在后面,狂犬吠到一半,劳蕾塔·弗农腾出手掐了她的通讯,租狗人正好讲到后半截“……从后面追上你。”
“准时?”
“准时。”
这次接话的换成邮差本人,将军隆隆作响的脚步声透过通讯悬到巴尔苏克脑后高处,背景里有陌生瓦尔基里扯着嗓子喊转移。邮差挂断了,卡罗尔和她的乡村音乐切回频道,如果不是大地深处仍在震抖,令人厌恶的气息四处弥漫,哥萨克几乎要疑心这不过是一次普通公路旅行,很快,雷雨就将过去,彩虹将在远处天际线上横跨两个州。
“真是技巧娴熟啊,斗牛士?”卡罗尔盯着屏幕上快速移动的标点,“动物保护协会一定对你恨之入骨。”
“今天这场确实入骨。”邮递员驴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这本该是个冷笑话,但谁也没笑,她只好默数着第五根枪剩余时限,并在倒数十二秒时将其投出。
希帕提亚基金会提供的这只琴盒灵装原本效果非常废物,是将从琴盒内部拿出的物品短暂赋予加强效果,使其在六秒钟内等价于灵装,但倒数结束后该物品就会化为灰烬。
在维诺加入希帕提亚基金会之前,它一度曾登上待销毁名单,决定保留它的人是研究员雅克·迪布瓦。
原因也很简单——雅克·迪布瓦恰好认识一位与它适配的瓦尔基里。
这位瓦尔基里只在刚诞生时和他见过面,是个西班牙人,满头褐红色长卷发,皮肤斑驳如鬣狗,灵装是一只老怀表,分针指向起始地,时针指向终点,秒针恰巧也占个废物能力——使物品的保鲜时间延长十倍。
于是当日后希帕提亚基金会签下邮递员时,这件灵装在研究员迪布瓦的推荐下顺理成章到了她手里,六秒与十倍达成组合效果,使从琴盒内拿出的物品拥有六十秒存续时间,具备一定使用场景。
枪剩下最后一根时,卡里略将军已被完全拖离城区,因此最后一根投枪在前方炸开,破除路口阻拦的死棘。
斗牛士退下舞台,将左手轻按在季米扬诺娃医生肩部,温柔地压了压,和对方交换位置。
摩托呜一声跳上公路,骸骨巨人紧随其后,武装悍马拖着其他形形色色装载瓦尔基里的车辆咣一声最后落到路面上,这只怪模怪样的车队摆上坦途,朝重型可乐卡车夺命狂奔。
当她们和刚重新搭好的路障组会面时,先锋十分礼貌地选择抬起车头飞过去,紧随其后的骸骨巨人死盯摩托,眼神一错不错,但步子迈得够大,路障恰巧从它两腿间逃过一劫。而处在第三顺位的武装悍马既无礼貌也不爱高抬腿,于是嗙地把路障再次撞飞——这也就罢了,车窗里面还叉出一只持弩的瓦尔基里,对原地看傻的路勤比出中指,这一组玩意旋风般刮过面前,如果不是地上残留的巨大脚印和车辙显示事实昭昭,工作人员还以为自己在暴雨中出现了幻觉。
跑直线对摩托来说相当之惬意,即使在刚刚的激斗中它挡风板碎得干净,车身满是伤口和凹陷,轮胎磨得几度起火,此时还是顽强不屈地奔行在公路上,且很快看见了卡车屁股。
机车鸣笛一声,车灯闪两次。
卡车鸣笛一声,车后灯双闪。
两匹好马打完招呼,机车凑近卡车屁股。
“噢,对了。”卡罗尔冷不丁道,“忘了告诉你们,车厢里只有一条‘劳拉’,你们得自己想办法上去。”
“把我扔上去,我可以爬……”热尼亚医生话音未落,看见维诺把怀表表链勾在指间,表身流星锤般甩出去,嗙一声砸飞了车后门的锁头。如此粗暴使用方式,老怀表饶是灵装也像河蚌似得开了瓢,三枚指针在玻璃后面完全失去方向,滴溜乱转。
可算知道这表为什么总走不准了。
在机车送货上门飞进车厢后,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季米扬诺娃医生忙不迭跳下座位,于心里打定主意这辈子宁死也不会再搭邮递员的车。
——————End——————
后续可点击↓
伟大的劳蕾塔·弗农领主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732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