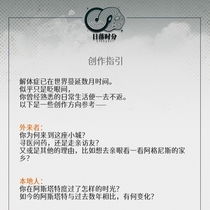『本群作者11月任务』
从以下四个关键词内,抽取一至四个词语作为核心,写一篇不低于1500字的故事,体裁不限,注。作业于【11月30日晚9:00前】发布至Elf主页,并复制网址同步提交至此处,以方便群主在主群提醒读者们参与评论。作业格式请参照原有作业(同人另需标注原作和cp)。超时未提交者将直接出狱。
关键词
1、大雨(鸫君)
2、柳暗花明(旬夜)
3、剪影(人形)
4、磷(灯宵)
【注】
【糖花❤戀戰】活動截止本月10日;
【百鬼夜行錄】第二期截止本月15日;
以上均可替代本月作業,請作者們選擇自己的任務或活動完成。

现在煌黑龙和贝希摩斯都救不了大家了,延时时间结束,开始砍头(悲)
再次感谢愿意参与本企划并努力滑铲打卡的各位玩家!
根据规则,本名单内玩家将被企划除名,角色视作世界观内死亡,并在七天内被清出主群。
由于全靠人工统计,可能出现偏差,如果有打了卡但是出现在名单上的请找企划主消除登记。
-未打卡猎人-
阿斯卡
赫斯珀
-未打卡圣职者-
艾巴盖尔
雷恩诺
艾思
不管各位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了退出,企划主都对以上玩家愿意参与本企划表示衷心的感谢。被除名玩家仍可以选择留在企划审核群投稿新人设重新参企,也可以就此离开。感谢您对本企划的支持与理解,我们有缘再见。
关键词:地面 神代文字
刻意放轻的脚步声在踏过漫长的阶梯后在楼梯口短暂停留,丹特刹住向前迈出的步伐,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用了一半却不知为何被放置的颜料。
“唉……今天这里人还真多。”
他用极小的音量感慨了一句,身体不自觉的转向右侧想继续说些什么,直到视线没有触及任何东西时才反应过来,这种自说自话的行为似乎并不怎么正常。
本来还想着来大圣堂上层巡夜,看来其他人的想法也是这样。不过,既然已经有人巡视就没必要再留在这里了,回去看看欧兰德的情况以后再继续巡逻吧……
丹特一边思考着接下来的行动一边转过身,提灯的光芒随着他转身的动作晃动,在周围的地面上撒下一小片昏黄色的温暖光芒。虽然那只是黑暗中的黯淡之光,但也足矣让拿着提灯的人注意到不远处地面上的异常。
——这是什么?
他俯下身看着地面上用蓝色颜料描绘的符文,在看到它的第一眼,丹特就意识到了那是什么。
——这是神代文字。
为什么会在这里看到神代文字?是谁在大圣堂的地面上描绘它?他无法掩饰心中的困惑,茫然的举起提灯向远处看去,但视线所及之处,中央的地面上有着大量远看意义不明的颜料涂抹痕迹,就如同他眼前的这些一样。
……尽是些无法理解的事情。
丹特无言的低头凝视着那些文字,那是一种奇妙的颜色,在注视着这抹蓝色的时候,就仿佛是看到了天空与海洋的交界处一般。
现在再想这些也没用,等下去以后报告一下吧——
他缓缓站起身,却在挺直身体的时候怔住。原本安静的耳畔骤然间充斥着不知从何而来的低语,声浪如海潮又如天穹一般将他包围。
——你可曾聆听过人们的低语?
无数个喋喋不休的声音撕扯着被迫聆听者的理智,头部剧烈的疼痛打断了他想要寻找声音来源的动作。手中的提灯开始向着地面滑落,丹特反应过来想要抓住它,但身体的动作与大脑的感知已然脱节,最终过分前倾的身体因为重心不稳同样向着地面倒下,发出肉体撞击地面的沉闷声响。
——你可曾聆听过世界的诉说?
他徒劳的伸出手,于是他的指尖沾上了大海与天空的颜色。
但那已非映于灰色瞳孔中之物。





文:阿萦
关键词:假面舞会、炸鱼、本人
文体:小说
标题:她的生活
她步伐轻盈,小礼服很衬她。
她走到他面前站定,说话很直接:“我喜欢你的嘴唇。”
她有一种古典的美,白得像雪,红得像血,黑得像乌檀木。
她先开口,选择权在他手上。
他惬意地靠在软沙发里看着她,评估似的端详了一阵儿才开口:“我们唇形有点像,你也喜欢自己的嘴唇吗?”
“是呀。”她的笑容天真而自信,没有丝毫不适与尴尬。
他笑了,甚至开始有点儿喜欢她,这个舞会不像他想象得那么无聊。
他不说话,她也不怯场:“不知我能否得到坐在您身边的荣幸。”
“哦,这恐怕不行。”这一次他没让她久等。
他放下酒杯站起身,她的个头比他下巴还略矮些,在他面前像个孩子。
他说:“下一支舞快开始了,我想去活动一下。”
她露出了可惜地表情,仿佛是她在婉拒他。
他向她伸出手:“美丽的小姐愿意跟我一起去舞池里转一圈吗?”
甜蜜的笑容绽放在她的脸上,她把手交给他:“当然。”
他不太喜欢这种老式交谊舞,他不喜欢交换舞伴的部分。不过其实他讨厌一切舞蹈,所以就都无所谓了。
他还是享受舞会的。
他喜欢因为舞蹈而兴奋起来的姑娘们,喜欢她们红润的面庞,喜欢她们随着呼吸起伏澎湃的胸脯。
他喜欢在舞蹈时近距离欣赏她们。
她跳舞的样子也很美。像是充满活力的小动物。食草的。
一支舞毕,她气息未平,他挽起她的小手,自然地带到了她称赞他嘴唇的地方。
她大概在轻轻地往他身上靠?他不是很在意。
她说:“您跳舞时的样子英俊极了。”
是了,她还在争取机会。
这不会是最后一句,他还在等。
她说:“我相信您面具下的面容一定更加英俊,只是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见到了。”
他笑了。
她看起来浅薄而急功近利,仿佛因不谙世事而天真。
但他相信她不是,如果她真的只是天真的少女,他甚至没有机会在这个舞会上见到她。
他说:“不了,甜心,今晚不行。
“如果下次舞会你还来称赞我的嘴唇,我恐怕会忍不住向你索要一个吻。
“让我们把更深入的交流留给下次,好吗?
“我喜欢你跳舞时的样子。
“特别美。”
他也喜欢她故作懊恼和羞赧的神情,她的白与红与黑。
但他今晚只想睡个好觉,独自从舞会离开。
天光初现,她回到了家。
饭桌上还摆着昨日没吃完的午餐。
炸鱼早就冷了,盛在盘子里粘成一团,盘底是一片油渍。
真是倒胃口。
她瘪瘪嘴,没去管它们。
她拉起窗帘,脱光衣服钻进被子里。
被子的填料很不好,盖起来不松软也不舒适。晒过几次反复拍打也无济于事。
被子里,黑暗中,她开始抚摸自己的身体。
昨天没能摘下那个男人的面具,生意不太好,她的身体也很难过。
她用手指攻击一样揉按自己的身体,像是不得法门地寻求快感,又像是要进行一些仪式性的破坏。
她的手指探向深处。
深深的。
深深的。
像是要破坏正在抚摸的这具肉体,却不能破损它的外壳。
真是神奇。
没有多少快乐,其实痛苦也一样。
眼泪流出来,干在脸颊上。
她没有擦去泪痕,没有喜悲地睡去。
她没有逃脱梦的荣幸。
妈妈尖锐的声音和皮肤上尖锐的疼痛混合在一起,深深地钻进她的脑子里。
“学好这些才有机会嫁个好人家!”
“你难道不想过更好的生活吗?”
“你怎么这么笨?别人都学得会你为什么学不会?”
“你又开小差了!你不用心!你态度太差了!”
“你看我干什么?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要我告诉你吗?”
然后是少女时代女伴的声音——
“天呐!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
因为我想让我妈气急败坏……
“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呢?”
只有完整的东西才会破碎,已经坏掉的东西……没人在意了。
“我从没想过你居然是这样自甘堕落的人!我看错你了!”
看错?你何曾看见过我呢?你们每一个人,都只从那个女人嘴里了解我,又有谁在意过我自己,我本人呢?
最后是桑吉的声音——
“哦,一个好姑娘。”
“长得不赖。”
“身材也不错。”
“你还会跳舞?”
“绘画也知道一些?”
“你真是个宝贝。”
“你愿意来参加我的假面舞会吗?”
我,愿意。
文:回音壁
关键词:深度
文体:小说
标题:下潜
评论:随意
有人认为时间是一条线,“现在”就是它的原点,一边是过去,一边是未来。也有人认为时间是一棵树,“过去”是扎入无数可能性的根须,“未来”是伸展向无数可能性的枝桠,唯有“现在”是孤壮的树干。还有人认为时间是一条长河,无数支流汇入“现在”,又有无数支流从“现在”汇出。
而每个时空治安官都知道,时间并不是以上任何一种东西,它不能用以上任何一种方式描述。它就像一片虚无的平原,过去、现在、未来……在这片平原上,它们是混沌的、糅杂的、虚无的。
时空旅行,就像是在平原上打井。
只不过,井里不会有清泉涌出来。
井会停留在平原上,或者自然塌方。塌方的井会把打井人连同井里的东西一起掩埋,掩埋后又是原本的平原。
平原不在乎。
一名治安官在时之平原上游走。
如果有人能从第三视角看到时空治安官,可能会产生“它并没有移动”的错觉。因为在时之平原上,空间本身就是混沌的,因此距离也是一个很难说存不存在的概念。
唯有当祂开始下潜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它是在“动”。
治安官落入井中。
祂有在平原上打井的能力,但祂一般不会这样做。毕竟,祂的职责是阻止无知的凡人打井,再把井填埋起来,而不是相反。
治安官开始下沉。景像开始改变。虚无、无形无相的“时间”转换为具体的影像,这就是“历史”。
祂看到一个老旧的房间,窗户对着西边,但对面的高楼挡住了阳光,让房间中的光线变得阴暗,渗透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颜色。
祂看到一个初老的男人,佝偻、瘦弱,肌肉松驰,穿着旧而廉价的衬衫,手里拿着破旧的枕头,枕头上留着唾液和涕泪的痕迹。
男人的妻子躺在床上,和男人一样衰老、肤色暗哑而粗糙,长久不健康的痕迹都反应在脸上。只是这些对她都失去了意义。毕竟,死人是无所谓健康的。
男人喘着气,开始流泪。治安官知道,他在悔恨。
治安官就在他的身后,但他无知无觉。毕竟,他对于治安官来说,只是影像罢了。
治安官微微开口,他的声音与男人的声音混合起来。
“时间是一口井。只要下潜得足够深,就能找回遗失在过去的东西。”
“下潜,下潜……只是不要忘记携带绳索。”
男人下定了决心。他似乎立刻就明白了要如何下潜。光线模糊了,影像开始改变。男人的形像慢慢变化,身体变得挺拔,头发变得乌墨而有光泽,松驰的肌肉变得紧致,而自信出现在那张变得年轻的脸上。
房间消失了。他出现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他睁开眼睛,像刚从一场恶梦中醒来。来自未来的记忆让他的精神稍有些迷离,但转瞬间,他就下定了决心,依循着牢记在心中的道路迈开步伐——是这个年轻的他本应不知不觉走上、但年老的他已记忆了三十年的道路。直到他完成了偶遇,那名少女,青春的活力和姣好的面容让她比阳光更加美艳动人。
治安官就在他身后,看着这影像。祂注视着少女,像注视一张名画。祂看着男人与少女交谈,与上一次不同,男人并没有毛毛躁躁地激怒少女,他熟知少女的想法,不仅是现在,还有未来三十年的。
治安官看着男人与少女结识,相爱。也看着男人创业、收获,看着他如同神助般赶上每一个风口、避开每一个雷区,每一笔投资都能拿到最大的成功。男人慢慢变老,但他的身型并没有变得佝偻,肌肉也没有变得松驰,少女成为妇人,又进入中年,但她的皮肤始终有光泽。
祂看着男人用绳索勒住女人的脖子。祂再次开口,让自己的声音与男人的自言自语混为一体。
“下潜,下潜……只是不要忘记携带绳索。”
祂看着男人再次取回青春,再次与少女偶遇,他选择成为一个普通的职员。他从不会犯下过错,也从不确立功绩,家境平实,小康安乐。
这一次是水果刀。而治安官的话语并未改变。
祂看着男人的人生。
工程师的人生。司机的人生。厨师的人生。家庭主夫的人生。快递员的人生。理财经理的人生。程序员的人生。农民的人生。海员的人生。老师的人生。流浪汉的人生。家政保洁的人生。饲养员的人生。作家的人生。音乐家的人生。主持人的人生。便利店店长的人生。逃犯的人生。茧居者的人生。每次人生都以一种凶器作为结局。
“下潜,下潜……不要忘记携带绳索。”
时空旅行就是在时间的平原上打井。每一次下潜,都会让井的深度更深。
空气逐渐变得滑腻,变成了某种像粘液的东西。阳光变成淡红色,又变成绿色,最终变成某种无法照亮任何东西的颜色。而影子变得耀眼夺目。
在建筑师的人生里,人们住在某种倾斜的弧线三角形的物体中。非法商贩的人生里,口香糖、椭圆形的珠子和一种带锯齿的短棍成为货币,人们用它们来交易一种粘稠的混合着沙砾的胶质。猎人的人生里,粉红色的、颤动的肌肉纤维牵拉在整个城市中,包裹着脆弱的神线维管束。护士的人生里,黑灰色有四十三对翅膀的蠕虫运营着正十二面体的短视频终端。注射大使的人生里,十二只半开半闭的眼睛吞食吱叫的粉红色黑板。镶嵌牛角与脚印吞食者的人生里,三角形的内角和随机改变,0和1之间偶尔有新的整数出现又再消失。要三悬念断三尖的人生里,雁霍布斯一的法螺零用感动苛其天人。
男人不再是男人,女人也不再是女人,虽然其中一个依然有着大概来自未来的类似记忆的东西,另一个在治安官眼中仍然美艳动人,但他们是某种由伪足、环节、尖锐的半流体和成捆的布满破洞的管子缠绕成的、会动的东西。
只有凶器依然是凶器。虽然治安官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但治安官按照它们最后的功能判断它们依然是凶器。
时空旅行就是在时间的平原上打井。每一次下潜,都会让井的深度更深。只要下潜得足够深,就能找回遗失在过去的东西。
只是不要忘记携带绳索。
治安官就是绳索,只是祂想要吊出井口的东西,依然没有找回。
下潜,下潜,下潜。
文:拾阶
关键词:深度
文体:小说
原作:《摩登三国》
cp:曹操×陈宫
#有一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cake&fork设定
抽烟易导致口腔溃疡。
陈公台过去从来没在意过这句医嘱。
当他还领着中牟县县令的俸禄时,陈公台一心想让自己死得快一点。这一隅之地的诸多琐事,日复一日,并不繁重,只是足够消磨掉人的意志。生逢乱世,人命如草芥,如果没办法改变它,那还不如早些透支掉这人生。
口腔溃疡反而很少来找他的麻烦。955作息的公务员,偶尔加个班,俸禄虽说不高,养活一家老小也绰绰有余。但凡谁敢像他陈公台这么不要命地摄入重焦油和尼古丁,大概都能维持个不上不下的好心情。只是偶尔溃疡长得不是地方,先被滤烟嘴蹭到,再被充满口腔的辛辣烟雾刺激,尖锐的痛楚足以让人倒抽一口气。
他倒乐在其中: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难得抓住这么一点活着的实感,挺好。
——
决心戒烟之后,陈公台才真正领略到这毛病的磨人之处。
右下角的时间早就变成了0打头,报表里的一行行数字全是重影。昏昏沉沉中,手指不自觉探进裤兜,捻了根烟出来。动作行云流水,本能一般,直到滤烟嘴含进嘴里才发觉有异。
青葡萄味的维C棒清清凉凉,像可供吸食的口气清新剂,提神有限,甚至连补充维生素的效果也值得怀疑——没日没夜加班燎出的一嘴溃疡丝毫没见好的趋势。
戒烟更易导致口腔溃疡。陈公台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想起当初那句不知道在哪听到的医嘱,心里头讪讪地添了一句。
有总比没有强。陈公台摇摇头,咬着戒烟棒猛吸几口,起身拎起椅子上的外套,准备躺在旁边的折叠床上眯一会。
兖州刚刚接手,即便有陈公台这个熟悉地情的本地成员在,仍有成堆的开荒以及交接工作要做。后勤采买了一批折叠床和睡袋堆在各自的办公室里。996乃至007的作息已经维持了几个星期,所有人都在靠意志力和意式浓缩撑着。
除了曹孟德。
小臂被从脸上挪开,嘴唇上传来濡湿的触感,还有点痒。陈公台犹迷迷糊糊,勉强睁开眼睛:“曹孟德?”
回应他的是一声轻轻的“嗯”,以及趁开口时探进来的舌头。
两个人哪一个都不清醒,曹孟德吻得毫无章法,勾着他的舌头来来回回地吸吮。加班太多就容易精神失常,关于他的老板最近时不时半夜跑来发疯这件事,陈公台已经习惯了。疼痛也敌不过疲劳,他重新闭上眼睛,予取予求,只是双手搭在了曹孟德的腰上,避免从狭窄的折叠床上摔下去的事故重现。
溃疡面很快渗出了血,舌尖齿间全是泛着腥的咸味,压上来的人反而疯劲上头,捧着他的脸吻得更加起劲。陈公台彻底痛清醒了,皱起眉,在曹孟德的后脑勺上敲了一下。
没反应。陈公台只好稍使了些力,又敲了一下。
曹孟德知难而退,发出一声轻轻的鼻音,听着是已经困懵了。
陈公台本想低低地骂一句,见状叹了口气,把他从身上搬下来,起身冲去了卫生间。
漱口的清水吐到洗手盆里,已经变成粉色的,搀着一些血丝,在惨白的灯光下格外唬人。更要命的是,满嘴的溃疡痛得人无计可施,焦躁得很。哪怕重新咬了根戒烟棒在齿间反反复复地碾,也丝毫无助于缓解。
算了,横竖这老板是他自己选的,担子也是他自己揽的。陈公台深吸一口气,往脸上拍了点水,戴上眼镜重新坐回了办公桌前。
晃动鼠标后,他往身侧看了一眼。
把他折腾到被迫继续加班的罪魁祸首鸠占鹊巢,正趴在折叠床上熟睡。电脑荧幕的光落在曹孟德的侧脸上,把浓重的黑眼圈和杂乱的胡茬照得格外显人憔悴,衬得面色更加难看。陈宫想了想,到底没起身去开顶灯。他扳开桌灯的开关,又把刚从曹孟德手里抢回来的外套披在了那人身上。
——
真正发觉这医嘱确有道理,已是身在下邳。陈文台捡起重焦油,抽得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凶。口腔溃疡重新找上门,发作的程度远甚于当初不分昼夜地疯狂加班。
下邳城几乎弹尽粮绝,负隅顽抗。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曹军迫于粮草压力,自行撤退。他如今每日无事可做,又总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做来做去,最终大概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来加班对这毛病没什么影响。陈文台吸着辛辣的烟雾,不无自嘲地想。
他拿下烟蒂,伸手在堆得快满溢的烟灰缸里按灭。滤烟嘴上无一例外地沾着血,说不清是来自于溃疡的口腔黏膜,还是干裂出伤口的嘴唇。
陈文台决心再去见一次吕奉先。他心知这一次,这位主公多半仍不肯听从自己的谏言。
他披上外套,看了看窗外灰蒙蒙的天色:冬天的雨格外阴冷,但愿它下久一点,逼得曹军早日撤回才好。
初十,大雨倾盆,漫天水幕。
临湘城北有一座小小的客栈。不过十来间客房,客人也是常住不满的。
炎炎暑气被暴雨驱散,昏暗的天色。凉爽的水汽让人忍不住泛起困来。掌柜兼小二正在柜台上撑手打着瞌睡,倒不是偷懒———整个大堂内也不过角落一桌客人而已。
恍惚中似有嘤嘤哭泣之声,奈何夏乏正狠,掌柜咂巴了下嘴,换了个姿势入睡。
坐在嘤嘤哭泣家伙对面的男子痛苦地揉着眉心,还要一遍遍地给对面那只妖怪倒茶,时不时温声安慰:“多喝热水。”
哭泣的家伙狠狠地擤了一把鼻涕,细长的狐狸眼肿得像门缝,半点也没过往的风姿。它哭哭啼啼地向桃花道人抱怨:“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就不应该下山,我要是不下山也不会遇见我二姑妈家三姨奶奶的外侄孙女的儿媳妇家表妹的堂姐的外甥,我要是不遇见我二姑妈家三姨奶奶的外侄孙女的儿媳妇家表妹的堂姐的外甥,我就不会去镇上,我要是不去镇上我就还是清清白白的好狐男……”
它可怜巴巴地哭诉自己的委屈:“您知道我们公狐狸过得有多难吗?母狐狸们根本不愁白嫖清白小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只需自己建一个庄子,就算知道母狐狸们身份可疑,那些做着妖怪痴心一片美梦的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送上门来。如今世道步入正轨,都是合法的买卖,只取一点点元阳,薄利多销,连地府的阎君上来查过几次都不曾取缔。”
它抹了一泡眼泪:“我们公狐狸呢,想取一点元阴那是千难万难,一不小心就要背上一条痴情的人命,叫那七十二道天雷劈个稀碎。”
“理解理解。”桃花道人将面前的茶杯推给对面的公狐狸,“那妇人虽然找我告状,但如今我见了你,气息清和纯正,倒确信你未曾害人性命,自是不会冤枉你。”
公狐狸打了个哭嗝,听桃花道人提起罪魁祸首,周身气息更是悲愤:“哇……她太欺负人……狐狸了!”
有道是乱世出妖祸,如今国泰民安,人世间一片祥和,妖怪们也大多安分守己。但修炼还是要修炼的,日日夜夜都要靠修炼才能勉强维持生活的样子。
新生小妖代越来越多,修炼资源也越发紧张,如何快速有效地改善修炼进度已经成为妖众们需要好生思考的问题。
泰山府君向来公正严明,经过妖界老辈的多番上访求诉,总算在人妖灵三界立下了新的规矩。
那就是交易。
合理合规的交易。
不违背人类的真实想法,不扰乱社会安定,不影响人类的健康寿命的前提下,通过交易获取少量的精元。
人是天道之子,数量之多,就算是取这微量的精元,也足以让新生小妖代们平稳地度过幼妖时期了。
若是某些急功近利或者是贪婪成性的妖邪,迫害了凡人的性命。那么就需要行走于世间的监察者出来维持秩序。
桃花道人,算是其一。
除了偶尔有比较强大的妖邪为害,大部分时间桃花道人接到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纠纷。
比如说被黄鼠狼用大母鸡在梦中交易的苦主在第二天早上发现收到的是一只瘦苦伶仃的小公鸡,比如说路遇美妇一夜云雨便想娶回家结果被拒绝就恼羞成怒上门诬告妖怪害人的贪心男,还有明明点名要的是身娇体软易推倒的美娇娘结果睡到的是美娇郎……
但是像哭得这么惨的公狐狸,桃花道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惨得活像隔壁攒了一年的坚果结果被人类无意中发现全部拉走的松鼠。
此事,还需说到三个月前。
公狐狸在这窝崽子中排行第二,且叫他狐二郎。
狐二郎原本在山中与父母为伴,虽茹毛饮血,倒也无忧无虑。只是不知从何时开始,父母看向他的眼神开始充满了愁绪。
"我家的二郎可怎么办呢?"狐二郎偶然听见母亲与父亲在洞里念叨,"这般大的年龄了,竟还奔于山间偏野里,丝毫没有身为妖族的志气。"
妖族的志气,又是什么呢?
他只是听说成型的妖怪都要下山历练,若有所成方才荣归故里。
他身边的姐妹,早早地便跟着伙伴们下山修行,只有他,伙伴一不小心都吃光了。咳……
总而言之,或许是到了下山的时机。
就今日下山罢!狐二郎这般想到,妖族寿命长久,倒也不需一时之间的告别。他整理了自己的小包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山洞。离开的时候,心中未免有些空落落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绪。
直到四个时辰以后,他才终于懂得,那是好像忘掉了点什么的情绪——他忘记问父母妖族下山历练到底是要做些什么?
好在遇上了他二姑妈家三姨奶奶的外侄孙女的儿媳妇家表妹的堂姐的外甥,虽然长相略有些眼生,但身上的气息俨然同出一辙。两只狐狸攀谈许久,总算确定了互相的亲戚关系。
那只狐狸见二郎懵懵懂懂,便自告奋勇做起了二郎的向导,告诉他山下不远处有座镇子,虽不是十几万人的大城,但也有几位狐族亲友混迹其中。他拍着二郎的肩膀,感叹道:"若不是世道艰难,谁又愿意远离家乡呢?"
狐狸问二郎,下山是想做个长久的买卖,还是随缘而定。二郎一向稳重,自然是打算先签订个中长期的合同。狐狸便教他:"我瞧你这化形也就略称清秀,靠脸吃饭显然是不太靠谱。尤其不可去寻那些单纯清白的娘子,否则难以脱身。你且去找个贪的,与她多些金银类的交往,来回几次,交易便可成了。"
狐狸叮嘱道:"你可要记住,第一次交易,你可一定要问'我与你讨件礼物可好?',她若是应了,才可拿些精元,否则是要叫府君大人抓去的。"
狐二郎追问道:"那怎么知道那女子是贪还是不贪呢?"
狐狸笑答:"这还不简单,你且多去那绸缎胭脂首饰铺子,专瞧那些逛得多买得少的。这类女子想来经济不甚宽裕。你再装作偶遇,言见之有缘,非要送些礼物。若轻易便送出去了,又不见回报,便是那种贪的。"
狐二郎顿觉言之有理,千恩万谢,背着小包袱便去也。
到得镇上,住得几日,真叫他寻上一位。这妇人新寡,时下流行的胭脂水粉说得头头是道,又极为贪嘴,便生袋里摸不出几个新鲜的银钱。狐二郎既瞧中了她,便巴巴地登门诉说了相思之意。
此地民风宽泛,倒也不太讲究寡妇二嫁。就是狐二郎长相太过普通,穿着朴素,妇人打量二郎的眼神便审视起来。
"你说爱慕我,爱慕在何处?"妇人追问道。
狐二郎支支吾吾,好半天才勉强说出贪慕妇人颜色这等话来。
妇人半信半疑,但眼中还是透露出些自得的喜色。见二郎呈上的玉镯,心中欢喜,看二郎顺眼了一分。便应道:"那我且看看你的诚意。"
二郎见事情有望,心中自是欢欣鼓舞,将自己小包袱里的宝贝换了好些银钱,买上最新的胭脂水粉绫罗绸缎,一日日地往那妇人家中送去。
送了半月有余,见那妇人神色松动,期期艾艾地说出了那句话:"我与你讨件礼物可好?"
妇人听了这话,眼中笑意便淡了。她瞪了狐二郎一眼,转身便进了屋子,那关上的屋门差点拍扁了二郎的鼻子。二郎心中纳罕,还未回过神来,屋门突然又开了,就见着原本送妇人的礼物一股脑从屋内丢出,砸回了二郎的脑袋上。
"我且道你有些诚意,万没料到竟然是如此计较回报的家伙!"妇人怒气冲冲地嚷道,将二郎赶出了院门。
狐二郎是一头雾水,却连忙抱住妇人大腿,一番哭诉道歉,连续几日又是连连不断地礼物送上。
且又过了半年有余,二郎心道时机成熟,又再次问出了这句话。
谁料又被这妇人劈头盖脸一通痛骂,之前送去的礼物再次原样退回。
狐二郎满腹委屈,只道自己真是诚意不足,连一点点微末的小心思都被瞧了出来,只得连连服软,继续了送礼之旅。
这般一而再,再而三,日子便拖了三五年。
狐二郎的小包袱空空如也,精元是一分不得。他心灰意冷,直觉这人世难料,妖族的志气也磨得七七八八。
他想,这下山的历练果真不是谁都能做得,他也不求荣归故里,还是回山里晒太阳吃些新生下来的小伙伴为好。
也不知道那妇人从哪里听闻到狐二郎要离开的消息,带着一众家属迈着步子怒气冲冲地找上门来,揪住他的衣领愤怒大骂,道狐二郎是个渣男,玩弄妇人感情。一群人围着指指点点,吓得狐二郎心神俱裂,一不小心现了原形,化做一只狐狸逃窜而去。
桃花道人拍掌而笑:“惨惨惨,你只道人欲之贪婪,却不知貔貅之性——许进不许出也!”
文:旬夜
文体:小说
关键词:本人
备注:来源于一个不知道结局的梦
1、
半吊子的咖啡店开在海边。
不算这片开发区最热闹的地方,赚钱的夜市开在半公里外的大沙滩上,到了晚上都灯火通明。
这里白日客人多,到夜里海风吹过海面像是下一秒就要将整个世界裹挟进深海中。
靠海的都怕风。
贺子桓来这的第二年就刮了一次台风,整个海边店面全都关了门。
回来那天他们顶棚被掀了一半,招牌“棋路”的路子剩了个“各”,足字旁进了海里,露出里面盘根错节的电线。
这店里三个店员兼店长都是他们自己,其中一个兄弟当初有些门路,内部价拿了这儿的店面。原来以为是中心地段,结果偏了点,当然这个“点”是那位哥们咬字着重强调过的。
反正,两年多,生意还算凑活。
来他们这儿的大多都是漂亮姑娘,年轻小伙,成群结队,有的开着小车,嫌弃中心区收费贵,就也偏到了他们这儿。
小咖啡馆,冰饮热饮有,甜点小吃也有。
贺子桓店后门对着沙滩。设了一个栅栏,成天日晒风吹,沧桑得很,表面剥落了,露出里面木头的纹路,上面用各色笔写着到此一游,或者是一排铁链扣着情人扣。
见到马栎杉的那天,贺老板正穿着沙滩裤,手上拿着个椰子对着愁苦的大太阳思考人生。
因为二店长严书棋为了给自家女朋友做刨冰,把厨房给叫的一团乱,而大店长程成橙烤羊肉肠给后厨搞得一股味。
贺子桓了撂挑子,抱着开好的椰子,抽根吸管就出来避难。
冰镇的椰子汁水顺着便宜的蓝白吸管顺进食道里,甜的同时还带着古怪的水果味。马栎杉坐在栅栏最外面的那个老旧木桩上看海面,还风吹着他的衬衫吱哇乱转,像是下一秒就要被吹飞的蓝白色风筝。
贺子桓走了过去,抓这眼前“风筝”的手,说道。“先生,这个是用来挂情人扣的,不能这么坐,哪怕你很轻。”
那时马栎杉回头看他,清冷的五官上露出一点温和。海风吹得碎发迷了眼睛,他说。“是吗,你看着也很轻。”
-
马栎杉是一个人来的。
将入秋的海滩成了这个沿海城市人们最乐意的来的地方,太阳不那么炙热,风吹在脸上依旧是暖的。午后海水滚烫又飞快冰凉起来。
海边的沙滩在夕阳里,会被海水和黄昏吞噬,砂砾一点点凹陷下去,露出里面死亡的贝类。
贺子桓在海滩边一共见过马栎杉四次。
第一次是在情人锁的木桩上,第二次是海边的灯塔。
那个废旧的瞭望塔已经很久没有使用,它的灯泡坏了,伫立在夜里像是海上的墓碑。偶尔会有飞过的鸟在上面休息。那天傍晚,他顺势望过去,灯塔最高处的空窗里露出一截白色的衣裳,一个青年人探出头,白色的衬衫随风飞驰,好像下一秒就要坠落。
贺子桓那时飞奔过去,手上给客人准备的烤鱿鱼和两扎啤酒都摔在地上。
沙滩稳稳接住它们,啤酒开心得吐着呕吐似的白色泡泡——噗嗤——噗嗤——
“喂!你怎么上去的!快下来危险!”
“你——叫我吗?”远远的灯塔上,青年人对了一个口型。他在海风和夕阳昏暗的光线里辨认对方的意思。
“我,叫,马栎杉——!”
“啊?”
“马栎杉——!
“什么妈,妈什么妈!你快下来!”
-
他和他在那座灯塔上喝过啤酒,向下丢过花生壳,当然还有谈天大笑时不慎掉落的鱿鱼卷。
晚上无人的海滩,他们的孤岛一样的灯塔里被海顺吞没。
直到夜晚结束,直到他们都沉沉欲睡,
不远处海平线泛起白肚,整个世界是听涛一般静谧的蓝白色。
那时马栎杉靠着空空的窗洞,融在那片蓝中,像是昏暗的白日,又像是坏掉的老旧电视机,放着冒雪花的港式音乐。
“很高兴认识你。”
阳光升起。他抓着手上的啤酒瓶,绕过黎明拥抱了眼前的贺子桓。
空气里有海风的气味,有不远处渔港船只的汽油味,有啤酒残留的麦芽气,还有马栎杉身上的味道,冰凉凉,带着冬眠前,植物残存的气息。
那并不像一次约会。
而是一次来自海妖的邀请。
海妖将出海的水手引诱进自己的巢穴,给予他编制梦境,并挖去他心脏的一部分,将自己放了进去。
水手并不知情。
-
冬日将至的季节里,海滩上会有烟火。
贺子桓的店里加他拢共三个店员。平日里忙的时候就连轴转。
还未正式步入冬天的时间里,来海边的人并未减少,就像有人爱去俄罗斯的冰天雪地里来露天烧烤一样。没有人会不爱烧烤,如果不爱,那还有火锅。
在海边支起铁架子,电烤摊子噼里啪啦,海浪还有远处中心夜市的灯光,像是把整个冬季都无限期延后。
马栎杉手上提了一堆礼物,被贺子桓抓来当苦力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步入精神病的恍惚。仿佛在说哥是来人间是喝露水的,您让我来撒孜然合适吗?
合适。
当天噼里啪啦爆汁牛丸和芝士焗土豆都表示很合适。
贺子桓是个生的好看小算盘哐哐响的奸商。
马栎杉穿着侍应生的衣服,被迫游走在沙滩和后厨,他看似轻车熟路,实则手上不稳。
但他能装。
当天的啤酒销量被卖出了新高。程成橙和严书棋在调侃贺子桓那嘴巴厉害,还能忽悠个这么好看的小工。贺子桓数着账单小票,回头看着故作镇静的马栎杉偷偷笑出了声。
新鲜的牛奶被冲进萃好的可可中搅动成旋涡。
热乎乎刚出炉的小食被运上桌,在嘴里嚼上半日能吞下人间烟火气。
他们忙碌地擦身而过,运作的咖啡机和后厨闷热的锅气,轮转在海风侵袭的冬夜中。有吹落树梢的雏鸟滚落,风吹乱它的绒毛,它暖烘烘又毛茸茸,发出“啾啾”的声音。
-
这一张条海边商业区,属于市内政府开发项目。前三年竣工才做了点宣传。
每日七趟车三小时一班,准点就开,从不等人。
入夜了。
夜深人静的山路上,末班车发出三声开车鸣示,车灯亮起,沿着漆黑的夜划出一道亮色,接着顺着山道蜿蜒而上。
贺子桓从店门里走出来时。
马栎杉正站在海边由着海浪将他的双脚一点一点埋进贝壳里。
远处唯一的电线杆发出明灭的光线。所有一切指向不明,只有一排黑色的剪影。
“你说,还有多久,它们会把我吞没?”他像在问他,又像在自言自语。
贺子桓走过去,学着马栎杉脱了鞋踩在海水里。
入秋夜里的水像针,密密麻麻钻紧骨子里,他们的脚泡在流动的水中,被带走温度,置换了属于人和人的亲密。
“真冷。”贺子桓握住马栎杉的手,指尖不轻不重地扣住,温度却冰得像是不属于人。
眼前人像是被一阵风吹来,落在这片海边,单薄的衣服和细瘦的手腕,像是随时都要消失的旅行者。
贺子桓看着他,忽然心头一动,将他们收握紧。“周末中心区有一场活动,你要不要来。”
马栎杉偏头在海风里望着他。“为什么邀请我。”
“为什么不能邀请你。”贺子桓很疑惑。人和人如果要发展亲密关系,他们都必须要获得独处的空间。——他也许是在向他约会。
“你想和我约会吗?”
贺子桓看着马栎杉,又低头看着他们扣住的手。“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马栎杉沉默着没说话,要说什么,很久,像找不到答案似的叹了口气。“贺子桓——”
“嗯?”
他走了一步,脚尖带动海水,发出安静的回声,水中的沙细而绵软,前倾的时会将脚趾尽数埋进去。
“邀请我是需要礼物的。”
隔岸不夜的中心商区,焰火被点亮在天幕炸开。那一刻,贺子桓在在河岸焰火里,感受到了唇间冰冷的触碰。他听见马栎杉轻又缓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如果可以,真想和你在未来看太阳。”
-
他等过他无数次。
在无人的街道,落雨的公交站,还有那些雨后晴空的咖啡店外。
他等过他,在无数个冬天和夏天。
然后让春秋沉在记挂他的长长梦里。
周末的商业街总是人来人往。
那天小老板在约定的地点等了某个人一天,他手里抱着那个作为他们初次“约会”的礼物。
商业区奶茶店里依旧有热可可的气味,混杂着不远处随手面包的小麦气味,贺子桓在太阳底下,一双映着光的透进虹膜,像是一颗浅黄色的琥珀。
他那天等了他很久,直到夕阳西下,那双琥珀色眼睛混进晚霞的橙红色。
没等到人的小老板把最后把礼物扔进附近的垃圾桶里。
那是个拍立得。他逛了一个晚上买的。
他本以为马栎杉会喜欢。
-
贺子桓回头看向店里的时候,海边远远望去一片漆黑。
程成橙和严书棋已经开始收烧烤架。
海边的咖啡馆到了冬天关门的时间总是早了些。
路上只有几个路灯闪烁,风从路两旁房屋的缝隙里吹来,他把手上的包甩了甩,进门的瞬间顿住了脚步。
“嘿,小马等你半天都要走了!”
“怎么才回来!?”
贺子桓愣住,他顺着方向望向后门的位置。不远处情人扣的木桩上,马栎杉穿着一件黑色外套,他回头看他,站起身,手上正提着一个行李包。
贺子桓觉得有些不对,他朝前踏出一步,远处的马栎杉却往后退了一下。
明明隔着那么远,他却看清了对方的表情,马栎杉只是看着他,眼神一如往日平静。
却不知怎么的好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他在害怕?
贺子桓心跳漏了一拍,下意识想朝对方走去。马栎杉却快了一步,提起行李就往外跑。
人的直觉究竟有几分准贺子桓也不知道.但他有种预感,如果现在没有追上那个人,他也许就会消失。身体的反应速度比往常快,可是黑衣的青年人窜进夜色里几乎找不到影子。
“马栎杉——!”
四周是深夜的海岸,狂列的海风被黑暗浸没裹挟着不远处的浪涛声。
“马栎杉!”
他又喊了一声,四周空荡荡一片。
下一秒,远处海滩废墟里传来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一瞬间,他满脑子是那个人刚刚看他的眼神。
黄白色刺目的光线像是一把利刃隔断了浓稠的黑夜。
他睁大眼,那一秒,黑色的海岸边,所有仓皇和恐惧,还有远处刺目的火焰全部映在了他放大的瞳孔里。
-
你有没有见过他?
谁?
那个在海滨瞭望塔上被炸死的,我的心上人。
-
贺子桓在一年半之后,离开了他的小咖啡店。
店里招到了新人。是个漂亮小姑娘,面试的原因是喜欢上大门后贺子桓设计的情人扣。
她有天问贺子桓,马栎杉是谁?为什么和他的名字写在一起。
贺子桓喝着果汁说说,哦,那是一个在瞭望塔被炸死的倒霉蛋。
程成橙赶紧过来把新店员揽了过去。“听他放屁。那个瞭望塔一年前遭不住台风塌了一半,后面政府给拆除了。我们这是半个旅游商圈,要爆炸死过人生意还怎么做。”
也是也是,谁都没有见过那次爆炸。
就像谁也没有见过马栎杉一样。
-
贺子桓一个人度过了很多的冬天。
冬日下雪的街道他习惯一个人,回头的时候,看自己的脚印。
那没有遇到过他的爱人,就像他至今无法确认马栎杉是否存在。
他只是在那个破碎的幻觉里,记得那场爆炸的大火。和他在废墟里掘出的属于他的残骸——那并算是一个人的身体,横截面平整光滑,像个人偶。
那个人偶静静闭着眼,浑身绷带,露出它断裂的手臂的胸腔,却长开手臂,像是拥抱。
又像是等待着他的挖掘。
他的马栎杉消失了。
他开始将自己藏匿进长长的梦境里,去重复那个遥不可及的夜晚——在某个四下无人的夜里,他提前一步,拉出即将离开的马栎杉。问他,我怎么才能救你。
那是他万分之一的祷告。
他想也许有天上帝会听到。
-
2020年12月12日。
贺子桓从梦中醒来。
那日清晨阳光普照。
冬日的风还未来得及席卷这座南风城市。
他披着风衣,从咖啡店里出来,路灯闪了两下,由绿转红。
导航开启,系统提示离他下一个要到达的目的地还有1.8公里。
头顶掠过影子,贺子桓抬头,望着天空掠过的鸟,按下了手机快门。
四周都是往来的上班人群,还有上学的学生。
远远有汽车鸣笛。
红灯转绿,人潮向前。
他手机里最新的照片,是鸟类空中一闪而过的剪影,像是某种模糊的幻像。 ——有人和他擦肩而过。
他说。“好久不见。”
十几岁出头的少年人背着单肩包,穿着白色衬衫。他比他印象里的马栎杉小了好几岁。他抬头看他,像是赴一场蓄谋已久的约。
“我来了,陪你看太阳。”
-END-
评论要求: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