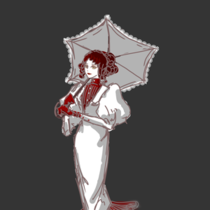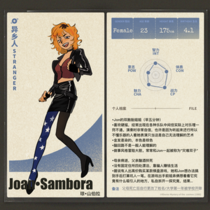双城之战同人,没玩过游戏所以只算动画,设定有出入当我吃了
评论要求:随意
金克丝小的时候其实很喜欢猫,但祖安哪有什么地方能给她留一份柔软的余地,只有偶尔在角落画的带着笑脸的猫头留下了点痕迹。
后来她被希尔科捡回去,希尔科并不约束她做任何事。那时候祖安开始大规模使用微光促进进化,她有时候就会带着一小瓶没封好的微光出去诱猫。但她在第无数次发现,自己手上掐住的是已经冰冷的死猫之后,就不再愿意主动逗弄流浪猫了。虽然,那些猫早在很久之前,就除了想要争夺她手上的微光之外,不肯接近她一步了。
但所有的故事总有例外,有一天夜里,还下着雨,有只湿漉漉的小猫勾住了金克丝的鞋子。
金克丝一开始没想再捡一只猫回去的,但是这只猫一直往她身上磨,她丢开它,它又向她爬来。她有些不耐烦,但在不远处看到了半个被啃到难以辨认的猫头之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把猫带了回去。
其实她也没怎么管,或者说根本不会管,但猫很快学会了在房间和街道中抢夺食物,然后再回到金克丝的房间里睡觉,就这样猫和金克丝一起成长起来。偶尔希尔科会给猫喂上几滴稀释了的微光,在药物的刺激下,这只猫越长越狰狞,连身体都泛起微微的蓝光,只有蜷起来睡觉的样子还像一只普通的猫。
后来,后来猫怎么样了?金克丝皱着眉头回忆,她头又痛起来了,很多事情模糊下去,面前的世界也扭曲变形,蔚的脸又浮现出来,她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是长大了的样子,她在对金克丝大喊,但金克丝听不清楚,只有不同的混乱的来自童年玩伴的指责在破损的一切里显得清晰又不可忽视。
金克丝想要知道蔚要说什么,她努力地盯着蔚,只能从她的口型中看到一个“死了”,什么死了?蔚死了吗?还是她在指责她害死了所有人?
那不过是一个意外!金克丝抱头尖叫起来,总是这样,所有人都这样说,她注定要给所有人带来不幸,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想要帮忙,我没想要弄糟任何事!
等得她再度找回现实,她发现房间里一片狼藉,而猫在她手边默默地舔舐着毛,不为所动。金克丝一下放松下来,她甚至哼起了歌,跳到桌子上开始从纸屑和木屑中找她想要的东西。
希尔科推门进来,环视了一遍她的房间,颇为自然地坐到她身边,把那只猫抱起来,顺着脊柱一路轻点下去:“金克丝,过来,帮帮我。”
金克丝知道希尔科需要什么,她打了个响指,从桌上一跃而起,辫子砸到希尔科抚弄猫的手上,猫伶俐地跳了出去,下一秒金克丝落下,被他抱住。她接过希尔科递来的注射器,木制的外壳上有着太多属于她的痕迹,她用它转了个漂亮的圈,然后抬手将它举到希尔科头顶。
金克丝以前开玩笑地抱怨过希尔科缺乏一些人类的面部表情,于是她画了个大大的希尔科漫画像,那被希尔科有意遮掩的半张脸上的义眼柔和地凝视着她,另半张脸又开始扭曲起来,该死的,世界又变得无法控制起来,她真的看见了蔚,她在和另一个蓝发女人相拥,她看起来是个高贵又可恶的上城人,随时可能夺走她的一切。她几乎能喊出什么,但又在张嘴的那一刻遗忘掉了。一定有什么东西出错了,她确信。她在真空中打转,想要抓住什么,但手上只有空气,蔚好像真的是个幻影,她和那个女人的影子被迅速擦除,什么痕迹都不留下。你什么都不配拥有!你注定失去一切!那些破碎的断凑的声音又拼出对她的宣判。
“没事的,金克丝,我还在呢。”希尔科的声音打断了她下坠溺水的过程,他温热的手按在她的后脑上,将她从冰海中捞起,传来人间的热度,他放缓了声音,再次重复,“你还没有帮我呢,金克丝,你知道的,我没你不行。”
“对不起,希尔科,让你担心了。”金克丝熟练地搞定了一切,如果忽视掉希尔科脸上的几个针孔的话,这就像所有之前发生过的一样完美,她像猫那样蜷起来,脸贴着希尔科的脸,小声说道。
“还是之前看到的那样吗?”希尔科搂住金克丝,语气柔和,“你看,猫也还好好的,你姐姐抛弃了你,但我和猫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这次不太一样。”金克丝顿了一下,又开口,“我好像看到蔚了,她和之前见到的完全不一样,我像见到了未来的她一样,甚至还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皮城佬在她的身边。”
“是吗?也许是你太讨厌那群混蛋了,不过很快我们就要把他们赶下高高在上的座位,去夺得我们本应该得到的一切,我们早该得到的,不是吗?”希尔科拆开金克丝的长辫,拿起木梳来,金克丝安静地坐在他怀里,等他重新为她扎起辫子。希尔科的动作很小心,甚至都没有弄痛过她,从最开始就是这样,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学的,金克丝胡乱发散着思维,享受着对她而言难得的没有任何鬼魂打扰的安宁时刻。
猫跳到桌子上,打翻一罐什么,染得半边身子成了粉色,下一秒又突然膨胀起来,化作黑洞吞没了一切,只有难听的尖叫声传递出来,它像是要死了一样在哀嚎着。
猫要死了吗?金克丝被哀嚎声唤醒了一瞬,发生了什么事?她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她面前的世界好像要被黑洞吞噬掉,只有希尔科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他顺着她的脊椎抚摸下去,像在安抚一只猫一样,他的声音很稳定,几乎只在片刻就稳住了快要失控的金克丝:“金克丝,你失去过很多,但你拥有我,还有我能够给你的一切,停下来,好吗?你现在很安全。”
“希尔科,你会永远爱我吗?”不知道为什么,金克丝简直要被悲伤所淹没,她凝望着那张看起来没有什么表情的脸,问出了一个她早就知道回答的问题。
“会的,当然会的。”希尔科微笑起来,那张僵硬的脸很少做出这样的表情,看起来有些诡异的不契合感。
“希尔科,你能不能不离开?”金克丝努力擦去模糊了视线的眼泪,又问出一个她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
“不哭。”希尔科也随之破碎,只留下他最后的祝福,“你拥有一切。”
在轰鸣声中她终于醒过来,对岸火光嚣天,照亮了蔚不可置信的脸。
后记:即使在金克丝的幻觉里,希尔科也没有指责过她。
以及:
我和我的猫都很想你
你醒啦,你没有猫,也没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