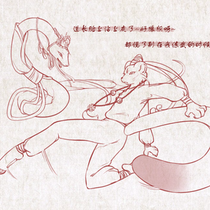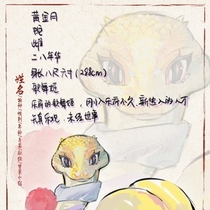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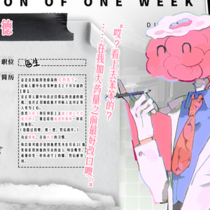
为了打卡那点冲黑卡,拼了(拼了(急速滑铲
之后冲隐藏
第五章上·时光飞逝
名冢琉斗操着一口粗声粗气但依旧夹里夹气的声音,把抱头蹲地的大汉骂了个痛快。
流山凛皇慢条斯理地拉开行李箱拉链,对着肢体扭曲变形的箱中受害者,投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审视目光,微笑道:“一会儿就送您去警局报案。”
箱中受害者打个了哆嗦,奋力蠕动挣扎着钻出行李箱,和神清气爽的名冢琉斗打了个照面。名冢琉斗笑容明朗,心情开阔,压着小鸡仔一样的犯人扬长而去。
案件最终被丢给了值班的警察,对流山二人而言,也算是告一段落。
时间在忙忙碌碌中匆匆消逝,很快来到6月5日。
由于活死人特别搜查司迟迟未能向公众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群情激愤的W市民众自发组织起了游行示威活动。
游行当日,警察的人手都被抽调去维持秩序,而名冢琉斗本着观望情况的态度,也加入了其中。
连绵的人群犹如鼓噪的海洋,一波波朝警署门前的人墙发起缓慢的冲击。人声鼎沸,各种各样的口号汇聚成嘈杂的声响,大咧咧地刮蹭着名冢琉斗脆弱的耳膜。
名冢琉斗拉远了与人潮的距离,望着不远处福神记者上蹿下跳的身影,心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想活死人的精力真的远比活人还要旺盛,这位活死人的坚定拥护者仿佛从未在人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疲惫之色,真是不可小觑。
漫长的时间在名冢琉斗忍不住打了个呵欠的时候被摁下了加速键,血色的液体伴随货车翻倒的巨响飞洒而下,兜头盖脸漫天散花,飘飘扬扬地降落在高架桥下人们的头顶及衣物上,晕染出一道道暗红的印记。难以计数的大脑组织在人群中炸出了一片惊悚的烟花。
之后便是混乱、惊惶与血色的狂欢。
名冢琉斗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叹了口气加入救援行动中,不知为何竟感到有些疲惫——对于平和的W市而言,近期的恶性事件似乎异乎寻常的多。
而这也许仅是冰山一角。
次日,名冢琉斗跟在流山凛皇屁股后面,跑到了活死人特别搜查司新闻发布会现场,神色游离地听完了整场发布会。
流山凛皇在会后找到他,摸了摸小狗的脑袋:“怎么了?”
名冢琉斗清清嗓子,低声开口道:“你不觉得望日会社嫌疑更大了吗?之前舞台的事情他们也难逃干系,这辆车虽然望日会社坚持说是失窃车辆,但未免也太过巧合了。”他的声音还是夹夹的,因此不怎么乐意开口说话。
“而且把人脑放在炸鸡盒中,未免也太过恶趣味了吧。”
流山凛皇坐在他身旁,凑到耳边:“我看到司长办公桌上文件里面显示望日会社似乎与外市黑帮有所关联,而且司长还标注了6月5日。”
名冢琉斗灵光一闪,他讶异地看向流山凛皇:“莫非货车被警方围追堵截指的就是这件事?”
流山凛皇不无肯定地微微点头,他起身,包住小狗的手把他拉起来,揣进口袋里:“休息一下?调查的事情有其他同事在跟进了。不过有些奇怪的是,今天早上点名的时候,似乎没有看到早见……”
名冢琉斗抖抖耳朵:“奥,是那个进入过仓库的人?我记得他的体温某天异常的低。”
“嗯,对。”流山凛皇望向大门,“他本来就是嫌疑对象之一,今天又无故缺勤,现在司里已经派人去他家了。”
殊不知,他们二人口中的早见,现时已然死于家中了。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