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橼
免责:笑语
“救命!救——”
“啊——”
今天是大学报道的第一天,我快乐地提着行李拿着钥匙来到宿舍,内心满怀憧憬,希望能有帅气、貌美或者才华横溢的完美室友。
但这一梦想,在进门的那一刻破灭了。
我的室友,被她的行李箱吃掉了。
准确来说,那是一款英式复古手提箱,上面还贴着发黄翘边的托运标签;如果我当时有机会仔细观察,甚至能够发现有一张标签写着1927年5月21日,但是我真的来不及仔细观察了。
我的室友,她被自己的行李箱吃掉了啊!
开门的刹那,手提箱摊开摆在地上,室友的双脚在箱子外面,而其他部分则在行李箱内部!
这是多么让人惊悚的场面啊,如果不是室友还在呼救,我几乎要以为这里是命案发生现场了。
赞美今日说法。
短暂的尖叫过后,我回过神来,赶紧抱住她的腿,将其往回拽,明明看着她的腰身也没有将整个两面开口都堵住,却怎么都拽不动。
“救命啊!”
我拔萝卜越发用力,室友的求救声越发痛苦。
我不理解,我不知道她是被什么挂住或者抓住了,这卡得也太紧了!
于是我探头,想从她腰身与手提箱边缘中间的缝隙看一眼对面情况。
一眼,蓝天白云;再看,纯白机身——等等,室友你为什么挂在一架单翼飞机上???
“那个……室友,现在什么情况?”
“What……啊不是,你叫我?”室友艰难低头,望向正抓着自己双腿的我,双眼蓄满泪水,“你抱住我了?”
“抱,抱住了啊……”本来是抱住了的,但她这一问我就有些不确定了。手上力度加重,又收紧了半圈,“这回真抱住了。”
“那我松手了!”
说着,室友松开了扒着单翼飞机起降轮的双手,还没有完全被压住棺材板的牛顿揭棺而起,各种力作用下,室友被手提箱吐了出来,压着我瘫坐在地。
“呼,谢谢姐妹。”
我抬手拍拍她后腰,表示不用谢。
稍后各自平复十分钟,我主动问起了刚才情况。“你这神奇箱子……”
“啊这个啊。”此时室友已经把手提箱关上了,听到我提问,这才再次打开。不过这次打开,里面就正常多了。
没有蓝天白云,也没有飞机,甚至没有外国佬的WTF。
是一水儿的贵妇化妆品。
然而刚打开一秒,室友又惊慌地合上箱子,深吸一口气,再次打开。
这次里面装的是毛巾等日常用品了。
她长舒一口气,重新接上刚才的话头,“看过哆啦O梦吗?”
“看过。”
“这玩意就跟时光机差不多,不过它是随机的——起码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搞清楚到底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刚才接连发生的意外。”
“……方便问一下,上次出现这种,意外,是什么时候吗?”
室友仰头望向天花板上吱嘎的军绿色电风扇,回忆道,“1916年2月21日。”
“……”我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那天,是我生日。”室友似乎没有发现我逐渐微妙的表情,擅自回忆起当年的故事,“父亲还在海外没有回来,只是让叔叔把生日礼物带回来了。”
“就是这个手提箱。”
“然后我拆礼物时打开它,就被吸到了这里。”
“好家伙,无痛穿越一百年??”
我一边惊呼,一边悄悄摁亮了我贴着防窥膜的手机屏幕,打算稍有意外就直接紧急拨号。
“哈哈,倒也没有。”室友笑着反驳一下,“我当时只是过来走了两步,发现周围不对劲儿后我就又跳回去了。”
“但是跳回去后也不对……我并没有回到生日当天,而是出现在了某个国外火车站的出站口。我本来当时还想再反复横跳的,但是当我爬出来后,有个‘好心人’帮我把落在地上的手提箱关好了。”
真是隔着几十年都能感觉到当时的绝望呢。
“再然后,我在英国生活了两年,直到几个月前才回国。哦顺便说,我是交流生。”她不太好意思的掏出了自己的护照。
我再次悄悄摁灭手机屏幕,与出口转内销的老祖宗握了握手。
这可是穿越了一百多年的、新青年与老祖宗的历史性会面啊!这年头要想见到一百多岁的美少女可真不容易呢!
“欢迎回家。”我冲着国际友人微笑,“就是有点好奇。”
“你说。”
“1916年你有身份证吗?”
“没……没有……”室友似乎有些不理解这个问题有何意义。
“哦,没什么,就是想跟你说,祖国绿卡挺难拿的。”
真的,没别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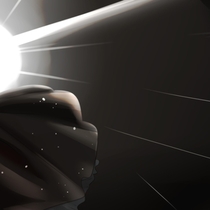



https://www.bilibili.com/audio/au3111437?typ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