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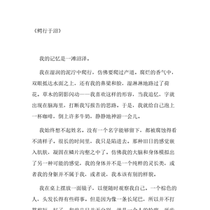




史无明何许人也?
街边遛狗的王婶子说他是个教书先生,成天蹲在拐角扯张布卖没人买的前朝古董的刘大爷说他是个瘸子,他那离了家的媳妇儿说他就是个无可救药的死脑筋,而被他收养的儿子说他是个病秧子。
可是要新来镇上的米小棠说……
“大叔,你的钱又给多了!”
“哦,是吗?那就当作今天的买菜钱,小棠,今晚再来我家吃饭啊。”临了,史无明还要摸一摸米小棠的头,好像同她缔结了一份无声的契约。这个大叔的手掌很大,米小棠看到过,这只手掌上不止有墨水的污渍,还遍布着老茧。
经常握笔会磨出这种茧子吗?
这是个总要多给她几个铜板,还要供她的饭的怪大叔,但是毋庸置疑,他是个好人。
米小棠是几天前到这个镇子上来的,虽然她最初的记忆是从别春州开始的,但就算只有别春州,要寻找一个人——光是一个村子都要找上几天——更何况对于她这样孤身一人的女孩来说,简直难如登天。
但是米小棠知道,虽然这件事很困难,但要是不去做,就一定会没结果。于是她踏上了旅程。
她会些做面食的手艺,可以去到招工的地方碰碰运气,不必担心饿死,这年头手艺人最吃香。
恰好,这个边陲小镇的一家面食摊子,操持摊子的老板娘打算跟着她那老大不小的儿子进京赶考。她也年纪很大了,而且也有些积蓄,去一次京城,对她来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独特经历,能让她多出一些吹嘘的资本——让别人觉得她没有白活。
“这些面食我都会做!”米小棠手上利落,话音刚落,一个薄皮大馅儿的酸菜馅儿包子已经落在案板上,当这个包子被放在蒸笼上蒸熟,里面的肉馅淌出的汁水会渗进面皮,变成香喷喷的金黄色,“我算账也贼利落,交给我准没错儿!”
就这样,外地人米小棠顺利解决了在镇子里的落脚问题。
“你是她姑娘?婶子真是,孩子都这么大了,咋不说声呢!”
“我不是……”
“不是啊,你真是,听风就是雨的,人家孩子是外地人,来找人的!”
“啊,对对,我找我大娘!姐姐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外地人呀?”
“哎哟!这么小就出来闯荡,外地人……最近来这儿的外地人就你啊!”
“没事儿!孩儿你也别急哈,来了这儿俺们短不了你吃的!这六个馒头给姐装了吧。”
镇上的居民过于热情,以至于打入内部的步骤都直接省了。
虽然这个镇上甚少有外来者,看看米小棠自己就知道了,她的到来像是一颗石子,让湖面激起了涟漪,这片湖里的所有水滴都想接纳她成为这里的一员,他们迫不及待地包裹她的生活,将她纳入小镇的怀抱。
这说明大娘或许没有来过这里,但小镇里有见过大世面的人。
除了教书先生,瘸子,无可救药的死脑筋,怪大叔,史无明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只是没人说得出他到底见过什么世面。在这个乡音泛滥的镇子中,他那口标准的官话就是他与众不同的证明。
“大叔,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啊?”
最后一道菜被放在桌子上,韭菜炒鸡蛋配上母鸡汤,搭上米小棠带来的两个饼子,就是今天史家的晚饭。史无明下厨很是熟练,从他招呼小棠来吃饭的第一天,少女就见识了他熟练生火、起灶、备菜等一系列流畅的下厨工序。
史家的小院子里栽种着不同的幼苗,现在正是生长的季节,它们幼嫩的绿色日渐变深,根茎逐渐粗壮、长高,这些植物无声地告知所有人它们经过了怎样的精心照料。院子的角落里有些被布包裹着的陈设,米小棠不知道那些究竟是什么,或许是些农具吧。
而屋内,尽管房子不大,但每个区域井然有序,书房里的书籍分门别类地整齐摆放,史无明的房间……米小棠没进去过,但是米小棠进过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暂且空着,被史无明用来招待他的学生和客人。据说这是他的养子的屋子。这间屋子的一切一尘不染,好像它的主人明天就会回来。
看来他已经很习惯独自生活了,也很习惯照顾一个她这样十几岁的孩子。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史无明将米小棠的碗里倒满鸡汤,里面的鸡肉几乎堆了起来,“我已经九年没有离开镇子了。对不起,我帮不上你的忙。”
“没事!您天天给我做饭,我应该谢谢您。”
“小棠真是个好孩子,有你这样的孩子,你的大娘应该会很欣慰。”
“大叔的孩子不是好孩子吗?”
史无明夹菜的手一顿,但他还是无事发生一般将韭菜鸡蛋放进米小棠的碗里,“他是个好孩子,但不是个乖孩子。”
“他对你很好,但是不听你的话?”
“小棠真聪明。那本诗经,你读到哪里了?”
米小棠咬着筷子,眼睛瞟到天花板上,那里有一只蜘蛛躲到缝隙里,这些八只脚的生物,总是出没在那些角落里,但是史大叔家很干净,它应该很快就会离开,“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后面我不记得了。”
“看到召南了啊。怎么样,觉得读书有意思吗?”
“我看得懂的就有意思,但是有的字太难了,我不认识,就没意思。”
“没关系,我会教给你。我的儿子很不喜欢读书,但是他有个地方和你一样。”
“是什么?”
“他也喜欢算账。”
“哇!那他现在是在做生意吗?有没有赚很多钱?”
“他是在做生意,钱嘛,他不愁衣食,每次回来也会给我很多东西。”
“真好!我将来也会给大娘好多东西!”
“小棠这么聪明,又有决心和毅力,将来一定会赚很多钱。快吃饭吧,菜要凉了。”
史无明大叔的儿子确实很有钱,每次大叔给米小棠的钱都足够她买肉买菜回来让大叔做上一顿丰盛的吃食,甚至还总是剩下多余的零钱,而这些钱史无明总是会让她收下,“你的跑腿费。”大叔说。
但无功不受禄,她只是跑了腿,这些剩下的钱就算加上她带来的饼子馒头包子也抵不上,她每次便自告奋勇饭后洗碗,收拾饭桌。她手脚很勤快,保证桌上一个油点子都不会有!
“小棠,你每次都这么忙活,快歇歇吧。”
“那哪行!”今天虽然大娘的下落还没打听到,但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大叔,你多给的那些钱能让我再多擦十几天的桌子呢!”
“那行吧,我是见今天天色晚了,既然如此,要不你在我这儿先住下?墨鹰的房间我一直收拾着,拿一套新被褥给你就行。”
“不用不用,唉!怪我,今天有外地人来镇上,我就和他们多聊了一会儿。”
“是问你大娘的事吧,可问出什么了?”
米小棠摇摇头,又叹了口气,她手上擦桌子的动作也慢了下来,但很快她忽然又振奋起来,她直起腰转身看向史无明,“不过这些外地人听说我和大叔关系很好,倒是问了很多大叔的事呢!”
“哈哈,我以前行走江湖,许是我的老朋友。既然如此,他们或许会来寻我。”
“大叔以前的老朋友?听起来你们的关系很好。”
“小棠,你为人不错,也会交到很多朋友的。不过可一定要记得辨别他人的意图,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友善的。”
米小棠隐约觉得史无明答非所问的话语中藏着别的意思,但还未等她琢磨出当中的特殊意味,史无明便催着她放下活计,“小棠,今天既然住下,可有什么字不会的,我来帮你再识些字。”
“太好了!谢谢大叔!”把碗最后一个碗稳妥地摞到架子上,米小棠在围裙上擦擦手,便立刻解开围裙跟着史无明进了书房。
夜深时,外面只有打更人提着灯笼,“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之后他咚地一声敲响手里的竹筒。史无明关上窗户,吹灭书房的蜡烛,霎时间,一声轻响穿透窗户纸,击中史无明面前的蜡烛,他立刻伸出手,烛台落在他的手中,没有引出令人惊觉的声响。
“来了啊,”他不紧不慢地拿过拐杖,将烛台在桌面上放好,拐杖落在地面上和着他的脚步声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声,将他的位置一步步地告知给房屋外的人。他就这么一瘸一拐地走着,嘴里念念叨叨,“别着急,别急……”
而好像听见了他的念叨,除了这枚暗器,窗外再无声响,直到史无明打开房门,屋外赫然已经站立几人,此几人虽穿着黑色披风看不出身形,但在月光下,他们手中的武器已经在无声地警告着他们的来意。
“几位来访,史某有失远迎,还望各位切莫责怪,”史无明手上没有动作,他将一手负在身后,另一手紧握着拐杖,“本以为各位寻我是陈年往事,此刻得见,却发现是未曾相识啊。”
“史老先生,”站在最前面的男人拿着手中未出鞘的刀同史无明拱手作揖,“既然您亲自出面,我们便也不为难那孩子了,和我们走一趟吧。”
“有事直说吧。”
“敢问史墨鹰,您可知晓?”
“正是犬子。看来他终究还是惹祸了。”
“只是生意上的往来罢了。老先生,你是读书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你应该懂的吧?”
“横竖不过一个‘利’字,你们和那孩子一样,人生匆匆几十余载,何苦为此所困?”
“您高尚,可惜我们同你那儿子一样,不过俗人罢了。”领头人道,“动手。”
他身边的人立刻拔刀,金属在月色下映出寒冷的威胁,“老先生,失礼了!”
此人步步逼近,史无明面无惧色,“以利相诱,以武威逼,我怎会不懂?”
霎时,拐杖抽中那人膝盖,男子腿上一软,拐杖举起径直冲男子面门而去!只见那人避闪不及,拐杖净如同金属利器般穿脑而过,男人还未发出半声呜咽,已是身躯瘫软,倒在地上,血流不止。
史无明甩去拐杖血迹,“小朋友,史某手法生疏,只望尽量不让各位走得痛苦。”
“你……!”他们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已经不只是个瘸子,教书先生,病秧子,他是个已经被江湖遗忘的剑客,“一起上!”剩下的黑衣人直冲而上。
“一起上?也好,良宵苦短,不可在这种事上浪费太多时间。”史无明握紧拐杖,如同那是一柄熠熠生辉的利剑,“穿翎剑史无明,请诸位赐教。”
月亮仍挂在半空,如果一直盯着它的身影,似乎很难察觉它的轨迹,他就这样一直看着月亮,那光辉如此冰冷,好像他的全身都再也无法温暖起来。不消片刻,那老人的脸挡住了月光,但他却并未觉得从寒冷中摆脱。
“我史无明管教无方,只是若是如此,便由我来教育犬子便可,怎可由各位代劳?各位就先去吧。”
忽然,一个重物落在他的旁边,他转动眼珠,那是谁的手臂?他太冷了,冷到几乎没法思考,而后一捧土撒在他的脸上,之后他的世界中连月光也一并消失了。
镇上的外地人离开得匆匆忙忙,第二天,镇上的所有人都再没见过他们,哪怕问史无明,他也只是摇摇头。
米小棠的线索断得悄无声息,她别无他法,最终只得再次启程,踏上前往下一段寻找大娘的旅程。
临行前她特意去和史无明告别,史无明特别叮嘱她,他的那个儿子——史墨鹰现在正在万都城做生意,如有困难可带着他的手信去投奔他。
“他要是欺负你,就和我告状,我是该好好收拾收拾他了。”
“好!要是墨鹰哥哥欺负我,我就给史大叔写信!”
米小棠看了眼院子里的那些幼苗,它们好像长得更加茂盛了些。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别管了,响应一下,活一下
慈善院在一场大雪中迎来了明和九年。
孩子们尚小,自然不懂明和八年与明和九年有什么分别。大人们则一早就起床,默契地压低了脚步声,穿梭在慈善院的宿舍与会客室之间,希望孩子们能睡个好觉,做个有意义的“初梦”。
信女醒得很早。
按理说,冬天她犯困,不应醒得这么早。但醒了就是醒了,置身于梦话与呼噜之间,也睡不回去了,只好爬起来,慢慢穿好衣服,提溜着垂到地板上的腰带,出了房间门。走廊上,这阵空荡荡的,她左看右看,正想循着去找人,突然一只手从背后伸来,接住她手里的腰带,并顺势缠上去,动作利落地打起一个结。
信女并没有动,仰起头,看见三根竖毛不服输地朝天,眨眨眼问:“诺诺姐,其他人呢?”
“欸,”ののもへ应着,边调整腰带结的位置,边说,“都忙呢。今天是元旦,怎么不多睡会儿?”
“唔,睡不着。”
“睡不着了啊。”
“嗯,睡不着。”
诺诺“哈哈”笑了两声,“那可麻烦了。做什么梦了吗?”
麻烦什么?难道必须在元旦这天睡到日上三竿才算好兆头吗?信女摇摇头:“没做梦。”
“没做梦啊。”似乎有些惋惜,诺诺接着说,“阿梅在厨房呢,你去找她要点早饭吃吧。”
“好哦。”
就这样向诺诺挥挥手,信女去了厨房。阿梅好像刚吃完自己的早饭,见她来,不免惊讶。于是重复了一段与诺诺之间的对话,女孩说今天就想在厨房吃早饭,阿梅自然不会拒绝,但她实在是没料到信女起得这么早,刚过“朝六刻(早上六点)”,还没来得及准备孩子们的早饭,信女便说自己可以吃剩的,这让阿梅难得皱了皱眉头。
信女不明白。元旦不能吃剩饭吗?
正在这时,从厨房门口传来熟悉的女声。
“阿梅大人,在下看日本桥那边卖的鱼新鲜得紧,就买了几条,您给孩子们……信女大人?”
“目目姐——”
信女高举双臂,朝门口的鬼塚目挥了挥。
早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许久没和阿梅两人一起挤在厨房里吃早饭了,女孩吃得很满足。可是吃完了又该做什么呢?寝室那边还没有人起来呢。听说小红和春龙胆正在会客室等待各鬼女家族的人来,她便起了心思,踮着脚钻过去,把两人吓得够呛。或许是新年,她们并没有真正生气,只是半嗔怪地戳了戳她的脑袋。
咯咯笑着,信女一屁股坐在客人位上,煞有介事地翘起小拇指,用“空气茶盖”擦了擦“空气茶杯”的杯壁,嘴里发出“噌噌”的声音,最后端起“茶杯”微微抿了一口,掐着嗓子说:
“近来慈善院情况如何呢?”
春龙胆看傻眼了。小红则“扑哧”一声,忍笑问她:“信女,在你眼里,鬼女家族的人都是这么说话的吗?”
“难道不是吗?哦,瑠姬姐姐好像真不是。”信女跳下座位,正了正衣襟,清了清嗓子,故意模仿出瑠姬那微尖微高的嗓音,道,“我来了!辰,去把这些东西分给孩子们!”
这下,春龙胆和小红都笑了起来。没个正经。春龙胆边笑边瞪她。小红正想继续说,话头却被其他人接了过去。
“哎呀,瞧瞧这是哪位小人精在模仿我们年轻有为的殿纳屋的下任家主呢?”
被一只手盖住了头顶,信女下意识伸手去抓。见春龙胆和小红都起身招呼“亚绪小姐”,信女“啊”了一声,激动道:“茗荷谷姐姐!”
自她在慈善院生活起,茗荷谷亚绪就经常造访慈善院,和孩子们也都玩得开。自从有身孕后,和儿童们走得更近了,浑身上下简直散发出一种母性的光辉——当然,前提是忽略那母性之下越发浓烈的鬼气。不过信女不在意,她本就和茗荷谷是同种族,茗荷谷身上的气味越浓烈,她反而越高兴。转身抱住茗荷谷的身体,得到身后春龙胆和小红的惊呼,以及茗荷谷稳稳的回抱,信女总觉得,或许生母的怀抱也是如此温暖可靠。
就这样挨着茗荷谷亚绪,信女一边听三人聊最近的宵禁和夜密廻动向,一边又觉得无聊起来。她不大喜欢听这些,听着费脑筋,不然去把大家都闹起来吧,大家起床了就好玩了。正这么盘算的时候,茗荷谷正好说起了水天宫,说什么今天水天宫热闹,“初次参拜”的人非常多。
信女探头问:“什么叫‘初次参拜’?”
“就是一年伊始去拜一拜神仙,祈祷一整年的好运气。”
“啊哦,为什么我们不去呢?”
“因为我们是鬼女。鬼女不信神,只信真蛇大人。”茗荷谷摸了摸信女的脑袋。
原来如此。信女点点头。但她其实对真蛇大人没有特别的想法。
“不过这几天水天宫门外会有非常多的摊子,你要是闲得无聊可以过去玩玩,记得按时回家就好……唉,这孩子!话都不听完就跑走了。”
春龙胆叹了口气。
“有这样的活力是好事。辰巳夫人若是泉下有知,也会高兴的。”
提起陌生的姓氏,茗荷谷亚绪感慨地摸了摸自己日渐鼓胀的腹部,缓缓喝了一口茶。
女孩跑得很快。
她自负体能比常人好,腿脚自然也利索,一路跑出路口,跑过大街,跑进商店之间的入口,歇了口气,这才不客气地敲了敲面前“里长屋”的其中一间的大门。
这个地方她不常来,却莫名其妙记住了位置。附近进出的邻居见一个陌生女孩来,都不免多看两眼,其中不乏偏下流的目光,这令她有些恼火。终于,房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接着障子门被打开,从门里探出身来的人看见她,惺忪的睡眼立刻睁大了,惊讶地问:
“信女?你怎么来了?”
“‘初次参拜’。”
“嗯?”
“去吗?”
“去……去什么?”
女孩更恼火了。这人平时就像根木头,非要她说明白才听得懂。磨了磨后槽牙,她一字一顿地说:
“水,天,宫!初,次,参,拜!去,吗!不去算了!”
“啊啊啊我去我去,你别走啊,你等我收拾一下……”
好在少年及时抓住了她的袖口,挽留住了她。
“可是一个鬼女和一个鬼之子去水天宫参拜人类的神也挺奇怪的。”
收拾完毕,晴出了门。两人走在街上,他忽然说道。信女不以为意,回他:“你拜就行了,我不拜。”
“为什么?”
“因为我信真蛇大人啊。”
女孩昂首挺胸,对自己的“有样学样”颇为满意。街上人来人往,并不会有人对两个孩子的闲聊信以为真,晴却没忍住笑了一声。被他笑得发窘,信女瞪他一眼:“你笑什么?你本来就是研究这些的,难道不知道我说的是正确的吗?”
“对不起,嗯,对,没错。”晴掩饰着嘴角,但不掩饰话中的笑意,那双不知是继承自谁的眼睛里盛满了晶亮的光,“我只是觉得你好可爱。”
“……”
这都什么跟什么!信女翻了个白眼,忍不住往前多走了两步。
但去初次参拜的人早已汇成了一条长龙,想多走几步都不容易。坐落在日本桥的水天宫平时也人多,这天更是成了个“香饽饽”,江户城里的每家每户似乎都想赶在这两天讨个好彩头,把信女和晴挤得在队伍外干瞪眼,最后只能跺跺脚,作了罢。
可是约都约出来了,总得做点什么吧?还没到午饭时间呢。
信女正这么想时,晴对她招了招手,示意她跟上去。她满脸困惑,但不疑有他,跟随少年穿过七拐八弯的小巷,走啊走,不知何时竟走到了城郊。信女频频回头,查看自己钻出来的巷子口,又看向少年的背影。当城里人山人海时,城郊自然空荡得只剩路途,以及半化不化的雪水,积出了一摊又一摊。
两人一前一后又走了片刻,晴才终于停下来。他微微向后退,好让信女看清他身前的东西——原来那是一尊没有她膝盖高的地藏石雕,端坐在路边,总是笑眯眯的眉眼里攒着星点残雪,又被少年拍去。
“既然拜什么都无所谓的话,那拜一拜地藏菩萨也可以吧?”晴说。
“唔,话是没错。”
少年便蹲下来,闭上眼,十分虔诚地向地藏菩萨双手合十。
“我本来也不信神,从没想过会参加初次参拜。小时候过年了,姐姐们会带着我在院子里玩,母亲也难得会露出闲适的笑容,就好像忙活了一年终于能喘口气了。到了饭点,她们会特意给真蛇大人准备好各类贡品,再祈求真蛇大人保佑新一年的平安,不过不准我拜,所以我只能在旁边看着,哈哈。”
信女沉默了一下。
真傻。她心想。出生在那样一个受歧视的家庭里,却对歧视自己的鬼女毫无恨意。从没见过这么傻的人。
但是。她又想。但是……
女孩撩起最外层的衣摆,在他身边蹲下,盯着地藏菩萨看,不合掌也不闭眼。
“那,从今年起,你每年都可以去参拜了。就说我允许的。”
“好啊。”
少年不假思索道。


【山林间的伙伴】
主线任务打卡
【序章】
咕咕——
杜尔萨拉的夜晚,雪白福木兔停留在了为她敞开的窗棂上。
“小雪你回来了。”伽蓝挠了挠福木兔的下巴,小鸟享受的眯起眼睛,蹭了蹭伽蓝的手掌。
“你已经探明那家伙的行动了吗?”
“咕咕咕!”小家伙骄傲的挺了挺胸脯。
伽蓝嘴角抑制不住的扬起了弧度:“好,就是明天了。”
——【翌日清晨】——
伽蓝带着图图茶来到了都拉克防具店前
“布里小姐,我来取之前委托的东西了。”
“哦!你们来了,稍等我这就去取来!”说着铁匠布里转身从储物间中取出了一个大包裹交给伽蓝。
伽蓝打开包裹,从内中取出一张崭新的面具来,这张面具形制十分奇特,宽颐广额,面庞夸张,五官线条流畅,又棱角分明,充满着某种古朴却又精致的艺术之美。
“老爹…老爹!”图图茶急不可耐的蹦跶着伸手够着面具。
伽蓝苦笑一下,将面具递了过去:“好了别急,试试吧。”
“耶!”图图茶一把抓过面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摘下头上的纸袋,把新面具套了上去。
“哇,老爹,新面具戴着好舒服哦,布里姐姐在里面塞了棉花吗一点都不会磨到脸诶!”
布里和伽蓝相视一笑,随后问道:“图图茶,戴上面具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
“诶…?”图图茶握了握双手,仔细的感受了一下。“这么一说,老爹我好像感觉我的力气变大了!”
“哈哈哈哈哈!”布里发出一声爽朗的大笑,“那是当然了,因为这张面具可不是一般的面具,而是……”
“随从防具。”伽蓝接过话茬。
听到这句话后图图茶愣在原地,反应了几秒:“……随、随从防具?那也就是说!!!”
“没错,图图茶,从今以后你就正式成为我认可的狩猎随从了。”
“哦……哦!”图图茶站定。
【第一章】
“穆希勒姐姐!”
“啊,是图图茶和伽蓝先生。”穆希勒放下手中正在整理的任务档案,“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伽蓝微微颔首示意:“打扰了穆希勒小姐,我听说这里发布了有关驯服野生骏羚的任务,就想来看看。”
“啊,没错!因为现在正是合适的季节,所以老板娘就发布了驯服骏羚的任务,接取这个任务的话……伽蓝先生是已经有目标了吗?”
“是的,我已心有所属。”伽蓝的嘴角微微上扬。
‘心、心有所属,好奇怪的形容。’穆希勒一边心中暗想着,一边将任务许可递了过去:“这是您的任务许可,请收好。”
“好的,有劳您了。”
得到任务许可之后,伽蓝立即带着图图茶出发前往乌拉盖山丘,在小雪的引导下,两人在正午时就到达了此前见到的那匹骏羚的栖息之处。
雪白红纹的骏羚与几只较小的白色骏羚依偎在一起晒着太阳,看起来像是一个族群,在感受到有视线看向自己时,红纹骏羚警觉的抬头开始环顾四周。
伽蓝发觉自己被发现之后,拨开草丛向骏羚走去,一人一兽目光交接,骏羚心念电转之间已经了然了来人的意图,它站起身来,轻轻地用头蹭了蹭它的眷族,示意它们走远一些。
“图图茶,在周围巡逻,不要让附近的痹鬃龙打扰我们。”
“哦,好!”图图茶提着自己的小砍刀一溜小跑的去了较远的地方。
“好了……现在就剩我们了。”伽蓝盯着骏羚说道。
“呼噜噜。”红纹的骏羚直勾勾回敬着伽蓝的目光,轻轻摇晃一下自己的头颅,前蹄开始轻轻的摩擦地面。
草原被微风拂过,发出一阵响声,就在这一片宁静祥和的景象当中,浓烈的战意在伽蓝与骏羚之间悄然酝酿,等待着爆发的时机。
伽蓝肩头微侧,稍一用力,背上的盾斧顺势而下,伽蓝顺手将之抛出,横插在远处的地面之上。随后一手负背,另一只手伸出向骏羚比划出一个的动作。
“来吧。”
骏羚眼见对方挑衅,后脚猛的发力,踏碎地面如一股怒涛一般直冲而来。伽蓝眼见骏羚瞬间已至身前,身体一侧堪堪躲开了冲击,随意挥手一掌拍在了骏羚的屁股上。
“嚎——”骏羚似是被激怒一般发出一声咆哮,随即浑身肌肉发力强行停下了自己的步伐,转身再次向伽蓝奔去,而伽蓝亦是不慌,竟在骏羚冲上来的瞬间双手按在马头之上借力一跃而起,稳稳的坐在了骏羚身上。
骏羚受此情形左冲右踹,试图强行将伽蓝甩下身去,但伽蓝就是凭着一身雄力紧箍住骏羚脖子不放,骏羚眼见不能甩脱,竟直直奔向一颗巨岩,横身一靠,借着撞击之力将伽蓝强行甩了下去,伽蓝在慌乱之中亦不忘翻滚卸力,但就在稳住身形准备站起身时却眼见骏羚再次突入至身前,前蹄高举随后携着雷霆之势迅速压下!
“糟。”伽蓝迅速侧身翻滚,千钧一发之际脑袋擦着羚蹄躲了过去,在狼狈的翻滚几圈后,伽蓝周身发力一个鲤鱼打挺终于是站了起来。
“哈,不愧是我看上的家伙。”
伽蓝改变战术,放弃一味的闪躲直冲骏羚而去,而骏羚也毫不示弱的扑向伽蓝,在二者相交之际,伽蓝奋起一拳直轰向骏羚的面门,骏羚在强吃一拳后竟也不闪不避,扭动脖颈用头上的独角挥击划伤了伽蓝的手臂,殷红的血液随着伤口汩汩溢出,但二者之间的战意更甚。不屈的战意在一波伤势交换之后,又见一波更强的攻势!
二人再次战在一起,骏羚不断的踢,踏,冲,撞,并不时的使用自己的独角挥击,而伽蓝则在不断的闪躲之中寻找着骏羚攻击的空隙回击,数度交锋,不顾伤势,战局瞬息万变,在两者的心中,在两者的眼中,在两者的攻势中不停反转!
“吼!!!”一声嘶鸣划破长空,骏羚开始抵足蓄力,而伽蓝也似是感应到接下来的一击便是战斗的终结,双脚踏定,双臂张开等待着骏羚的冲击。
“碰!!!”随着一声巨响,骏羚使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宛如一道惊雷一般直冲而来,而伽蓝这一次却没有选择闪避,而是直直的用自己的身躯接下了骏羚的冲击。强大的冲击力携着雷霆之势带着伽蓝不断向后退去,随着一声怒吼,伽蓝双脚再次踏定地面,雄力再催停下了骏羚的脚步,双臂肌肉暴起用全身的力量箍住骏羚的脖颈将之向地面摔去!
“轰——!!!”
一声巨响过后,尘埃落定,伽蓝依旧如一尊金刚怒像屹立在大地之上,而骏羚则倒伏在地上,大口的喘着粗气。
“哈……哈。”伽蓝左手摁住鼻孔,从鼻腔中擤出一道瘀血,看着跪倒下去的骏羚。
“是我赢了。”伽蓝单膝跪下,从怀中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杜尔萨拉胡萝卜。“怎么样,要不要做我的伙伴?”
骏羚似是无奈的摇了摇头,鼻腔里不满的呼着气,但还是叼起了递过来的胡萝卜。
“哈——好羚儿。”伽蓝伸手抚摸着骏羚的头,嘴角带着微笑。“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做——”
“仲夏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