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那样一条狭缝。
浑浑噩噩地,我不知该对眼下的事态摆出一副什么样的态度。我应该感到悲伤吗?我应该为此而流泪吗?还是说我应该转身逃走呢?
没有被悲伤淹没,没有被恐惧吞噬,甚至于我的面部肌肉都已经不听使唤。我的心底好像已经干涸,流不出一滴情感。
事到如今,再向谁去质问“为什么”也根本是徒劳无功,这件事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得到了答案又能怎么样呢?受到了惩罚又能怎么样呢?
人类真的好脆弱啊。这样的种子埋进了我的心里。
我在傍晚的七点十五分走进浴室。
今天也会和三千院同学见面。昨天也是、前天也是。
我们会聊一些关于我们各自的生活的事情,聊一些我们吃过的好吃的甜品,聊一些去过的风景好看的地方,聊一些……
我们的将来。
当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毕竟我没去过很多地方,也没吃过很多好吃的甜品。我只能发挥我一向引以为豪的想象力,去不时地附和一下她。然后我们都会露出笑容,即使是透过浓重的水雾,我也能肯定她一定是在笑。
我的生活是不是已经能够走上正规了呢?
我是不是开始对于明天,亦或是更近的,更远的未来有所期待了呢?
我眯起眼睛,在暖烘烘的水池中开始等待。
哒、哒、哒、哒。并不算重,很沉稳且匀速,脚步声在这一方略显狭促的空间内回响起来。
我知道是三千院同学来了。
她大概是裹着白色的浴巾吧?每次见到她我都想感叹一下,作为舞者的身材管理真的……很严格。这种美丽也许是含有一定的残酷在的。
然后她开始解下浴巾,我也应当在这个时候开口问好,作为对话的开始。
“今天也、晚上好……三千院同学?!”
……我的声音是不是有些,太、雀跃了?我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带起一小片水花与她的轻笑。
“嗯,晚上好,山鹿小姐。”
我是喜欢她的声音的。比我们这些同龄人要沉稳,饱含矜持,但肯定也不会失去张力与年轻人的稚嫩,还有一种唤起人们面对上位者时的激素的高贵感。或许她也会很适合唱一点……美声的,或者一些需要特殊的声线的,歌……
“嗯……山鹿小姐?在想什么吗?”
我回过神来,她确实在用关切的表情看着我。这或许意味着我已经发了一段时间的愣,毕竟在这朦胧的雾气中,我实在很难感知到时间在走动。
我赶紧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不、没什么!……只是在想,三千院同学的声音很好听……说不定会适合唱歌,嗯。”
“呵呵,说不定吧?虽然我没有想过要唱歌,但尝试一下或许也不错。”
嗯,即使是尝试也是好的。她这样的回答就是最让我开心的了。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也和我说过这样的话。
“说起来,山鹿小姐……如果你不会感到冒犯的话,我可以帮你找适合你的声线的,写歌的人脉。”
“当然,是出去之后。”
……嗯。我知道的。昨天我们的浴中相谈其实并不是以那么轻松的气氛结束的,其原因大概还要全部归到我的头上——长话短说,我有些呼吸困难,所以逃走了——所以,她这大概是……在,主动地缓和气氛吧。我想。
“……那个、……谢谢!我…没什么能帮得上三千院同学的,抱歉。”
“不过,果然……我也还是想,自己来写……起码一部分!不是说拒绝的意思……因为,毕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正常生活。如果三千院同学愿意帮我的话,我真的很感动!但创作,果然还是属于我的……”
……怎么就说出了这样的话呢?明知道她大概是以此客套一下,礼尚往来,也并不应将其当真,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就顺着它向下思考,然后像是呕吐一样把想到的东西一气地说了出来……
“那种事情啊。只要和对方说一声就好了吧?”
“…嗯、好的。我知道的!……因、因为是三千院同学帮我找的合作…所以、一定也……明明是、…”
……
就像被温柔地摸了头一样,三千院同学的一句补充却让我的鼻子开始发酸。我拼命地咬住下唇,顿了又顿,深呼吸了又深呼吸,最终还是没能吐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
哽咽、抽泣,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然后我真的被摸了摸头。
“……之后,一起去我以前去过的一家店喝茶吧?我感觉他们家还不错。”
……好生硬的话题转移,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或许刚刚好。
“嗯……!一定!…我还没怎么试过,在店里和朋友一起喝茶…所以,说好了的事情,我会希望它发生。…”
……但是,实际上是很难的吧?比起那个,我更想和三千院同学一起再烤一次蛋糕……
我抬起头来,希望从她的眼里看到一点肯定。
她却闭着眼睛。
“三千院同学……?”
她没有回答。
“三千院同学……?!”
她从水里站起身来。
我看到她没有双腿。
我放声尖叫。
…………咚、咚、咚、咚。…沉闷的敲击声在我耳边响起。
这是心脏跳动的声音。
我知道我现在的表情,但我应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
我知道我现在身处何处,但我应该往何处去?
我知道我现在眼前所见为何,但我应该向哪里远望?
我找不到答案。
末了,我把曾经紧紧抱在怀里的,攥在手心的,咬在牙关的,再也不会兑现的东西一一抛弃,然后转身离去。
就像从来没得到过它们一样。
在那条狭缝之间,我进退不得。向前是碰壁,向后是深渊。
我自问:“我该怎么做?”
我不知如何作答,我良久无言。
活动准备笔记:
音箱线路√
背景音乐编辑√
转场音乐编辑√
播放时间轴√
应急音乐片段√
校对工作√
二次检查√
心得:
和有能力的人共事还挺愉快的
须弥山同学是个好人 人缘很好
山鹿殿(描了好几遍)也就算了,塞壬(描了更多遍)小姐的意思是 ?(。_。;|||)
湖湖 说不定也有唱歌的 天分 吧。
吧?


马车越沿着道路前行,风就越喧嚣。鲜少有人见过切利的海岸,书本上说海岸是细腻的白沙堆积而成的,蓝色的海水由远及近将远方的土地送来,仿佛在此地藏宝的巨龙。书上还说白色的泡沫是美人鱼所生,她们在昏暗的海底吐息,歌声被包裹着遥遥抵达海面,化作喧嚣中几不可闻的一部分。还有远洋回来的人,对儿童讲述航行中最常见的海鸥,那是最灵敏的鸟,喙尖是黑色,而喙又是黄色,稍不留神就会抢走食物。当你抬头望去,会看见白色的羽毛,羽尾点缀着黑色,这样的变色与海洋相似,同样是蓝色的表面漂浮着一链链白沫。
塞勒涅如今八岁,在餐桌上听够了大人的聊天,缠着父母要去海边玩,决心自己去看看归人们所描述的“海岸”。路途较远,马车颠簸,小姑娘透过窗抬头望,只瞧见了湛蓝的天。母亲笑着劝她:“马上我们就到海岸了,心急什么。”
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海岸,而是海边港口。他们一家下了马车,支付车夫,大手牵小手融入了市场的人流。
摊位接着一个摊位,商户们忙着手上的活计,时不时观望四方。有的商人对着客人百般招徕,展示商品,有的则闷头收拾着商品,喷洒着水,或者用毛巾擦拭,或者摆放得更美观。有的商铺甚至都没有人,空空立了一个牌子,写着临时有事。小姑娘被家长牵住手,东张西望,大踏的步伐停不住,几乎下一步就要奔向看琳琅满目的新奇玩意儿了。
父亲提着包,也不知是在看什么,眼光转来转去没有目标。母亲拽住孩子飘浮的步伐,在铺满瓶瓶罐罐的小贩前停下来。这些香料的质量太好,也有可能是儿童的嗅觉更敏感,塞勒涅靠近时,实在是忍不住打了个小小的喷嚏。轻飘飘的气味惹得她鼻子发痒,对神发誓,在厨房里我从来没有这样!她心中委屈地呐喊,也算是给自己打气,于是抽了抽鼻子。母亲轻抚她的头“打喷嚏不可避免,但是这样对着商品可不礼貌哦。”责备似的轻拍两下,“不是说过用手背捂住口鼻吗?”女孩依言掩住口鼻,女人又补充“记得用手帕,下次可不要这么粗鲁了。”
摊主听了,只觉好笑,但并未多言。看了看低头被训的小女孩,他马上转向自己的顾客“夫人想要什么香料?”。他皮肤相对黝黑,一看便知是常年日晒才有的肤色。眼睛睁得大看得清,嘴皮子快手也快,不及女主人回应,摊主便开始了推销“这些是新进的香料,不呛鼻,而且下锅加汤,味道醇厚。”他右手的玻璃瓶里是淡黄色的粉末,捏住上端递交给客人,“您瞧瞧?”
他确认这家的女主人接稳之后,分一瞥余光,左手翻找一番,随即又从摊位捞出一个一个透明瓶子,里面的白色圆柱状颗粒随着摇晃上下翻滚。“这边则是新研发的一种香料,不需要严格把控用量,比最常见的盐方便许多,一种就有多种调味料的混合效果。”
女主人犹豫片刻,做出了一番取舍。之后他们又逛了很多商摊,买了些零嘴、父亲和女儿都心动的小玩意,或者一些正经有用的家具。购物的过程在女主人的严格掌控之下,虽然购物过程多有曲折,但对于艾诺姆长期居家的独女来说,实在是一番新奇体验。
书上应该是这么说的,“海岸上的细沙,是由海水从世界各地带来的。一是海水侵蚀陆地岩石,这样的沙砾是海岸的原住民。二是海底的土壤被海浪携带至陆地,三是内陆河流将陆地泥沙带入海洋,这些便是从海的那一边,或者是从内陆,来到海洋的移民。”
塞勒涅蹦蹦跳跳地,东张西望,心里暗自下了结论:海岸就是这样的!有着从不同地方来的人,他们也是沙子,聚集在这里,共同形成了这片海岸。
四处望去,大多数商人都是黝黑皮肤,或者晒伤有了斑点。她心里更加肯定:这些人都是被打磨了的沙子!
母亲拉了拉她的手,提醒她“走路就应该有走路的样子,这样小心摔倒。”小姑娘远在,天边的思绪也就这样被拽回来了,只好看着目光所及之处。路边的老人蹲坐在地摊前,佝偻着腰背,和周围那些精壮的男人们相比,他实在是太瘦小了,仿佛要被人潮吞没。塞勒涅小心瞥一眼老人,他头顶缠绕着褪色的头巾,脸以及胸口的皮肤近似于铜色,刻印着无法平整的皱纹与疤痕,粗麻衬衫的领口被磨损得几乎破碎,甚至最顶上的两三个系绳孔不在了,怪不得他袒露了大块的胸口。
老人就这样蜷缩在摊口,几乎不抬头主动招徕顾客,空空留一张折揉的防水布与躺在其上形势不甚喜人的水产品,脚边放了一桶水。塞勒涅看不清,那些商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似乎也不大,能刚好握在手里的样子。她思考着,很努力的拉了拉母亲的手,用自己的视线示意方向 “妈妈,那个爷爷好可怜,我们去看看吧。”母亲微微笑着,对女儿所展露的善良非常满意,点点头便牵引了过去,主动像那位可怜的渔夫问好:“请问这些是什么?”。言毕松开牵着女儿的手,轻拍以矫正略微的驼背,再顺势往前推,又收手稳在肩头,轻巧控制住了塞勒涅。
“伯伯?这是什么呀……?”她娇滴滴地问,想蹲下身子凑近仔细瞧,却被母亲控住,只好僵硬站着。
“……”老人迟疑地抬头,眼睛还是迷蒙的,似乎是看着他们一家,又似乎梦中苏醒。几乎是一种本能,“小姐……”他呓语几声,“这……这是海滩上的贝壳与海螺。”他指点着这些产品,就像是清点家中的子嗣,言语克制,却不知不觉流露熟悉,末了非得贬低一句,“不过是些破烂玩意罢了,夫人小姐随意看。”
塞勒涅被钳制得痛了,稍微用力,弯腰蹲下,随手拾取了一物。这东西一掌大,握在儿童手里稍微有些勉强,表面粗糙,灰黑的泥块凝固在其上。螺旋状向外延展,有极大的口,向里看是橙色肉色的内壳,藏了内敛微闪的粉末。谁能想它肮脏不起眼的外表下,里面躲藏了这么柔和的颜色。
“小姐喜欢鹦鹉螺?”
“鹦鹉……螺?”这哪里像鹦鹉了……?
“说是,小姐你看这个形状,圆盘一样,口又大,特别突出,像鹦鹉嘴。”老人尽力组织语言,还想讲更多,“小姐是第一次来海边吧?”
“是的。”塞勒涅往下看,摊主伸出静脉虬曲的手,她便将那鹦鹉螺还回去。
“我为小姐清洗一下。”他拿起胶刷,沾了点桶里的水,来回擦表面“海螺呀,是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的。”似乎是将表面的泥沙刷净了,他把鹦鹉螺在衬衫上随手擦干,递给塞勒涅“放在耳边试试。”
这鹦鹉螺干净时完全不一样,红褐色的纹路从中心发散开来,乳白的壳抚触平滑细腻。塞勒涅小心捧过,放至耳边。
先是周遭的吵闹被隔绝了,若不是还睁着眼睛,不敢相信还立在原地。之后是微小的,一阵阵的,如同蜂鸣般的细声。塞勒涅皱起眉,屏神静气,仔细辨听。她细微地调整角度,使螺口很贴合耳朵,竟听到了呼啸的风。她想到了暴雨的切利,风划过树林也是这样的急,那么风掠过海面也肯定是这样的声音……海,没想到小小的鹦鹉螺里面有海!
塞勒涅微微张嘴,说不出话来。怔愣着,慢吞吞要将鹦鹉螺还回去……这怎么能还……?这可是海……这可是海啊……!
她吞咽口水,鹦鹉螺的锋利边角刺得她手心疼。可即使如此也不愿松开,目光上上下下,喉头发梗:没有办法的,母亲不一定会同意她的请求……
“送给你吧。”
有如振聋发聩。老人云淡风轻地复述一遍,打消她的疑虑:“既然喜欢,就送给你吧。”
接着,他自若拾起一个椭圆的黑物,“夫人要不要试试开蚌?”
话题即刻被转走,母亲没来得及督促塞勒涅道谢,就点了几个贝壳,支付了价钱。塞勒涅连忙用裙子擦了擦鹦鹉螺,再揣进口袋,也蹲下来看老人开蚌。
暗灰的刀侧插进缝隙,老人的手腕用力,刀身一上一下,蚌被迫门户大开。和外表的污泥不同,里面是粉白的肉,中间环拥着七彩的珍珠。它们的形状不如贵妇人所佩戴的那般周整圆润,但阅尽首饰的女主人是首次看见金色与紫色的珍珠,一时之间惊叹连连。
三个蚌开下来,不仅有金有紫,甚至有双珠连串。据说这是象征“喜事成双“。的确盼了个好彩头。用海水简单洗净泥沙后,珍珠被包裹进手帕,交由男主人收存了。今日的海岸之旅也到此为止。回程路上,母亲念叨着最令她意外的珍珠,计划着如何做首饰。父亲搂着女儿,微笑看着妻子,时不时点头表示认同。
“那这个紫色的就留给塞勒涅吧。做一枚小巧的胸针。只是点缀服装,就不必在意形状了。”
女人捻出那小小一珠,送至女儿眼前,左右转动再收回。塞勒涅看着紫色的光泽在眼前一闪。那道光泽原是来自路边街灯,越过窗户,成为了窗帘的漏网之鱼,正正好投射在珍珠上,才映照出紫色珍珠的美。珍珠表面有细碎的闪点,而皎洁的暗紫色并不晃眼,令塞勒涅回想到,曾有一次夜半惊醒,偶然发现了扑朔夜空:星月从舞台上退下,深沉的幕布笼罩了舞者,兀自留白。
父亲看她出神,换了个话题让女儿接:“珍珠如此美丽,是因为蚌多年的养育。”
“养育……?”
“是的,珍珠最开始只是泥沙,不断被包裹住小珠粒,才成为现在的样子。”
塞勒涅仰头看着父亲,长长“噢……”了一声,便不再多语。随后父母亲欢快聊天,内容如何她也听不进去了。不一会儿马车停在家门口,塞勒涅收拾好物件,猫着脚回到房间,把鹦鹉螺放在窗台上。
推开窗户,黄昏的风带着一天的余热,冲洗了这间房间。这里没有海风的湿咸,没有嘈杂的人声鼎沸,没有珍珠。
塞勒涅空空拿起那只鹦鹉螺,细碎的海浪拍来,海岸所见又回到眼前。沙子在劳作,被风雨打磨挫切。海岸上有着她见过的与不曾见过的一切,却唯独没有珍珠。珍珠就不可能存活于海岸。纵然珍珠与沙子同源,起初无何不同,但受蚌壳的保护,成为华贵美丽者。
十多岁的小女孩突然惊醒,回头环顾自己的房间。这里有舒适的床铺,有合适的新衣,有教导的书籍……她早已被包裹住,从外貌举止到言论谈吐,优渥的家境期待着她以后成为优雅的妇人。她不止一次反感母亲严格的教育,甚至会偷懒使坏。但此时她前所未有的意识到,自己所背负的沉重期待是某种安身立命的方式,是摆脱沙子原貌的机会。她会成为珍珠。不如说,她要成为最耀眼夺目的珍珠。
三个月后,艾诺姆家的女主人将定制好的胸针别到女儿胸前。此时已入秋,家中准备了秋日的新衣。正巧女儿三个月以来十分温顺,无论是书本还是乐器,都过分努力。刚巧今日要与几位朋友茶会,便为女儿定购了新装。
到场时,几位夫人皆是笑吟吟的。塞勒涅紫发及背,末梢卷发是近几日的努力。白色底衬,搭配午夜蓝的罩裙。胸口一枚银白胸针,百合翻折,瓣朵柔软,枝茎处缀了紫色珍珠。紫色珍珠最奇,色润不华,敛声映人,与女孩的发恰相应,沉静优雅。袖口翻花,手指初显细长,指甲粉红圆整。裙摆提起,躬身之姿轻巧如舞,
“各位夫人贵安,小女为塞勒涅·艾诺姆,为艾诺姆家独女。”
起身抬眼,略略一瞥,笑意盈盈,不浮不沉,宛若珍珠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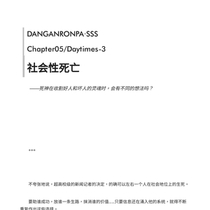








短,超级短
大半夜突发奇想码的,有问题等我明天醒了再改【。
补一篇和珍珠逃跑有关的日记!
其实主要是想写一些一般人对圣女的态度【
所以这部分就请当做是露露觉得自己记录了不该记的东西,所以撕掉藏起来了!
====================
XX年12月12日
说起来,这两天都没有看到珍珠的身影……
虽然我们圣女并不会一直都在一起行动,但到了晚上就寝的时间,大家还是都会回到寝室的。
珍珠也并没有像我那时一样犯错,应该不是被关了禁闭……
尽管我们也曾问过玛歌修女,可她始终不曾做出回答。
只是她脸上的神情实在有些奇怪。
XX年12月13日
今天在中庭,我似乎“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话。
那两位正在交谈的神父和修女应该是知道圣女没有听力,所以并没有顾忌从旁经过的我吧?
尽管我也没能从他们飞速开合的嘴唇运作中读懂全部的意思,但靠猜测也能拼凑出一些事实。
珍珠似乎是逃走了。
那位年轻的神父是如此义愤填膺,他说的那么快,以至于我只能分辨出只言片语。
“明明是被神选中的圣女”
“如此光荣的使命”
“怎么敢逃走”
不过比起他激动的样子,那位看似温和的修女更让我记忆犹新。
我对她有印象,因为她经常会偷偷塞给我们一些玛歌修女不允许我们吃的糖果,还会教我们修行时偷懒的诀窍。
可是这样一位温和的修女,那时却露出了十分为难的样子。
“虽然确实是些可怜的孩子,但怎么能逃走呢?”
“她怎么可以这么任性,怎么可以不为我们去死呢?”
(此部分被凌乱地划掉了)
原来,他们是这么看待我们的吗……
确实,弱小的我想要为大家派上用场,就只有献上自己的生命这一条路……
可是,如果我们还对生有所渴望……不!不行!一定是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才会让我这么胡思乱想!
我已经选了这条路了,不能回头了。
(此句被描了数遍,甚至划破了部分纸张)
雷涅,尤莱亚,我好想见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