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叶烟:
见信如晤。
现在是来到这个岛上的第四天早上。
原谅我这么久才给你写信。平时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连线电话,连睡觉的时候都在一起。现在换成这么古老的联系方式,反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对你的思念写下一句仿佛就会在心头生出两句,写也写不完,便不再无端赘述,给我徒增烦恼。
我很想你,并且永远爱你。
说实话,我现在在岛上无论碰见什么事情也不会惊讶了。这个岛上面居然会有一个很小的监狱,而我之前和你提过的桃泽姐弟就住在那间监狱里面。
可能那个监狱有什么秘密,我不知道。他们就像活在荆棘城堡里面的王子和公主一样,城堡就是他们的堡垒。
必然不会是因为正巧发现才住进城堡的。自古童话故事中的城堡都有着编号,住着公主。或者住着巫婆。但是我无意做屠龙的勇者。
少年在恶龙的眼中看见了恶,所以他杀死了巨龙之后,自己便成为了巨龙。我们自小彼此依附着,如果我必须成为恶,那希望你能在我身边,看着我成为那条蔑视一切的恶龙。
但是并不能。
说起来桃泽姐弟,最近总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领不管是身形还是年龄总和你很想,用余光看见他总能给我一种你还在我身边的错觉。那天在监狱探索完成之后,领留我在监狱午睡。我因为太过困倦也没有拒绝。
现在想来,如果被你知道的话,那么必定少不了和我大闹一番,吵着嚷着要和别人决斗。想来如果我作为姐姐看见你和别的人——不论男女一起睡午觉,也会十分不开心的。为了避免回去之后你的狗鼻子能闻出来我身上的味道,我还是先向你道歉,并且允许以后在我心情好的时候你可以和我一起睡。
如果我们还有以后的话。
这样想起来,可能诗织小姐对我的敌意便在这里。我并不是对桃泽领一个人抱有好感,而是对这对姐弟都乐得看见。但是平时和诗织小姐接触过少,可能引起了她的误会。
诗织小姐虽然说比我小,但是和我交谈的狮虎完全感觉不到障碍,可能是因为诗织小姐真的十分懂事和成熟。我觉得我得找一个时间好好和诗织小姐谈谈。我愿意和诗织小姐成为好朋友,而不是因为领的关系成为敌对方。
毕竟能让我天生好感的人不多了。
如果你看见诗织小姐,也许也会和她亲近——这是我允许的。我在诗织小姐身上看见可太对和我相同的东西,不同于磁铁,人天生就会和与自己性相相似的人亲近。在我们以前学团体心理辅导的时候,也有学过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就有相似亲近原则。
所以如果有机会见面,希望,希望你们好好相处。这并不是愿望,而是来自姐姐的威胁,谢谢。
现在大家也都在寻找着离开这里的方法,发生了许多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这些,我可能将这些当作科幻故事,在床头讲给你听。但是我处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若还是这样讲出来的话,并不知道会语无伦次到什么地步,只能讲讲开心的事情和你听。
十分想念你,并且爱你。
叶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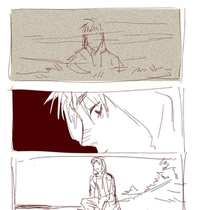

静间蓝一直落在队伍后面,随一行人一道出了深泽家。
眼见那栋气派的建筑即将隐于林间,青年皱皱眉,动作比话语更快一步,匆匆扔下一句“抱歉,先走吧”,便再度返回深泽家门前。
“啊,静间先生?”
深泽美琴似乎正准备出门,见他来,不由瞠目。
“您这是……有什么东西忘在我们家了么?”
美琴歪歪头,不解地问。
静间迎上去,莫名有些难以开口,四下望了望,才摇头答道:“……不是。我有事找实——你的妹妹。”
“嗯?找实琴么?那我去叫她来吧!我们家有些大,您走来走去的,容易迷路了。”
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深泽美琴笑眯眯地又进门去。
这是在防他再进去调查么?……还是他想多了?毕竟深泽美琴原本就很随和热情。
罢了,他再次转来的目的也并非重新调查深泽家,等一等也无妨。
只不过室外终究不如室内阴凉。他擦了擦汗,感到袖内的东西轻轻碰撞,忽然不自在起来。青年便环视四周,恰好,一朵明黄色的花映入他眼帘。它悄悄地躲在墙角处,任由杂草将它肆意淹没。
他记得自己看过。昨晚初次来古宅的时候,他曾看过。但他现在才注意到。
有些不凑巧,但又极其巧合。
他漫不经心地思考着平常并不会特地留意的事,耳旁便响起一阵吱吱呀呀的门响。静间蓝抬头,看见深泽实琴走出门外,不由上前两步。
“……静间先生。”
实琴站在门口,随手掩过门去:“我听美琴说,您找我……”
静间点点头,从袖口里拿出藏了许久的东西出来——是几个动物形状的挂饰与小玩偶。样式虽无太大变化,但做工却足够精致。此前在动物园里“买下”的时候,这些小东西仍沾染尘灰与霉迹,但他后来尽力洗干净了(甚至又引起了高桥九歌的怀疑),现在总算能够“拿得出手”。
“上午去动物园的时候,纪念品商店里有这些东西,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他极力保持语调平静,见她不说话,就又立刻补充,“不喜欢也没关系,不必勉强。”
深泽实琴并没有接过。
“……给……我?”
尽管面无表情,但女孩的眼里闪烁着些微的困惑。
“嗯。小——女孩子会喜欢的吧。”
她微一蹙眉:“……为什么,要给我呢?”
青年叹了口气。他索性蹲下来,尽可能与她齐平,仍旧摊着手里的东西,皱眉笑了笑。
“也没有为什么。”至少是无法说出来的原因。
“……我觉得……您还是给美琴,会比较好,给我……”实琴再度陷入沉默,似乎是在措辞,几秒后才又继续道,“美琴她一定会喜欢的……”
他轻声问她:
“那你呢?你不喜欢么?”
“……”
她愈发困惑:“我……我不知道……”
可这能令她看上去与年纪相符的神色很快也消失无踪,实琴重新面无表情,平静地问他:“……真的要给我么?”
他点点头。
片刻,女孩才缓缓伸出手,从他掌中挑了一个挂坠。
“谢谢您……”
“……没事。”
她捏着挂坠,直直注视他,又盯了一会儿,才移开视线。那双深潭般的眼眸里一派平静。青年被她看得不自在起来,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就听她忽然说:
“……静间先生,真是个奇怪的人。”
我也这么觉得。他竟被自己的心声逗得笑了一笑。
实琴垂眸,看他收回其他东西,又道:“那些……还是请您送给美琴吧。……谢谢您。”
“嗯。没事。”
“如果您没有其他事的话……”
“……没有了。抱歉,还让你特地出来。”
实琴摇摇头,打开门,再瞥了他一眼,简短道别后,径直关上了门。
静间蓝望着有些掉漆的大门,心下松了一口气,也终于感受到新换的里衣被汗浸湿了大片,他挠挠头,走了出去。
——却不想在林荫处看见了抱着双臂的弥生小百合。
静间蓝立刻刹住步子,警惕地看向女性。而弥生笑意明丽,精致的妆容令她看上去攻击性十足。
……她回来干什么?偷听?还是说也是找深泽姐妹有事?他猜不透她。
察觉到了他的戒备,弥生举起空空两手,说:
“我只是好奇您回来干什么。”
“……”
“顺便赶走了吵着要偷窥的高桥小姐。”
“……帮大忙了。”
这是真心话。他实则一心想着把东西送出去,完全忘了高桥九歌还在队里。他这学姐娱记出身,嗅八卦绯闻可是一绝。
“然后就看见了静间先生‘不为人知’的一面。”
弥生笑眯眯地补充道。
没想到居然被她抓了把柄,静间蓝有些头疼,干脆直奔话题:
“……你想要什么?”
“您不必这么紧张,我不会吃了您。”她从荫蔽下走出,几步来到他面前,低声道:“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如果要调查,两人一起不是更方便?”
说罢,她将目光投向那栋静立的宅邸。
“深泽家的秘密太多了。不仔细调查一番,我们恐怕无法安全离开这个岛,不是么?”
静间蓝没有回头。他审视着弥生小百合,试图从她那双微微上挑的眸子里寻见什么。半晌,他淡淡说道:
“叫我‘静间’就行。”
“哎呀,”她笑看他,“那不如叫我‘小百合’吧?”
“……弥生。”
“真见外。”
※小百合ALL太好吃了中之人发出想吃粮的尖叫(你

深泽家探索终结于侍人房内。没料到钥匙就藏在这里,众人皆是有些回不过神,但深泽美琴招了招手,就将一行人领至深泽家的别馆——算了,也是无可奈何。静间蓝暗自耸了耸肩。除却客人茶室的准备室中,一闪即逝的女人面孔之外,之后的探索并没有什么可谓“出奇”之处。
当时,在场七人中只有静间与弥生小百合恰巧同时看见了。两人沉默片刻后,黑发女性笑了笑,说:
“刚才那该不会是——”
“是错觉。”他斩钉截铁。
“哦?两个人能同时看见的错觉?”
“……那就是倒影。”
“可倒影也得有实体啊。啊,静间先生是想说,”弥生歪头,“那是我的倒影么?”
青年一愣,想起女人面容上的斑斑血迹,顿时尴尬,只好清了清嗓子。
“抱……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我相信总有科学解释。”
她扑哧一声笑起来。
“哎呀,我开玩笑的。没想到您逗起来这么好玩。”
“……”
静间蓝大步流星地出了准备室。
别馆面积也不小。小路隐匿于久未打理的绿植后,曲径通幽。推开大门,一股淡淡的霉灰味扑鼻而来。七人鱼贯而入,跟在美琴后面,听她交代注意事项与可使用的区域。听说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好觉时,身旁的高桥九歌不由松了一口气。不过,交代完毕后,深泽美琴不知为何,颇为认真地拉弥生小百合的手,皱着眉头说:
“小百合姐姐,那个……如果要住在这里的话,晚上……晚上一定要乖乖待在房间里哦。”
弥生眨眨眼,似乎有一瞬在犹疑些什么,但随即化作满面笑容,答应了美琴。
美琴便也安心地笑了。
正巧,深泽实琴自门后走了进来。见实琴来,静间蓝想到衣兜里的东西,不由皱了皱眉。实琴的目光并未在他脸上多作停留,而是径自落在黑发女性略显憔悴的脸上。她笑了笑,看了看众人疲惫的模样,出声问道:
“实琴、美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上午探索动物园的时候弄脏了衣服,你们这里有多余的换洗衣物么?能借给我们穿穿么?”
实琴与美琴对视一眼,点点头道:“有的。”但随即声音骤减。“……不过,是……的衣服,所以……不能给你们,”女孩罕见地有些踌躇,低声说罢,又恢复了正常音量,“只有一些之前帮工的衣服……可以么?”
弥生笑道:“当然可以,谢谢你们啦。”
静间便随其他人一起道了谢,心思却仍停在实琴刻意模糊的回答上。复又听见弥生小百合问得别馆内可以洗衣服,青年不禁安下心来,有些难耐地松了松衣襟与领带,等着深泽姐妹为他们取来换洗衣服。
尔后,也不知是谁提议的“将就在这里洗个澡”,场面瞬间变成了“排队进浴室洗澡兼闲聊”。女孩儿们(考虑到年龄分布极其不均,静间犹豫着要不要改为“女性”)迅速打成一团,疲惫令她们刻意回避了一些惊心动魄的场景,只挑着其中有趣的部分,大谈特谈。而男性们——他与泽和就站在一旁,沉默地眺望天际。
“天气真好啊。”
高大的男性眯眼笑说。
“……嗯,”静间含混地应了一声,顿了顿,轻叹道,“有点热。”
“哈哈,待会得好好洗个澡。”
鸟飞云行,蝉鸣四起。风里裹着暑气,拂过耳畔。时间仿佛与人一样,也偷得片刻清闲。
静间淡淡一笑。
“是啊。”
洗了澡,换了衣服,七个人面面相觑。这身仿佛能上溯至昭和时代的服装着实与几个现代人不太能合得上,但有衣服穿就好,大家也只是相互笑了笑。静间蓝没有说话。他注意到了衣服上的暗纹,绣在这套还透着日光气息的衣服上。是一朵绽放于梶叶里的椿花。
而在上午,他们这队调查动物园时,另外一队调查的是公寓。通过交换信息,静间得知了公寓里也有一户人家,衣柜里放着深色暗纹的衣服,和实琴衣服上似乎是相同的。这样一看,说不定就是他们身上这件……也就是帮工的服装么?
这时,弥生小百合问道:
“实琴,这个图案……是你们深泽家的家纹么?”
“……”
深泽实琴瞥她一眼,态度骤然冷淡下来,她毫无回答之意,环视一周后,微微鞠了一躬。弥生无奈地笑了笑,稍稍俯身道:
“哎呀,我是不是问了什么不该问的?不好意思哦。”
实琴摇摇头。
“各位……下午不是还有探索么?请加油。”
然后径自离开了别馆。
※仔细想了想还是不响应泽和老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