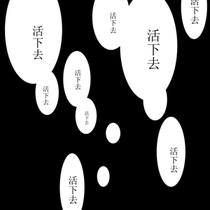截止到目前第一批家族与首领人设已经征集完毕,感谢投稿的各位首领
家族(首领)名单如下
甘伽家族(Diya)【已满】:
http://elfartworld.com/works/415451/
拉杰冶尼家族(帕德玛尼奥·拉杰冶尼)【已满】:
http://elfartworld.com/works/463226/manga/
恭喜各位已经被选为最强候选家族,辛苦了~
11.7更新:
由于各种原因原本的Nacht家族暂时退场,企划人设延期到12.1日,守护者人设依然招收,之后也会再采纳1-2个新的家族进场,给各位带来疑惑实在抱歉。

正式企划书:http://elfartworld.com/works/415225/
人设纸:http://elfartworld.com/works/415230/
Q&A:http://elfartworld.com/works/41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