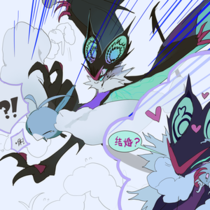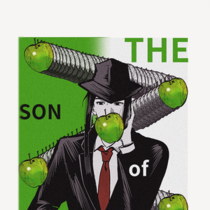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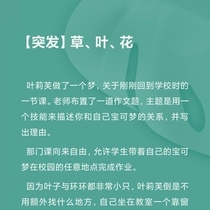

看到时尚达人宣传的时候小唯正独自游走在街头。
黄昏时刻的阳光斜角打在城中河道上,泛出一片波光粼粼。和朋友一起体验项目很有趣,独自感受异国风光也不差。路过某家商店时看到有不少人围在落地窗前讨论着什么,但听语气不像是争吵的氛围。出来玩自然要热情参与一下当地人民的日常,小唯凑近试图搞明白他们究竟在看什么。
“是喵喵大师!”
“有登刊的机会,那可是最棒的时尚杂志!”
人们都在热切地探讨,拥挤和吵闹让小唯只抓得住只言片语的关键词,然后就被从后方挤上来的人推搡出去。但有关键词也足够,小唯寻了一家报刊亭,用一份杂志的钱和一张讨人喜欢的嘴,获得了老板的热情安利。
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就着夕阳余晖小唯快速翻阅着手中的时尚杂志,还没看完,但小唯已经不打算看下去了。简单来说,不是他感兴趣的范围,但是把书带回去给十月看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正当小唯即将合上杂志准备起身离开时,腰间的某个精灵球晃了晃。
看来自己的宝可梦有点别的想法呢。对宝可梦十分纵容的小唯伸手摸向腰间时脑中已经复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但他的手摸到正在晃动的确切的那枚精灵球时,神色变得有些微妙。
那个位置,是沙奈朵的精灵球。
甩手丢球,小唯看着漂在身边的沙奈朵陷入沉默。
自己的沙奈朵,尽管有着飘荡的裙摆状结构,但确确实实,是雄性来着。
因为丢球而导致合上书本的动作被打断,时尚杂志此时正摊开某一页摆在小唯腿上。而摊开的那一页上,是一位身材高挑的模特拍摄的写真图。
一位身着黑色礼裙的女性侧脸,从手中的花束和头顶的纱网来看,还是婚纱。
嗯……倒也没有规定说只有女孩子可以穿裙子,而对于宝可梦来说更不必强行用人类的观点去束缚。
但看着沙奈朵用念力飘起杂志并将那页写真后的店面介绍摊向自己来表达意愿的沙奈朵,小唯脸上的微妙神色更甚。确认过沙奈朵的意愿,小唯叹了口气。
还能怎么样,自己的宝可梦,陪自己走了这么多年的劳模队副队长,当然是满足啦。
“好好,我们明天就去看衣服,顺利的话当天就能拍完出图,怎么样?”
得到满足的沙奈朵在空中转了一圈,给了自己的训练家一个贴贴之后主动钻回了精灵球。
事实上第二天的临时行程比想象中顺利得多。
向接待人员表达了是自己的宝可梦想要拍摄的意愿后,婚纱店的员工表示本店的服装均为人类款式,宝可梦摄影另有专店并为小唯提供了地址。向沙奈朵确定只是想要照片而非写真图里的指定店面和款式后,小唯前往了店员提供的宝可梦影楼。
影楼不小,似乎还兼有服装出租服务,不时能看到主人和宝可梦一同换装后推门而去。而进店后的沟通也不愧于专业的宝可梦影楼。
在小唯叫出沙奈朵阐明需求,并表示细节部分全由沙奈朵自行决定后,造型师唤来了一只爱管侍,从外观来看,这是一只雌性爱管侍。“让宝可梦们直接沟通,效果可能往往要比和我们的效果更好呢,而且爱管侍已经是我们店的老员工了,很值得信赖哦!”
感知到造型师发自内心的认可和赞扬的爱管侍发出了愉悦的叫声,而后又投入进与沙奈朵的交流中。
不愧是广受好评的影楼,即使一向对于穿着打扮没什么讲究的小唯看见打扮后飘出来的沙奈朵也要真情实意夸赞一句十分好看的程度。
基于沙奈朵本身的裙摆状结构,从腰部套上的层层叠叠的大纱裙不需要裙撑也能蓬起,并随着沙奈朵的飘行而微微摆动,让点缀于其上的流光摇曳如夜空中的星星辰。腰部向上则是简单的深v款马甲,起到衔接作用的同时也注意避开了胸口的鳍状部位,原本被成为对训练家一片真心的部位在黑色的配色下似乎变得更艳丽了些许。
双手部分则带上了同样黑色的手套,右手却举着一捧纯白的花束。抬头看向头部,王冠样式的头饰被超能力固定于头顶悬浮,是王冠又更像光环。头饰下半部分固定的黑纱将面部遮盖住了八九分,从飘扬起的缝隙能窥见那其后的一只红瞳,在造型师进行了化妆之后平日含着温柔笑意的眼睛此时更多却是锋芒和杀机。
本就觉得沙奈朵的新造型似乎和预想中有点差距的小唯看完同样以沙奈朵意愿为主导的成品照片后心头的不确定逐渐扩大。等到沙奈朵卸完妆回到小唯身边,另一边的写真也已经打印好,电子档则传入小唯的邮箱中。
返程的路上小唯看着满足了心愿,连在自己身边漂浮时似乎都更活跃一些的沙奈朵终究是没忍住开了口:“沙奈朵,你这个照片拍的时候主题真的是婚纱吗?我怎么感觉你当时相比于婚礼更像是要上战场……”
沙奈朵似乎被说中了什么,但并没有立刻回答。
中途他们去了邮局将用来投递稿件的照片寄往宣传上的地址,沙奈朵仍未对小唯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
直到回到住处,沙奈朵飘去隔壁十月的房间带回来一本书。
那是一本小说,书中的主人公的家族受到敌对势力攻击,以至于才举行婚礼没多久还处于蜜月期的主人公再次换上一身黑纱出席了葬礼,随后她将穿着这身衣服坐镇家族,悼念自己的家人,也为敌人们送去一次次葬礼。
其实并没看完整本书的沙奈朵不知道剧情的前因后果,也没能理解书中人物的种种爱恨情仇,它只看见了那副插图、听到十月吐槽的只言片语。
所以它想换上一身与之相似的服装,它想告诉自己的训练家——
【我将为你战斗,为你带来每一场胜利。
并,永远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