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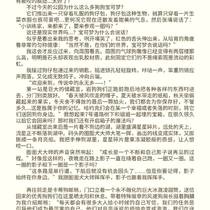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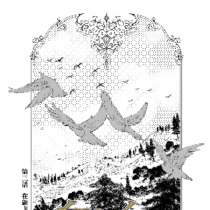






时间线是混沌的,字数是无限膨胀的,但是我写完了呵呵呵呵呵呵呵。
====================================================
眼睛一闭一睁,然后来到一个陌生的空间,这对白砂五月来说是如呼吸一样自然的体验。有时候是新的交流和讯问,有的时候是把他关进狭小的禁闭室。这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镶嵌在他两侧下臼齿上的电击器。它们的信号与自己的颈环相连,而颈环里装着五次份的麻醉剂,无论是让他原地昏睡还是进行人道处决,都是那些研究员按一下按钮的事。
生命依靠吞噬而生,白砂五月想着。他吞噬那群白大褂的情感,吞噬送到他面前的一切血肉,活人;而那群人吞噬掉他的音乐,他的身体,他的...自由?
很少有人跟他提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也很少在乎。从有自我意识开始的18年,光是“隐藏”这一点就已经让他竭尽全力。音乐是他最喜欢的东西,这不是谎言。他喜欢这些振动,无论是弦音、吹奏,亦或是演唱,他能感受到自己,也能感受到他人生命的鼓动,那鲜活的,令人垂涎的——【疯狂】
18岁前的每次演奏,都已他手臂的鲜血淋漓为休止符。
藏起来藏起来藏起来藏起来藏起来藏起来——
不要被“■■”看到——
他舔舐着自己小臂上的鲜血,脑海中回响着飘渺的记忆。
“妈...妈?”
他记得温暖的水声,轻柔的哼唱;他记得女声的尖叫,摇晃的臂弯;他记得那些癫狂的呓语,血色的眼珠。
我生下来的是个怪物,她说。
要藏起来,小怪物,她说。
不然你会和我一样,被贪婪的访客折断翅膀,扔进暗无天日的深渊,她说。
永无自由,她说。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约定,尽管懵懵懂懂,他依旧努力隐藏着自己的异常。
直到18岁时,他与所有人一样躺进了那个机器,再次醒来时,就被关进了那个曾存在于学生们口口相传的怪谈里的监狱。
他观察着每一个进来的人,咽下每一份递到他手里的血食,直到他被穿上束缚衣,冰冷的机械强制撑开他的口腔,为他安上量身定制的枷锁。
从此之后,他吞下再多的血食,演奏再多的乐曲,都听不见那个声音了。
海妖被折断翅膀,堕入寂静的深渊。只有岸上人投来的饵料为他带来新的声音。
比如,“自由”。
少年很久没想起过这个词了,直到又一次的“捕食”实验里,他的猎物没有挣扎,没有逃跑,只是安静地承受着痛苦,直到停止呼吸。
他在断气之前一直嘶哑地呢喃着“自由”。
这里为他许下了什么样的愿景?我的音乐让他看到了什么?
白砂五月平生第一次后悔自己下口太快,让这件事成为了永恒的谜团。他询问着研究员之外每一个他能接触到的人。经常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仆小姐说那是一种麻烦的东西;接手策划演唱会的春日哥说那是“飞向空中的权利”,还有“对外面世界的憧憬”。
“即使死亡?”
“即使死亡。”
他最喜欢的食物依旧微笑着回答他。
好贪心啊,白砂五月想,不过没关系,他也很贪心,贪心到想吞下整个世界。
那是他第一次自己敲定演唱会的主题——“鸟与海”。
即使坠落也没有关系,海妖会在礁石上歌唱,给予他们最终的安宁。
这场音乐会永远不会有听众,但他拿起小提琴,奏响深渊的安魂曲。
不出所料,两个周后他收到了一纸轻飘的否定裁决,取代而之的是另一套索然无味的演出方案:“让所有人都幸福”的音乐,应用着他的作曲原理,把乐句都变得粘稠甜腻。在白砂五月看来,那就像是孩童无意间掉落在沙土上的、吃剩的糖块,而蜂拥而至的蚁虫踩踏着同类的尸体,得到了此生无忧的食粮。
白砂五月最后看了一眼观众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模一样的,幸福而满足的笑容。
啊——这可太无聊了。
他转过头,面无表情地走上豪华的囚车,车上的“工作人员”全副武装,围着他忙碌不停。
“口枷上锁,确认;手铐上锁,确认;脚镣上锁,确认:手臂拘束器上锁,确认。”
“感官隔绝,确认。拘束衣捆缚,确认。”
折翼的海妖被再度投入深渊,随着他喉中不被允许的歌谣沉入众人的梦境。
这次,白砂五月睁开眼,看见的是熟悉又陌生的天花板,从睡眠仓里爬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架着,也没有束缚带。虽然有个奇怪的人和一群奇怪的鸟说了一大堆奇怪的话,但他不觉得这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自相残杀?他和这群人又算不上多么熟悉,现在顶多变成了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而已。他不在乎生,也不是很想死,那就再看会儿热闹吧。
白砂五月打了个哈欠,活动了一下进来之前被电得隐隐作痛的下颚,左手摸索着冰冷的机器外壳,开始了醒来之后的第一次小小“演出”。
遗憾而幸运的是,没人注意到那混入众人心跳的敲击声,没有熟悉的电击,那些黑白色的鸟雀也没有叼着那些迷你机关枪,给他来上一梭子。
真是新奇的体验,小怪物疑惑地眨眨那双漂亮的紫色眼睛,这能说是“自由”吗?
刚刚那些黑白团子结束耸人听闻的宣言后,有人不着痕迹地和他人同行,有人带着恐惧的迷茫去探索楼层。等所有人都离开之后,白砂五月才慢吞吞地走向电梯。嗜吃的小怪物决定先去食堂看看,接下来无论出去也好,出不去也罢,总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嘴。
随着电梯门开的叮咚声,白砂五月赞叹起自己的幸运:他最喜欢的厨师就在那里。那个金发的青年似乎正在捣鼓着那些厨具,又时不时停下手中的摆弄,思考着什么。
白砂五月背着手,灵巧地潜行到罗勒身边,而金发的青年早就发现了他,笑眯眯地同他打招呼,又问他要不要开个小灶。
看着桌上那些新鲜的食材和齐全的厨具,白砂五月眨眨眼。
“一杯仿制特调吧,今早吃得很好,有点意犹未尽。”
罗勒知道他在说什么,白砂五月坐上一旁的椅子,乖巧地等待着自己的加餐。他曾经和厨师合作过一期网络节目,掩盖在那天特别仿制菜品真相上的是“万圣节特约”和“吸血鬼与狼人主题”的幌子。白砂五月咬着吸管,哼着小调啜饮那杯粘稠的“果汁”。
“五月哼的是之前出的新曲吗?我好像没有听过?”罗勒手里的厨刀未曾停下,刀刃切断食材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很是悦耳,白砂五月在可旋转的餐椅上扭来扭去,“不,这首曲子还在那群书呆子的手里审核,但是肯定能过审啦......”
白砂五月喝掉最后一口“果汁”,捏起杯边搭配的盐橄榄。他喜欢这种腌渍果的口感,一如怀念他第一次咬碎眼珠时带来的惊喜。
“多谢款待——”
“对了,五月晚餐想吃什么?”罗勒笑眯眯地拍了一下五月凑过来想顺走黄瓜条的手,“这是用生食刀切的,不可以吃哦。”
“那就...蔬菜餐吧!今天上午虽说吃得很好,但也有些腻......”白砂五月讪讪地摸摸被拍的手,那黄瓜条看上去新鲜得很,清新的果香挠得他心痒痒。
作为开小灶的回报,白砂五月答应帮罗勒去问问其他人的理想菜单。
于是小怪物雀跃着去其他楼层了。
白砂五月闭着眼按下一个楼层按钮,出来的时候却正撞上他熟悉的女仆小姐。
“哇,是最棒的女仆staff芝之!”
匆忙经过的女仆嘴里在念念有词,差点忽略掉向她热情招呼的怪物,“.......啊!白砂五月!”
“女仆姐姐刚刚在念叨什么,连我的问好都没听见?”
不小心无视掉怪物的后果比较严重,女仆深谙这个道理,她略显慌乱地理了理自己的裙摆,“我刚刚说的给大家准备的甜点...白砂五月要不要来试吃一下?”
“哦!那我要吃!”
小怪物伸了个懒腰,亦步亦趋地跟上女仆,并决定看在她负责了他无数场演唱会后勤的份上,忽略掉刚刚听见的话。
虽然女仆小姐的保质期短,但是个好人。她有很多好吃的手工零食,也经常来帮他打扫房间,整理手稿。白砂五月坐在高脚凳上晃着腿,喝下加了柠檬片和方糖的红茶,酥脆的现烤曲奇让他心满意足。芝之同样在安静地忙碌,她正在把烤盘中的曲奇一块一块码放到铁盒里,看上去这些饼干是要作为正式的茶点,出现在某个相对正式的桌子上。
他舔掉嘴角的饼干屑,喝下最后一口酸甜的红茶,躁动的食欲得到了最充分的安抚。女仆小姐严正拒绝了小怪物热情地拥抱,按着他的肩膀“礼貌送客”——毫不留情地将他推出了房间。
好吧,现在应该是去找一件趁手的乐器了。
“管理员,黑白团子——”
“chi!白砂五月找管理员有什么事chi!”
白砂五月伸出手,黑白毛色的山雀自然而然地停在上面。他低下头,用鼻尖蹭蹭鸟雀柔软的羽毛。
虽然有哪里怪怪的,但确实是生命的味道,小怪物深深吸了一口黑白团子的背毛,隐秘地吞下口水,“麻烦你带我去去有小提琴的琴房,可以吗?”
“没问题chi!请跟随我的指示走chichi!”
黑白团子尽职尽责地挥舞着翅膀为白砂五月指路,一直到琴房的门口。
“就是这里了chi!”
“嗯,谢谢你,黑白团子......”
少年轻轻抚摸着黑白色的鸟雀,看上去只是在享受毛茸茸的乐趣,而鸟雀也不曾抗拒,也未曾意识到小小的身躯正逐渐靠近怪物的嘴边。猝然间,白砂五月张大了嘴,将黑白色的鸟雀连着自己的手指一同咬入口中。
意料之外的,他的口腔里没有丝毫羽毛濡湿的触感,反而是来自手指的剧痛让他皱起了眉。他的唇齿之间溢满了温热咸腥的液体,但小怪物毫不在乎地吞咽着,直到聒噪的鸟雀重新回到他面前。
“不可以吃管理员chi!”黑白雀气呼呼地闪现到空中,“这违反了规定chichi!”
“哎呀,小气鬼。”白砂五月舔舔被自己咬伤的手指,“你们有那么多,让我吃一个也没关系嘛。”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chi!再出现这种情况就把你关起来chichi!”
黑白雀气呼呼地跟着其他来支援的同类飞走了。罪魁祸首看上去对这件事毫不在乎,在确认自己右手手指上的伤口已经止血之后,他悠哉地推开琴房厚重的的门。
这里的琴房非常开阔,房间两侧的墙壁和地板上陈列着各式乐器。外侧的房间除了陈列乐器外,似乎还担任了旧时代livehouse的功能,房间的尽头是一个简易的舞台,具黑白雀所说,如果想要单独练习,可以拐进另一侧的小练习室。
白砂五月摘下耳机丢在隔音地毯上,踮脚从墙上取下一把小提琴,简单确认琴身状态后就将琴架上肩膀,随手拉响四个空弦音。
饱满的音色在琴室中回响,又逐渐消弭于空气中。
小怪物很满意,这把琴与他在第一次演出后从公司那里得到的“奖励”不相上下,甚至还要更加流畅。
他拎着琴,几乎是跑上那小小的舞台。当他刚刚站定,就看到一人从练琴隔间推门而出——
岛津明成,最让白砂五月头疼的人。
在社会研究部里见面的时候,岛津见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道谢,感谢他的演唱会安抚了鹿儿岛事件后的民众。
但是在白砂五月眼里,他是一个无比复杂且枯燥无味的宫廷古典乐集合体,还让他加班三个月,剥夺了他难以数计的睡眠时间的存在。
好吧,他多少也是个听众。
白砂五月喊住了岛津明成,邀请他来听自己的练习曲。板着脸的大叔总算停下了脚步,他席地而坐,示意他开始演奏。
台上的演奏者拉响第一个音符。
这是只有一个声部的D大调卡农独奏,略显单调,却是演奏者最喜欢的练习曲。
一把小提琴,一个演奏者,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听众。
今天,他亲爱的听众是一款磅蛋糕。
磅蛋糕,与其说存在时间悠久,不如说是大道至简。虽然一板一眼,但是口味丰富,难以捉摸,也最能体现“原料”——【人生】的味道。
这是怪物无法理解的人,自然,他也不会想要去“捕食”。若是毫无敬意地去染指“未知”......
白砂五月想到了,曾经那个因为聆听自己饥饿时作出的曲子而癫狂的研究员。
那下场可不会太妙。
一曲终了,演奏者微微欠身,而听众则非常认真地为他送上掌声。
“下次加点奶油涂一涂吧,磅蛋糕先生”
岛津先生对五月这样突兀而奇怪的发言并不在意,他只是温和地笑了笑,“原来我是磅蛋糕呢,我的家乡也有这种蛋糕。”
“啊,那下次见面,磅蛋糕先生给我讲讲你的家乡吧。”
岛津明成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消失在那扇厚重的门后。
终于,白砂五月成功地从壁橱里翻出一个小提琴包。将琴,琴弓和松香通通收纳好后,小怪物重新戴上耳机,拎着琴包雀跃地出了门,开始在楼层里漫无目的地闲逛。
很快,他隐约听到了风的声音,还有机械中内置风扇的声音。
小怪物驻足在游戏室门口,透过门缝,他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蓝色——常守春日。
第一次与常守春日见面的时候,白砂五月就觉得,这个人,一定很好吃。
这是白砂五月对常守春日的第一印象,同时,他也对常守春日这么说了。
他感觉到身后的特勤人员紧张地端起了架势,蓝发的青年却在微笑着安抚那两个人。
小怪物的脑袋里冒出了小小的疑惑,他意识到这个人似乎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又或者,那是他无法理解的东西,却有致命的吸引力。
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
常守春日不会沉溺于五月即兴创作的催眠曲,却答应了他的“请求”,许诺分给他自己的尸体;不出几天,白砂五月甚至收到了来自常守春日,以“研究”为名送来的血包。
小怪物戳了戳放在“投喂口”尚且温热的血袋,又看看房间上面的摄像头。
咦,那些白大褂居然真的允许了?
白砂五月迅速抓起血包塞进嘴里。尖锐的牙齿撕开裂口,小怪物拼命地吮吸着,吞咽着,生怕镜头后面的人一个反悔,夺走他最爱的甜点。
要是能一直吃到这么美味的零食就好了,白砂五月想。
此刻,小怪物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来到常守春日的身后。守护者正在全身心地享受着放松的一刻,五月自然不会打扰。他只是安静地关注着屏幕上的动态和春日的操作,并在游戏结束的同时发出合适的感叹。
“好厉害!春日哥能教教我怎么玩吗!”
其实在刚刚的那场“观赛”中,白砂五月已经对这台机器的操作学了个七七八八。在春日的允许后,他启动了4D赛车。
整体操作接近真实,但为了模拟高速前进而设置的出风口实在太煞风景了,五月拧紧了眉头,那风里夹杂着他人难以察觉的机械味道,他实在喜欢不起来。
很快,白砂五月失去了对这个游戏机的兴趣。他微微偏头,瞥了一眼常守春日的脖颈。
他能听到那里的搏动,他想咬下去,想品尝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挣扎,他的惊愕,他的坦然,他的虚弱,他的死亡——
在这之后呢?他将迎来什么?
他意识到那甚至不是有意义的休止符,而只剩下无穷无尽的虚无。
白砂五月不是美食家,他的进食只为裹腹,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品尝”和“美味”。不过,当真正的盛宴出现的时候,他不会拒绝。
可怜的小怪物,他知道那之后同样意味着他的毁灭。
所以,可以再等等,再等等......白砂五月从不缺乏耐心,他想看看他的“蓝莓蛋糕”会走向什么样的末路,在这之后他可以吞噬一个怎样的人生。
“砰”的一声,面前的游戏机响起8bit的结束音乐,五月操控的车在终点线前撞到了围栏。
意料之外的走神让怪物的模仿到此为止。守护者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但怪物知道自己只是虚有其表的空壳。于是他咽下一些话语,将自己转换成另一种样子。
“春日哥之后有什么打算吗?我们好像有一段时间出不去了,我会....忍不住演奏的。”
守护者伸出手,像是安抚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嗯……我这几天大概会和我的其他朋友一起四处看看?说实话我们也在寻找一些针对现状的办法,不过说实话不太放心其他人就是了……”
“不放心其他人?自己一个人不好吗?”
啊——人类是这样呢,在这种时候抱团,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个”,我想要的是......
“是这样的,白砂君,我们每个人,单独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为了寻找办法,我们需要齐心协力,但是又有可能有叛徒会企图破坏这样的和谐,所以才说不放心……”
“我倒是随便啦,因为你知道我‘不是人’呢......所以,能填饱肚子的话,我在哪里都无所谓。”
不对,不对,也不是这个。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帮你介绍,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有这样的觉悟吗?”
“觉悟?你是说...准备?要和那些研究员一样准备很多仪器或者在头上贴什么东西吗?或者找一个空空的白色房间,大家都戴上隔音耳机?”
对!是这个!
“不,只是说这条路很危险,你做好准备了吗?即使...失去生命,也没问题吗?”
啊......白砂五月,再耐心点,摘掉一层伪装试试,对,试试这样......
“一遍又一遍......你是在质疑我吗,烂好人?”
“不,只是有点担心罢了,我不能把任何人平白无故扯进来。”
应该再激进一点,打破禁忌也没关系,这是只有用“脆弱”才换的来的东西——
白砂五月张开嘴,小指勾住自己的嘴角,毫不留情地向外拉扯。他的口腔内侧完全暴露在空气中,那套黑色的牙箍锁套在灯光下泛着寒光。
他们都很清楚,这个东西的含义。
“这样,也能说是平白无故吗?”
常守春日沉默良久,最终点了点头。
“好吧,我会向我的同伴介绍你的。”守护者如是说。
“那我就等着你的消息啦,春日哥。”白砂五月蹦跳着向后退两步,然后挥挥手,“希望下次春日哥能教我玩一些更有意思的游戏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