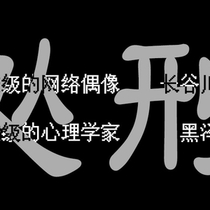我鈤了狗,这真的是推线吗,为什么和主线剧情完全没关系
——————————————————————————————————————————
森林这种东西果然还不如遗都好玩呢,瑞贝利安丧气地想着。
之前圣木之森的探索让瑞贝利安好好的吃了个鳖,腿脚受伤没能好好捣乱且不提,莫名其妙的艾丽西亚又处处碍手碍脚。当然这也不是最关键的,现在瑞贝利安最在意的不是艾丽西亚,也不是如何拆散瓦尔哈拉
而是那个蓝不拉几。
讲道理的话,瑞贝利安觉得蓝不拉几是死是活和他没关系, 毕竟他打心眼里讨厌这个自闭暴躁又别扭的蓝色半卓尔。只是在森林里受伤的蓝不拉几居然遭遇了濒死的危机这一点出乎瑞贝利安的意料。
别死啊!蓝色的!
这个祈祷确实是瑞贝利安打心眼里发出的。只是这并不是出于善意,而是纯粹的等同于小孩子不想自己还未玩够的玩具坏掉的心理。瓦尔哈拉的队员们显然对于瑞贝利安如此关心蓝感到惊讶,然而大家似乎误会了瑞贝利安的本意,反而莫名其妙地以为他回心转意——不过就算如此这个功劳也会落在艾丽西亚头上。
就在瑞贝利安抓耳挠腮地催促着艾丽西亚治疗蓝的伤势的同时,真正关心半卓尔少年的队员们找来了一个纯种卓尔来帮忙。那个纯种的渣滓少女(瑞贝利安擅自给薇塔塔的昵称)叽里呱啦说了一堆让瑞贝利安彻底懵逼的不知名名词,而低智商的瑞贝利安自然听不懂期间的利害关系,对他来说只要蓝不拉几能够活下来就够了。比起让玩具很快地坏掉,能修复一点是一点就是,哪怕玩具的本质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但这对瑞贝利安来说根本无所谓。
只是脑子简单的他并没有料到,三流修理工的渣滓少女竟然把玩具改成了一个让瑞贝利安碰都不想碰的人形自走炮。
他醒来之时,做出来的第一个表情竟然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微笑。这无异于让瑞贝利安感到了看见100万个艾丽西亚程度的吃惊
这个蓝不拉几....“重生”之后似乎变得脑子有坑起来了,瑞贝利安一脸黑线地想着,顺便忽略了他自己的脑子其实也不怎么正常的事实。虽然蓝变成这样让瑞贝利安深感角色重合的危机,但是比起属性撞车什么的,人类战士更加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
“瑞贝利安君!你为何摆出这样的表情!”
“小瑞小瑞——你怎么啦?”
你们俩还好意思问老子怎么了——!?
瑞贝利安的手臂上一如既往地挂着名为艾丽西亚的挂件,而与此同时,他的耳边又再度多出了一只蓝色的苍蝇在嗡嗡叫。性情大变的蓝不拉几一改以往的阴郁与不耐烦,热情地关怀着一直紧锁眉头的瑞贝利安。
拜托,我不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艾丽西亚和你好吗!离我远点我就开心了好吗!!
瑞贝利安向奥列格投去求助的目光,而回应他的却是队长同情的摇头和叹息
....是时候找借口脱离瓦尔哈拉了,迫真
伴随着瑞贝利安的惨叫,瓦尔哈拉又再度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
————————————————————————————————————————————————————
树林子,又TMD是树林子
看到周围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瑞贝利安像死去的僵尸一样翻起了白眼。第五季似乎在刻意和他作对,把它丢进了他完全不想再次看见的地形,也许是之前圣木之森的旅途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过心理阴影,所以现在瑞贝利安只要一看到树林子就会一脸的忧愁。况且众人被传送来的时间点也不怎么合适,现在是漆黑的深夜,四周伸手不见五指,除了能够辨认出这里的地形是松林之外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对于周围本能警惕的瑞贝利安更加崩起神经
“小瑞小瑞,这里好黑啊”
可恶,不仅要紧绷神经,还要预防神经性头疼。瑞贝利安抽搐起嘴角,任着艾丽西亚抱住他的手臂。没怎么见过世面的风元素裔显然对于现在的状况充满了不安,所以本能地跑来寻找能够为她提供安全感的存在。
但为什么是老子,战士翻起白眼思考自己被艾丽西亚缠上的前因后果,照理来说她应该亲近本就是熟人的奥列格,或是同为女性的叙泽特。就算是刻意挑选异性,颜值比瑞贝利安高到不知道哪去的蓝和阿伦德尔也应该是首选。假设是因为蓝的肤色和种族而抱有芥蒂——虽然这位女孩子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人——那么性格绅士沉稳,又礼貌而且关怀女性的阿伦德尔也绝对是少女杀手。瑞贝利安数来数去,从自己身上找到了成吨的讨人厌的缺点,到头来受欢迎的要素自己一点也没有,所以这便让他更加头痛起来。
最终的结论是,艾丽西亚脑子有病。
就在瑞贝利安认真思考拜托艾丽西亚的方法的时候,一行人凭借德鲁伊的光源勉强行进到了一家民宅前。宅子前昏黄的灯光像忽明忽灭,似乎是在刻意指引旅人一般,然而那感觉随时会熄灭的灯火却又透着一丝不详的气息,似乎诉说着房屋的主人其实并不希望访客的造访。
对于这样诡异的宅子,瑞贝利安是不屑于打扰的。对他来说这样还不如睡在树杈上安全。但瓦尔哈拉的队员们明显不习惯睡树杈,尤其是艾丽西亚,这个娇弱的少女如果睡树杈一定会难受得失眠一整晚,而她白皙的皮肤说不定也会划伤,没有精神的话第二天如果遇到什么突发情况遭遇危机的几率也会....
不对不对,干嘛要想这个小崽子的事!瑞贝利安晃晃脑袋,把脑中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关心艾丽西亚”的念头无情地赶走,随后继续冷眼看着众人的行动。
奥列格殷切地敲着破旧的木门,似乎希望房屋的主人能够出来迎接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住宿的场所。这个小矮子还真是不长记性,之前被圣木之森的村民们无情地赶走的经历显然并没有影响到奥列格一丝一毫,但在这种深夜敲门,换作瑞贝利安做主人的话他绝对会毫不留情地骂出一句“滚蛋!”然后再用力踹上一脚,绝不会为他们提供住宿。
等了半晌,门后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瑞贝利安伸了懒腰眯起双眼,打算看奥列格的笑话。
就在此时,门内闪过一丝银光,转生为半妖梦还是梦妖的蓝眼疾手快拽过侏儒的领子才避免了他被破相的惨剧。当然,被那东西砸到可就不止是破相那么简单了。吓得差点没哭出来的艾丽西亚更是抱紧了瑞贝利安的胳膊。
不过....对方只是个拿着锄头的惊魂未定的农妇而已嘛。
对方瞳孔紧缩,握紧锄头的关节发白,并且不住地颤抖着扫视在场的众人,脸上的湿润以瑞贝利安的经验来看八成是所谓的冷汗。在农妇的目光扫视到艾丽西亚的时候,瑞贝利安轻轻捏住了自己的剑柄。
如果这个女人打算做什么,下一秒就把她砍成两半....
好在阿伦德尔及时地收走了妇人的锄头,这个举动无意间也许救了惊恐的女人一命,不论别人,至少瑞贝利安对于任何人都是抱有杀意的。
可惜,可惜了,这一点都不好玩。
不出意料,瓦尔哈拉在解释清楚情况后被对方带有歉意地招待进屋,而瑞贝利安则百无聊赖地坐在一边把玩着另一只瑞贝利安的小耳朵,并没有参加谈话的意思,当然也对谈话的内容没有丝毫兴趣。
不过....与农妇攀谈的人们中,有一个家伙让他觉得格外刺眼。
蓝不拉几——
一扫以前的厌世与阴郁,现在的蓝开朗又健谈。如果说以前的他的暴躁易怒和痛苦的回忆与记忆是瑞贝利安在瓦尔哈拉最大的乐趣之一的话,现在的他只不过是一个让他感到恶心的虫子罢了。看着他灿烂的笑容,瑞贝利安更是恼得牙直痒痒。
凭什么那个蓝不拉几就这么解脱了啊....
如果他被过往继续折磨下去的话多好啊,如果他能露出更多痛苦的表情多好,如果他能为自己的无力永远懊悔下去多好!可是现在的那家伙算什么鬼!
为什么他能够那样自在地笑下去!
凭什么他可以,我就不行呢——
瑞贝利安稍微发现了,他觉得蓝刺眼的原因并不是憎恨
而是嫉妒
嫉妒他能够得到永远的解脱,嫉妒他能够有救赎,嫉妒他能有另一个家伙给他带来更好的结局。瑞贝利安不了解蓝,不知道他对于这件事的感想,然而对他来说,那便是“救赎”,从黑暗中脱身投入永远光明与温暖的未来的救赎。
为什么他可以.....
如果受伤的是我,如果我也遇上了一个半梦妖,那么名为瑞贝利安的人类是否能够得到幸福呢
将牙齿咬得咯吱作响,瑞贝利安用血红的双眼死死盯着蓝的耀眼笑容。
原来那便是得到幸福之人的笑容吗
可恶
可恶
可恶
那个蓝不拉几....不再是玩具了
我对他失去兴趣了
那种躯壳,破坏掉就好了
对啊,如果堂而皇之地行动会遭遇队友阻止的话,只要伪装成是意外,只要趁着他落单,甚至只要在他们睡着的时候....
轰的巨响打断了瑞贝利安的思绪,他回过神来看过去,窄小的木屋中不知何时竟多出了一个无头怪物,而那怪物正发了疯一般袭击屋内所有人。
说着....机会就来了啊?
挑起嘴角的瑞贝利安拔出背上的巨剑,在一旁开心地开启了旁观者模式。
无头的怪物似乎是遂了瑞贝利安的意愿一般,死盯着蓝不拉几不放。说不定是那个家伙的肤色太过显眼了呢?瑞贝利安此时也觉得蓝不拉几十分显眼,显眼到就像是白色纸张上的黑点。如果能够从纸张上撕去那个黑点该有多好!所以在怪物掐住蓝的脖子之时瑞贝利安几乎要欢呼出来。
不过瓦尔哈拉的众人不会坐视不管,大家似乎很努力地想要救下那个蓝色的家伙。尤其是艾丽西亚,她用尽浑身解数攻击着无头的怪物。而少女的努力似乎有了效果,一道闪电啪地被召唤 了出来,并且正中怪物的背部。
怪物的手松开了
啧
瑞贝利安有些不满地瞪向艾丽西亚。
果然要先解决掉那个小鬼....
不对,哪里不对
放下了蓝的怪物正在寻求下一个目标,而它的目标是....
艾丽西亚
正面对上那个家伙,这个弱鸡风元素裔能够撑多久?
那怪物坚硬的手指只要稍微一用力就能捏碎那个女孩的头骨不是么
那个怪物轻轻一挥,艾丽西亚所仰仗的藤蔓啊,闪电啊,就能被轻而易举地破除不是么
在其他人拉回怪物的注意力之前,那怪物能有足够的余裕去把风元素裔打成肉酱,顺带着把那只小狼崽像捏蚂蚁一样捏爆
艾丽西亚,可是老子的猎物,怎么会让你抢去——!
一声怒吼,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思考,战士的巨剑带着呼啸的剑锋挥向那怪物的脖子。而之前还在执着的蓝不拉几此刻似乎被瑞贝利安忘了个干净,现在他的眼中只有这个想要伤害艾丽西亚的怪物
破坏掉他!粉碎掉他!
“咣当!”
金属撞击的声音发出,瑞贝利安的手被震得发麻,怪物的硬度超乎了他的想象。但也并不是徒劳无功,这一击成功地让怪物把他定为了最大目标
可恶,果然那个小崽子就会给老子扯麻烦。
瑞贝利安朝地上狠狠啐了口吐沫,准备发动更强的攻击。然而此时,怪物却像着了魔一样离开了房间。
莫名其妙的家伙,看了眼毫发无损的艾丽西亚,瑞贝利安暗自松了口气。
“瑞贝利安君,你没事吧?”
“!!!”
这个蓝不拉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本来被转移了注意力的瑞贝利安这下又再度怒火中烧,只是在队友们高度戒备的现在他也不好从中作梗,战士只好无奈地压抑住自己的怒火,从牙缝中勉强挤出一句话:“今天算你捡了一条命。”
屋子所隶属的村庄似乎注意到了这里的骚动,有人在朝这里赶来,但这些都和瑞贝利安没关系,他静静地坐在角落,不断将拳头握紧又松开,指甲渐渐将手心按压出淤青,但本人似乎没有察觉到一般依旧不停地重复着这些动作。
“呐,小瑞?”
瑞贝利安抬起头,艾丽西亚正手捧茶杯站在他面前,旁边的小狼崽晃着尾巴吐出舌头绕着他跑来跑去。
“做什么,我现在没心情陪你胡闹”
艾丽西亚递过茶杯:“小瑞心情不好吗,你一直一脸生气的样子呢”
“不需要你关心”瑞贝利安愣了愣,还是勉强接过热气腾腾的茶杯,轻轻晃动着杯中散发着热气的液体。
“发生了什么事,可以和我说,不用憋在心里哦!”
“...都说了不需要你关心”
“是因为蓝的事吗”
瑞贝利安僵住了。
虽然不知道艾丽西亚是如何察觉到这一点的,但他显然并不想提起这个话题。对于蓝的厌恶此刻又像海啸般翻涌,瑞贝利安的手指越捏越紧,直到“啪嚓"一声将茶杯捏成碎片,任凭滚烫的开水流淌在手上,和从被瓷片刺破的手掌中流出的血液混杂在 一起,他的手也没有松开。
“不要给老子提到那个家伙”瑞贝利安浑身颤抖着,但却意外地没有怒吼出来,他只是保持着平淡却带着颤音的语调低声念着,“那个随随便便就得到了幸福的家伙——真是如同粪坑里的排泄物一样,这种没有任何活在世上价值的家伙,毁掉就好了。”
艾丽西亚并没有发表什么评论,她只是静静看着瑞贝利安的双眼,小小的手掌轻轻掰开瑞贝利安的拳头,小心翼翼地清理着伤口。
似乎是找到了什么发泄口一般,瑞贝利安深吸一口气,垂下头去盯着地板:“为什么...那样的小杂种都能触到光明呢”
不懂啊,不懂
神为何要和他作对,将他丢人无限的黑暗,哪怕是曾经给予他过一丝丝希望的曙光,却又毫不留情地立刻熄灭。
难道自己被称为渣滓的卓尔都不如吗?
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所以才要这样惩罚他吗?
难道自己就没有回到阳光下的希望吗?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就慢慢在阴暗的角落腐烂好了,什么救赎,都是笑话!那些背叛了黑暗擅自离开深渊的叛徒,就像那个蓝不拉几,一定要狠狠地制裁他,把他拉回来!
“小瑞...”
耳边又响起了少女的声音,瑞贝利安不耐烦地连看向她的脸都没有,只是用鼻孔哼了一声作为回应
“小瑞,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约定...?
“如果小瑞不知道什么是温暖的话,就让我教给你吧!”
“我对这本笔记发誓!今后我会一直在小瑞身边,而且会让你明白究竟什么叫做‘爱’的!”
“我会让小瑞得到幸福的”风元素裔少女坚定地伸出双手,第一次环抱住瑞贝利安的脖颈,“如果小瑞在嫉妒蓝的话,就由我来帮你让他反过来嫉妒你吧!”
少女的身体很暖,像有什么魔力一般,让瑞贝利安使不出力气去推开她
又是这种胡话
又是这种不切实际的约定
又是神派来戏弄他的所谓的“曙光”
反正也是谎言吧?反正也会在某一天像之前一样背叛我吧?
但是....好想就这样溺死在这谎言之中啊
瑞贝利安闭上双眼,第一次没有对少女发出拒绝之声,他将头埋入少女的臂弯中,像只被驯服的野兽般静静享受着抚摸
“艾丽西亚”
“怎么了小瑞?”
“你也别忘了我们的比赛”瑞贝利安吞下口水,用沉闷的声音低声宣告道,“在比赛完成之前,不准离开我”
“我是很好胜的哦,才不会逃跑呢”艾丽西亚笑着回答了
“那么加上一个赌注吧”瑞贝利安抬起头,“如果我赢了,你就把你的笔记本交给我”
“诶——那如果我赢了呢!”
瑞贝利安顿了顿,半晌才开口:“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你”
艾丽西亚笑了,那是瑞贝利安此生见过的最为灿烂的笑容。
“说定了哦小瑞,我是不会输的!毕竟笔记本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呢!”
为了笔记本吗....果然是天真的小崽子。瑞贝利安笑着脱离了艾丽西亚的怀抱站起身来,打算去和队友汇合。
“而且,我也想得到小瑞呢!”
战士停住了脚步。
他笑了,那并不是看到了什么痛苦的事情而发出的扭曲的微笑,而是被一种久违的不知名情感所驱使而出现的笑容。那种情感在他很小的时候曾经出现过,那是他还在佣兵团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人递来的一碗热汤之时出现的。
“走着瞧吧....”
“还有还有!小瑞如果想欺负蓝的话,我会阻止你哦!”
“哼,真是个让人没办法的小鬼”
一下下也好,暂且沉浸在这温暖之中睡一觉吧。
晚安,瑞贝利安。


自“噩梦”事件发生之后,观察对象“哈克”的状态仿佛回到了刚进入研究所的时候:服从研究所的一切指示,配合研究所的一切实验,但不相信研究所里的任何人。
不管怎么向他追问“噩梦”发生时他看到了什么及之后频频被噩梦缠身时又梦见了什么,他都闭口不答。哈克的这个状况让研究小组的成员束手无策,他们只能选择冷处理这一方式。
初期大家只是将他的反常当做事件遗留的影响,过段时间就会自然恢复,但渐渐地,哈克的反常表现越发明显,其程度也越发激烈。
然后,观察对象“哈克”于某日攻击了前去做例行取样的护士后逃跑。
这时研究所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当尼努提克匆匆赶到抓捕现场时,已经有三名护士一名研究人员负伤,两名护士昏迷。而抓捕目标仍在逃跑中。
“……虽然对你很抱歉,但是已经没办法了。”丹格其利老教授有些无奈拍了拍尼努提克的肩膀,接着他通过对讲机向所有参与抓捕的人说道,“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抓到哈克!决不能让他逃出研究所!”
“不管用什么方法?就算是会伤到他也无所谓了吗教授!”
“是的。”
“……教授!”
“尼努提克先生,如果你有时间在这里与我争论,倒不如去抢在别人前面抓住哈克!”
听了老教授的话后,尼努提克一声咋舌,便是转身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开始回想自己观察哈克这么久以来,他最长出没的地方。
“……只能一个个地方找过去了。”
当哈克从通风管道口跳下来看到刚巧来到这里的尼努提克时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而后显露出了强烈的攻击性。
还未等尼努提克开口,哈克就已经率先将他扑倒在地。
“哈克!冷静点!!”
“哈克!”
一番争斗后,他与哈克拉开了距离。尼努提克的手臂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哈克弄伤了,血止不住的往外流。
“告诉我,哈克。你遇到了什么?你在害怕什么?”
“我……只是单纯的实验体吗?”
“实验体?你在说什么……疼。”手臂上的伤不断传递着疼痛感,当尼努提克被疼痛分散注意力的那一刻,哈克再一次准备逃跑。
然而在他转身的那一刻,就在刚才埋伏好的研究所成员从暗处窜出来,使用针对他制作的抓捕器让他动弹不得。见无法挣脱抓捕器的拘束,哈克更是猛烈的挣扎了起来,期间更是发出了如同野兽一般的嘶喊,他的这副样子不由得让一些年轻的研究人员感到不寒而栗。
“对不起,哈克!”同组的同事一边道歉,一边压制着他。
尼努提克捂着手臂上的伤口,看着其中一人有些粗暴的抓住哈克的头发,将冰冷的特制麻醉剂注入了他的体内。
“…………哈克。”
这是尼努提克第一次见到哈克这样疯狂的状态。
在被关进那间纯白的房间后,哈克的精神状况似乎变得更不安定了。他开始利用身边的一切尝试自杀。为了阻止他这一行为,已经许久没有使用的拘束服再次被发挥它的作用。但这并不能阻止哈克的自杀行为。
最终,哈克全身束缚被牢牢的绑在床上,嘴中也被塞了东西阻止他咬舌。
他被夺去了自由。
尼努提克曾对此提出意见,但全部被老教授驳回。查看哈克状况时要求一定要两人同行,避免哈克再如当日做出攻击性的举动。而尼努提克则被老教授警告绝对不许单独接触哈克。
“就算现在你是哈克的搭档,也不能单独接触!”
“但是教授,这样不是办法!一直拘束着他,剥夺他的自由……这样的我们和当时利用了他的组织有什么不同?!”
“现在只能如此!等那家伙回来以后,他就能恢复自由了!”
“那家伙?教授,你要对哈克做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当哈克睁开眼醒来后,他感觉头很重,这种感觉让他感到了难受。等他缓过神来,他注意到自己躺在观察室里,边上是正写着什么的尼努提克。
“哈克,感觉怎么样?”注意到哈克醒来的尼努提克放下了手中的记录表,凑到他身边关心的询问道。
“……”
没有回答的哈克稍侧过头,看到了自己正挂着的点滴,还有一旁柜子上的电子钟。
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
十二月二十六……?昨天不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吗?为什么……
“尼努提克。”刚叫出他的名字,哈克便被自己有些沙哑的声音吓到。
看着哈克对自己声音的沙哑而感到有些惊讶的样子,尼努提克便立刻倒了杯水,然后把他扶起让他把水喝下去,“恩,我在。”
喝完了水感到舒服许多的哈克直视着尼努提克的双眼。
“……发生了什么?”
“什么发生了什么?”
“……”
记忆出现大片的断层,他不记得这二十多天发生了什么。而尼努提克的笑容不知为何让他感到了疑惑。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尼努提克沉默了片刻,而后扬起了与往日无异的笑容,“什么也没有哦,是你的错觉吧?”
“………………是吗。”
即使他不知道自己被抹去了这段时日的记忆,但这异样感和尼努提克与往日无异的笑容,让哈克对尼努提克这个年轻人产生了不信任感。
为什么要对我说谎,尼努提克。


十二月二十五日 雪
1、
坐着盯住房门一整晚,但却一直没有等到谁进来。
意识变得模糊起来的时候,外面的天空已经泛起了光亮。
我在凌晨终于入睡了。
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外面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音乐声。
难道这一夜真是个平安夜吗?
我摇摇头,嘲笑着突然出现在脑海中的这个念头。
为什么自己还活着呢?
我站在洗手池前用凉水擦脸,试图让自己变得清醒,想要找出接下来该做的事情。
总之还是走出房间吧。
打开门的一瞬间,走廊对面的钟鸣响起来,装饰华丽的座钟里飞出了木头小鸟,发出“礼物”、“礼物”的尖细叫声。
与此同时,我的脚碰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一看,地上有个扎着缎带的纸盒。
红色的盒子和黑色的缎带,怎么看怎么都像束缚着不断膨胀、几乎要溢出来一般的恶意与不祥。
不过,这时的我,竟然觉得兴味盎然,拉开缎带,揭开盖子,拿起里面的东西时,几乎要笑出声来。
这是把手枪。
除了重量以外,它的形状和质感和我之前的那把M37没什么区别,我举着它瞄准钟面正中偏下,那只仍然聒噪着的小鸟。
“圣诞快乐。”
枪口并没像我想象得那样射出铅弹、塑料弹珠、木头塞子或者任何一种子弹,穿过空气,撞碎木板,弹开发条、齿轮和金属零件,把它击得粉碎。
枪口只是喷射出一面红色小旗。我站在那里,像个傻瓜一样。
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抑制住想要疯狂大笑的冲动。
啊啊,这个游戏,似乎让卷入其中的人都变得不正常了。
从走廊上经过时,我得知,雪乃小姐不幸身亡,“红皇后”们恰如其分地,为她安排了具有节日气氛的死亡方式,正如主办方送给我们的那些“圣诞礼物”一样。
“既然是游戏,那么就沉浸其中,把外面的世界和生活都抛在脑后,彻底地把这艘漂浮在空中的飞艇当成舞台,套着规则所形成的手铐脚镣起舞怎么样?”
这场游戏的组织者,似乎是想传达这样的事情。
“Jingle Bell”的音乐声越来越近,响亮而欢快,接着仿佛驶过的车子一般带着喧嚣声渐渐淡去了。
2、
我站在船首,看着玻璃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以及下面灰色的大海,飞艇在云层下面飞行,沉重的云团像要压下来一样,周围光线昏暗,弥漫着暧昧不清的气氛。
突然,灰色的云团下面,有什么细小的东西飞舞起来。
仔细辨认了一下,竟然是小小的,闪烁着微弱的白色光芒的雪花。
雪片从云层中不断降落,
我凝视着这些落入大海的雪,似乎隔着双层玻璃都能感到周围那寒冷刺骨的空气,假如它们在建筑物、平坦的地面或是树木上堆积起来,一定会形成美丽的雪景,而这些雪花就只能在飞艇窗口投射出的橘色灯光映照下急速下坠,最后在浮起波浪的暗沉海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不是有点凄惨呢?从小溪进入河流,从河流进入大海,作为水蒸气飞向天空,成为云,在寒冷中成为冰晶,最终又回归广阔无垠的水的世界,谁也没看到过它们的姿态。
它们只是这样诞生,然后消亡而已。
不过,四周一定非常安静吧,或许能听到雪花簌簌下落的声音。
我从舷窗那里离开的时候,感到稍稍释然了一点。
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染上恐惧、悲伤、慌乱,而我作为年长的男性,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局面,保护和帮助弱者,尽我所能履行我的职责,反而深深陷入猜疑和愤怒,这是非常可耻的事。
虽然还想再多听一些、再多看一些、再多思考一些,无论如何也想找到什么方法,让剩下的人一起回到地面上,但是,我的时间似乎已经不多了,接下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额外获得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结束。
至少我可以留下一些什么吧。
讨论再一次开始了,不知为什么骑士没有禁言,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会场上了,还是想要大家进一步地相互指责、互相怀疑呢?
想到有可能从这里开始就被驱离会场,一言不发地等待黑暗降临,突然觉得有点庆幸。
我依然维持原来的怀疑对象。
认为确凿无疑是红方成员的家伙们开始转向无辜的旁观者。
因为上一轮怀疑我的雪乃小姐死了,我照例背上了很大的嫌疑。
指向我的人中也有我相信属于“爱丽丝”一方的人。
请睁大眼睛看看吧,不要再逃避了,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每句话都是有意义的,从一开始到现在……
凤条院六一被投票处决的时候。
一色一心被投票处决的时候。
忈被推向辩论席,最后坠落大海的时候。
还有现在这个时刻。
3、
宣长被投票处决了,随后就是又一个黑夜,还是什么也没来得及说。
我内心仍然存在着一线希望,能够从黑暗中再看清点什么。
不过大概不可能了。
只能期待这张纸片有人发现。
如果我几个小时后还活着,死因,以及
如果我死了,请和
并不但
……
……
……
啊,终于听到敲门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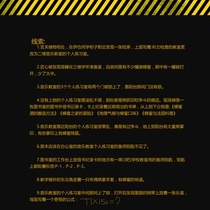
时间是十月底,天气已经渐渐转凉,呼吸间透着冰冷水汽的空气一下子顺着喉管冲进肺里,就像是忽然窜起的火焰从身体里升起,蜷曲跳跃的火舌瞬间堵住了空洞的气管,灼烧混合着窒息的感觉让尹洛不由得捂住嘴狠狠咳嗽起来。
刚出门就被空气呛到,尹洛平复着剧烈的呼吸暗自想着,今天可真是倒霉啊。
伸手扯了会儿斜挂在身上被同一个实验室的同学笑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古董”的墨绿色布包,他深深呼吸试图让冰凉的气体唤醒自己还有些迷糊的大脑,顺便冷却今天从起床开始就跳动得有些快的心脏。
过速跳动的心脏导致身体内血液含氧量下降,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氧供给,四肢莫名沉重,大脑一片昏沉,某个区域的精神却高度集中,太阳穴一下一下鼓动着,高声尖叫着刺痛神经。直觉叫嚣着不安感,胸口弥散着好似会有某种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一般的焦虑,尹洛却无法分辨这到底是期待还是害怕。他自嘲地抿唇,倒是觉得现在的感觉和以前每年体质测定时跑一千米时站在起跑线上的感觉差不多,虽然最后能够及格,不过总分不怎么好看就是了。
他再度深深呼吸,试图赶跑脑中吵吵闹闹的杂乱思绪,将注意力集中在路边的景色上来。
天空是难得的干净,泛着冰霜般的淡淡青色,东边是一轮微红的朝阳,接近太阳的天空被阳光刺目的白所掩盖,稍微远离一点才能看出浅浅的橘色,却又很快过渡为微微带有些许凉意的粉色,和通透的蓝晕染成一片。
无风无云的晨间,布制的鞋踏在坚硬的石板路面上激不起一丝声响,枯黄了许久的树叶慢慢悠悠从枝头打着旋飘下,树下堆积了不少在这寡淡的世界里堪称浓墨重彩的落叶,日渐光秃的枝桠不知何时已经从夏日浑厚的深褐褪成了水洗一般的浅棕,黑色的鸟扑棱着羽翼落在细长的枝上,长长的尾羽摇动着像是某种奇妙的舞蹈,枝桠轻晃间让人担忧脆弱的枝干是否会就此折成两段。
科技楼两边在盛夏还开着月季的花坛现在只剩下光洁坚硬的泥土,早被挖去的土地上连坑洞都消失不见了,只余下一层浅浅的霜。大楼外壁如久放的书页泛起古旧的黄色,边角处还有剥落的墙壁能看见内里灰黑的水泥,新安装的玻璃大门清楚地映出来往人群漠然的表情,晦暗到让人几乎分辨不出砖石与人的区别。通风太好的楼内只是稍微减缓了外界冷空气入侵的脚步,温度却是没升高多少的。明亮整洁的楼内与楼外可以称得上是“历史厚重”的外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正常的嘛,尹洛暗暗想着,毕竟比起外表,还是内里更加重要些,前段时间装修后连他所在的实验室都舒适了许多,只是墙壁被粉刷得惨白惨白的,晚上在白炽灯的照耀下更加阴森,不得不说和各种逃生场景有几分相似。
尹洛的实验室在地下一层,和他一个小组的成员在隔壁找了间空屋子,并把桌子也都搬了过去就当成了办公室在使用,最近还新增了一张躺椅,现在是连午休都可以不用回去了。
“师兄!早上好啊~”推开门冲尹洛笑得露出一口白牙的青年是去年新进的研究生,到现在在实验室已经待了一年多,一直跟着尹洛做课题。说是尹洛带着他做课题,实际上由于某些原因,实验室的同伴们都不让尹洛碰仪器,所以与要动手操作仪器的部分都是那研究生完成的,尹洛的工作就是算数据,找资料,设计步骤,写论文啊等等不需要碰到仪器的部分。
“师兄,这个是昨天晚上测到的数据,我可是一直守到了凌晨三四点来着……”说着研究生就张大嘴打了个哈欠,揉着眼睛一副睡眠不足的模样。他冲尹洛摆了摆手:“师兄你先看看吧,我去补眠了。”
接过研究生手里的U盘,尹洛淡淡“嗯”了一声,他一直不擅长与人交流,即使没有镜子他也能想象出自己现在的表情一定僵硬又刻板。
身后的门被轻轻带上,“啪嗒”一声落了锁。尹洛像平时一样拿出了电脑,插上电源,将U盘里的数据和图像读入电脑,一行行符号与数字在眼镜上反射出惨淡的荧光。伴随着键盘敲击的声响,他渐渐放空大脑,全心全意沉浸在这个由数据构成的庞大世界里。
————————
一开始是轻轻的敲门声,门内果然如预料一样毫无动静。研究生驾轻就熟地旋转把手,令人欣喜的响动过后,门向里打开了。
房间里端坐着打字的年轻人有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略略比普通的短发长上那么一点儿,据说是这个人嫌弃理发店太麻烦而自己剪的。研究生偷偷笑了一下,哪里是嫌麻烦,其实只是单纯地不想去人多的地方而已吧。那人厚厚的镜片总是会反射出各种光,让他的面容一直掩盖在眼镜下,让人瞧不清楚,比如现在,电脑屏幕上飞速闪过的各种数据字符给镜片镀上了一层淡淡的荧光,过于复杂的式子让研究生看得有些头晕。
摇头赶走纷乱的思绪,研究生定了定神伸手拍了那人一下,咧开嘴笑了:“师兄,还在忙呢?”
尹洛被突然出现的拍打吓了一跳,即使那动作很轻,他还是不禁全身僵硬顿住了。
“师兄?”见尹洛没有反应,研究生好笑地重新叫了他一声。
“……嗯。”尹洛应了一声,紧绷的神经放松的瞬间,脑海里纷杂的数据公式渐渐散去,之前一直堆积到大脑某个角落里的五感似乎也回来了,他这才感觉到空荡荡的胃里仿佛有火焰在燃烧。瞟了一眼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点,错过了饭点的胃袋呻吟着渴求着食物,尹洛只好先灌下一大杯水填一下,已经放凉的液体顺着喉管直直地灌注入胃里,凉意瞬间传遍了四肢,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看到尹洛瘫着一张脸面无表情地抖了一下,已经很熟悉这位师兄习性的研究生了然地点点头,自然而然地从背包里拿出一块压扁了的面包递了过去:“师兄你又没吃饭吧?喏,这块面包还能填填肚子。”
尹洛也不客气,点头嗯了一声就接过了面包拆开包装吃了起来。
“啊对了,有件事我差点忘了……”研究生一拍脑袋,“之前我来的时候碰到老师了,他让要你去找他一下,就在办公室里。”老师就是指带着尹洛所在实验组的导师。
尹洛很快解决掉了这顿时间堪比下午茶的午餐,转身便上了八楼。导师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的八层,每次他站在电梯里听见拉着电梯厢的铁链嘎吱作响的时候,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操心这古老的电梯会不会掉下去,但事实证明它还是挺靠谱的,至少在尹洛乘坐的时候从来没有出过事故。
尹洛导师所在的办公室并不是像一般人想象中一个教授该有的干净整洁,相反那间屋子十分杂乱,漆得雪白的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和简报,窗子旁边巨大的白板上也用磁石订着不少写满了字的纸张,旁边还用马克笔画着标记和各种图像,书柜和桌子一样乱,好在这间屋子楼层较高,看起来还算明亮。
比如此时此刻,导师顶着一头发际线日渐上升的光亮脑门从满桌的纸堆间抬起头来,温和地对尹洛笑笑,就算作打招呼了。
日常对实验进展、学业情况等的问话过后,导师轻咳一声,状似不经意地问到:“尹洛啊,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去做理论呢?我这里还有几个课题,都很适合你啊。”
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尹洛本能地回答到:“不用了,我想做实验。”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仪器总是会那么容易坏掉,即使每次得到的数据都那么不尽如人意,他依然不想放弃。
“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导师小声自言自语到,随即脸上又挂起了过于温和的笑容,如果是他带的其他学生在这里,肯定能看出导师的不自然,然而在这里的是尹洛,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发觉,依旧端坐着等待导师的问话。
“尹洛啊……学校有一个交流的项目,对方是一个叫做‘MC’的研究机构,和我们学校签订了长期合同,希望能够有学生去交换生活一段时间。”导师顿了顿,看着尹洛,“我这里刚好有一个名额,打算派你过去,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MC?Modem Codec?Material Control?Maneuver Control?Multicarrier?Magnetospheric Constellation?难不成是大学?简写为MC的啊……难道是Montgomery College?Mercedes College?总不会是Marin Catholic吧? 尹洛默默想着,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加利福利亚那里的天主学校和学校有什么交流项目……
导师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回答,再仔细看时发现尹洛像往常一样瘫着脸,坐姿端正一动不动,厚重的眼镜隔绝了外界探究的眼神,让人无法辨析表情神色。明明尹洛看上去一本正经一副正在仔细思考的模样,但导师莫名其妙就是有种“啊这个人是不是走神了果然还是走神了吧”的感觉。
“咳咳。”实际上导师自己手边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尹洛本身也不是一个能说话的人,再等下去恐怕也不会得到什么答案,于是他便轻轻咳嗽两声示意尹洛注意过来,“既然你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嗯……嗯。”尹洛想了想,还是同意了。
见尹洛答应,导师高兴地笑笑,眼角边的皱纹又多出了不少。他语速稍微快了些介绍完那家机构是做关于电子设备方面的研究,实验室的材料或许对那家机构有用处,签订合同的话或许还能得到一笔新的科研资金。另外由于MC研究的是很前沿的设备,大部分没有面向市场,或许尹洛还能够亲自体验一番最新的科技。
最新的科技啊……尹洛走出导师办公室的时候,脚步罕见的有些飘忽。能够继续做实验,还能够碰到最新最尖端的仪器,接触最前沿的理论——这些毫无疑问对他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有研究表明,人在面对害怕的事物时会感到紧张、心跳过速、血液上涌、四肢发软,但这样的反应与身怀期待鼓起勇气、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切困难而充满信心时的反应是一样的,说不定早上的奇怪感觉就是后者呢。
这么想着,尹洛走路的速度都快了些。
地下一层的屋子窗户在墙面的上边,窗沿几乎贴到了天花板。几缕仿佛秋日般清浅的云絮悄悄蔓延出来,愈发冰凉的天空如烟波般淡薄,一片飞鸟的剪影从窗台一闪而过,带起扑簌的羽翼摩挲声渐渐散去,所有的响动又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