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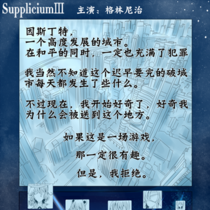
DAY 1
“长官先生”
-----------
我们像海里的游鱼,追随着点点亮光,毫无目的,直至坠入永恒的黑暗。
-----------
“请叫我长官,新兵。”
鸦影看着面前——黄色的,有着黑色核警示花纹的蛋——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发出的声音。
“就是在叫你,”蛋的语气颇为严肃,“你这个新兵,不知道要叫长官的吗?”
鸦影沉默了一会,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女孩子会怎样做呢?
她歪了歪头,扮出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笑脸。
“好呀,长官先生。”
蛋满意的晃了晃,鸦影想,看来是把自己当成小孩子了呢。
很不错。
-----------
鸦影想起她的长官,真正的长官。
当时自己还是个新兵,和其他同样带着一身青草泥土味的新兵蛋子们整齐地站在操场上,烈日暴晒,她感觉她黑色的羽翼几乎都要散发出烤焦的味道。
然后她看到了她的长官。
逆着阳光,她甚至可以看到他白色的翅膀闪闪发光。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教官了。”
……长官他,是白鸦。
几乎完美的白鸦,强壮,聪明,身材高大,年轻,充满了力量感和压迫感。
鸦影看了看左右两边的同期,每一个都至少比自己高了一头。
即使对于乌鸦的体型来说,也过于矮小瘦弱的自己,站在这里真是格格不入。
-----------
鸦影靠着墙边坐在了地铁长椅上,她看着“长官先生”蹦跳着,也“坐”了上来,停在了她旁边。
“要吃糖嘛?长官先生。”
鸦影打开了自己背着的包包,从里面掏出了金平糖罐子,倒出了两粒,塞到嘴里,然后侧着头看着黄色的蛋,伸着手把罐子举到它前面。
“不了。”
“唔……”鸦影收回了罐子,盖好盖子,又装回包包里,之后又拿出了一罐。
“还有其他口味的,要吃嘛?长官先生。”
“……不了。”
鸦影打开包包,像是小孩子摆弄心爱的玩具一样,拿出了一罐又一罐的金平糖,又放回了包里。
“……我们这是在哪里呀?长官先生。”
“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才能回家呀……?长官先生。”
“不知道。”
鸦影失落的低下了头,手攥着包包,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好想回家呀……长官先生……”
-----------
鸦影在训练场上被叫住的时候,她刚刚结束了新一轮的体能测试,结果非常糟糕。
她想,也许自己真的不适合做这个,所有的数值都不合格,也许很快就会被踢出队伍,打包回家吧。
她回头,看到的是自己的白鸦长官。
“你很介意自己的身体?”
长官居高临下的看进她的眼睛里。
“因为身材太小,缺乏力量,看起来像个没长大的小女孩,这点让你感觉自卑了?”
……够了,真不想从你这个完美的白鸦口中听到这些话。
像是读懂了鸦影的心思,她的长官继续说道:“你认为是缺点的地方,也会带来相应的优势,比如体重轻带来的灵活迅捷,是其他学员不能比拟的。”
他爽朗的笑了笑,拍了拍鸦影的肩膀。
“只是一味的沉浸在自卑中,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可是你对自身才华的最大浪费哟!”
鸦影抬起了头。
“而可爱的外表,也是具有迷惑性的,你要学会充分利用这一点,毕竟人们对‘小孩子’的警戒心是最低的。”
-----------
周围汇集了越来越多的光点,像萤火虫一般。
“开心一些了吗?新兵。”
黄色的蛋发出了机械性的声音,仿佛里面还掺有一些关怀一样。
从蛋的裂隙中,光点越来越多的飞了出来。
“哇——”
鸦影两眼闪闪发光,伸手去抓面前的光点,但是它们太灵活了,在她面前晃了两下,又倏地飞走了。
“呀……等等我!”
鸦影站了起来,抖了抖翅膀,追着光点飞了起来。
而同时,这些光芒也像是有意识要她追逐一样,汇聚成了一队“萤火虫”,朝着角落的拐角飞了过去。
很好,她追着我的“萤火虫”去了,果然乌鸦的习性就是喜欢亮光……
留在长椅上的蛋原地转了转,缝隙里溢出了更多的光芒。
-----------
“乌鸦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亮闪闪的东西。”
随着这句话,她的长官手里攥着一把亮晶晶的项链,吊坠等东西,在她眼前晃了晃。
“所以今天这课就是要你学会克服它。”
鸦影努力压制着想要伸手的欲望,抬起头看着她的长官,她看到他白色的翅膀羽尾也在微微颤抖。
“长官你也有这样的弱点吗……?”
她的长官愣了一下,旋即哈哈大笑了起来:“好歹我也是乌鸦啊!”
她记得之后的那些日子,拼命的与本能抗争,每次败给本能之后,都会摔得痛不欲生。
……简直就像在建立新的条件反射一样。
-----------
光芒汇集越来越多,整个地铁站都被温暖的黄色光芒所照亮,鸦影追着亮光越飞越远,绕过了站台,飞过了拐角。
蛋转了转身体,看起来像是在看长椅上鸦影留下的金平糖罐子一样。
就引诱到最里面的角落解决她吧……
“萤火虫”排着队飞向了最后墙角的角落。
鸦影毫不犹疑地跟着飞了过去,娇小的身体瞬间淹没在了墙角的亮光之中。
“——??!!!”
小姑娘不见了?
长椅上的蛋突然紧张了起来,强光过后,它视野中失去了她的身影。
它不停地切换不同的亮光,每一个亮光都可以提供视野,它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地铁站全方位的视角,可是都没有她的身影。
它看到身边的金平糖罐子倒在了一旁,糖果撒了一地。
“这样轻敌是不对的哟,长官先生。”
声音在蛋的后面响起。
“有亮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你的视野不可能是全方位的哟,长官先生。”
蛋转了一圈,看到了鸦影站在后面,手里拿着水瓶。
这是……?
它看到散落的金平糖,闪烁着不寻常的光泽。
水瓶中液体发出淡蓝色的颜色,从瓶底逐渐融化的蓝绿色“糖果”上翻滚着气泡。
“你的攻击方式就是那些萤火虫吧?”
她举起了瓶子,朝着蛋的缝隙倒去。
“没有了它们,核心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吧……?”
不,快回来!
散落在角落的光点迅速的又向回聚集起来。
“太晚了哟,长官先生。”
蓝色的液体灼烧着机械的核心,连同着地铁长椅一部分都被灼烧融化,散发出奇怪的味道。
“你……是从什么时候……察觉到我要杀你……的……?”
核心最后发出了机械化的声音。
“好歹我也是个士兵,‘只做不问’这点基础我还是知道的。”
空了的瓶子被扔在了地上,汇集过来的亮光在鸦影背后,给她拉长了一个深深的,长长的影子,隐藏在阴影里的面孔上再也看不到像小女孩一样天真的表情,取而代之是轻蔑的笑意。
“……再见了,长官先生。”
-----------
再见了,我的长官。
她想起那时她跨过沾满了血液的白色羽翼时,脑海里唯一的声音。
这些可都是你教我的呢,我的长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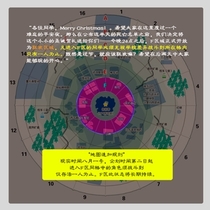

烟蒂落进烟灰缸,她往窗玻璃上吐出一口烟雾。外头在下着大雨,水珠沾在玻璃那面,她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那根被他抽过的烟,愣愣地看着高楼下在雨中穿梭的车辆。
在这之前她刚囫囵吞下两块奶油蛋糕,他坐在客房深蓝色的皮质沙发上看着她,看她的勺子一起一落,一下剜去某些生命。他觉得她越发不可理喻了起来。
面粉和奶油在她的肚子里融为一体,她蹬开躺在她通往大床路上的高跟鞋,黄色的尖头鞋被抛起,而后又落下,依旧躺在灰色的地毯上,间隔分明就像她被一刀划开的人生。
他们一起倒在床上,并排躺着,起先一言不发,而后她开始呓语。她总爱呓语,他却恨那些她喃喃细语的片段,没有一丁点儿关乎他,不过是一些她的妄想。
她现在肿胀着左脸颊,旁人问起她都说那是智齿痛惹得祸,但那上面青紫交错,熟识的人或许还会看到他的拳印。但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也不是真正关心她,他们也不喜欢她蹙起眉头吐出的那句“You Muggles!”,语气尖锐,仿佛他们真如傻蛋一般。他们甚至有些同情他了,交上了一个神智错乱的——他们思索定语,最后抛弃“女友”而选择了“情人”一词。
但他们还是待在一起。她现在躺在他身边,胳膊上还带着他们刚刚搏斗后的痕迹。他用水晶的烟灰缸角猛击她的胳膊,她则提起高跟鞋尖敲击他胸前的肋骨。不论哪一样都很疼,但他们此刻都躺下来了,在白色的床单和柔弱的席梦思上。她的左胳膊还在疼,伴随着每一次心跳传递着血液经过那被攻击的地方。她又开始回想曾经。
她从没打过这么惨烈的架,她当年可不是干这些的,如果她的魔杖还在手边,她或许会抛弃高跟鞋,魔杖直指他的心脏,读一句“Stupefy”就能证明她所说的曾经都并非虚假的记忆。但是可惜,当然了,她的魔杖并不在她的手边。
她也曾和他叨念过霍格沃茨,世界上最神奇最美妙的地方,但他嗤之以鼻。
“你在胡思乱想,这都是假的。”
“不,那是真的,只要你能去上一次,你马上就会明白,对于曾经我从不撒谎。”
这是他们无力的对白。
她的胳膊真的很疼,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她也是偶尔才会在记忆中找出相应的场景。
“我的胳膊还在疼。”
所以她向他抱怨道。
“嗯哼,正巧,我的肋骨也还在吱吱叫唤。”
“它让我想起,在霍格沃茨时我也弄疼过胳膊。”
“哦,拜托,您不用在这样的情节上也绞尽脑汁编出一个故事的,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别再对我说这些胡话。”
他翻了个身,伸长手臂拉过头顶上方的枕头,将它枕在头下,撇过头不理她了。
她独自起身,胳膊又在痛了,她试着忽视那疼痛,但失败了。忍耐对她而言依旧是多年来难以学会的技巧,不论是面对愤怒还是面对痛苦。绝望?她的脑中忽然闪过这个词,随即又被摁下了。她又点起一根烟。
烟雾中一切似乎又回到她身边了,胳膊和脸颊的青紫都褪去了,她穿起巫师长袍,拍拍外套上的灰尘,跨步走过中世纪拱栏。
走在她前方的人同样一袭长袍,蓝色的编带表明他拉文克劳的身份。
Ravenclaw,Ravenclaw。她把这个词在口中咀嚼了两遍,能再听到这熟悉的词语真是令人怀念。
她看到年幼的自己向对方央求着决斗练习,她这才想起自己当年也算是决斗俱乐部的成员。
多可笑,那是她不过十岁,痛只是停留在肌肤表面的概念,从未深深刺入肺腑,伤得她满口鲜血。
多拉,那是她可爱的小多拉,仰着头走在她拉文克劳的学长身边,蹦蹦跳跳的脚步像尝了糖霜那般雀跃。
她从烟雾中看见他们手执魔杖,一边是十一英寸的紫杉木,一边是九又四分之三英寸的樱桃木,两只魔杖对准对方。她思索起这张决斗练习的最终胜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她才三十岁不到,怎么会这样健忘?真是该死。
答案还没从她脑中的馄饨中完全抽离出来,她忽然想起那时的场景,另有一根魔杖搅入了这场战斗,那是一根十三英寸的柳木,被一只保养良好的手拿着,那手指长且有力,除了克制不住的颤抖之外一切都很完美。她想起被对方拦在身后时的感觉,吃惊中夹带埋怨,但在那个身影被击倒时,却又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上升,震颤她周身。
眼下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帮助她回忆当时的片段了,她记得唐·璜在蓝光闪过之后就倒下了,但还不等她走到他身边查看他的情况,那双因疼痛而颤抖得更加剧烈的手就握住了他的柳木,将尖端对准了缓缓走上前的拉文克劳。
Papilio·LEE的那双眼睛在她的记忆中一晃而过,那眼睛是什么颜色的?蓝色?银色?她又记不清了,离开那个地方不到十年,却有太多东西伤害了她的记忆,她明明记得当年她还很迷那冷峻面庞的学长的。
或许当年她还深陷于小孩子的情迷意乱之中,可现在不同了,她有得是时间,身边的男人已经开始打鼾,鼻息间带着种可悲的平稳。记忆如一带录影带,她拼命按住暂停键,将时间拉回至那场唐·璜和papilio莫名其妙的决斗上去。唐·璜她是再熟悉不过了,灿烂到泛滥的男人,其他部分都很完美,但就是不适合做一个巫师。如果他是麻瓜,她这样想着,一定会过得很好,一辈子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几度爱恨情仇辗转反侧,最后找到一个愿意交付自己的伴侣,一口气活到九十几岁。另一个男人呢,papilio乍一看就是和唐·璜完全不同的人。像是城市高楼尖上挂着的银色月亮和田野天空中扣着的金色太阳那般,他们格格不入。俊俏的容颜倒是都在他们身上停留了,但一个叹息着一个愚笑着,引向不同的宿命。她记得多拉每次见到papilio时他都沉默着,像是在脑中思考最深刻的问题。她曾经希望他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能穿透彼此的肌肤,但他不是的。他沉默着,站着,坐着,生死情爱或许也曾在他的脑中打转,但就像克里姆特的油画那样,他常常摆出那种姿态,那种明白一切都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事情,在那一切进行的时候,还有很多奇怪的面孔或狰狞或慈祥地在高空看着他。于此相比,唐·璜有时也会沉默,绝大多数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但有一次,圣诞节放假时她回了家,皮箱放在门廊,她转头就看见她的哥哥坐在沙发里,慌张爬起迎接她时还不慎被手中的烟头碰着了手。三两步蹦到她面前,她透过家中壁炉那有些暗淡的火光看到两道泪痕。她从未见过唐·璜哭泣,也不敢想象那哭泣。他还有什么烦恼呢?一切在他身上看上去都那么完美,他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有时候她真的觉得,比起沉默寡言的papilio,那个夜晚的唐·璜更让她难以接近。
烟还点在她的指缝间,她很习惯地又吸了一口,总结了刚刚的回忆,那不是属于她的战斗,真奇怪,她怎么又想偏了?她明明记得自己在一年级的时候是打过一场真真正正的巫师决斗的。
视线扫过一旁乱糟糟的桌面,红金配色的杂志上,那两块刚被吃完的蛋糕的碎屑还留在那上面。过往她每每想起甜品,总觉得有一种愉悦之情从心底跳跃而出,像是能带她回到还点着蜡烛,烤得暖烘烘的学院休息室里那般。沙发软得能让人陷进去,周围尽是学长学姐们的笑脸,她红着面庞凑在学长们的身边,听他们聊O.W.Ls,聊魁地奇,聊恼人的同学和一些平稳年代里的新闻。然后她可以枕着身边不知是哪一位学长的胳膊在逐渐上升的温度里入眠,最后被一个Mobiliarbus给送回自己的被窝。
多好的生活,多美的过去。她呼出一口烟,不由得感叹。
其实比起烟草她此刻更希望能有酒精的抚慰,能呼麻自然是更好,可她手头现在没有余钱。
回忆拉远,追溯着她当年的决斗继续前行,然后定格,放大,她想起了另一个孩子,奥利弗·德·美第奇。一个有着一头红色长发的意大利男孩。她不想去理解为什么唐·璜会对意大利人有那么大的意见,她还是觉得奥利弗很可爱的,一双绿色的大眼睛乍一看就让人心生好感,后来她听说唐·璜一见到绿色眼睛的姑娘就要载跟头的传闻,心里还咯噔了一下,可惜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平平静静,她的生活还是不起波澜。奥利弗一向喜欢和人交流,咋呼起来的时候一点不输那时候的自己。有多拉和奥利弗一起出现的场合,她敢保证,如果格兰芬多塔再低那么上那么一点,他们一定能用叫声把它掀翻。这样回想起来,她完全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进行过巫师决斗,还是在双方都是一年级新生、大家一同见证下的堂堂正正的决斗。
于是舞台上只剩下他们二人,视线聚焦,仿佛光束只打在他们身上,两具身体,两个年轻的灵魂。
她几乎想不起为何要战斗。她夹着烟反复确认自己的记忆,最后想起那时她寄放在休息室的施洗约翰不见了。但她很快又想起这只不过是她的借口,她心里清楚得很,好斗和不甘寂寞才是这场决斗的真正导火索。
骑士们出手时会如何?礼毕之后,他们的手心是否也会出汗,他们的胸膛是否也会起伏,他们的双腿是否也会颤抖?她想起他们双方行礼,然后背靠背迈步。然后转身。然后,两倍的“Expelliarmus”。他们几乎是同时脱口而出。
蓝色光芒一闪而过,几乎照亮了在场每一个人的眼睛。当然谁都不会指望一年级的新生打出怎样精彩的决斗,但场下还是有呼声的,就像是麻瓜世界中,再无聊的打架斗殴都有围观者喝彩那般。结局也是恒定的,呼声过后,一人倒下。这是数百年来的规定,对战必然要有一方落败,就像灰头土脸和趾高气昂永远对等那般。她记得当时她后脑勺着地,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结局对现在而言没有意义,失败也不过是对她那时任性的惩罚。烟蒂从点着的尖端开始下落,掉在了她的裙子上,她伸出手扫开那团灰烬,然后又感受到了自胳膊传来的疼痛。
她从没想过未来将会以这样的形式降临在她身上,窗外的雨还在下着,砸在每一个地方。
桌子上还放着她下午时分做到一半的剪裁工作。她喜欢拿着一把大剪刀将杂志上看到的喜欢的东西统统剪下来,从胶水贴在自己的本子上。有时那是一副画,有时是一两句诗,但多数都是当下最火的服装造型,由身材火辣的模特展现在铜版纸上。但今天不一样,她剪下的是难得的诗句,又是一句来自遥远东方的诗。她几乎要产生那个地方人人都是诗人的错觉,倾吐出口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人以纸记录,然后集结出版,远渡重洋送来给她这样的人看。
那首诗里,那个东方诗人写雨,和她当下一样的雨,她平稳地看下去,看下去。然后那诗说:
——当我把一段烟灰弹落,另一段烟灰已经呈现
她被文字提醒了,也弹了弹手中的烟灰,然后继续读下去:
我把一个人爱到死去
另一个已在腹中
她转头去看床上的那个男人。情爱在一瞬间变得难以分辨了,她将手上的烟留在烟灰缸上的夹口里,转身往那男人的方向爬了点,低下头看着他。
奇怪,她突然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了,眼前一阵模糊,她竟连他的模样都看不太清了。相反的,曾经逝去的青春年华中的那些人们全又都回到了她的眼前,一个个穿着她熟悉的巫师长袍,笑着闹着走过她熟悉的霍格沃茨的角落。
她突然涌出了几滴眼泪。她又是谁呢?她只是一个金发紫眼的女人。她没有了名字。
有些夜晚,有的男人称她“多多”,她会突然抬起头,无所谓的眼神变得凌厉,从此再没人敢那样叫她。
这样就对了,她想到。
她从身后抽出那块属于她的枕头,拿在手中。她闭上眼睛,在心底默数十步,然后猛然转头迎向还在沉眠在梦中的他。
她的手上没有魔杖,但她高喊着Reducto,而后枕头代替魔杖狠狠地落在他身上。他从梦中惊醒,正想询问何事,却见她张大了嘴巴,从喉咙最深处吼出一句Get out you son of bitch。
他慌了神,他从不知道她会这样,她不是应当是一个可爱调皮的姑娘吗,怎么会变得如此可怕起来?入睡前对她的厌恶在此时转化为了恐惧,他觉得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于是他扯起自己的衣裤,顾不上皮鞋的左右脚,一边用胳膊阻挡她的攻击和吼骂一边拉开房门,溜了出去。
她停下了攻击靠在门边喘气。然后似乎又想起来什么,她丢开手中的枕头,飞奔到窗口去低头看。
她看到他穿着昨夜皱巴巴的外套,万般无奈地迈入夜晚的绵密细雨中。
她笑了,迈步坐回床上时,她的动作已十分优雅。她瞥了一眼刚刚还未读完的诗,那最后四行文字躺在她剪下的小纸片上,像是被关进阿兹卡班的囚犯,无处可逃。她终于笑了起来,拿出了她还是唐娜多拉时的语气,读完了那首诗:
雨落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声响
没有谁消失得比谁快
没有谁到来得比谁完整
没有谁在雨里,没有谁不在雨里
TBC
迟到的第二章,先向这章和我互动的朋友说一声抱歉……尝试了好几遍正常叙事最后都因为不满意删掉了,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真的是很抱歉(……
然后第二章的剧情其实是①多拉加入诺拉教授的决斗俱乐部并且在俱乐部中碰到了Papilio ②多拉央求papilio陪她练习巫师决斗,结果半路老唐不明所以冲出来挡枪,被打倒之后送去医疗翼治疗 ③因为树猴是老唐变的,所以老唐住院了之后多拉找不到自己寄放在休息室的树猴,误以为是奥利弗(其实更多就是她想打架)的问题所以找奥利弗决斗
文章里的时间线是自家ULparo里多拉的R5故事,想写出一点毁灭前的忏悔,不知道有没有把这种感觉传递给大家……
那首诗是余秀华的《雨落在窗外》,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适合多拉,特别是那句“我把一个人爱到死去/另一个已在腹中”,完全符合我对于多拉的定位,喜欢得不得了也被这句话虐得不得了……
最后再次和看了这篇文的朋友们say一声sorry……对不起我又播撒负能量了(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