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典狱长卡维莱克很少前往维稳科的办公地点,每次有新的任务发布,所有维稳科的成员都要到监狱内部的办公楼去,在一楼的会议室聆听他的指示。
这让他们得以从近距离观看那面高墙,和多年以来“监狱”这个词给人的印象不同,这里并没有高大的灰白石墙和铁丝网,外墙呈现着浅浅的赭石色,囚室所在的的建筑也和普通的公寓楼没什么区别。铺在地上的灰色碎石砾让环绕着楼群的广场看起来像个运动场。
但是,牧羊犬们知道,这里每一处都设置了机关,每一处都安装了监视器,地上和地下都进行了加固,同时配备了具有相当战斗力和经验的狱警。这里的犯人身体内也植入了监控情绪的测量仪,以及在恩典暴走之前会释放麻醉药剂的控制器。
设计这座监狱的人显然不希望它给予这栋建筑里的囚徒压迫与恐怖的感觉,而是希望它尽量显得和平、明亮、开放,但是,典狱长对此保持着完全否定的态度。
卡维莱克似乎觉得,这个地方充满了无法学会控制恩典,拒绝学习控制恩典,或是利用恩典伤害别人以获取利益的人。只有让他们从心底体味到震悚,才可能进行下一步的反省或赎罪。
又或者他并没有考虑后面的事情,安抚、教育、保护、给他们赎罪的希望和机会是别人的事,他只是一直坚持着强硬态度,对一切表面顺服的犯人保持审慎和怀疑,指出罪行、制裁罪行、把可能发生的罪行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并没有错,再没有比卡维莱克先生更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了。
赫西亚坐在能容纳五十人,像间教室一样的会议厅里,盯着正操作着全息投影的典狱长。维稳科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永远只占据着前四五排座位,就算是人数最多的时期,这间屋子也从没坐满过。
——如果能够再坚决些、再果断些,像他一样完全不会动摇,熟悉的亲切面孔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消失掉了呢?
在维稳科工作时间比较长的成员对典狱长都怀有尊敬、顺从、抗拒和某种程度的亲切感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情。每一次看到那张头发花白,像用凿子切削成的雕塑一般的脸,赫西亚总忍不住这么想。
但是,这次典狱长出人意料地,明显在因为什么事而动摇着。
2、
“昨晚的事情大家都还记得吧,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去找到那个不守秩序的小混蛋——”
卡维莱克根本没看听众,而是把眼神投向会议室的后方,仿佛那里有人,或者其他什么活物正在移动。
赫西亚也忍不住朝那里瞥了一眼。但一闪而过的只有云层掠过太阳投下的阴影。
“昨晚停电的时候,研究所里有‘羊’跑出来了……他的照片在这儿。”
卡维莱克把印着彩色照片和档案的纸张分发给维稳科的同事们。
赫西亚吃了一惊。昨天夜间巡视完宿舍和监狱,赶到研究所时已经快夜里两点了。当时研究所的供电已经恢复,秩序井然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之后自己一直在二楼走廊守着,直到早上八点左右才离开,在这期间,外面虽然黑暗,但左侧、右侧和对面的办公楼都开着灯,如果真有什么人悄无声息地离开,只可能是在断电之后到恢复照明的这段时间,或是从自己视角无法触及的一楼或者地下室出来。
——为什么会感觉不到呢?
赫西亚按了按太阳穴。明明有维稳科的成员在,还发生了这种事,这让他感到有些挫败。
直到坐在前面的卢卡斯细心地数好每一排的人数,把一叠纸递到他面前,他才把注意力转向资料。
赫西亚发现,模样像个孩子的“羊”几乎没有什么详细信息。资料上除了能力描述,身份、真实姓名、实际年龄、履历档案一概不知,甚至连他是属于“羔羊”还是“黑羊”都不清楚。
想起昨夜受到“噩梦”困扰的“羔羊”和“黑羊”们,他们仿佛身临其境一般感受着痛苦。潜意识中释放出的力量尚且如此,清醒而有意识地使用“恩典”竟然能影响到“牧羊犬”,这真的是个孩子吗?赫西亚看着那偏长的白发和毫无波澜的平静眼神沉思起来。
3、
弗罗恩岛面积不大,但是教堂、图书馆、学校、码头、商店街和树林里到处是可以藏身的地方,海岸线又遍布着巨大的礁石,其中为阴影遮挡的洞穴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要搜索整个岛屿的每个角落非常困难。维稳科甚至动用了直升机在空中搜索,几乎整整一天过去了,依然还是没有找到“羊”的身影。
赫西亚、卢卡斯、吉恩、阿多尼斯和赫伯特几个人已经搜索了有墙壁的地方的每一个角落,现在他们穿过树林,准备再次在外面找一找。
赫西亚沿着海岸线走着,打算到码头附近看看。那里有交错停放的小型帆船和渔船,还有一些废弃不用的集装箱。或许“羊”就藏在那个地方。
冬季的阳光照在海面上,把水雾染成金色,远方陆地上的城市也笼罩在柔和的光晕里,浪花舔舐着岸边的礁石和沙滩,海水显得比平时更加湛蓝深邃。
码头附近有建在礁石上的水泥建筑,似乎原本是作为接待登岛人员的登记处使用,现在已经废弃了。门和窗早已朽坏,因此有人把它们卸了下来,那座方方正正的小屋经过日晒雨淋,已经与棕色和黑色的礁石融为一体,空洞的窗口和门就像岩石的缝隙一样。光线从它们一侧投射过来,让它们一半沐浴着光辉,一半沉在黑影里。
看着那栋小屋,以及下面交错咬合的方形石块,赫西亚突然想起了某种东西。
——浅棕色和浅黄色的……纸箱……
——用透明胶带封口,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上。
4、
“全整理好了,我们明天出发。”
父亲背对着他直起身,擦掉额角的汗水,盯着那些纸箱子。关节上缠绕着橡皮胶布、布满伤痕和茧的右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身后传来了吵闹声,母亲只穿着背心,把上衣缠在腰里,海藻一样的黑色长发披散下来,她像呵斥雏鸡一样驱散开一拥而上的弟妹们,把锡制的平底盘子抱在胸前不让他们碰到,然后从里面捡出没有干瘪的无花果,一一塞进他们手里。
他看了看仓库外面的小家伙,她抱着叫不上名字的盆栽,像猫一样把身体藏起来,只露出半张脸和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她的嘴角贴着纱布,左眼的淤青还没褪去。
他抬起头看着父亲的脸。
“莎洛姆可以搭我们的车去圣弗朗西斯孤儿院吗?”
“没问题。”
光线从仓库顶上的天窗照进屋里,有无数灰尘在不停舞动,看起来像是什么活着的东西。
……
……
……
“看啊,是雷暴。”
“哇,真是惊人。”
“云和云像是要干一架一样呐。”
年长的同事们放下手头的东西,从拆开的杂物箱之间穿过去,一起挤到窗子前面,仰头看着灰色和黛色的浓云在天空中像两个巨人一样彼此撞击,闪电和火花就在云的一侧绽开,把云团的一面映成青白色。下面的山、树木、房屋建筑,甚至教堂穹顶的彩绘玻璃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那道光芒也照亮了他们的脸,兴奋和专注的表情和小孩子没什么两样。
……
……
……
“……下次不要带这么多啦!”
即使隔了这么远,他还是能听到夹杂在海风的呼啸与海浪的轰鸣之间的,得意忘形的大笑声。
他看见教给他活下去的技巧,让他把这座岛屿当成心灵的一部分,允许他寄予全心全意的尊敬与信赖的长辈,正站在栈桥上和家人挥手作别。
船舷上漆着花体字母的白色渡轮像水禽一样分开波浪,高高地鸣响汽笛,那个人站在鼓胀的行李箱和一堆大大小小的纸盒中间不断招手,最后竟滑稽地跳跃起来。
直到渡轮越来越远,变得像一尾鱼,一只贝壳,一枚石子,最后在远处的城市边缘消失了。中年男人才意识到有人在看着自己,他窘迫地抓起头发,之后勉强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不要光站着看,过来,帮我搬东西。”
……
……
……
或许因为“羊”在潜意识中发动的能力不够强大,或者由于研究所的屏蔽设施发挥了作用,昨夜的噩梦没有影响自己,但现在,赫西亚看到眼前的景物改变了形态,岩壁上的阴影变成了来来去去的人像,起伏不平的浅褐色岩壁作为幕布衬托着他们的行动,自己进入了梦中世界,就像午睡时进入浅眠一般,大脑已经确认自己身处梦境,但身体却无法挣扎醒来。海浪声变得若有若无,四肢沉重得像灌了铅一样。
——这就是那家伙的能力吗?
并非噩梦,而是幻影。或者说,是“遗憾”所聚合而成的幻影。
这种感觉一点都不好,“牧羊犬”咬紧牙齿,试图把目光移开,尽量不在脑海中回忆那些形象和他们的声音。
长久以来他尽全力履行着“犬”的职责,认为只有摒除恐惧,意志坚定,比“羊”更早看清眼前的目标,才有资格带领他们、安抚他们。没有受到恐怖和担忧的折磨,现在却被虚假的幸福所迷惑,这是决不能允许的事。
即使这样,他还是忍不住,想要多看一眼逝去故人们的面孔。
5、
突然,那道岩壁上出现了站立的人影。
他面对大海站着,柔软的金发垂在肩上,双手伸进口袋里,白色的外褂像海鸟的翅膀一般随风飘舞。燃着的烟从他的嘴巴和鼻子里吐出来,烟蒂闪烁的火光,变成了几不可见的小小火星。
于此同时,通讯器里传来急促的喊声。
“……赫西亚,发现目标了!”
——真是够了。我在干什么啊。
虽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去,但重要的伙伴和友人就在身边,面前还有更多的相遇,现在可不是沉浸在回忆和感伤中的时候,赫西亚加快脚步向海岬奔去,晃动起来的幻影渐渐失去了颜色,像沙子被风吹散,消失在湛蓝的海洋和天空之间。
他看着那个人垂下头,双手环抱着身体蹲下身去,身后的影子越来越短,最后,变成了一个银发的少年。
少年似乎意识到了“牧羊犬”的接近,回头朝他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转身敏捷地跳到下方的礁石平台上,试图攀着岩石到沙滩上去。
“喂!”
他试着向目标喊话,但少年没有停止的意思。
赫西亚加快了速度,联络设备上显示吉恩和赫伯特正在海滩上移动,玛尔斯他们的直升机也早已降落,而卢卡斯正越过树篱和灌木,从林子里通往海边的小径上向这里奔跑。
少年的动作出乎意料地迅速,道路尽头是断掉的岩壁,假如让他钻进下面的岩洞,从相反方向溜掉的话,大半天的辛苦就白费了。
赫西亚转身向路边跑去,压低身体伏在地上,在少年的脚切实地踩到沙滩的瞬间,用半自动手枪射出了麻醉弹。
少年像只鼬一样身体一扭,低头躲过一块凸起的岩石,第一枚子弹在那石块上弹开了。
但随后而来的第二枚子弹拖住了他的脚步,他的脚下开始摇晃,浅浅的脚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后,那个小小的身体向前倾斜倒下,刚好倒在了面前出现的一双手臂中间。
是金,他的脸上依然看不出什么表情。
6、
“为什么小家伙要那么跑,还要差遣我们这样费力地去找呢?如果是恶作剧的话,玩累了就会自己回去了吧。”
其他的同事已经离开,或是正在带“那孩子”前往研究所的路上,只剩下卢卡斯和赫西亚在防波堤上慢慢走着。
“大概没那么简单。”
赫西亚回答。
卢卡斯低头思索了一会儿,突然开口问道。
“赫西亚前辈,有没有受到‘恩典’的影响?”
“……啊,有的。”
“真是意外,看来这种‘恩典’比想象得强烈。”
“是啊。”
接着,年轻牧羊犬好像想要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又停下了。他左顾右盼,终于还是眨着眼睛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虽然这么问有些冒昧,赫西亚前辈看到了什么呢?”
年长几岁的同事眯起眼睛,露出了怀念的表情。
“重要的人和事物,失去的……以及非常想要得到的。”
“……果然呢。”
卢卡斯仿佛因为经历了同样的感受而觉得释怀一样,轻轻吁了口气,
“假如那是永远也取不回来,或是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会不会想要一直在梦境里待下去?”
“也会有想要做出那种选择的人吧。”
赫西亚盯着风平浪静的海。
“不过还是能用自己的双手碰触到的世界更好。不管那家伙的意图是什么……感谢他,让我意识到这个。”
=======================================================
*借用一下前辈和后辈,十分感谢,如有OOC或剧情冲突请戳
*梦剧情只占便宜不吃亏有点耍赖,我就只这么玩一下
*其他同事加油……

※除NPC以外的学生的死亡均已获得中之人的同意。
※若对剧情有疑问,或剧情有问题,请及时询问、私信企划主。
-----------------------------
“山本美奈子,我喜欢你!”
“所以跟我在一起吧!”
八月二十九日。
渡边摇因一氧化碳中毒而亡。
九月二日。
黑姬山千叶被从高空坠落的钢筋贯穿致死。
九月十七日。
月见奏被坠落的广告牌砸至重伤,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九月二十一日。
秋本秋失足从校内楼梯上摔落,后脑遭剧烈撞击,不幸当场死亡。
接连不断的意外事故加深了学生们的恐怖,死神的手再一次伸向了三年三班。
三年三班也越发的分散,渐渐地,谁也不相信谁。
现在的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已经竭尽所能。
十月五日。
结城刚于学校天台坠楼身亡。
遭受牵连的是他的挚友五十岚拓人。据五十岚口述,当时他们二人起了争执在天台扭打起来,途中结城撞上了防护网,但没有想到那个位置的防护网固定部位已有些老旧,在撞击下松脱。结果结城因惯性跟着跌了出去。
受牵扯的五十岚在跟着摔出去的瞬间紧紧抓住了另一侧的防护栏,一边则紧紧抓着结城。
他说当时还能听到底下学生的尖叫。
赶到天台的教师唯一救下的是差一点跟着坠楼的五十岚。
最终,这件事被警方定为意外事故而结案。校方则让当事人五十岚回家休息。学生们在这段时间里都在议论这件事,认识五十岚的人则纷纷表示同情,毕竟他失去了他的挚友。
但是,三年三班的学生们对这件事似乎有别的看法。
借着送讲义的机会,樱井夏树来到了五十岚的家。给他开门的是五十岚的父亲。
“你是……请问有什么事吗?”
“您好,我是五十岚拓人的同学樱井夏树。我是来给他送这几天的讲义的,顺便班级里有些事想和他说。”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家?”
“……进来吧。”
五十岚的父亲并不怀疑眼前这个看起来十分乖巧的男孩子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也拿出了他口中所指的讲义。
在将樱井迎进门以后,五十岚的父亲带着他来到了五十岚的房门前。
“拓人,你同学来了。”
(哦,让他进来吧。)
五十岚的房门被打开了。
里面光线昏暗,他似乎是把窗帘拉了起来,但没有拉严实,一些光线透过缝隙照进屋内。他坐在桌前面对着电脑,双手都缠着一层薄薄的绷带,似乎还贴了点膏药。
“那个五十岚……”
“有什么事进来再说吧,樱井同学。”
看着五十岚的笑容,樱井选择进入五十岚的房间,在进门的那一刻,五十岚还不忘提醒他把门也关起来。
看樱井似乎有些遗憾,五十岚笑道:“你不是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我想都不是些想让别人听到的事吧。”
话说到这里,想必五十岚已经很清楚他来的目的了。
关上门以后,樱井就十分直白的询问道:“五十岚同学,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我知道了什么呢?”
“樱井同学,不要绕弯了。说吧,你想知道些什么?还是说,你怀疑我做过了什么?”
显示屏的光映照在五十岚的脸上,一定程度的扭曲了他的笑容,这不由得让人感到一丝阴冷。
“……关于‘死者’,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恩,这方面的话我的确是知道了一些。”
“那么——!”
“但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难道为了大家不是应该说出来吗?”
“我只要我和美奈子能安全,其他人与我何干呢?”
“五十岚同学!”
“说起来,樱井同学剪了头发呢。”
“是为了谁剪了头发吗?”
“……”
“呵呵,樱井同学有喜欢的人吗?”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这么说吧。”
五十岚站了起来,走到了他的面前。如此近距离的直视让樱井有些紧张。
“你愿意为喜欢的人沾满鲜血吗?”
送走樱井后的五十岚拉开窗帘,外面的天空一片火红,现在已是黄昏之时。
翻开收在抽屉里的日记,五十岚看着上面因岁月而发黄破旧的纸张不由叹息。藤本不是“死者”,秋本不是“死者”,刚也不是“死者”。
那么“死者”会是他们中间的谁呢?
五十岚合上日记,看向了抽屉中散乱的照片。他亲手让三个人步向死亡。然而这三人都不是“死者”,“灾厄”仍在继续。难道说“死者”其实是自己?
“……这下真是说不准呢。”
自嘲的五十岚笑了起来。
关上抽屉,再次看向窗外的他突然想起了挚友死前露出的那难以置信的表情,以及眼中的绝望。
恐怕他早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些什么了吧。
毕竟结城都猜到了他就是害藤本自杀的人,也是公布了照片的人,更是让秋本死亡的人。
不愧是挚友呢,这么了解自己。
都让他感到有些可怕了。
这么想着的五十岚打开了之前偷偷拿走的结城的手机,收信箱里最新的一条信息便是事发前一日,他发给结城的信息。再删掉这条信息后,五十岚翻看起了手机里的相册。
里面有不少他们三个人的照片,还有他暗恋的女孩子的照片。
照片中的他多数不是那么帅气的,有时候还都是出糗的时候。偶尔还会有结城的脸出现其中,全是嘲笑自己的表情。
“真是过分啊……都不把人拍的帅一点。”
“果然还是很难受呢。”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但他却不曾对亲手杀害挚友这件事感到后悔。
“只要能保护我爱的人,哪怕是地狱我都愿意前往。”
“这就是我的正义,所以原谅我,刚。”
“或许我很快就会去见你了呢。”
十月二十七日。
五十岚拓人于家附近的公园遇刺身亡。



EDAS问题Q&A
Q:各个boss之间的关系是?
A:原一郎是黑手党的始祖。其余组长是当初集结开始原一郎亲手带出来的,分裂之后现在算是平起平坐,但还是对原一郎有一种尊敬一般会叫他“大哥”
Q:地上地下是个怎样时代的建筑景观?
A:都是现代,也有很少一部分是欧式。
Q:组队的四人之间需要做什么?
A:需要做的就是在主线出来之后商讨剧情,小组作战方便计分
Q:几个组之间分别的职责?
A:之后主线开始地上地下小组之间就是对打。
Q:各个组的boss可否攻略?
A:可以的
Q:地上地下如何连接?
A:地上通下去的甬道。地下其实是雾之枭很久很久以前造的一个人造自然监狱。
Q:地下的物资怎样获得?
A地下除了没有阳光还有通天达地的树干其余的和地上差不多
Q:地下四组被赶到地下过了多久?
A原一郎22岁开始集结,2年发展势力,24岁被赶入地下。到现在一共6年
Q:地上是否有强制宗教信仰?
A有的。而且每一年都会有活祭品,也就是人。但是因为确确实实没有发生过灾害,人们也是很信奉。
Q地形图?
A之后会有的
Q地下的可以有办法去地上么?
A找到甬道,这一点第一章会放出来
Q地上地下如何获得联系?(本人见面可否见面交流或者仪器交流)?
A没办法联系。
Q地上地下是否有对方详细人员名单?
A没有
Q地上的气候变化对地下的影响?
A没有任何影响
Q通天达地的树根”这是一种什么植物?
A就是树,但是树干长到了比地下更深的地方。
Q具体的大事年表?
A雾之枭建立时间不明。兄弟争权10年前。黑手党建立8年前。逐入地下6年前。
Q科技的发展程度?
A现代科技
Q地下本身有原住民么 我们和原住民是什么关系?
A原住民是囚犯,共生关系
Q组队地上和地下的战斗以何种形式决定胜负【分数如何计算?约架是个人还是团体?
A这个企划书中有写,,,,小组约架是为了之后算分数还有判断角色死亡用的,约架还是个人,但是必须是从和自己敌对的组中约。
Q战斗的场地都会涉及到哪里?
A主线会提示,大部分是在地上
Q地上地下对彼此已知的防御措施?
A知道的很少。会采取很谨慎的防御。例如雾之枭会派人一直看管甬道入口
Q武器争夺是地上地下之间吗?
A:是的
持续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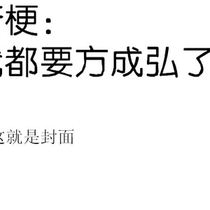


回过神发现自己正走在陌生的地方,天已经黑了。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有月光的缘故并不暗,我停下脚步,打量起周围的环境。看样子这里不是什么偏远山区,确认了这点之后稍稍松了口气。
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本来想去酒馆,结果也不知怎地就迷迷糊糊地到了镇里学院的门口,等反应过来走错地方的时候,自己又正站在铁匠铺前面发呆。
大概这次也是走神的时候走错地儿了吧...这样的话也没必要担心什么,大不了只是被当成私闯民宅或者非法入侵的可疑分子,到时候跑就是了。
我对自己的脚力还是很有自信的。
话说回来,似乎也没看到类似于民宅这一类的建筑啊?脚边也是柔软的草地,真是亲近自然。
感觉到有些渴了,我取下腰间挂着的酒葫芦。凭着拿在手上的分量感就知道里面还有液体的可能性不大,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即便如此我还是拔掉塞子,仰面往嘴里倒了倒。
果然并没有喝到什么,但是舌头还是尝到了点甜味,虽然完全不够就是了。说起来这个地方能看到星星啊,像洒在巨大黑色画布上的细小的牛奶滴一样,真好。若隐若现,总让人觉得是不是自己看错了,然而却是真切看到的。
真好啊,星星这种东西,不管是说“看到了”还是说“没看到”的自由都有,也不会有任何人跳出来说“你说的不对”。这样想着心情也变得轻松了,我收起葫芦带上兜帽,晃晃悠悠地继续沿着小路走。
脚下的小路并不知道通向哪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延伸出来的,但是既有这样的路,说明平时肯定有很多人从这边走。背后是一片小森林,隐约可以听到树叶被风吹动发出的“沙沙”摩擦声,又走了大概十来步,四周便是一片寂静了,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走啊,走。脚踩着土路发出的声音真是奇妙。
说真的,要是再见不到人,我估计都要开始一蹦一跳了。不过就算我跳了,也算不上是所谓的“雀跃”吧,毕竟也不会飞,什么的......
正想着这些有的没的,突然,前面出现了像是集市一样灯火通明的热闹场所。不,虽然我语言表达能力很糟糕,但是“突然”这个词用得一点也没有夸张——就像是本来没有的东西凭空出现了一样——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又走神了的原因。
......
算了,管他呢。
你瞧,一路上没有看到半个人影,也没有活物的声音(当然除了我自己发出的动静),途中路过疑似“居民区”一样的建筑,透过外围的铁栅栏往里窥探,尽管能够感受到动静,却还是给人“死寂”的感觉,都忍不住怀疑“妈呀我到底到了哪儿”了;然而现在突然看到明显是人类(至少是活人,对吧?)的活动场所,当然是心中的感动压过惊讶与奇怪。
总不至于再发生什么不好的事,这样想着,我接着往前面走去。既没有加快也没有放慢速度。
前方不远处的光亮和热闹的氛围与我现在身处的安静的阴影里感觉起来截然不同,甚至——虽然还没去过但我敢打赌——肯定就连空气,给人的感觉也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这样比喻肯定夸张了不止一点——那边是活物的乐园,而相比起来这边却是死气沉沉。
甚至都能清楚地看到那条(其实并不存在的)明暗交界线。
有声音在叫我过去。
一直往前走,直到迈过那条分界线。
感觉像是进到一个新的世界一样。
耳边似乎响起了少女的低语。
“欢迎,来到永夜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