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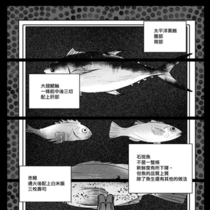




“如此这般,梅斯菲尔德小姐。”特蕾莎端起红茶杯,啜饮一口,“让我们达成联盟,为了更广袤世界中的胜利吧。”
说这话的时候,特蕾莎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霍莉·梅斯菲尔德的宠物蛇,内心惊慌失措。
——好可怕!好大一条蛇!好可怕!
“更广袤的胜利……你指的是什么呢?”霍莉笑眯眯地喝了一口花茶,伸手摸了摸宠物蛇的头,“好了波波,等下就陪你玩哦。”
蛇有名字……哦对宠物蛇,有名字很正常。特蕾莎努力移开视线,让自己不要再关注那条蛇了,“您的话,更多的金钱……之类的吧。以及如果您愿意成为我的盟友,”特蕾莎放下红茶杯,拔出新锻造的佩剑。剑柄上的紫色水晶环绕着白色的大颗钻石,她将佩剑深深插入地面,“我也会为我的盟友提供保卫。我们互不侵犯,我们一荣俱荣。如果您愿意,您可以成立您的教国,或者单纯在您的领土里富集所有的财富。如果您愿意成为我的盟友,为我提供盟友的合作,那么,我的剑也将为您挥舞。”她拔出佩剑,插回腰间。
“听起来倒是挺不错的。”霍莉继续笑着,她的蛇在她手下“嘶嘶”地吐着信子,“但是你要怎么保证,我是您的盟友,而不是您的粮仓呢?”
“这个您大可放心。”特蕾莎立刻拿出一个紫色的吊坠,水晶虽然暗淡,但依然发着微弱的光芒。“这是我的魔之契约。您将您的魔力灌注其中,合以我的魔法,契约即成。在契约内,我绝无可能对您出手,我的魔法将在您的物体和人员身上全部无效,而物理层面的攻击也会被尽数挡下——您看如何?”
“这个听起来倒是挺好玩的。”霍莉拍拍手,“你既然都来了,空手而归倒是我这个主人公的不是了。你能为我提供金钱的入账,那么先说好,你需要我的什么?”
“我需要您的……一点资金支持。”特蕾莎狡黠一笑,“为表诚意,我为您带来了一箱礼物。”她侧过身,让出背后的一只宝箱,拍拍手,风魔法打开盖子,一箱财宝显露无遗,“微薄小礼,不成敬意,望您笑纳。”
“嗯,波波,去。”霍莉的大蛇爬了起来,特蕾莎慌忙让出一条路。大蛇将宝箱围在中间,头伸到箱子里,嘶嘶吐信。“那么,我们签约?”
“好!”特蕾莎立刻将盟约递了过去,“请您和我一起握住它。”
霍莉握住了契约。
“在此,我,特蕾莎齐柏林,以魔力发誓——”“霍莉·梅斯菲尔德,以魔力起誓——”“我愿以我的国之兵马换取支持……”“我以我的金钱支持换取兵马的使用……”“以刀兵之利,护财宝不失。在此,起誓。”
契约亮了起来,红色和紫色交织,跃动着,像一颗跃动的心脏。
“我们将所向披靡。”特蕾莎面带笑容,看着眼前的英气少女。骁勇的骑兵,卓越的骑士,引领死亡吧,杜拉罕。
“这是你的愿景吗?”拉斯洛并没有动面前的红茶。她身着骑兵的军装,马靴擦得锃亮。
“拓土开疆,是每一代意欲成为君主之人的愿景。”特蕾莎主动拿起了茶杯,啜饮一口。她的眼光扫过女骑士的剑,扫过女骑士。“无谓的征伐会带来毁灭,但一个统一的帝国,将带来长治久安。”
“那么您觉得,您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是恺撒或者屋大维?”拉斯洛轻笑一声,“再强大的帝国也将迎来土崩瓦解的一天,更何况,你真的有手腕,能管理好一个偌大的帝国?”
“我将尽我所能。”特蕾莎垂下眼帘,“团结一切我能团结的,消灭一切我不能团结的。就这样。”
“党同伐异,排除异己,不过如此。”拉斯洛轻轻摇摇头。特蕾莎沉默片刻,“愿闻其详。”
“兵者,无外乎进攻与防御;政治,无外乎团结与对外。”拉斯洛朝特蕾莎点点头,“并非对你的党同伐异抱有见解,而是对你党同伐异的对象不置可否。你要团结谁?你又要消灭谁?你的剑,不可盲目挥舞,你的盟友,不可盲目选择。你想党同伐异,那就要明确,谁是你的朋友,尽可能多地结交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尽可能少地结交敌人。”
“受教了。”特蕾莎叹了口气,“敢问恩师是……”“一个过去的人。”拉斯洛的眼帘垂了下来,终于接受了特蕾莎的红茶。
“小姐可想过将自己的力量为什么所用么?”“我只为自己而活。”“人总要有个目标。”“我想活下去,得到自由。”
特蕾莎点了点头,将茶壶向拉斯洛的方向推了推,“再来点茶么?”“不必了。一杯足矣。”“抱歉。”“也不必歉意,只是足够了。”
“与拉斯洛小姐一番谈天,受教颇多。”“言重了,特蕾莎小姐目光远大,日后定能做出一番事业。”“承蒙谬赞。望拉斯洛小姐……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仅为自己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