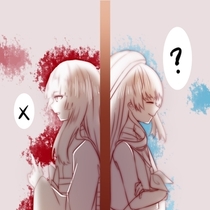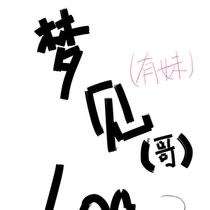今晚要上演的是:一幕沉重的悲剧。
“领,你们的宗教……有祭祀这一环节吗?”
似乎古今中外,不管什么宗教都有祭祀这一环。人们仿佛要向先人或者神明奉献一点什么才能表示自己的虔诚和忠心。中国古代就有用牲口祭祀的传统,用活人祭祀的——似乎很少。
不过叶家听说有用活人祭剑的,在很久之前老祖宗在书上也写过,我不知道正不正确,也不想去评判这种标准的错误——如同我一直知道的那样,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掠夺。你获取了金钱,那必定有人失去了金钱,你获得了快乐,那必定有人失去快乐。有牺牲才有回报的话,那我宁愿牺牲的是他人,而成就的是自己。
但是我们现在在岛上,似乎活物只有我们这些人。如果领坚持要祭祀的话——必定是会出血的。
“祭祀?当然会有。应该说哪个宗教都会有祭祀的吧。”
我皱了皱眉头,现在还会用活物,甚至说是活人祭祀的宗教,都不是什么被承认的宗教。
领似乎看见了我皱眉,问我:“大家都会开心地投入神的怀抱的。叶衍不想见到伟大的神吗?”
伟大的……神吗?
我对这样一位人物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但是很少有宗教会说献祭了之后就一定会见到神明的——不知道领哪里来的这种感觉。
我问道:“领见过神吗?”
领稚气的脸上露出了狂热的笑容:“我?我会见到的。”
“那领这几天是在准备祭祀吗?“
“是。”领兴奋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领小的时候,或者一直以来受的是怎样的宗教教育。但是将这样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交给领和诗织小姐这样的孩子,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我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去干涉领现在想做的事情。我向来不擅长去干涉别人的事情。
我:“领的信仰……可以和我讲一下吗?“
桃泽领:“总之我们的神是位无所不能的神。“
唔……
无所不能,那何必不抹去自己的踪迹?中国有很多神仙都是靠着常说的香火来维系自己的生存的,不知道领的神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能感知到他的存在。因为神能实现我们的愿望。“
说起来,无所不能的神的话,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实现信徒的愿望的。毕竟信仰这件东西,似乎都是在想神明祈求什么。祈求出色相貌,祈求如意郎君,祈求死后安宁,祈求心灵平静。尽管有很多宗教的神明并不能实现自己所有教徒的愿望,但是凭借那零碎的几个就可以将宗教发扬光大。
比起那些神明,这位可以随时实现教徒愿望的神似乎过于伟大了一点。也幸好并没有很多教徒的样子,不然可能和圣诞老人一样得爬烟囱送礼物。
我好奇地问道:“领被实现过什么愿望吗?“
“我还没被实现过,但我有想被实现的愿望。”领想了一下,又摇了摇头,摆出困惑的神色:“不,是神想实现的任务。”
神想实现的愿望自己不能实现的吗?
我不知道。神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他用实现别人的愿望来让别人帮自己实现愿望。怎么说都感觉有点奇怪……术业有专攻这种?
“有我能帮上忙的事情吗?”
领认真地看着我,突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拖着着声音说道:“叶衍——
“当然能帮上大忙了。”
我突然想到之前我睡在监狱里的时候做的那个梦,一朵玫瑰花从食道插入我的心脏。那种痛楚和被贯穿的感觉就算是现在我还是可以清楚的记得。被玫瑰花吸食殆尽。
而现在领的眼神,仿佛就是在看送上门的大餐一样。
他向我这里考了一点,盯着我的眼睛:“你也会想见到神的吧?“
我不由地打了个寒颤,说道:“想见到……的。“
领满意地勾起嘴角,在我面前点头说道:“嗯,叶衍也是好孩子啊。“
说着,我被领带到了他和诗织小姐住的监狱面前。领之前下山之前叫我和他走,说带我去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来这里。
“叶衍以后就睡这里吧。和他们在一起不安全。”
不安全吗……我不知道领知道了什么。
我看着在月光下的监狱,寒气从脚底慢慢缠绕着我。我突然想起之前看到的一句话。
今晚要上演的是:一幕沉重的悲剧。
今晚要上演的是:一幕光荣的救赎。
我听见了我自己的声音,重复而机械地说道:“好的。“



山里风钰的屋子炸了又炸,聚灵殿几个长老都奇怪这倒霉孩子是不是灵纹又刻坏了,而我们的未来的煌钰七长老正如他们所猜测的那样,又一次在爆炸声中灰头土脸地毁了一张高阶阵图。
风钰气急败坏地推开材料屋子的门,屋子角落里堆满了朱砂灵墨和种种此世难寻的练器材料,而对于聚灵殿来说这些只不过是一份普通的弟子练手之物,像这样的屋子他们每个真传弟子都有一间。风钰无视了这些东西,提起绣金裙角踹开高高堆起的流炎铜原石堆,扣扣索索从里边摸出最后一张高阶阵图。她谨慎地拍拍阵图上的灰,小心揣进了怀里,仿若这张纸是她生命最后之重。
彼时她尚且年幼,高阶阵图的绘制也是堪堪入门,但以她自诩天才的性格似乎并没有那么容易放弃,于是别的真传弟子炸了三张阵图,她把这几个月领到的所有高阶阵图炸光了。殿中长老们半是喜半是忧,弟子有上进心总是好事,就是总怕哪天这座山头所有屋子都得给她重修一回。
果不其然,当她控制着灵力流过阵图上最细微的纹路中时,这张纸发出了不堪重负的脆响,仿佛蛀虫啃噬腐木,门柱朽坏倒塌。这声清脆响亮,细听还带着点趣味的韵律,风钰却只觉心头一紧,十指连弹几乎是瞬间在身前布下了七八个早已准备好的中阶防御阵。
整张纸在咔嚓声中蓦然化为灰烬,灰烬散落一地亮堂堂燃起了火光,在那瞬间的亮如白炽后又明灭数次,一切在极短的时间里突兀爆炸开来,她惊得跳起来,伸手试图去够旁边的紧急防爆装置,却只是徒劳地往前了几步,随后就被气流抛飞晕了过去。
她悠悠转醒,又躺在了病床上,脑海中即刻思考的却是录下灵纹时的错误之处,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爆炸,便是她这样习惯了焰火煌煌的人也不由得有些错愕。她一手撑着头思索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纤长睫羽在脸上投下阴影,眼底还带着些刚醒的迷茫,夕阳橙红的光侧过来打在她半张脸上,她脸上的绒毛显映出来,仿佛整个人融在了光里。
李商陆觉得她温柔极了,这个场面让他想起夏日傍晚轻薄的炊烟,城里最好的绣娘织出虹色柔软的布,晾在竹竿上被风吹动泛起波纹。风钰似乎是意识到有人在看着她,抬头望向门口却只见一片迅速消失黑色的衣角,还是幼童的尺寸,似乎还能从上边看出主人些许的慌张无措。
对于她来说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她很快淡忘了这个孩子,投入到她无尽的灵纹实验中去。直到她成为长老,幼童长成独当一面的青年,李商陆偶尔不那么忙的时候还是喜欢看看她,看她的眉眼看她发明新阵法时候的欢欣,也看看她偶尔休憩时望着天空略有些发呆的样子。
有时候李商陆会嘲笑自己连和她搭话的勇气都没有,无情地干了许多不得见光之事的家伙在感情一事上居然意外的纯情,他哥李商枝天天听他吐苦水听得一见他带着那副烦恼的面孔走来就捂住耳朵用便秘般的表情示意他离远点。
李商陆总归是消停点了,他终归是意识到煌钰长老始终只钟情她的那堆灵纹和阵法,他也开始越来越忙,很久才能回殿里一趟,看她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
七长老从没意识到还有人这样看着她,也许在她心里这确实是个变态行为,所幸她常年不出门,又经常头一低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编纂灵纹去了,不然这么傻一孩子多半是要被风钰揍上一顿。直到李商陆登上掌门,风钰终于知道有这么个人,但是掌门是谁与她并无太大关系,她只要有一个稳固而安全的避风港做点她爱做的东西就可以了。
他们仍然像是陌路人,做些各自的事,直到现任掌门的名气在各派间开始流传,风钰觉得聚灵殿开始变得更好,她似乎有了更多的研究资源的时候,李商陆终于闲下空来,顺路去看了看她现在是否还在干和以前并无二致的事,风钰也终于从自己的世界中走出来,看见了站在那里的新任掌门,她觉得他也许是来看看新的阵图,就像以前老掌门做的那样。她歪头向他笑了笑,对他招手想叫他跟进屋看看新画的阵图。
李商陆意料之中的愣住了,直到女孩子疑惑的脸在他面前放大,清新的兰花香扑面而来探进他的鼻间,随后衣角被扯住,他就这样莫名的被拉走了。风钰在他面前拿着一堆新画的阵图一张一张的讲着,他就这样听着,这个场面仿佛重复了无数次,风拂过桌面掀起柔软的阵图,他慌乱起身去抓那几张因风而起的图纸,却意外的碰到一双柔软的手。李商陆黑色的衣角在风中飞了起来,他的周身是尚还在漂浮于风中的长卷,如今同色的夕阳从被风吹开的窗子里探进残光,青年长身而立。
风钰觉得自己似乎发现了那么一些有趣的,和灵纹的有趣并不相同的东西,她抽开手,灵纹卷轴噼里啪啦地砸在青年身上,这让他显得狼狈了起来,风钰笑着帮他拾起整理好那些散乱的卷轴,带着他离开了这间屋子。而此时夕阳隐于山,暮色四合,女孩子脸上温柔的笑意隐藏在逐渐黑沉的天色里。
他们终将遇见,也终将成为后人传说的逸闻之一,被说书人写在话本里,将这段故事说给那些还未曾听过的人。
"你听说了吗,天玑阁那个阁主……"
旁人的窃窃私语淹没在嘈杂的声流中,妖修敏锐的耳朵却捕捉到了这一段声渐低微的故事,在这难得的闲暇时光里还能听到这样有趣的东西,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缘分。
"那个天才吗?"
北冥涛百年一熟的黄金茶在茶汤里沁出细碎的金色,他提起茶壶自斟自饮,凝神听着那尚未说完故事,完全没注意到身旁少城主越变越黑的脸色。直到并不是那么好脾气的少城主踹了他一脚,他才笑哈哈地将茶壶递了过去。
这只是澜沧城里天泉楼一隅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少城主早已成为了城主,天玑阁也不知道换过了多少个短命的阁主。
他曾经的故事都已经变成了话本上的传说,曾经低调如他现在也已经变成了为人八卦的内容,就如同当年他听过的那个漫长的天玑异闻。直到那次不期而遇,他从未想过他有一天会以这样的方式认识这个异闻故事的主角。
诡异的浮空岛一如往日漂浮在这个地方,仿若一座巨大的结界隔绝了天空,无人知其存在之始,也无人知其何时沉落。琼云鸟起落于此,他慕名而来见识一年一度的候鸟南巡,它们从遥远的云山极北飞往禹州,中途未曾停留,一批又一批的降落在群岛之上,只有这个时候,群岛的天空是白色的,下着红白相间的雪,间或透露出灿金的阳光洒在那满天的飞雪之上。
他长久的凝视着这场大雪,反手按了按肩胛骨,妄图飞翔的翅膀在筋骨的内侧颤抖,带来一阵温柔的痒意,他明白那并不是天空也不是雪,是雄性琼云鸟争斗间落下的羽毛。
这个时候的浮罗群岛处于最危险的季节,常人是不敢进入的,而他却在满天飞羽中看到了一个白色落满肩头的身影——这个家伙正在和一只雄鸟打架,葛苏越略有些愣住,一个化神期的小家伙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群岛,真应该夸上一句勇气可嘉。
他跳了起来,翅羽在空中划过银蓝色的弧线,他伸手拽下那只看似委屈得不行的琼云鸟丢回了鸟群。似乎只是一瞬,他又站回了原来的地方,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个人还犹自挥舞着棍子,一招一式清灵完融不似化神期应有的僵硬。
但是看起来还是有点滑稽,葛苏越这样想着,便也这样笑了起来。远处的家伙慢慢放下了手中的棍子,摇了摇头,找了个阴凉的地方拂去身上的羽毛,他抬头望着满天大雪,灰色的瞳孔映着天空,仿佛那是两颗无机质的玻璃球。
葛苏越不站在那了,他离去的痕迹很快被新的落羽覆盖,偶遇的年轻人确实很有意思,但也只是旅行中匆匆而过的谈笑罢了,只是他从没想过还会再次遇见这个有趣的年轻人。
仿佛约好的一般,在禹州这片太过广袤的土地上,他们擦肩而过的次数不下五次,葛苏越陷入了沉思,甚至开始怀疑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别有目的,但是他还是有着自信的,尽管他已经老了,但除了那些绝世的天才和老怪,这世界上并没有能胜得过他的人。
他们再一次相遇在合欢楼名伶的台子前,葛苏越装出一副浪子的轻佻笑脸,摩挲着身旁侍女的细嫩脸颊,看的却是台上戏子风流。合欢楼戏子的腰肢柔媚舞姿艳丽堪称一绝,他看了不知多少回,总是会有些腻味。推开身旁侍女,正待离开却转头望进了一对灰色的招子里,那里反射着世间众生百态却唯独没有他自己。
眼睛的主人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同样回望过来,对他笑了笑,做了个口型,仿佛叫出了他的名字,葛——苏——越。
葛苏越不免感到疑惑,这世界上认识他的人并不少,却不应该有这么年轻的家伙,也并没有那双独特的眼睛。更何况他们从未相见,除了那几次擦肩而过。他一向是想到就会去做的人,向那个人传音约下了见面的地点,转身离开了合欢楼。
戏子还在咿咿呀呀的唱着甜腻的歌曲,吴侬软语在舌尖徘徊许久才慢慢吐出,他接到了意料之中的传音,心想不枉费一次测算,留下了一锭纹银悠悠离开。
直到很久之后他们谈起这场以相互怀疑为始的约见,无托笑言仿佛一场孩童幼稚的约架。两千年过去了,万物起灭生息,琼云鸟仍年复一年徘徊于藏禹之间,他们一起来看过一次琼云鸟的迁徙,,葛苏越还记得初见那个尚且修为低下却勇于搏斗鸟群的家伙,想到当年有勇无谋的化神修士如今也成为了道修后辈口中的大能人士,他不免笑了出来,无托莫名其妙地拍了拍他的肩。
他们立于落羽之上,听着鸟啸潮鸣,一如当年。
静间蓝步伐一收。
他本打算取下晾晒干净的衣服就走,小女孩的背影却映入了眼帘。她正收下最后一张洁白床单,努力纳入自己怀中进行下一步折叠。或许是听觉太敏锐,他甫一接近,她便有所觉察,立刻转过头。
“……打扰了。我来取衣服。”
“啊……好的。换下的衣服放在往常的地方就好。”
“嗯。”
她毫不惊讶。
青年轻咳一声,绕过她,走近衣架,取下自己所需的东西,不自觉在手腕上裹了一转,这才又问她:
“我那天听美琴说,你以前的学习成绩很好?”
饶是她也没法料到他唐突的问题。深泽实琴愣了愣。
“我……嗯,因为……也没有其他事可做。……美琴,美琴也很优秀的。”
“我知道,看得出来,美琴很聪明,”他笑,没有说出那句“你也是”,顿了顿,继续问,“那……作业呢?你们关系这么好,不会互相帮对方写作业么?”
第一次调查深泽家时,他们在某个储物间里发现了写有“みこと”的课本。但因为是平假名,并不能立即确定主人是谁。不过书本上常能看见各种涂鸦,静间心下推测应当是美琴的。
毕竟他才见过她别具一格的涂鸦。
实琴摇摇头。
“美琴她喜欢恶作剧。而且,我们的字迹也不一样,会暴露的。”
静间蓝点头。看来那本课本的确是美琴的了。那么……“不受重视”的人,会是他眼前的这个小女孩么?
他没能问下去,总觉得还不是时候,况且这样的问题他也无法问出口。
正在犹豫时,深泽实琴却抢先开了口。
“那个……”
她似乎在踌躇些什么。见她微微蹙起眉,青年心下微有诧异。很难见她主动开口说话。于是他“嗯”了一声,好让她继续说下去。
“静间先生……为什么,会来这里,这个岛上?”
……为什么?
“我是指,这次旅行。”
嗯?静间眨了眨眼:“旅行?……也没有为什么吧,只是突然想来旅游了。”
无论是打定主意抛下研究出门旅游,还是选择了这个航线和公司,都仅是冠以“突然”的小概率事件。可偏偏这么小的概率让他阴差阳错翻了船,漂到既已取消的目的地上,如今整日面临谜团与死亡。
这真的只是——
“我……不觉得这是巧合。”
谁知小女孩替他说出了心里话。她一贯平静的眸子里似乎有什么闪了闪,随即沉至眼底。
“我不觉得……您来这里,是巧合。这一切,一定都是出于‘那位大人’的意志。”
等等,谁?
深泽实琴仿佛猜到了他想做什么,丝毫不给机会,又匆匆说道:“请您尽快离开这个岛吧。不然,时间不多了。”
旋即,她抱起装满床单的木盆,向他微微鞠一躬,便转过身去,径自离开了。
过了好一会儿,青年才从震惊与思虑中抽身。失去温度的日光再次炙烤,虫鸣重返耳畔,而他盯着深泽实琴离开的方向,不由得攥紧了手中的衣服。
谜题接着谜题。好似滚雪球般越积越多,而他们此时所掌握的确切信息,不过细枝末节的边角罢了。
静间蓝换好衣服,合身的衬衫竟也能令他涌起三分安心。将换下的衣物放好,他走出房间,一眼便望见走廊上的丽影。他愣了愣,不禁出声:“弥生?”
黑发女性转过头来。她不知为何也换上了最初的那套礼裙,手上提着一双高跟鞋,赤脚站在那里。
“……你不是先走了么?”
“嗯,是走了,”她将双手背在身后,“外面实在太热了,不如回来换件凉快点的。顺便等等你。”
说罢,偏头朝他狡黠地眨眨眼。
“等我干什么?”他走上前去。
“刚才看你在和实琴聊天,好奇你是不是又问出了新的东西。”
走近了才发觉,她的妆容似乎比往常要淡一些。他应了一声,想了想,遂将刚才的“新东西”都说了出来。没什么好隐瞒的,因为他仍然一头雾水。弥生小百合听罢,也蹙起眉,反复念了几遍“那位大人”,又投降般摇摇头,表示自己同样毫无头绪。
想也知道。他轻叹了口气,决定换个话题。
“今泉呢?今天没去找他?”
“今泉?”她问。
“嗯,今泉。”
“今泉啊……”
“嗯?”
“今泉他,”话语一顿,她笑了笑,“今天不找他,就找静间你。”
“……哦。”
那估计是明天再找吧。他没有想太多。又听她笑问:
“哎,你说,现在我们要是去庭院,会不会碰见那个女鬼?”
“……那不是女鬼。”他没好气地纠正。
她故作惊讶:“哦?那是什么呢?”
“死人。”
“原来如此,”她严肃地点头,“死人拿刀追杀我们。”
“……”他磨了磨牙,“要么就是傀儡。”说完连自己都觉得可信度为零,他赶忙又补充:“我是指,用线操纵的那种。”
“提线木偶?”
“差不多。”
弥生小百合笑了起来。她踮起脚,在木质地板上踩出两三个雨点似的节拍,几步拦在他面前,眉眼里满是亮晶晶的笑意。
“你真可爱,静间。”
“……”
青年有些恼火,可他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被她笑得丢了面子?还是因为她忽然展露出少女般的笑靥,让他一时乱了阵脚?他不曾深究,只是瞪她一眼,随即绕过她,大步向外走去。
他也从未想过,没有意义的重复背后是否同样毫无意义。
门外即是盛夏。

* 胡扯pt.2
艺术性……是什么?
浅井思考着这个问题。
她太忙了,完全没有空去看看画展,听听音乐会,演唱会可能也抢不到票。最容易接触的还是普通的电视剧和手机软件上连载的小漫画。
既然能够被人为地用文字、语言或者是其他方式记录下来的事情,必然会有它们各自的意义和独特的艺术性吧。思想并不深刻的浅井只能够这样考虑。而且每个人对于不同的艺术品的看法都不一样,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浅井是真的不觉得在学校里找到的那本画册她欣赏得过来,但是面对十羽漪玩味的笑容,她又不好太过直接地说“不哦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个东西有艺术性,反倒是真的好让人恶心”。不过她也没有那么想,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个恰好落在了浅井的可接受区。
于是她委婉地向十羽漪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十羽漪听完了以后也没有表示什么,看样子是巧妙地顺利糊弄了过去。
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东西具有艺术性呢?
难道跟男孩子喜欢看成人爱情动作片是差不多的吗?听说99%的男人都看过那样的影片,这个传闻的真实性应该还是有待考证的吧。
——会不会,是色情狂啊?!
浅井使劲摇头,不像不像。
——会不会,欲求不满?
醒醒,别瞎猜了。你看人有什么时候准过啊?
浅井在某次事件之后看人就慎重了许多。就像是第一次见到今泉和十羽漪的时候说的一样,还是需要稍微提防一下陌生人的。实际上她也相信,第一面就能较为了解这个人是不可能的。
有的人比较友好,会把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这样的接触会比较容易,也会融洽一些。
而如果是带着假面的人,你还要想法方设法地去窥视他的真面目,或者索性要努力地取得他的信任,让他在自己的面前把面具取下来。
瞎猜只能凭运气,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去慢慢摸索,一步一步地和人交好再判定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自己交往。要是和自己合得来,那就继续好好相处多多指教;如果十分不碰巧,三观不合不是一路人,干脆利落地马上说再见,对大家都好。
“因为我觉得——她是自愿的呀。”十羽漪说出了他认为的艺术感所在的地方。但是浅井还是不懂。
这是应该是她一时半会儿都没办法理解的点吧。
浅井记得这种内容的影片分类还挺多的,从场景、人设、还是其他乱七八糟她也说不上来的角度去分。也许十羽漪看重的是你情我愿而不是强买强卖吧。强有强的好看,双向也有双向的好看,嗯,大概是这样,看每个人的口味而已。
也不知道十羽漪喜欢怎么样的女孩子呢。他说过他的前女友没办法引起他的兴趣,却又没有提到他喜欢的女孩子拥有什么样的特点。但是看起来他好像还挺喜欢木棉花的,从朋友的角度来看也没问题,至少可以慢慢地挖掘出他的喜好。
好像想偏了。
浅井恍然大悟,她想这些干嘛呢,想这些没用啊。
罢了,不想了,再想也没个结果的。
* 胡扯pt.1
明明才刚遇见十羽漪,却让人停不住地想念。
也许是细胞中的DNA 都在表达想要了解他更多。
浅井坐在海边,觉得有点寂寞。
大概不是一见钟情,但是又无法解释这样的奇怪感觉。
应该是从游轮被撞击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十羽漪给她套上了一个救生衣。看上去真的是无法让人放下戒心的人,在某些时候真的让人非常地安心,也感觉可以依靠。
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你是唯一的光。即使是日月星辰都无法比拟。
这种一般用来形容小偶像的彩虹屁,浅井通常是没办法这么容易就想出来的。就算是被拜托了,也要绞尽脑汁大半天才能够拼凑出短短的一句,跟马上就能在转发框里打出一大段话的人不同。
登岛之后醒过来没有看见他,浅井确实是有些担心的。她去问今泉,今泉也只是说他大概能靠自己活着吧。偶尔在海边遇到他,浅井真的几乎是要跑着过去了,但是她只是朝他挥了挥手,和他说,是十羽漪先生啊。
没事就好,能够一起离开就好了。
浅井坐在沙滩上喝着自己的龙舌兰,看着十羽漪和木棉花还有安藤一起打闹。如果回去以后也能够像这样聚在一起,喝喝酒,再点一些小食。要是有驻唱歌手就好了。啊,还有,他们能坐在室外就更好了。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今时今日能够认识十羽漪,一起流落孤岛,一定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推动着他们。
或许,就连十羽漪也在推动着这一切。
“你有信仰吗?”
浅井有一次不经意之间问过十羽漪这个问题。
“唔……暂时没有耶。”十羽漪回答得非常轻巧,“怎么了吗?”
“没,在岛上别的地方有看到这些相关的东西而已,就问一下。”浅井说。
“如果信哪位神能够得到好处的话,也许我也会选择信一下。”十羽漪笑眯眯地补充。
这样的想法也没有错,利益一直都那么诱人,而人也总是趋向于利益的。
浅井得到了这样的答案,算不上满意也不能说是失望,希望能够结束这个话题:“要是你找到了这么棒的神的话,记得告诉我一下哦。”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的话,能够稍微听一下我的愿望吗?
她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平平安安地离开这个充满了怪异的岛屿。
这几天相处下来,每个人之间的羁绊也在慢慢地加深。不管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伙伴,还是要偶遇才能碰上的其他人也好。浅井希望,可以一个也不少地好好地离开这里。
她不知道许愿了以后需要付出一些什么。她知道许愿实现了以后一般都需要去还愿,但是那也是在愿望实现了以后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见了太多的死亡,浅井觉得人命其实也就是这样吧,轻飘飘的,一吹就消失了。即使如此,她也想要紧紧抓住。
至少把那一团光芒,留在自己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