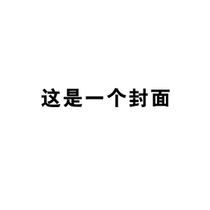白色的屋子里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强烈的光线反射在白色的墙壁上,亮的刺眼。视线可及的范围之内全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墙面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地。白色的衣服白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
人工所造就的白昼永不停歇,像是烙印在心间的痛苦一样,灵魂得不到安息,肉体也没能好好休息。这是所有被塑造成珍贵物品的孩子们都要经历的纯白色的灾厄,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出口,那扇和墙逐渐融为一体的门再也没有打开过。
半梦半醒之间不知道是大脑开始出现幻觉,还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东西,纯白的墙面上似乎是出现了一扇窗,那窗很高很高,但透过窗能看见纯白所没有的东西。苍翠的树木敲打在玻璃窗上,还有雨滴在什么东西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安静的很有节奏感,又像是什么都没有一样。
但是那窗太高了,真的太高了。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孩子们早就没有逃脱的力量了。
将死的热情终究是熄灭了,闭上眼睛在黑暗之中,带着朦胧的冷意逐渐袭来,黑暗令人想要落泪般的安心。
于是在这之后,不知是被注射了什么,身体逐渐变得不能动了。还有那些柔软又强硬的拘束带,屏蔽了所有声响的耳塞,阻隔了光线的眼罩,在它们的陪伴下,剩下的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了。
>>>
( )
还活着。
一如既往的某个日子,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抬起手静静的看着,然后慢慢地握成拳再松开,如此反复。能实打实的触碰到手心的皮肤,整个身体都躺在柔软的床铺上,房间不大却令人安心,窗外有着紫色的圆月,虽然诡异的让人心悸,但却不是漆黑如墨色的纯黑。
那这样就足够了,一切都还有的挽回。
只要不是,只要不是那个噩梦的话——
>>>
十二点的时候,仿佛是收到了一个讯号一样,城市还在睡着,人却都醒了过来。像是幻觉又不像是幻觉,如雷鸣般的钟声响了起来,紫色的天空中和下雪一样飘着红色的花瓣,还有礼花爆裂开的声音和烟火明灭的火光,一切都像是安息日的盛典,美的让人心颤。
这样的东西一定是假的吧。
凛醒来后眼神并没有在注视着什么地方,只是呆呆的盯着前方,而不过是一分钟,便重新找回了自己。
换好衣服后站在窗边,外面那些真真假假的东西鲜明的烙印进了眼睛,真假早已无所谓了,一切都不过是这场末日展开的祭奠而已。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休息过了,拜其所赐,他也很久没有活着的感觉了,但这或许是他自找的也说不定,唯有在混沌之中才能保持平静,这种灰暗的灰色感会比鲜明的黑白让人觉得好受的多。
但是灰色,我并不是喜欢灰色。他不带丝毫感情的这样想着。我不应当喜欢什么东西,拥有个人喜好是不被允许的,我自己不应当对什么抱有别的感情,我只要记住主人对其的感情就行了。
若是那个会为我冠上他的姓的男人不喜欢这样暧昧的感觉,那么总有一日,我走进他所在的白昼或极夜之中也是在所不辞的事吧,哪怕我会被烧成灰烬。
而等再度拥有意识的时候,眼前的景色已然完全陌生了,倒不是说来到了未曾来过的地方,只是明明前一刻还在自己房间里,接到消息出门来到指定地点后,有一段记忆就凭空消失了。
>>>
头好痛。
凛因为头痛有些苦恼的皱了皱眉,此时出现这样的表情实属失态,毕竟牢牢掌握所有事情是出身于那个无名之家的私人管家们能做到的最基础的事,就算精神状态不佳,脑子里的弦紧的像是要崩断了一样,这些也绝不是能被忘记的基本准则。可是他已经累了很久了,真的是太累了,间歇性的失忆加上因为环境突变造成的头痛,灵魂仿佛是在叹息一样,连咆哮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在安安静静的碎掉。
然后凛才意识到,已经很久很久没听到队友的声音了,原本那位可靠的领队应该早就能发现自己的不对劲了吧,而那只小狮子也很久没出现了。
地下铁附近空荡荡的,暂且算是安全,可是隐约的咆哮声和血的气味丝毫没有散去,紫色的月亮挂在天上亮的人眼睛生疼,在这样的环境下完全安不下心来,但是没有办法,一切都一如平常的不寻常。然后那些嘈杂的声音和潮水一样的涌了上来,越来越响越来越响,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改变,直到那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它们就出现了。
——是「龙」。
战斗几乎是在瞬息间就发生的,正如声音消失的一刹那那些龙的出现,凛分神的时候能看见地下铁附近的商铺里面黑漆漆的,然后像是有人在一样一瞬间点起了灯,可那照出来的影子分明是龙的形状。
这一片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入侵的,为什么完全没有意识到——
一股热浪袭来,凛的大脑中和平常相比晚了那么一小会才发出警报,这很不寻常,仿佛那并不是龙而是什么自己熟悉的人一样。堪堪接住一击,能闻到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像是布料或者皮肉什么的,还有几缕发丝被烧却的味道。随后是裹着雾的什么东西冲了过来重重的砸在地上,而那东西接触到衣服上的金属时,传来的也都是金属互相碰撞的声音。
然后裹在这之上的雾散去了,在自己身边的明明白白确实是龙,此时队友们都不在身边,就算是有些麻痹的思想也不由自主的紧张了起来。
……他们到底在哪里,不会有事吗。
在全身心的投入到战斗之前,脑子里还能分神去想的,也仅有这件事而已了。
>>>
“给我清醒一点!你们两个!”
最开始察觉到不对劲的是切尔茜,这位在队伍中最年长的领队一如既往的优秀,也一如既往的可靠。
眼前的状况看起来有些超现实主义了,平日里勉强算是关系良好的两位队友和见到仇人一样扭打在一起,刚刚走过的大道上已经满是焦黑的痕迹和被什么东西冲撞出来的巨大坑洞,恢复清醒后才看清楚之前在战斗的时候因为不明原因逃跑的那些「龙」们,其实全都是被幻觉吸引,或者说驱逐到这里的一般市民,他们都或多或少因为被战斗的余波波及到受到了不小的伤,切尔茜冲上去检查了一下附近看起来伤的不轻的几名普通民众,姑且算是还在呼吸,在尽力躲避了现在后面那两位瘟神的声光特效,并为重伤者紧急处理之后,切尔茜才叹了口气,转而着眼于眼下的情况。
“可恶……完全听不到我的声音吗?刚刚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切尔茜冷静的开始分析,眼下这个情况上去劝架实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门大炮和铁拳吃一发可不是说着玩玩的,能骇进去吗?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用骇入来解决幻觉,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在不伤到这两个人情况下结束这一切——
一边想着,手上动作却不停,切尔茜的手指灵活地在虚拟键盘上操纵着,显示器上的队友状态栏已经明明白白的被刻上幻觉标记了,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不试试怎么知道。
等准备好后屏幕上出现了画风粗糙表情滑稽,但是酷到不行的EMOJI表情,切尔茜将视线从屏幕移到正在战斗的两人身上,手则是率先锁定了凛开始骇入,而进度条出现的时候,像是祈祷一样不可控的咬住指尖,手套皮革的味道和灰尘与血真实的让人安心,等到提示音出现的一瞬间,所有的慌张都消失了,切尔茜睁大了眼睛,一如所有充满爱与希望的热血漫画一样——
“生效吧……给我好好的回到现实里来啊——你们这帮让人操心的家伙!”
>>>
仿佛真的有神听到了祈祷的声音,凛的动作突然停顿了下来,那边LEO刚好在装填中,瞬息万变之中这小小的一次停顿并没有造成什么可怕后果,然后凛瞬间抬起头环视四周,在看清自己的对手到底是谁后面色依旧沉稳的看向切尔茜。
“……LEADER?”
“看前面!”
早在切尔茜开口提醒之前凛就已经重新投入到战场之中,火舌舔过脸颊,万幸没有留下大伤害,电光火石之间拳头已经和火炮近接来往数回了,但当LEO利用开炮的反作用力冲来的时候,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于心不忍没有下死守反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因防守不力直接被砸进小巷子之中。
切尔茜二话不说冲进去的时候,凛刚刚好从墙面上掉下来,能很明显的看到巷子中那面墙上已经有了个大坑,甚至还能看见隐约的人形。
“没事吧,凛!”
“没、没事……咳咳。”凛从一片碎石堆中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这一下力度不小,他看起来有点不太清醒,不过勉强还能站着。只见他抬起头擦了擦嘴角的血,眼睛却牢牢盯着LEO会出现的地方“比起这个,那只小狮子没关系吗。”
“我说不准,情况有点特殊……”切尔茜赶忙跑过去扶着凛,“嘴角出血可能是伤到内脏,那站不稳的样子腿似乎是骨折了,你要当心点。LEO他现在是精神暴走的状态,我试过了,没能把他带回来。”
“……那就,交给我吧。”凛嗓音低低的,有气无力的笑了笑“这种事,我也不忍心让LEADER来做啊。”
然后凛表情微变,一瞬间就将切尔茜推了开来,下一秒有什么东西砸了过来,凛勉力反击之后,差点又被嵌进墙里。
然后又是新一轮的战斗。
>>>
“O……LEO……LEO!!!”
LEO好像如梦初醒般停住了动作,他还举着那台巨炮,能量是满的,这一炮下去估计灰都不会剩下,可想而知要是他真的开炮了,眼前这两个队友会变成什么样。
他的队友……
“我……”
“没事了LEO……”切尔茜咳了两声才能好好的说出话“我已经探查过了,这浓雾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它会使你看到的人类都会被错认成龙……”
LEO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后,袭来的是无边的愧疚感,他能听到有人在说话,但是已经没有多余的经历去理解那话里都说了些什么了。
“……所以说这不是你的错,我们回去吧……大家都伤得很重,不赶快治疗的话——你听见了吗,LEO?”
然后LEO就冲了出去,义无反顾的。他是为了复仇吗?可让队友受伤的不正是自己吗,这样一来谈何复仇。他是在保护群众吗?可等他醒来之后也不是没看到被误伤的一般市民,就算在他们的幻觉里这一切都是龙的过错,可他没办法欺骗自己。
他是在宣泄自己的仇恨吧,那天生的没由来的憎恶感,只要将他们丢出去自己就还有救,为此就算抛弃掉重要的东西也——
“等——”
“LEO!”
LEO消失的地方,正是第一真龙检体【N·洛亚路亚】的所在地……这孩子与生俱来的直觉,还真是好的可怕啊。
>>>
“……你是要准备追过去的吧,LEADER。”
“是啊……”切尔茜有些苦恼的敲了敲自己的头,她另一只手还在扶着凛慢悠悠的往前走“不赶快去追不行啊,真是个让人不省心的孩子。”
“可你也放不下他不是吗,就算在这几乎全员受伤的情况下……咳、咳咳!”
“好了好了少说两句,说的你不担心一样。”
“确实是啊……”凛无奈的闭上了眼摇了摇头,语气里却有藏不住的温柔“看到他那样子就没办法放下不管呢。”
“但是,你也是。”话题一转,切尔茜停下了脚步,神色冷峻的看向了凛“……说起来,你需要好好放松一下了,凛。你的状态很不好,我想你自己也知道吧。”
“……”凛一时间表情晦暗的扭过头不知道在看着哪儿,然后回过头有些拘谨的笑了笑“您费心了,LEADER。我……确实是状态不佳,但是这影响不了什么。”然后像是为了在这伤痕累累的情况下证明自己并无大碍一样,凛还耸了耸肩“……只是高压能让我的思维放空罢了,这样就不会去想一些无聊的事了。”
“……如果这样能让你高兴的话。”
“谈不上,但是这样让我很习惯。”凛停住了脚步,然后在切尔茜疑惑的目光下摇摇晃晃的坐在了墙边“LEADER就先去找LEO吧,我随后就到。”
“你是知道我不放心把你一个人丢在这的吧?”
“我知道,但是……”凛犹豫了一会儿,才像是找到了个好理由一样小心翼翼的开口“……就算是给失败者的一点点私人空间?”
“队友之间谈什么胜负啊……”切尔茜挑起眉头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算啦,败给你啦。赶快跟上来哦,我就在前面……不然我是会回来找你的。”
“遵命,女士。”
等到切尔茜走远了,凛才小声的这么说了一句。然后他摊开手掌。掌心里是一枚闪着光的金属物件,一看就充满了超现实主义色彩。物件上充满了锈迹或者说是血迹,隐约的有股不祥的气息,背面用粗糙的手法刻上了“暴走”二字,显而易见不是什么用完后还能全身而退的东西。
“……至少有机会的话。”
还是不要让别人受伤吧,如果由我牺牲就能解决这一切的话。










*大概因为公园行程太沙雕了,作者并不能写出任何严肃的东西。现在想起公园脑子里仍然全是沙雕小段子。
1.
在矢崎晴树眼前的是一具尸体。
无论看到多少具尸体,他可能都无法适应这种令人作呕的感觉。虽说从他来到安乐岛以来已经见过不少更加可怖的怪物,但尸体与怪物不一样。怪物更能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而尸体更容易使他想到死亡。
那大约是具穿着和服的女尸。她的全身已经高度腐烂,使人根本无从人认清她的长相、年龄和死因。弥生小百合不愧是职业护士,似乎对这具随意地埋在小树林的尸体没有很强烈的不良反应,她走过去蹲下查看,而矢崎压下了心中的一丝不安,走过去帮忙。
它全身上下已经找不出一块完好的地方,裂开的皮肤组织十分艰难地挂在骨头上,似乎碰一下就要全部碎在泥土里。而已经几乎只剩骨骼的手紧握着,似乎在抓着什么东西。
矢崎打开了那只手,找到了手中的一颗被糖纸包得完好的糖。
什么人在死的时候会紧握着一颗糖呢?
也许是个孩子。矢崎想,大概只有小孩子会觉得一颗糖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也会因为得到一颗糖而感觉非常满足。
而从这具骨架来看,去世之人显然比孩子大得多。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糖对于去世之人来说非常重要。矢崎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但似乎这只是普通的糖。
没有人该被随意的埋在这种荒凉的无人的小树林。但矢崎毫无办法,他们自己都无法离开这个孤岛。
矢崎晴树站在尸体前默哀了一会儿。
2.
“……说起来,美琴你还记得铃铛的约定吗?”
一行人路过沙地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深泽实琴的声音。
他们无意偷听,但实琴说得光明正大,他们也不能堵住耳朵。
几秒后他们听见了深泽美琴的声音。
“嗯……啊,你是说藏起来的那个铃铛吗?你不提起我都快要忘记了……”
美琴似乎思索了一会儿,又开口道:“说来我们当初的约定是什么来着……是说找到对方的铃铛就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实琴:“是啊,当初美琴找了好久呢。”
美琴带着撒娇的语气抱怨:“结果还是没找到嘛,真是的——到底藏在哪里啦?”
实琴似乎轻笑了一声:“嗯……我忘记了。不过不要在意啦,我也没有找到美琴的铃铛嘛。”
深泽实琴在说谎。
矢崎晴树在回集合地的路上一直在思考这件事。
他们在公园里发现了美琴藏铃铛时写的纸条,而深泽实琴明明在纸条后面写了一句话。
“找到了哦。”
不出意外,那应该是实琴的字迹。
矢崎晴树也许能明白深泽实琴是怎么想的。那是属于她自己的温柔,两边都找不到总比其中一个找到铃铛来得要让人开心。但她如果不想让深泽美琴知道找到铃铛的事儿,她为什么要在纸条上写下那句话呢?
而深泽美琴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想过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写下的纸条呢?
又或者,她们两个人其实都心知肚明?
3.
脚下的地板突然变成了血沼,疯狂拉扯着矢崎下陷时,他的大脑是一片空白的。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危险,却是至今为止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这时粘稠的血液已经没过了矢崎晴树的腰部,他不敢挣扎——虽然没有经历过,但他知道在沼泽中的剧烈动作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身后那个仿佛好多个人的肢体拼出来的女孩还在唱着歌,她唱得模模糊糊,但歌词却清晰地传入矢崎的耳朵。她唱着笑着,轻松地朝这边走来,那歌声使矢崎头脑发昏。
矢崎晴树今年二十一岁,他从没有想象过自己的死亡。而这时明明血沼刚没及他的下巴,他却已经觉得自己有了窒息的感觉。血腥味从他的所有五官钻入身体,渗透了五脏六腑。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在一秒一秒飞速地下沉,而灵魂却向上飘去,似乎要脱离身体。
——死亡的感觉真的十分糟糕。
他看到自己眼前有耀眼的五颜六色的光。像是在在舞台上演出时打到脸上的聚光灯,让他有些睁不开眼睛。
后来他再提起那个场景时,已经记不清自己当时都想到了什么。但在他即将陷入沼泽,窒息而死时,在他看见五彩斑斓的光之后,他的脑海中的确出现了一些东西。
包括家中刚吃完饭的父母,包括出发前拜托他带纪念品的朋友,包括和他一起计划拍短片的同学,包括他还没写完的论文,包括相苏町。
他算是还处在人生刚开始的阶段,回顾自己的前二十一年,他算是走得顺风顺水,包括家庭、学业、恋爱,他虽不算万事皆顺利,却也几乎没碰过壁。他多次想过离开安乐岛之后要做些什么,甚至在心里列了个清单,但是似乎一切都要结束在这里了。
在他即将失去意识时,他听见了一些声音。
“晴树,振作一点……!”
“……醒一醒!”
“晴树!”
……
“你也别死。”
他猛然睁开眼,发现同伴们拉着自己的手,而自己的身体也在一点一点的上升。血腥味仍然让他想呕吐,但那种窒息的感觉已经缓解了大半。
他跪在地上,全身的力气都被掏尽了。他感激地看了一眼同行的人。
谢谢。
Fin.

青年爬上山。山道并不好走,前不久才下过阵雨,泥泞的路面不断啃咬他的皮鞋。但路很好认,他不是路痴,来过几次自然也就记住了。况且山道通常是笔直的,尽管会被深浅不一的绿色植物模糊边界。
宅子位于半山腰,挂着“深泽”的门牌在闷热的空气中和大门一样纹丝不动。这次他没有再做什么奇妙的梦。奇妙的梦若是做过太多次也会变成现实。而他其实并不喜欢这些梦变成现实。
青年不知自己为何会想这么多,照往常来看,他并非如此心细善感之人。
不过,偶尔一次也无妨。
于是,他转身走进树林。向深处走了几步,尽可能不去更深处,挑了一个能完全藏在背面的粗壮树干。林荫在他头顶招摇出一片微热与光斑的海洋,沙沙作响。
他想了想,说:
“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就像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登上那艘游轮一样。你知道么?生活总是这样,看上去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实际上你并不知道。”
他又笑了。
“或者改一下,‘人生总是这样’——一个还差四岁而立的人来说这句话是不是不够有说服力呢?”
青年一贯是不擅长表达什么的。职业要求他学会去表达一些客观事实和科学规律,但他其实在讲堂上照本宣科也没有关系,总之台下的学生很少有听进去的,更遑论听懂并反馈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他更多地,还是习惯面对深夜的荧光屏幕、白炽灯下的雪白纸张,将那些专业领域的东西悉数记录下来。
这些令他想破脑袋、伴他熬过无数夜晚的东西,最终将刊载于网站上、杂志上,或许还会进入图书馆里。但这些东西会传下去么?
他想,不会的。
这时,他听见背后有轻微响动。不同于风、光或热造成的自然声音,显而易见,他察觉出背后有人。和他只隔了一个树干,大概是不小心,踩了踩脚下的落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女孩的面容来,他曾将她比喻为人偶,现在这个想法也不曾改变。他又想起了那个夜里端茶而来的机关人偶,想起自己在某个清晨失败的点茶经历,奇怪的是,回忆淡远了。
“深泽实琴。”
“你好,深泽实琴。”
“说起来,我们还没有正式打过招呼吧。每次见面都很匆忙,也没有时间像这样聊天。……这算是聊天么?”他觉得有些好笑,“算吧。虽然你好像不喜欢说话,如果你不介意,就当它是一次奇怪的清晨闲聊吧。”
在酷暑来袭之前。
树叶沙沙。青年似乎听见背后落下一声“嗯”,可是太轻了,淹没在林叶间,来不及拾回。
“因为工作关系,我很少有不熬夜的时候。写论文、弄研究,不知不觉就到了四五点。”
夏天的四五点已是晨光熹微。熬夜使得大脑会在短时间内异常兴奋,而他兴奋的大脑在瞥见跃出高楼的鱼肚白之前,往往会先捕捉到忽然四起的鸟叫虫鸣。
“你听过四点的鸟叫么?”
“……其实和平时没什么区别。但因为万籁俱寂,听起来就会特别突兀。”
“我也不懂它是不是在唱歌,我的专业不研究动物。总之,挺吵的。”
“吵到你会觉得……自己还活着。”
“你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背后没了动静。
他其实看不透这个小女孩。旁人都说深泽姐妹大概十四岁,但在他看来,她似乎活得更久。以时间衡量年龄在她身上是否适用呢?抑或是,应该用“经历”来衡量她?
说到底,人究竟能否彻底看透除自己之外的某个人呢?
多奇怪,人往往连自己都看不透。
他叹了口气,继续道:
“主动去感受‘活着’,与被动感受到‘活着’,我还是更喜欢前者。”
“我经历了很多‘身不由己’,现在也正经历着‘身不由己’。我想你也一样。……也许不一样吧,你是‘甘之如饴’?”
“我不知道你和你姐姐究竟经历了什么。至少我现在不知道。但我……其实挺享受这样和你聊天的。像什么电影小说的桥段,记不得了,大概是有这样一个桥段的,只是隔在人物之间的不一定是树干。”
背后的人又轻轻踩了踩树叶。这次是故意的。
他低低笑了起来。自他大二或大三以来,他便很少像这样笑了。诸多原因令他收起了少年的纯真。
“不仅是在这个岛上,只要是生活,就必然无法预料下一秒会遇见什么。只是岛上的生活无限放大了生与死、恐惧与悲痛。”
“你经历过‘日常生活’么?”
“无数个‘按部就班’同时朝不同方向延展,立体的、四维的、更高维度的……”
“……没事,你忘了吧。就当是一个作者为了凑够字数在胡言乱语。借了我的心、我的嘴、我的神态动作,表达一些无稽又荒唐、幼稚又无趣的感想。”
青年拿出手机,滑开解锁。没有信号的手机被他当做时钟与相机。
“哦,到时间了。我该走了。”
他收回兜中,站直了身子。树干苍老的纹路硌得他后背作痛。他自始至终没有回过头去,看一看树干那头的人究竟是谁。
“再见,深泽实琴。下次再见……或者待会就会再见,也说不定。总之,再见。”
他径直走下山去。
温度随日光的浓烈开始升高。与蒸发作斗争的泥泞继续咬着他的鞋跟。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除了那一句飘过耳畔的“再见”。
但他其实不确定那是否是“再见”,也有可能是“谢谢”,两个字,五个音,都没有分别。
青年走下山去。
又做回了“静间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