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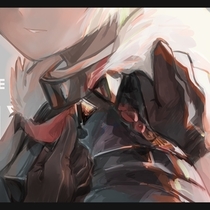



没啥营养,虽然ddl过了但写都写了就干脆发了叭.jpg
————————————————————————
哗啦啦——
听见金属滚落台面的散碎声响,西屋造也将手上的铁块浸入冷水中,伴着水受热的滋滋声转过身看向前台。
“造也君,这次也麻烦啦!”
被堆放在桌上的那堆废铜烂铁,或者说曾经是武器的废铜烂铁的主人对西屋露出笑脸,他衣服湿了大半,头发跟外套甚至正在往下滴水。
“太糟糕了,怎么突然就下起了暴雨啊,外套都变重了。”
落汤鸡两下脱下外套跟上衣,一边抱怨着一边拧着衣服。
正在翻看武器的惨状的西屋造也眉头一跳:“离目鸰小朋友,能不能不要把雨水拧到我的店里。”
“啊,抱歉抱歉。”鸰挪到门口,远远地又朝造也喊,“可是有什么关系嘛,你店里这么热,地上的水肯定很快也会干的啊。”
没有理会对方找的借口,造也一把将台上的废铜烂铁扫进下面的回收格:“一周前才给你做的新武器,你怎么做到这么快又给弄成废铁了?”
“我也没注意。”鸰像动物抖毛一样甩了甩头发上的水珠,“或许是这周的任务有点多吧?”
虽然西屋造也并不在意顾客都会怎样使用他所打造的东西,但从他认识离目以来,对方弄坏武器的频率实在夸张到有些离谱,也怪不得离目从不定制价格过于昂贵的武器,大约是觉得便宜的坏了也不心疼吧。
“你还是早点学会控制自己的力气比较好吧,虽然从钱的角度来说,你总是来光顾我的生意让我挺开心的。” 西屋走回工作台前,“这次武器的要求也跟之前一样吗?”
“对,和之前一样就好哦。”离目轻车熟路地探过身把钱码进收银的抽屉。
“那你随便找个地方坐一下,我先忙完手头的活。”
“虽然按大家说的那样控制我自己的力量可以省下不少的钱,但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控制’的感觉,一点都不轻松舒适。”鸰把上衣搭在门口,拖了把椅子坐到台前,“我平时已经够不自由了,实在不想再多费别的力气了——”
“不自由?你是天门的吧,天门规矩很多吗。”
“还行?虽然规矩也有不少,不过加入天门之前我更不舒服,现在已经好多啦!毕竟从人出生到这个世上开始就已经是不自由的了,之后尽管再怎么去努力寻找生存之道,也只是在不自由的前提下试图相对轻松的活着而已。”
西屋造也瞥了一眼鸰说这话时候的表情,他趴在前台看着自己,还是一副笑眯眯的什么都不在意的模样。
“真没想到能从小朋友嘴里听到这种话,最近不看少儿频道改看哲学频道了?”
“造也君……你在我家电视周围装了摄像头吗?!”
“是句很有你风格的笑话。”造也敲着被烧红的铁片,很给面子地扯了扯嘴角。
“咦,我还以为这句话可能挺好笑的呢。”
咚咚——
敞开的店门被敲响的声音打断了没营养的笑话,两人抬头看向门口站着的信使。
“西屋造也先生在吗,有您的信件。”
“在的哦!”离目鸰举起手,从椅子上弹起冲到门口接过信件签收一气呵成,西屋造也本人忍不住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然地成为另一个我。”
“反正造也君也要签收的吧?”鸰拿着信封正反看了看,正当造也准备阻止他拆阅个人信件时,他却将信件递还给了造也。
“信封里有炸弹吗,怎么这次不说‘反正造也君也要拆阅的吧’然后擅自拆开了?”造也狐疑地接过信件。
“只是因为没有拆开就知道里面的内容了。”
鸰指指信封背面的火漆,凹凸的纹路简单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央都立天门高校的章标。
“从几率上来说比信封里有炸弹还稀罕呢!不过也不是很意外,毕竟造也君做的武器是我用过的最耐用的!”
“耐一周的用?”
“哈哈哈,不过这样一来我就是造也君的学长了呢,不如现在开始喊我离目前辈如何?”
西屋造也一目十行地阅读完信件,犹豫片刻后又将信纸塞回了封袋中:“我不会去天门高校的,准确来说是我不打算升学。”
“真是奢侈呀,轻易放弃进入那么多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地方,这种机会可是很难出现第二次的哦?”
“世人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渴望拥有的也不是天门能给我的啊。”
信封被放在一旁,短暂停顿的叮叮打铁声再度响了起来,“用你的话来说,读完国中后经营少泽叔叔的这家武器店就已经是对我来说‘在不自由的前提下最轻松’的道路了。更别说我根本不想喊你前辈。”
“好可惜!不过我能明白哦,因为我当初选择进入天门也是因为差不多的理由。”
“你想喊别人前辈?”
“前半句啦,前半句。天门为了抑制绝望性大破坏出了很多力,还为灾后重建做出了很多贡献,对世人来说无疑是‘正派’一样的存在吧?而引发绝望性大破坏,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各种灾难的绝望暴徒大约就是他人眼中的‘反派’了呢。”
“你是想说你有英雄情结?”
离目摇摇头,跟着又点点头,“情结谈不上,但或许只有成为了前者才能让我变得轻松一些。”
“虽然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东西,不过既然已经进了天门了,你现在有感觉到轻松吗?”
“有吧,但是人总是贪婪的啊!”
离目鸰蹬了下台侧支起椅子,将重心集中在一条椅子腿上。
“就是这种摇摇晃晃的感觉,不稳定,也永远没法真的腾空。”
“拿开你的腿,店里的椅子万一被坐坏了是要赔的。” 西屋造也走到台前,一把把罗出鸰所需要的武器,“你看看是不是这些。”
“哇!造也君这次怎么速度像飞一样,我还以为要在这里坐很久呢。”
“之前估计着你总会需要的,就提前准备了一套。”
离目兴奋地握住武器挥试两下,随后逐把将武器装进匣中,拿上门口的外套准备离开。
“造也君万岁!雨也停了,下周再见啦!”
“欢迎下次光临。”看着随着鸰站起的姿势自然倒回原地的椅子,造也罕见地没有嘲讽这个“下周”。
聒噪的元素离开了,店中顿时变得空荡起来,只剩下铸造师以及被封闭在室内的熔炉闷鸣地回响着。
“与常理相悖的东西是无法和现实长久融合的,更何况想要轻松地活下去这一点本身就很不轻松。”
西屋造也看着椅旁地面上的一小滩水迹,不知是说给空气还是某人地喃喃道。
“开始准备下一套武器吧。”

感谢大家人设期以来的精彩创作和积极参与企划的热情。企划组在昨晚20:00后,对所有报名角色,按照企划书所写审核标准,综合各项因素,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赋分统计与商讨。
最终,我们暂定场内名单(25名角色)如下。对于没能入场的角色,我们深表遗憾,也衷心感谢您的积极参与。
称号 姓名 部署 性别 人设地址
元吉他手..........矢吹 正月............后勤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116/
动物会话..........四野 银丸............研究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189/
气象学家..........穗波 海海凛........研究 女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3241/
道具师.............水原 艾琳.............后勤 女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079/
元牙医.............平竹 一辉.............人事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2661/
元标本师..........凪川 正明............研究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051/
元踏白将..........战场崎 空式........对危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438/
元情报科..........入間 練馬............研究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2676/
除灵师.............小野寺 烟岚.........人事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037/
赌徒.................未来 永劫.............人事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158/
元律师.............滝 壹成................人事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7602/
信使................鸠原 光.................后勤 女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138/
模特................玉城 あいか.........人事 女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043/
剧作家............二宫 卢娜.............人事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134/
元赞助人..........笼目 亡礼...........人事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7183/
元教员.............天明寺 领............对危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463/
元民族志学者.花开院 无纯........研究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164/
陶艺家.............草野 忠................研究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345/
经济学家.........律野 风凛............研究 女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262/
元黑客............浅羽 利树.............中枢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6588/
元自杀介入者.明野 松籟............人事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234/
美甲师.............梶 弘明................后勤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086/
元恐怖片演员.藤原 真由子........人事 女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4250/
元飞行员.........飛鳥 阿諾德.........对危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7124/
清道夫.............离目 鸰.................对危 男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57536/
企划群号将私信以上玩家报名账号。请在6月30日晚18:00前加入企划群,逾期未加入则视为放弃入场。
若玩家放弃入场,请私信企划组。企划组会顺延其他角色入场。
正式入场名单将在确认入场完毕后,与序章结末一同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