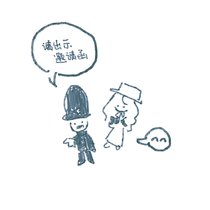评论要求:随意
“你也会明白,所有人都会明白,我们生来就一直在被污染……”不死的怪物絮絮叨叨,嘴里冒出了血色的泡沫,冒着血丝眼球顺着肌肉的脉络游向手臂,试图接触那柄刺入它体内的直刀。
“我只是在抗拒污染,抗拒那些天生的诅咒……”
怀方试图抽出直刀,但为时已晚,在眼球接触到武器的一瞬间,无数红丝攀缘到银面,将其牢牢抓住。于是他后退几步,靠在天台的铁门上,从腰间抽出了手枪,瞄准了眼前的怪物。
“停下!停下!难道你不理解吗?你应该有所体会吧!”怪物大叫着,它的体力已经无法支撑它做出更多的反抗,只能倒在地上,绝望地向敌人对话:“难道你不曾畏惧时间吗?”
怀方重新审视眼前的怪物。
它的身体吞噬了数个人类,它的爱人、它的亲人、它的朋友,还有它的宠物猫,这些被吞噬的个体被血色的肉丝融合在一起,聚集在不死的怪物身上,扭曲的肢体成为了怪物的工具,时不时抖动着,就像还拥有生前的痛觉感知一样。
只是一只怪物而已。
“我们从出生起就一直在失去,我喜欢的玩具、我的梦想、放学后的时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所有我爱的和爱我的,都在被时间污染。”它向前一步,试图接近自己的审判者:“你也一样吧?你也在失去过什么吧?没人是不曾失去的,所有的爱都会被时间褪色,我只是保存自己所爱的一切……”
怀方扣动了扳机,子弹命中怪物的脑袋,半个脑壳伴随着黑红色的粘稠向后飞去,背负众多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扬起尘埃,却仍不肯死去。
“我不会死的……”它失去了半个大脑,还在那呢喃着:“因为这是我的愿望……”
确认目标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怀方通过手环给队友发送了消息,准备进行最终的收容程序。
“你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怪物嘲笑道:“每个人都说人生是不断获得和失去的过程,没有失去就不会有获得,但最后你们都会死,一无所有的离开……”
“都是骗子……明明每个人都还在为了失去而痛苦,却还欺骗别人,说什么一切都会过去……”
“就算接受了失去,也还在失去……”
“回答我……为什么你不说话?!”
城市的霓虹灯在怪物的背后照耀,这里的风很大,即使没有空调也很凉爽。
“别急。”怀方又一次向怪物的心脏扣动扳机,虽然无法致死,但能保证其丧失行动力。
“你会后悔的……”怪物趴伏在地上,现在的它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却还用着古怪的诗意去表达:“等吧,等皱纹爬上你的脸庞,等白发污染你的黑丝,等疾病剥夺你的健康……等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会想起我……”
怀方张开嘴,说出了第一句话:“那就等到时再说吧。”
“像你这样大脑空空的人……”
又一声枪响,怪物一声闷哼。
“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但如果你想要攻击我,那我可要攻击你了。”怀方警告道。
“你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句话也不好判断是否属于攻击,怀方宽宏大量,不计较了。
“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所有一切都没有意义。”他回答:“但我没必要为了意义活着,不是所有事都需要答案。”
他看着怪物,眼中没有一丝动摇。
“即便你要成为蒙上双眼的愚人,时间也会毫不留情……所以人类才会有繁衍的欲望,想要留下什么,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残忍的时间……但这不过是将污染延续,把诅咒传播给下一代……只有我才是答案,只有我才可以对抗时间。”
不死的怪物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头,张开嘴,它的悬雍垂无限膨大,结出了鲜红果实。
“你也可以获得永恒的生命。”它的声音从深不见底的咽喉下传来:“一个交易、一个祈求。”
怀方略一思索,快速瞄准射击,“嘭”的一下将悬雍垂的果实炸成了血花。
不死的怪物闭上了嘴,沉默地看着怀方。
“你怎么还不死?”怀方问道。
“你怎么就是油盐不进?”怪物反问道。
“是我在问你问题。”
“……”
怪物沉默片刻,终于叹气:“我不会死……愿望已成……这是绝对的规则……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回答什么?”
“为何……你不畏惧时间。”
“我只活在此刻。”
沉默,无言,一丝光亮升起,怪物回头看去,太阳也在城市的天际线沉默着,墙面反射橙色的辉光,城市开始繁忙,车水马龙,嬉笑怒骂,又有风吹过,一刻不停。
“时间很残酷,但又没有那么残酷。”怀方嘴角勾起一抹不曾被人看见的笑意:“至少,它还留给我们不少时间,可以去看太阳升起。”
怪物沉默良久,缓缓闭上双眼,它还活着,仅仅是在享受阳光。
朋友啊,请享受此刻吧。


There is nothing new in Red River City
强尼从来就不是一个大胆的人。他想起自己不管是失手杀了人躲到教堂寻求庇护,又背着所有人跳上车逃出橡林镇。还是刚到红河城时壮着胆子替帮派在西城区讨债、砸场、“卖货”,最后为搏出头趁乱开枪打死了那个老警察局长。都是弗兰克——不,现在该叫芙兰卡了——陪在他身边,给他打气,替他出谋划策。
“喂,强尼,要不我们俩想想办法瞒过血注那边的人,吞了这批货一起去达拉斯混。”
所以当芙兰卡在躺在床上,在他耳边兴致勃勃地这么说时,他没多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满脑子都想着“这可比飞叶子爽多了”的强尼一直到红河城郊外的约定地点等待买家,都甚至没有丝毫考虑过这心血来潮的谋划后面藏着多么大的失败可能性。
当他们看到披着风衣的那个矮小身影从车上下来时,连芙兰卡自己都没想到,他们等了将近两小时后等来的不是灵装的买家,而是完全在预料之外的人——弗农领主。
车前灯的强光直射在强尼脸上,逼着这个已经被砍掉了两只手,像滩烂泥一样伏在碎石地上的男人从那些一幕幕走马灯画面的恍惚中回过神来。从额头流下来的血模糊了他的视线,只能隐约看到芙兰卡也同样倒在地上,喉咙上插着她自己的那柄灵装匕首。站在一旁的领主脱下沾了血的手套,嫌恶地扔在芙兰卡的脸上,跟着逐渐崩解的尸体一起化成飞灰。
当强尼和弗农领主那双湛蓝色的眼睛对上时,身体此刻才突然被激活了恐惧的本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领主朝男人走过来,捋平裙子蹲下身对他嘲弄:“居然还没死,乡巴佬的命可真硬。”
“橡林镇离这不远,把这个杂碎丢回去。”夜里一阵凉风吹过,领主飘起的裙摆拂过强尼满是血污的脸。她带来的保镖立刻粗暴地将濒死的男人塞进轿车的后备箱,尚留有几分意识的强尼嘴唇翕动,还想说些什么,却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棕榈宫的大门向外敞开,充足的暖气从里头直冲出来,搅散了入夜后聚集起来的凉意。在弗农的眼里看来,这座曾经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所有人钱包和灵魂的赌场如今就好像被拔去了尖牙,滑稽得像路边的小丑。
“万分抱歉,弗农小姐,不不,领主……”新任的经理一路赶来,忙不迭地向她频频低头致意,解释自己刚才正在为最重要的开场秀作准备。劳蕾塔并没有在大门等太久,也不在乎眼前这个据说是凯莱布从拉斯维加斯挖来的经理人嘴里那套说辞想表达的到底是歉意还是辩解。
“走,要到她跟我约好的时间了。”她将脱下的风衣递给经理,披上披肩示意让男人为她开道,领她去见她的那位生意伙伴。
玻璃穹顶下挂着的镀金天象仪被替换成了闪烁着五彩光芒的霓虹灯,宽阔的中庭被摆满了发出沉闷响动的老虎机,钱币在散落时碰撞到一起的声音在赌客中唤起一阵激动,兴奋的叫声在高墙内来回纠缠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原本大堂正中央那座高大的战神雕塑像也不知所踪,转而被几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取而代之,不停地在轮换的广告中转播着赌场内各处景象。
棕榈宫是劳蕾塔和凯莱布当年在红河城建成的第一座赌场,也是他们在这座城市的起点。现如今,这座如宫殿一般繁华的地方也开始显露出了疲态。而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把整座棕榈宫焕然一新,在前面领路的这个家伙确实有点本事。只是可惜,专制的弗农领主并不乐于见到如此巨幅的变化。
“老板她就在里面,这个点刚刚好,正好是开场秀开始的时间。”经理满脸堆笑,弓着身以近乎谄媚的姿态为劳蕾塔推开角斗场的厅门。
矮小的领主只向里踏了半步,浓重的脂粉味便裹挟在各色人群的嬉笑声里向她扑来。没有呐喊,没有喝彩,也没有赌上性命的血腥搏斗。昏暗的环境里几束暧昧的灯光在照射着四周每一张被魅惑的蠢脸。原本属于瓦尔基里使用的八角笼彻底消失不见,只有一群袒胸露背的舞者在盛满香甜气味的酒液的舞池里搔首弄姿。大厅里的所有人都沉溺在脱衣舞的刺激中,这副充斥着低俗香艳的场面令劳蕾塔不得不皱紧了眉头。弗农领主尽力无视掉四周俗不可耐的愚人们,用自己碧蓝的眼睛扫过厅堂一遍,最终才在一处高台角落的沙发上看到了那头她熟悉的红发。
“我不知道你还喜欢这种玩意。”穿过人群的领主甩了甩手,无言地驱离为生意伙伴倒酒的女郎,顺势在沙发的另一端坐下来。
红色的暴君见到她,只是板着脸把手里的威士忌一饮而尽,拿起酒瓶给自己再续上一杯。两人沉闷的氛围仿佛一层无形的罩子,隔绝了那些身上又少一件衣物的舞者引来的阵阵口哨和欢呼。
“回来这么久了,非要我联系你才肯从你那破宅子里滚过来,好一个忙碌的生意人,弗农,”谁都看得出来凯莱布心情不佳,黑帮首领翘起二郎腿,将自己陷进沙发中。他懒得寒暄,直接质问道,“我的那批货呢?”
“在我的破宅子里,”劳蕾塔端坐着,保持着自己应有的仪态,“被那两个小杂碎碰过的东西我需要仔细检查一遍,免得哪天就发现其中一两件被不知来路的乡下修女握在手里。”
“怎么,我卖什么东西现在还得过你那一道?”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电话里就讨论过现在搞灵装交易还太早。”
“我跟你通话是出于对生意搭档的责任,才特地通知你,不是他妈的在寻求你的意见。”
“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把这个当回事,所以我才不得不出面替你擦屁股,凯莱布。”
“放你的狗屁,你意思是我现在不配坐着,得听你的教训了对吗,老东西?”
两人脸色愈发难看,争吵的音量越来越大,最后猩红的暴君一把摔碎酒瓶,琥珀色的液体溅到了劳蕾塔纯白色的长裙上,晕开一片。飞溅的玻璃碎屑打掉了灯球,刮破了挂在墙上的油画,甚至还有一部分划伤了周围众人。惊得赤身裸体的舞者全都噤声退到后台,看客们也纷纷离开这处是非之地。
听到异响的帮派成员立刻直闯进大厅,看到引得首领大发雷霆的竟是弗农领主,一时间也怔住,在犹豫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毕竟两位瓦尔基里之间的争端,无论如何都不是普通凡人能够介入得进去的。
干掉这个布鲁克林来的混球。
劳蕾塔的脑中突然又响起那个苍老低沉,带有颗粒感般沙哑的声音。这嗓音她再熟悉不过,大半月前她还在洛杉矶处理生意时,就已经听到了这个属于曾经的自己,“他”的声音。
“滚出去!”凯莱布怒喝着命令他们离开,当偌大的圆厅里只剩她和劳蕾塔后,侧过身的凯莱布腹部突然吃了一记脚踢,吃痛的暴君立刻反应过来,咬着牙迅速抓住领主的脚踝,把劳蕾塔甩到高台下,振碎了落点附近所有的桌椅和大理石板。
以瓦尔基里的超人体质,这一下甚至没能在劳蕾塔的皮肤上划出一丁点伤口。只是她还未能来得及起身,凯莱布就已经抢先一步赶到她身侧,卷挟着气流以肘代刀向她的面部刺来。劳蕾塔将身子别到一边,将将避开了凯莱布这记肘击,但地板就没这样的好运了,被击碎的地面应声碎裂,裂痕四处伸展,将整个大厅的地板破开碎成初冬时节开裂的冰面。
劳蕾塔抓住瞬息而过的机会,双手撑在地上抬腿朝红色的身影再次猛踹一脚,逼得凯莱布不得不侧身躲避。“红凯尔”毕竟是混迹黑帮出身,近身斗殴对她来说无异于家常便饭。趁着“老弗农”收腿之际,凯莱布伸出两只手臂一把抱住矮个儿领主的双腿,压着劳蕾塔直直朝堆满碎石和扭曲金属的地面砸下,躲无可躲的庄园主只能硬吃下这蛮横的撞击。弗农领主并非不善战斗,只是在单独面对速度更胜一筹的帮派首领时,她总会被对方抢占近在咫尺的先机。
但她不会就此作罢。
凯莱布在扬起的烟尘中只是稍有松懈,劳蕾塔便以闪电般的速度伸手抓住她的脑袋后那头扎眼的红发,不给她留任何挣扎的余地,用头朝她猛撞过去,直逼向凯莱布那张今晚直到现时现刻仍然板着的脸。凯莱布没想到自己常年合作的生意搭档会使出这样的招数,措手不及结结实实挨了这一下。红色的暴君只得松手向后踉跄几步,没等她从眼冒金星的劲里缓过来,凯莱布还模糊着的视线里几缕金发已经向她逼近。一下,又一下,劳蕾塔出拳的速度比凯莱布想的要慢,但每一拳落在她交叉格挡在身前的手臂上时都好像带着无比的力道,感觉只要对方再出下一击,骨头就要被这迟缓却沉重的直拳打断了。
劳蕾塔满心愤懑,脑子里回响着同样缓慢,扭曲且病态的笑声。她清楚地知道,那是来自曾经的劳伦斯·弗农的恶意。
与此同时在她耳边响起的,还有从凯莱布嗓子里冒出来的开怀大笑。
“脑子被我撞傻了吗,小混球?”不知为何,劳蕾塔胸腔里燃烧的怒火被这清脆的笑声浇灭得一干二净。
“这样才对,老家伙,”红色的暴君干脆就地躺下,在一片狼藉里摆了摆手向矮个子的领主示意就此打住,“这么久了,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那副端着的狗屁样子。”
今晚从头到尾都只是某个牛仔借机撒气罢了。
凯莱布和劳蕾塔在一些事情上总会产生无法调和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她们俩的过去也有过不少。只是像今晚这样大打出手,不论是对弗农领主,亦或是猩红色的暴君而言都是头一遭。于是劳蕾塔也不再将自己紧绷着。她在被她和凯莱布弄得一塌糊涂的圆厅里,挑拣出一张尚且能用的沙发软垫一屁股坐在上面,趴开着两条腿长吁一口气。全然丢掉了刚踏进这里时自恃高人一等的仪态。
劳蕾塔瞥了眼身旁的凯莱布,以平缓的语气向生意伙伴退让了一步:“你要搞灵装交易我可以不管,只是你得再重新找些你和我都信得过的人去处理这档子事,我这几个月给两个州的那些个议员四处打点,就快成了……只需要再等些时日,就能把橡林镇扫进我们的口袋里,你也清楚我当初把弗农庄园的位置选在了和那个镇子相邻的地皮上是为了什么。”
“我他妈又不是强尼和芙兰卡那样的蠢货,但我现在暂时对橡林镇和那个教会没有想法,天晓得休斯敦派来这里的那些政客和条子有多难笼络……你干什么?”
劳蕾塔突然翻到了自己那条羊毛的针织披肩,趁着自己的生意伙伴抱怨时披在了对方身上,遮住凯莱布在那些本来就破破烂烂的布条缝隙间露出的身体。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穿的都是些什么玩意,牛仔,”自己身上的长裙也裂开好几道口子的领主替凯莱布理了理衣领,“明天让伊克斯来我这一趟取走你的货,至于红河城新出现的问题……哼,你的城市,你自己搞定。”
劳蕾塔站起身拍了拍裙摆,从角落里捡起凯莱布的牛仔帽戴在头上,稍微遮掩自己凌乱的发型。她和凯莱布摆摆手道别,勉力保持自己的步子尽可能平稳,朝大厅外走去。
“对了,”劳蕾塔似乎突然想到什么,回过头对凯莱布露出微笑,“新的棕榈宫我不喜欢,那个新来的家伙我也——”
“你以为我喜欢?”凯莱布立刻打断话头,“我累了,等明天我再差人给那个拉斯维加斯小子一点警告。”
她们都知道“警告”意味着什么。
弗农领主今天也一样疲累,所以当她回到庄园内的宅邸,感应到自己的收藏间里有个瓦尔基里的气息时,她还下意识地以为是自己养的那条劳拉叫来替她接货的卡罗尔。要不是因为某位脾气甚差的牛仔,按劳蕾塔今天原本的安排,她应该亲自接应自己特地让巴尔苏克运来的收藏品。
都这个时间了,卡罗尔还赖着没回自己的养狗场,怕不是又想跟她厚着脸皮用另外一条劳拉抵掉赊欠了差不多两个月的租金。劳蕾塔不想再多费心力,不顾自己身上令人发笑的衣着搭配,从墙上取下用来打鹿的猎枪,一把推开收藏间的门。
“卡罗尔,要不要尝尝当一头被猎人盯上的鹿的滋味,嗯?”劳蕾塔举枪瞄准了房间里那个背影,才发现对方头上那顶尺寸过宽的鸭舌帽和她戴着的牛仔帽一样滑稽。逗留在房内的瓦尔基里下意识地将双手高高抬起,弗农庄园的主人一时间也对出现在自己屋里的陌生瓦尔基里感到了疑惑。
“你是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