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的超烂,复健。和我互动的大家都是对话体超抱歉的。大概是有八千字出頭吧,沒出息地低空飛過混個活躍投稿。】
【睡了。】
川端由纪子深吸一口气,在心里打了个小小的问号。
自称VON大人的猫似乎已经对不停地受到学生的反抗感到厌烦,只是一脸怠惰地在台上接受着少年少女们的愤怒和恐慌。
由纪子完全无法理解那只猫为什么站起来的时候下半身完全看不出猫科动物该有的骨骼,只是两只被棉花强行填充起来的棉布棒,坐下来时却变成真正的猫才有的折足。但是没有关系,对现在这个情况来说,考虑现实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体现出来的意象,重要的是构成这个场景的感觉。沙子对她说道,而由纪子并不想接受这种说法。
这就是所谓的魔法吧,意象(Image)与象征(Symbol)的魔法。川端由纪子为自己做出了解答,与此同时,她心中困惑的沙子也被逻辑思维的淡场推平了。
回顾之前那只自称VON大人的猫咪所展示的魔法,不外乎是对心理产生作用,归咎于催眠似乎是项不错的选择。唯独最后砸下来的乌龟就像是个天大的玩笑似的,让由纪子对自己的判断力失去了信心,从周围人的反应来看,自己似乎不是唯一一个看到相同景象的人。
集体催眠……?由纪子推出这个看来最为可能的答案,但是她被沙子所否决了。
而且,她也想不起来一丁点有关于签署合约的事。因为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象。思维的沙子在川端由纪子心间的那个问号上悄悄低语,这个轻柔的劝解让她放弃去思考关于乌龟和魔法的事。正在这时,那只自称是使魔的阴阳脸猫跳下他的讲台,摇摆着尾巴向着他们身后的方向走去。由纪子的思维也就被这些声音慢慢带回到现实中。随后,由纪子看向身前的少女。对方还跌坐在地上,似乎是没有从魔法的情况中缓过劲来。
也难怪。由纪子想着,向对方伸出手去,想将少女拉起来。“可以站起来吗?拉住我的手吧。”她向对方说到,对方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意外的有点沉。由纪子想着,握住那双细软的手,将对方扶了起来:“怎么样?脚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吧?”
对方摇了摇头,摸索着背后拿出一块书写用的白板和笔,慢悠悠地写出圆润又整齐的一句“谢谢,请不用担心我,只是刚才有点惊讶罢了”。
“没法说话吗?”由纪子疑惑地问到,随后注意到对方脖子上包裹着纯白色的绷带,“对不起……”她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笔记本和纸,同对方继续沟通,“总之我们先离开这边吧,待会儿安定下来了再聊。”
正在他们用纸笔对话时,那只猫已经带着其他超凡人级的学生离开了大厅。由纪子只好拉起对方的手,快步跟了上去。所幸,使魔并没有再给他们准备什么奇怪的惊喜,只是带着他们来到一座狭小的六层塔。塔看起来也与魔法学院的城堡装修如出一辙,只是更为简朴,也更狭小,螺旋状的梯子处于塔的正中央,围绕一根直通天花板的巨大圆柱,暂且不论结构,直感上给人一种看不到楼梯尽头的恐惧感。
由纪子跟在队伍的最后,用力地握住梯子的扶手,扶手摸起来很干净,似乎没有疏于打扫。反之,稍弱的灯光仅仅能做到照亮房间的程度,全无大厅那里灯火透明的景象,但华丽的欧洲风格未减。由纪子对观察四周并没有多少兴趣,只是用纸笔随手写了一下自己的名字,随后递给了刚才简短地聊过的女生。
半刻之后,对方也递回来一张纸,纸的中央写着樱井未希四个字。
“嗯,这个名字念做Miki吗?我可以就这么叫你吗,以前认识的人里有人和你同姓呢。”由纪子用纸笔回问对方,未希点了点头。由纪子能隐约地猜测到对方无法说话的原因,不过,向第一次认识的人问起对方的伤势实在是很失礼,对方也不一定想提起这件事,由纪子便将那个疑问憋在了心里。
楼梯不停地向上盘旋,圆柱形的四壁给人一种逐渐聚拢的错觉,越往上走越能感觉到地心引力的威迫。由纪子仿佛能看到楼梯下的空间,所幸建筑是无缘于透明的设计,因此不用担心高度的问题,但由纪子还是能感觉到有什么令人头皮发麻的东西似乎要抓着人向下栽倒。
“由纪子的脸色不太好,是不舒服吗?”未希用白板问。
“有一点,因为突然想到自己可能在很高的地方。”由纪子翻过去一面笔记纸,写下一句自己也不确定真伪的话。
“恐高症?”
“也说不上,只是单纯有点怕?大概是因为我看不到楼梯那头有什么的原因。”由纪子回答道,两人最后停在了四楼的楼梯口,由纪子因为对房间的位置了无所谓,便随意选了其中一件房间,在向对方告别之后进了卧室。
由纪子思维的沙子已经静止了很久,却在进入房间的那一刻重新活跃,顺着她的脊髓向下爬去,直击心脏。
房间的整洁程度与宾馆不相上下,桌面上摆着透明的玻璃杯。由纪子为自己倒了一杯水之后,躺在床上开始梳理起自己的思绪。魔法学院和会说话、一点也不可爱的阴阳脸猫咪,超高校级的魔法使与超凡人级的她,一切都好像在讽刺着平凡的世界。就在这时候,沙子又开始低语了:“向这个奇怪的世界妥协就输了!”
“是的,我知道。”由纪子小声嘟囔着,抚平心中的沙子,但是那个沙盘不停地留下浅浅的指印,“我不会向魔法学院和超高校级的魔法使妥协的。”
沙子愤怒地在她的心房绕圈,如同波浪般拨起事端:“我想你也知道为什么,是吧?”
“因为她们实在是太不令人信服了,这个说服的环节与概念偷换写得并不是很晓之以理,让人觉得缺乏逻辑证据与同理心,内容也很空洞。”由纪子自信地回答道,“在证明自己拥有或真或假的魔法能力后,只是一味地煽动听者的自卑心并强调超高校级的魔法使的能力,试图建立一个上下级似的关系,这不是很让人不爽吗?还有就是,这些话背后的逻辑给人一种身为超高校级要施舍给我们这些没有才能的家伙什么东西——飒!来崇拜我吧!来崇拜给予你们能力的超高校级的魔法使吧!这样的家伙和世界一样,没有什么让人信服的资本。”
“正是如此。”沙子相当满意由纪子的回答,潜回她的心底,由纪子感到自己从折磨性的思考中解放了。她将视线重新转回了现实。
房间内部完全看不出任何电线存在的痕迹,理所当然也没有缆口或是电插座,之前经那只猫介绍,这里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是由魔力驱动,这让由纪子不由得忧心起自己的ipad能否用魔法充电,好用来消磨时间;日光灯很明亮,用来读书应该会是不错的选择;衣橱则很不起眼,里面的衣物款式一致,不过意外地还算合身。
是有人事前量过吗?由纪子心想,不过她很快否决了自己,毕竟,所有学生的卧室都是靠其主人自己抢来的,不存在事先知道卧室主人身高身材的情况,可能只是恰好服装是标准尺码吧。她拿起来一套换洗用的衣物,随后打开卫生间的门。
由纪子拧开水龙头,脱去衣物,等待水流漫过身体。一刻也不停地水声反而带来静谧。
梨津奈现在在做什么呢……由纪子想到自己小学时代最好的友人,如果梨津奈仍然遵守着她们之间的约定,现在应该已经是个很出色的人了吧。她有绝对的信心,那是梨津奈在某处成为超高校级的文学家或是其他什么合适她的职业的信心,因为梨津奈就是那么合适做那行,一般人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心情是一百的话,梨津奈喜欢文学的程度就是百分之一千。
又有才能,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梨津奈,怎么可能不会成功呢。
由纪子注视着打入手心中的洗发液,轻柔地摩挲起自己的头皮,然后是发根,一来二去将头发全部洗好之后再打上润发液,重复这些步骤三次左右之后,才彻底地进入放松的状态中。这样麻烦的保养方式,也是由纪子从梨津奈那里学来的,如果是以前,由纪子应该不会做这么“女孩子气”的事。
蓄起的长发也好、文静的语气也好、端庄的仪态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对梨津奈的粗浅模仿。
由纪子知道想要改变自己,变得更为讨人喜欢的心情,是从认识本多梨津奈开始才有的。如果梨津奈没有与自己同桌,由纪子也无法想象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或许会变成某个高中里平凡的、男孩子气的运动型少女吧,又或者是为了学习成绩闷头读书的书呆子。由纪子对那样的可能性倒是有一丝的向往,但是那绝不是受欢迎的人的正解。
“呼……”她吐出一口气,等待水流冲走头上的泡沫,然后开始用沐浴露涂抹肌肤,顺滑的液体在搓动中产生出大量的乳白色泡沫,她吹落了其中一朵,轻轻弹破巨大的肥皂泡。
啪嚓。
好想梨津奈啊,但是现在还不能去找对方。这个想法将她拉回了现实,她再度打开水龙头。做完最后一次清洁后,她为自己裹上毛巾,撩开头发上的水汽。吹风机震得人耳畔嗡嗡直响。
我要出去。川端由纪子盘起湿淋淋、条状的长发,好擦干自己的身体,我一定要出去见梨津奈,因为我们约定好了……但是,绝对不能通过那只猫口中所谓的“魔法”的方式。如果不是通过平实的努力达到目标,川端由纪子知道她一定会懊悔不已。
她开始编麻花辫。
沙子已经完全睡去,而她的心情也明朗起來。
在重新整顿过自己的状态后,由纪子推开房间门,走下樓梯。不知道是否因為事情突如其來,大家都沒什麼心情出門的緣故,只能看到少數幾個人結伴在高塔內來回走動。由紀子調整好步調的速度,向他們一開始醒來的房間走去。
雖然會說話的貓稱呼那個地方“傳送之間”,但那肯定不是城堡的入口,而只是某種象征性的童話開端。真正的入口在由紀子看來應該另有別處,只是這所“魔法學校”本身被超高校級的魔法使通過某種手段隱秘了事情的本質。
一開始醒來的房間,在由紀子現在看來實際上非常地擁擠,而且也並沒有任何家具擺放在其中。地板上雖然還畫著法陣,可看起來只是用普通顏料繪製出來的,充其量只能得到美術老師的一句“畫的不錯”的評價,完全沒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內。圖案本身既沒有發光,也沒有其他的特殊之處,看起來與畫在小學操場上的地板畫無異。
房間本身比明亮過頭的大廳要暗上不少,由紀子接著手機手電筒微弱的光源探查,卻並沒有看到暗藏的通風管道。不知為何,由紀子在這裡醒來的細節已經變得模糊了起來,是因為那時候頭腦不清嗎?但如果是那麼多人同時擠在一個如此狹窄又沒有通風的房間裡,應該會覺得悶熱吧……
回溯自己的記憶,由紀子卻不知為何覺得好像事情已經過了很久一樣,很難在自己的大腦里捕捉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最先開門的是一個黑頭髮的男孩,在他之後,其他人也都魚貫而出,接著,所有人在交談間發現自己曾經讀過一封關於魔法學校的信……就在這裡。由紀子注視著華麗的大廳中央,在那裡,一個銀白色的背影矗立著。對方從肩寬來看是男性,但銀白色的頭髮要留得稍長一些,體型似乎也比一般的男高中生要來得纖細。
“哈咯。”由紀子向銀髮少年打了聲招呼,“是來探索傳送之間的嗎?裡面什麼都沒有喔,地上的圖案似乎也只是普普通通畫上去的東西。”
對方似乎並沒有理會自己的打算,而是徑直走了進去。由紀子靠在門口,看著少年的背影來回踱步。不可能再找出來什麼了,由紀子心想,是因為貓說過那些話,因此不信任我嗎?還是說⋯⋯就在那一刻兩人的視線相交了。
隨即由紀子意識到那個人並不是在看著她,只是看著身處於某處的“觀眾”而已。
“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銀髮少年說到,就像宣布一項新發現似的,由紀子從對方的眼神中猜測出來,那個人是在等待別人的誇獎。
“啊⋯⋯非常厲害。”由紀子不確定地回答道,對方似乎對這個反應很滿意,但是,從頭到尾,他的視線都只是在由紀子身後的“某處”而已。真的在和我說話嗎,由紀子狐疑到。
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人並非是出於對由紀子的不信任,只是相反,對自己太過自信了而已。
是奇怪的人。由紀子這樣判斷到,雖然被超高校級的魔法使平等院稱為“超凡人”,但那只是才能,無關他們的個性,在這些沒有才能的孩子裡,有個性相較他人異常者也說不上是什麼怪事。
“為什麼一定要自己去確認一下呢?”由紀子問。
“我來決定就好。”
“只是這樣而已嗎?”
“聽不懂你的意思。”
“唔,請問能讓我和你一起看看四週嗎?”
少年沒有回答也沒有拒絕,由紀子將那當作是默許,同對方一起走向大廳的方向。魔法掃帚跳著舞,扭動著自己猶如腳部的帚穗,令人聯想起迪斯尼的動畫。由纪子看着这幅场面,才再度有了自己身处于魔法学院的感觉。如果这些也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的话,魔法的存在或许不是那么遥远也说不定。
“那个啊,”由纪子小声地向着白发少年说道,“我该怎么称呼你比较好?”
“法华津伊御。”
“法华津同学你好,我是川端由纪子,现在想成为文学少女。对了,法华津同学,能帮我个事情吗?”由纪子问。
“说来听听。”
不知是否因为由纪子一直跟着对方的原因,她注意到法华津的表情略微软化了一些。
“帮我把其中一个扫帚抓住好吗。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对那只猫来说应该也不是什么犯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也没关系。”由纪子放柔了语气,请求对方道。虽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但就是想试探魔法的能力极限。
“我来做吧,你站到一边去。”法华津说,“你想做什么?”
“挠他痒痒。”由纪子在扫帚间挑肥拣瘦,随后锁定了一个帚尖看起来更为稀疏的。
“啊?”法华津似乎是没有听清自己的回答。
“也可以说是性骚扰学校员工,总之想拜托你抓住其中一个扫帚,扒开帚穗那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其他地方也是。”由纪子换了一个说法。
“啊!”对方脸上的表情绷不住了,由纪子倒是颇为欣赏这种反应,“我说你啊,为什么要拜托我这种东西!”
“说成是什么都无所谓啦,我就是想看看那个东西到底会怎么反应。你会帮我的吧,法华津同学毕竟是男子汉。”
“哦!你一定没见过像我这样充满男子气概的人吧,那就让你来看看我男子汉的一面吧!由我来展示完美地性骚扰!”法华津看来跃跃欲试,话音未落就抓住了其中一个扫帚,扫弄起帚穗的底部。扫把在法华津的身下剧烈地抖动了一会儿,随后放弃了抵抗。
对方如此积极地参与“骚扰”,完全是由纪子没有料到的局面。已经失去了动作能力的魔法扫帚被法华津粗暴地扒开穗子,由纪子问对方:“怎么样,有看到电子机关或者别的什么的吗?”
“我可除了穗子以外完全没有看到!你也来吧,看看木棒这块。”法华津催促着,由纪子俯下身去,看了看法华津固定住的帚柄。
“来吧,来看看那只猫是不是在装腔作势。”由纪子敲了敲帚柄,然而,那扫帚在被她碰到的那瞬间又挣脱出两人的束缚,飞到一边去了,落得两人满身灰尘。由纪子捏起自己的毛衣,慢悠悠地试着抖落上面的灰。
“竟然敢逃跑!”法华津看着扫帚消失的方向,似乎还有想追过去的打算。
“大概是害怕我们探明魔法的奥秘,或者只是想故作高深吧。超高校级的魔法使不可能存在,因此,多半是不想让我们发现‘魔术’的奥秘。”由纪子笑道,“好啦,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那就只好下次多几个人再说了。”
“那个人有那么糟糕吗?”法华津问。
由纪子回答:“我觉得他是虚伪的胆小鬼。”
“虚伪就虚伪呗?”由纪子并没有料到法华津会接这句话,法华津并没有在看着自己,而是像之前那样眺望着不知何处。又被他的视线推开了。由纪子想。
“你不虚伪吗?我不虚伪吗?世界上的人,无论怎样,多多少少都会有虚伪的一面吧。啊,我确实是不够虚伪,但我觉得川端你很虚伪。”
“我吗,我很虚伪?”川端由纪子重复道,试图从中找出逻辑推导的过程,不过,她摇了摇头回复到,“法华津同学真是个很奇怪的人,……啊,不要误会,这是褒义的,我觉得这样很好。”
“嗯,我看也是。”
“怎么说,感觉法华津同学和其他人对距离感的感受不太一样,我觉得大概是好事吧?”
“当然是好事啦。”法华津张开双臂,像是过独木桥的孩子那般轻松,又像是男演员俯瞰着南瓜般的观众那样轻笑了起来,“只要我觉得是好事,那就是好事。”
***
之后,两人又一起去调查了顶楼,川端回到四楼的时候时已经快到门禁的时间了。出人意料的是,门口站着一位金发的少年。
“啊,你好。”川端出于礼貌向对方打了招呼,“晚安。”
“你好。”
“忘了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川端由纪子,被他们称作‘超凡人级的文学少女’。”老实说,是句在不太恰当的时候冒出来的开场白,但由纪子经过一天的事情很疲惫,因此并没有太多的闲心准备自己的自我介绍,“你呢?”
“我是深濑弥成。”
“深濑同学一直站在门口是怎么了,因为睡不着吗?”由纪子停下掏出钥匙的手,看向对方的双眼。明明脸上的表情说不上严肃,对方的眼神不知为何给人一种不近人情的感受,是双非常克己的眼睛。由纪子想。
“不,也说不上,只是在进房间前整理下自己的思绪吧。”深濑回答。
“啊,要不要来交换一下情报看看?要喝茶吗,还是水就好了?”由纪子掏出钥匙,打开卧室的门,“还是喝水吧?毕竟有点晚了。”
对方站在门口思索了一会儿,不过还是点头同意了。由纪子从房间里拿了玻璃水杯出来,随后两人端着水杯,在楼梯间喝起了因为心理作用、味道有点怪的凉水。
“说来抱歉,煞有介事地请你出来,我的情报却很简单。猫降下的乌龟不见了,传送之间的图案貌似只是普通地画在地板上的图案了,然后,扫帚没看到什么电线之类的东西,所以应该不是机器人——不过,判断的标准也没有那么简单啦。”由纪子叹了口气,“你那边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情报吗?”
“嗯……我和另外几位一同逛遍了所有的区域,顶楼那边被封锁着,大厅的门也全部紧锁,没有打开的机会。还有就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深濑摩挲着手指,直直注视着前方,看不出冷漠的双眼中在想着什么,“我不是在猫出现的时候被魔法击中了吗?被击中之后脚小指虽然有种钻心的疼痛感,事后我去检查的事后,却并没有看到任何伤痕。”
“连淤青都没有?只是有疼痛感?”由纪子歪了歪头,“深濑同学你如果确定的话,我有个奇怪的假设,可以说说看嘛?”
深濑点了点头。
“如果说所谓的魔法其实都只是某种催眠的手段,我们现在真正的肉体身处于某个空间,这里只是单纯的虚拟空间——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当然也有可能是别的手法了,科技发展到现在,VR也不算什么罕见的东西了吧。就算是别的手法也好,我只是想说明,我们感知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它实际存在的样子。”
深濑皱皱眉头,似乎是在思考什么,过了半会儿,他回答道:“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仅仅是我基于感性和随机的猜测啦,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至少能解答一些目前的情况吧?老实说,我都快被这个地方所谓的魔法给说服了。因为这里的魔法仍然遵从我们的逻辑发生,”由纪子摊开手,强压下沙子的躁动,继续说了下去,“以我刚才所说的背景为基础,就到了下一个问题……”
“猫所说的自相残杀是否等于现实意味的死亡。”深濑将半张脸埋在自己的手背后,由纪子看不清对方究竟是以怎样的表情说出的这句话。站在楼梯上的由纪子点了点头,并继续说了下去。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这不是真的,却有人这么想的话不就很糟糕了吗?觉得杀掉别人只不过是帮对方脱离了VR或是催眠制造的环境,又或者觉得其他人都是游戏里的NPC,然后展开了好像时下流行的糟糕生存游戏小说一样的剧情,想象一下就会觉得很可怕吧。我想,我们应该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过的人。”由纪子的食指来回拨弄起自己溜出辫子的发丝,将其挽成圆环状。深濑似乎对这个提议不以为意,却仍未抬起头直视她的脸。
两人的视线在半空交汇。
“我不觉得会有人这么做。无论如何,人都不至于堕落到那种程度才是,更何况是……对站在顶点有执念的人。”深濑低下头去。
由纪子张开双臂,沉睡的沙子形成金色的波涛,一浪叠一浪打上了心房。
她笑了笑回答道:“但是也会有那种人吧?有的人会装出来一副圣人君子的样子,实际做着令人讨厌的勾当,也有的人虽然看起来就是随处可见的家伙,但内心里面正在想着骇人听闻的事情吧?反过来也一样。就算是单纯地戴上人格的假面也好,这样的情况哪里都是,不是吗。”
“不,我不觉得那是假面。”深濑抬起头,那双蓝眼睛分毫未受由纪子影响,只是从由纪子看来,那张脸上柔软的部分又减少了一分,“只是人本能地想要变成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有这个愿望的心情绝对不会是假的。”
“诶呀,你说得对,我说了奇怪的话,很抱歉,本来是不该说这个的。”由纪子点点头,“深濑同学这样的想法,我很喜欢。”
“没关系,毕竟是在这种情况下。”深濑摇摇头,将手中的玻璃杯还给了由纪子,随后从楼梯上站了起来,“川端小姐,你也觉得很累了吧。已经是该睡觉的时候了,先回去吧。”
他们走出螺旋式楼梯间,随后在走廊上道了晚安。由纪子知道沙子已经被推平,她松开自己的麻花辫,随后坐在床上,开始读那本为了消遣放在背包里的书。《二十一世纪经典文学分析》,这本书被她买来当做是闲暇时的读物。她翻开其中一页,缓慢地读了起来。故事的原文是篇有点长的童话,却在分析中被分解成无数个小小的字节,故事本身讲的是一个修整天空的少年神的故事。
“星星掉下来了,我便缝补星星;月亮掉下来了,我便悬挂月亮;如果是太阳掉下来了,我便重新为其炉心填充火焰。”她读着,好像已经能看到那个修正天空的少年,他出现于那段分析字里行间,又在句号后隐去了。
由纪子心间的沙子慢悠悠地攒动,但只有寂静,这寂静让她再度变回了一个人,她闭上眼,一头栽在床上。
“晚安吧。”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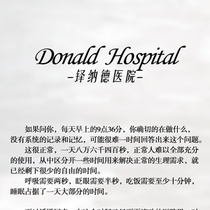
忙到暴毙,抽空摸鱼。
讲真徒然堂一屋子的俊男美女,真不像是什么健全的纯纯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正经店铺啊!!
瞎互动一发npc,希望鸟哥不要啄我。
——————————————
赵衔对那些子怪力乱神之事虽不甚热衷,却也不能说全无了解。
至少他心里头清楚:
这世上约莫是不存在甚么女鬼的。——便就是有,这画中的那一位,也决计不会是多年前溺水而亡的那位李小姐。
器物生灵,谓之灵器。人有七情六欲,物亦有想念心思。
赵衔自四年前起,时常走南闯北的外出游学,统共下过两回江南,俱走的水路。南边的夜风柔而凉,出得秦淮畔,便至姑苏城,他盘一条画舫,自吴门往下,夜宿姑苏河上,看灯红酒绿一片霓虹,不唤歌伶美姬,也不饮酒,只泡一壶清茶,合了袍子卧在船头,半梦半醒间夜色消退,石拱桥后的便微微泛起鱼肚白来。
这景色已是美极,可说到姑苏,于赵衔而言,又不得不提另一处地方。
那处桃花灼灼,水榭风流,赵三公子初时误入其中,险些以为自己乃误入了那陶潜笔下之桃花源,一时胸中大震,因想起自身许多纠葛,顿觉悲上心头……只那树枝上鹩哥叫声嘎嘎,方叫人重返世间。
说一句实在话,赵衔当了这么十数年的公子哥,架鹰放狗、赛蚂蚱逗鸟的事儿虽谈不上专业,却也绝不生疏,那家的鹩哥叫成这般,叫声粗嘎中隐隐还似藏着股嘲笑之意,怕不是主家都提不出来见人,是要被笑掉了大牙的。
可见仙境却是不俗的,景不俗,鸟儿也不俗。
也亏得他心中想了甚么,从不放在嘴上,否则少不了还需狠吃一顿排头。
及至被那仙人般的店主引了路进了门,赵衔这才知自个儿究竟是入了那般的龙潭虎穴,一脚踏进了那样一个仙山头。
他瞧着匾额上‘徒然堂’几个大字,再看看垂帘后或坐或卧的谪仙玉女,心里头明白过来,忍不住探手摸了摸自己怀里的钱袋子。
这那里是什么桃花源,分明该是那桃花瘴才对。
当日空手归去,便耐不住令小厮研了墨,将此间见闻洋洋洒洒挥毫一通。墨迹未干,却又觉不妥,添添改改许多时间,最后便只留下寥寥数语,并一张桃园醒春图,三月后赵衔归京,同旁的游记一并交予那书肆老板印了出来。
见写着:
“昔人有言:忽逢桃花林,外人不足道。今余一朝入梦,误入桃源……观山水之可爱,闻垂髫之兮兮,少顷有天上人和光而至,飞鸟落其臂,落英妆其鬓,点余入得一门,正首好一块悬堂木,上书:徒然堂……内室丝竹雅乐,清丽非常,隔帘观仙人娇客几多,人影绰绰,环佩叮咚,窃窃絮语,不敢多闻……后出此园,再不闻仙音雅乐之声,举目四望,不复见仙人化境,已然姑苏城外粉墙瓦黛,是谓人间矣。”
他笔下写这徒然堂仙姿邈约,妙不可言,心里头如何想的,却不得而知。只一本《散游随记》印出,逢人问起那徒然堂,赵三公子虽笑脸温文,却只道有缘者自见之,旁的话,是半句不多说的。
赵衔抚着手下那幅山水画,画作自入赵府大门,便未曾有半点异动。
若非胸有成算,若非提来这桩事儿的人是常山,他倒真不免要怀疑此事真伪,疑心是谁人故弄玄虚,诚心要框他取乐了。
可既然开口之人是常陆之,这般疑心便很没有必要,显得小人气性了。
物虽生灵,却不知寻常器物之魂魄常人难见,有缘人方可视之。只有那心气里夹了怨、裹了恨,叫那本清透的东西摔在泥潭子里染了一身赃污的器之魂,才头次在芸芸众生眼中留了形,种了根,摸得着瞧得见了。
这山水画里的‘女鬼’,赵衔心里琢磨,或者将将生灵无多少时日,尚还未到最糟那一步,可观那王公子一事,怕是也只差临门一脚,是清是浊,俱在方寸之间。
有关这事儿,他信心很足,却半点没打算同常山说道。
因想着,常陆之这般的人物,素来是要将事情辨个是非黑白,不得个准儿那是不肯罢休的。他自爱这般品貌,也往往敬重三分,可真要亲身对上这倔牛脾气,赵衔还是拱手作个揖,且饶过他罢。
且他赵叔明,为人不似友人这般坦荡又磊落,腹中的百般心思千种盘算,却是说不出口的。
*
赵衔最终决意管一遭闲事,与常山一同往那王老爷府走一趟。
得知他也要同去,常山虽面上表情未变,但视线中明摆着写满嫌弃。他惯知道这赵三,衣食住行无不精、无不细,很有些文人穷讲究的毛病,这与他的性子委实不合,因而平日并不如何乐意与其同行。
兼之这画卷之事,现下虽平稳,他却知实则凶险异常,自身为了公务涉险,尚没甚么好说的,要叫赵衔处险境,却是心中不愿了。
这般想着,常山便有些想拒绝,张口说话干巴巴地:“此番案件,虽与叔明你不无干系,却也无需……”
无需后面他没说,倒是难得委婉一回。
可惜这份难得没人珍惜。话音刚落,便见赵家家仆牵了马赶了车,一路至两人身前。马是好马,那马车果然亦十分精细讲究。一小厮打了帘,赵衔就在一边作揖请他上去。
说话还极好听,极有道理:
“若真个同已故的李小姐相干,那王公子怕是尚且身处险境。此事宜早不宜迟,迟则生变,陆之兄还请上座。”
两条腿从城东跑到城西,硬是连个轿子也未想起来坐的常陆之将喉咙眼里头堵着的那好些拒绝之词便就又咽了回去,他一掀袍角,大步一抬乘上了赵家的马车——两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的,谁人都知道的道理。常山人虽倔,却并不在公事上争什么意气,虽那王公子与他素不相识,但到底是一条人命,说不记挂,却也是不能的。
赵衔亦上得马车来,择了个位子坐了,他给小厮打了个准信,马车便缓缓驶动起来。
马车内铺了香垫子,边角都裹着毛料,一边置着一方案台,赵衔不知在何处按了几下,便见台下缓缓弹出一抽屉来,再朝边上一推,就又打开一扇格子门。
赵三慢条斯理的从中取了茶器,慢条斯理的拨了下头烧着的炭火煮茶,便料到是这番情景的常山移开眼,并不怎么乐意理会这厮。
他无话可说,赵衔却有言要道。他拨着炭,状似不经意般问常山:
“此去王家府上,李氏经年旧案要如何查,陆之兄胸中可有成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