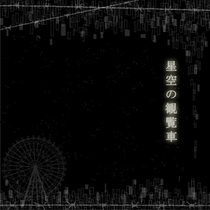3149字。
道具制作的引子(……
VS 达老师(上
队友名单:Fla、铁塔、弥撒
maya我的肝简直快死了……
=======================
命运的流向 7
气温逐渐降了下来。
费伊在宿舍醒来时打了一个哆嗦,被子已经不够暖和了,但这已经是他最厚的一床了。
原本有暖气的日子一下子令人怀念了——他艰难地从被窝里钻了出来,时间是清早,虽然没有了电子设备,但他的石英钟准确地显示了时间。
早与晚在现在的学院里已经失去了意义。
只不过生物钟依然发挥着它的效用,让他准确地在这个时间点醒来。
“……”
费伊·叶茨坐在床上,抬头看向对面Kuriki的床位。
床帘拉着,他自然看不到kuriki的身影,这会儿的宿舍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安静的。
就算是学院被魔族入侵了的现在Kuriki忧虑的也不仅仅是学院的现状,信件已经无法从外界寄来,但假期里那几封信的后遗症仍旧存在,费伊有时候在半夜醒来依然会发觉他独自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容焦虑。
……Kuriki知不知道他在担心他呢。
费伊想多半是不知道吧,但这没有关系,反正他亦无法解释这关心的由来,宁愿在暗中默默地做些什么。
他轻轻握了握拳。
自那以后——自魔族入侵学院以后已经过去了数月时间。
事情的进展比大家预想得还要缓慢,老师虽然公开说明了学生们可以协助清除魔物,却没有说到什么样的地步他们才可能对教学楼进行清扫。
而失踪的老师亦都没有下落,新闻社刊发的报纸上说有学生发现达梓老师正在学校里肆意游走,毫无理智地袭击着过往的学生。
“……”
费伊深深地呼、吸。
学院仍不安全,尽管宿舍已被证实仍然是安全地带,但他们总是要离开宿舍的,尤其是食堂被占领、只有礼堂供应食物的现在。
只要离开宿舍就有可能遭遇危险……
费伊其实知道他或许不该如此偏袒Kuriki,毕竟对方早已不再是当年来到他居住的森林里的小男孩。
但无论是他或者East一定都无法放着Kuriki不管,仅仅一分也好,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做到些什么。
“呼……”他呼出了长长的一口气,开始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走下床。
所以他也有自己的打算。
这个打算在这一学期还没有开始前就已经产生。
费伊·叶茨拿起了桌面上的书。
昨天晚上他再度复习了书里的那一部分,那是罕有的讲述魔法道具的书,其中的一种道具引起了他的兴趣。
——手镯。
那是种附加了契约的手镯,可以将特定的两个人联系起来。
再加上几个他预想中的配件后在假期里费伊准备在学期中制作这个道具——只可惜魔族突如其来的入侵打破了他的一切计划。
可讽刺的是,魔族入侵反而让这个道具变得更有必要了,他没有告诉Kuriki这件事,至少要等到他完成了这件道具他才打算把这件事说出。
……原本这个道具,他是应该和校长一起完成的。
这个思绪瞬间在心底泛起一片苦涩,费伊甩甩头把思绪抛走,他把书合上,开始走出宿舍。
说来——单就表面而论,费伊·叶茨不相他的某些同学那样热衷于把魔物驱逐出校园。
他更多地是按着自己的步调在走,他从一开始就认为把魔族驱逐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如果以持久战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可以做的事其实还有很多,巩固自身就是其中的一环。
所以他还是选择了在现在这个时机里去制作这个道具——学校里已经如同冬日的气温让呼出的空气变成了白雾。
“友绊手镯吗……”
这个名字被记载在书本之上,它是友谊的象征,能够将远在他方的朋友用这个简单的手镯联系在一起。
呼出的白雾飘飘飘、直到上空消失不见。
他依旧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点灯或者使用魔法照亮,他看得见,他继续向南走去。
——他必须去图书馆查询这个道具所需要的最后一点要素。
幸好图书馆没有被占领,真的,幸好。
虽然假期以来费伊已经很少去那里,但图书馆对他而言仍算是某种寄托。
脚步越过了植物园与食堂,两侧魔力的光芒都在不断流动闪烁,魔界蝙蝠依然在他前头的路上肆意飞舞,它们看起来并不打算攻击他,但这种事向来没有什么保证。
费伊还记得那天他在植物园里。
这些蝙蝠似乎是因为血腥围而争先恐后地向他靠拢,不堪骚扰的他终于还是使出魔法将它们打落。
而后和Louisa相遇——而后他顺利回到宿舍,East果然如他所料的那样回到了宿舍,而West也在后来追寻着气味回到了宿舍,他们各自有伤,却好歹平安无事。
几人都花了一点时间来休养生息。
唯一的问题是East的变大粉用完了,他从费伊那里取走了还剩下的一些存货,因此后者决定去完图书馆后前往森林采集一些蘑菇。
“幸好森林也没事啊……”走在路上的费伊发出了轻声叹息。
某种神秘的力量保护了学校周边的树林,它们并未因缺乏光线而死去,而是依然沉默地伫立在远处的天边如同静默的石像。
森林一贯是费伊喜欢去的练习场所,无论是对于魔法,还是对于制作魔法道具——这一次的道具也是,他必须要用到炼金术,泥土也就变成了不可获缺的一部分。
“——”
说到炼金术。
他们的炼金术老师Shadow也因为达梓的失踪而陷入了长期的低迷。
就连费伊拿着自己的预想去找他询问时得到的回答也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就算他本人不愿意承认,达梓失踪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
费伊·叶茨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好。
联想到仍然被困的校长,他总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可他什么也无法说出。
毕竟情况各有不同,他没有意义、亦没有资格说任何安慰的话语。
“唉……”费伊小声地叹了口气。
他站在广场边缘抬起头,以往这里是不少学生爱来的地方,但魔族入侵了的现在大家都已经失去了散步的心思,这里变得冷冷清清,只用蝙蝠的扑翼声和他的呼吸。
……还有喷泉。
坐落在他们被传送来学院时的法阵附近的喷泉依然在不停歇地洒落水珠,若是平时的话、一定可以看到水花里隐约闪现的彩虹……
“……”
回忆过去毫无意义。
曾经沉浸在换生灵记忆中的他再明白这点不过。
可费伊·叶茨仍是站在那里闭上了眼睛,风和水的声音流过耳侧。
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其实相当怀念平和的校园时光,当那些事情开始成为回忆时它们才显得如此重要。
黑暗。
沉稳地围绕着他的黑暗。
费伊·叶茨似乎能在这片黑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只要周围没有任何事物来干扰他的话。
只要——
“……?”
声音。
他忽地听见远处似乎有什么声音正在向这里靠近。
“什么……?”
那声音听来像是从树林的方向走了过来,脚步很轻,轻到几乎能够逃过换生灵的双耳。
然而他的耳朵曾经在森林的深处历经锻炼,在那里他甚至连一朵花盛开的声响也能捕捉,成为人类后这样的感官逐渐退化,却也不会放弃这样的响动。
这样危险的响动。
费伊几乎在一瞬间紧蹦起了身体。
那脚步声就在他这样做的同时略微停顿,紧接着它仿佛是放弃了隐匿似的径直向这里冲来。
——好快!
在心底惊呼发出的同时费伊立刻睁眼,可那脚步主人的速度远超他的想象。
眼前的黑暗中一个身影一闪而过,男子的身体让他多少有些眼熟——
“呃!”
攻击已经迎面而来。
腹部传来了剧烈的冲击,下个瞬间他就发现原本固定的视野腾空而起,风属性的魔法即刻发动,他在空中稍稍稳固了脚步才终于落地。
——千钧一发之际他凝聚起了风阻挡在身前多少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红色的眼睛在黑夜中一闪而过。
紧接着那个身影再度消失,下一波的冲击来自右侧,附带了雷属性魔法的拳头在黑暗中闪烁出了刹那花火。
“啧……!”土元素被紧急召来,可就算有着土墙阻隔那冲击依然扩散到了他的身体。
五脏六腑都在剧烈疼痛,就算是在植物园面对那个叫卡姆的魔族的幻影时他也未曾像这样直接受到冲击……!
“——”耳边传来一声野兽般的低吼。
虽然如同野兽,可那个声音、费伊曾经听过。
魔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诧异地抬头。
因注意力的分散而变得薄弱的土墙瞬间被攻击挖掘,巨大的冲击降临,他的身体一下子被抛向了远处。
“咳、咳……!”
鲜血——啊,又吐血了。
费伊趴在地上,耳边充斥着喷泉的水声,视野因冲击而变得模糊,在朦胧的视野中那个身影正在向他走来。
猩红的双眼。
呼吸间吐出的气息带着狂暴的因子。
手背上电光噼啪作响。
可其实费伊更加熟悉他的另外一种形态,那个时常被人调侃与West相似的模样。
“达梓、老师……”
——在这种场合下遇到已陷入狂暴的达梓老师。
生还的概率大概小到根本不用计算。
视野伴随着冲击带来的朦胧逐渐暗淡了下去——
“费伊!”
然而这个声音的降临瞬间将他的神智从坠落的边缘拽回。
费伊吃力地睁开眼睛,眼前的达梓老师身边不知何时又多出了几个身影,魔力的光芒四下流动。
战斗——已经又一次在他面前展开。





3120字。
VS 卡姆(下)
和Louisa详细的打赤果过程后补(土下座
赶着打达老师去了……
=============
命运的流向 6
上学期临近期末时学会的魔法。
能够利用肉眼捕捉到对方的弱点,并且通过攻击那里造成大量伤害的魔法。
西芙与Kuriki的火焰撞在了一起,那只魔族向上腾空飞起,在半空露出的面容在火光下露出冷笑。
费伊把极度中二的咒语藏在了心底。
魔咒的声响相互交错,不同的声音与语言交织在一起。
张青猛地跃至半空,长枪尖端陡然划破空气,尖锐的声响伴随着魔法的光芒。
大约是谁的魔法(应该是西芙?)让她得以停在那里和魔族相互交锋,费伊听见魔咒的声音,那声音比起咒文更像是某种经文。
余弦的人偶冲上天空加入了战局,Elisa擅长的植物系魔法无法触及天空的高度只能以他不擅长的魔法进行攻击。
冰与划空声构成不了好的场面。
他抬眼看见天空中的身影一闪而过某个徽章般的印记,它闪烁得太快以至于以他的视野依然无法捕捉。
费伊·叶茨又凝聚起了冰结成的箭,风元素围绕其上作为引导。
——等待。
他可以等待对方露出破绽的瞬间。
“East!”他听见一边Kuriki的声音,混杂在几段魔咒的声响中,“你看这样——”
说起来家妖精擅长什么样的魔法呢?
他知道East最经常使用的是风与水的魔法因为那可以用来清扫宿舍里细小的角落。
光与暗的魔法East偶尔也会使用,但这种隐藏在家中的小精灵,最擅长的——果然还是隐藏吧?
一如费伊·叶茨最擅长的当是伪装一般。
箭被突地放出。
从地面而来的冷箭根本不被天空中的魔族放在眼里,长鞭在挥舞间就将腾空的冰箭挥开。
“切。”——但这不算在预料之外。
又一支冰箭凝聚成形,费伊想他或许很喜欢箭的外形,犹如在森林之中狩猎时的模样。
他是什么时候拥有这样的记忆的——
带着风的冰箭径直穿梭进西芙火焰之中,它穿过火焰的缝隙径直刺向它的目标。
半空中魔族陡然解开了腾空的魔法,四散的冰棱将所有能阻挡他的力量一一排除。
“可恶!”他听见张青的声音。
——刻印、仍然看不见。
冰箭落空。
即便是在下坠过程中对方依然保持着警戒。
费伊调整了准星。
原本落空的冰箭瞬间掉转方向从上而下向对方砸去,紧随而来的是余弦的人偶。
魔族的幻影再度停顿在半空,冰锥从他手中升起砸向那些从上而下的攻。
“——轰!”
一声巨响。
身边的风忽地一下腾起,被压缩的空气以超高速冲向了空中的幻影!
破风声一瞬间让他耳边什么声音也无法听到,费伊·叶茨站在一片轰鸣声中,瞬间像是回到上学期期末的那片海中。
但他不在那里,那片海早已回归己身,它的感官此时此刻能够赋予他力量。
出主意的Kuriki已经捂住了耳朵,被隐藏在冰箭魔咒下的攻击不偏不倚击中了空中的目标。
“……!”
幻影略微晃动了一下。
爆烈刻印有一瞬间出现在了已瞄准的箭尖上。
“——”
箭出。
轰响在半空中散开余波。
张青忍不住微微一缩,拙仓濯也不能幸免被波及。
炸开的冰棱差一点儿波及到了逐渐下降的人偶。
Elisa暂且收住了手。
西芙显然和他瞄准了同一目标,火莲与冰箭同时抵达刻印的位置,同样被魔法包裹的元素并未影响到彼此。
耳边隐约地传来了“咔哒”的声响。
半空中之前明明是实体的“幻影”逐渐崩溃破碎、掉落的身体逐渐消散在了空气中——
“费伊!”
耳边忽地传来了Kuriki的叫喊,费伊转过头。
——但下个瞬间他的视野就被蓝白色的冰覆盖。
“什……”
这句话实际上没有一个字是完整说出口的。
巨大的冰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地面上升起,排山倒海般的冰锥一下子撞在胸口将他推向了远处!
“该死、Ku——……”
他视野的最后,是Kuriki和East被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冲开的影子。
黑暗。
费伊·叶茨发觉他又回到了黑暗中。
这种黑暗他似曾相识,他万分熟悉,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徘徊在这样的黑暗中。
他是换生灵。
换生灵的孩子——据说他们从小就孤僻、孤独,他们不合群,仿佛有着与年龄完全相反的苍老。
费伊·叶茨不知道他在旁人看起来是不是这样的。
他还记得他回到班级时看见自己的书本被丢进垃圾筒,明明是同龄的孩子回过头来看着他露出窃笑,恶质或者不恶质的笑意都像尖刀一样刺在身上。
他还记得他逃课去图书馆里看书,翻开的书本上满是森林的画面,他走进森林里总有着不切实的熟悉,他宁愿在这里而不愿回到人群。
他还记得他自以为习惯却其实不过是个借口,他的道路蜿蜒进森林深处。
——费伊·叶茨似乎一直在离人类越来越远。
他还记得他曾经坐在宿舍楼的观星抬上这样思索,他一直记得在这样的地方有时侯会遇上校长。
可是这样的事其实从来都没有发生,他所期望和以为的事很多都没有发生。
就像他曾以为他还能安稳地度过这个学期、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他与校长之间发生的一切一样。
“咳……咕、呣……”
费伊在黑暗中醒来时喉头仿佛卡住了一块铁锈,从四肢百骸传来的疼痛完完全全地超出了他之前的预想。
——冰锥……
对,他在最后被对方的冰锥击中,现在是被抛到了植物园里的某个角落吗?
撞击带来的伤害叠加上之前被长鞭扫过时的伤变成了冰冷的疼痛,从胸口的地方渗进了内脏深处。
“呜……”喉头一片腥甜。
费伊在起身时抹去了嘴角的鲜血,换生灵的感官在一会儿之后才重回身体,四周——看起来并没有那些魔界植物。
“看样子……我的运气不错?”在疼痛中他喃喃着自嘲。
——Kuriki被冲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还记得那时攻击的范围太过巨大,他和Kuriki都被波及、却被冲向了不同的方向。
费伊有些担心那个曾经被他替换了的孩子,可眼下就算他在那里以他的状况恐怕也什么都做不到。
幸好还有East在。
在昏迷前他捕捉到的这个场景可以算是最大的慰藉,费伊扶了扶额,觉得额角刺痛。
——如果是East的话,一定会保护好Kuriki的。
费伊丝毫不怀疑这一点。
他叹息着努力在疼痛中挣扎着起身,疼痛虽然一直残留在神经末梢,却不能阻碍他继续在黑暗中摸索道路。
……回宿舍去好了。
因为宿舍现在依然安全。
如果他是East的话,一定也会把Kuriki带回去……
“砰!”
魔法与魔杖撞击发出了小小声响。
“你是……”站在魔杖之后的少女眯起了眼睛,“费伊?”
“……Louisa?”费伊·叶茨微微一愣。
——第一学期时曾与他一同进行任务的少女。
“你怎么会在这里?”他忍不住问。
“这个问题是我要问的才对吧?”Louisa挑起眉,“你怎么一个人……还这副模样?”
费伊·叶茨忍不住露出些许苦笑。
他知道自己的模样一定是狼狈至极,方才与魔族幻影战斗造成的擦伤仍留在身上,衣服破了、满是擦伤。
再加上魔界蝙蝠骚扰他后留下的咬伤——因为它们实在太过烦人,所以费伊忍不住出手将它们打落,所以才会不小心攻击了Louisa。
“我正准备回宿舍去。”他说,“你呢?来这里清除魔物吗?”
“嗯,毕竟得帮助学……咳、这学期没课,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个了。”她回答。
“说得也是。”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看来就只能将这作为他们的学业。
校长被软禁了的现在,学校能不能持续下去都会是一个问题。
事已至此老师们也一定会出手吧——如果单单是魔族的幻影就已经有那样的强度,那么魔族的本体大概只能由老师们来出手解决。
费伊叹了口气看向远处的天空,现在他之所以能够看到事物全靠Louisa手中的魔杖。
没有了电和光源,接下来位于深海的学校气温一定也会逐渐下降,条件会变得越来越恶劣,就算不是因为战斗,恐怕也会有人因为这样的景象而精神崩溃吧。
他漫无边际地想着,可越是细想越觉得未来的道路满是泥泞和黑暗。
“你还没说你在这里做什么?”Louisa的声音忽地把他拽回现在。
“我?”费伊顿了顿,“和你一样。”
为了清楚魔物而来——
这样的理由今后大概会用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吧。
无论真假。
“是吗?”
“嗯。”
准确来说的话大概多少有些差异,但费伊不想去解释这其中的缘由。
要详细去叙述那些因果大概太过复杂,犹如命运河流复杂的分支,以至于他宁愿用别的事情来将之代过。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红色的果实。
“吃吗?”他问。
“……这是什么?”
“是那边魔界植物的果实。”
“这种东西吃下去真的没问题吗?”
Louisa看起来相当迟疑。
费伊于是露出了笑容。
“没问题的。”他说道,“味道还不错。”
“嗯哼……”Louisa看着手中红色的果实,“不过费伊,你是这么知道这些的?”
“咦……?”
对啊,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费伊·叶茨没有看到。
在他方才醒来的地方,黑暗中无数冰封的藤条掉落在地。
3058字。
VS 卡姆(上)
我恨打斗(。
响应一下队友——虽然其实战斗极简化了|||
=========================
命运的流向 5
“校长”这个词,其实只是一个称谓或者一个代称。
仔细想想他从一开始就这样称呼着校长——从头到尾,一直没有改变。
费伊·叶茨并不是不知道校长的名字。
在他第二次看到对方、得知对方是校长时就已经一并知道了他的名字。
但是在这学院生活的四年中,他一次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名字。
因为没有人去呼唤它,就算是这所学院的老师也只是称呼那人为“校长”而已。
不知不觉中他称呼校长时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那不仅仅是某种指代,更多的是一种特指。
——特指某个人。
某个对他来说、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人。
费伊·叶茨在黑暗中徘徊。
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失去了换生灵的感官,他四周的一切堕入了黑暗。
可他很快就又再度回过神,他意识到East的光球还在微弱地闪烁着,他还没有失去光源。
意识带来了明亮,他看见一侧的Kuriki略有些担忧地看向他,他由是冲对方点了点头,“我没事。”他说。
声音比他想象得更加苍白无力,干涩得仿佛浸湿后又干燥的纸,一碰就碎。
而他自身也一如这样的话语,他能够做到的事少之又少,只不过是这所学院中普通的一位学生而已,他又能够做到些什么?
“重要的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费伊继续说道。
“的确。”East点头同意。
距离他们听见Leila老师的声音后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从最初的茫然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原先的困惑逐渐消失不见,新的困惑与顾虑却又再度升起。
费伊站在原地悄悄地吸了口气。
校长是被囚禁了——真相并不是最坏的那个预期大概是不幸中的万幸,只是被囚禁就意味着总会有办法能把校长救出,理解到这件事花不了太长的时间,但突如其来的状况仍让他用了很长时间来整理思绪。
紧接着他们又陷入了一阵沉默,像这样意料之外的状况总是会让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像平常一样反应和决断,费伊和Kuriki也不例外,East没过多久就又变回了原先的大小,但他手中的光球依然没有消失。
Kuriki看着变回原样的East,似乎露出了一瞬间的呆滞。
“总之先按原计划回宿舍吧。”费伊最后说。
虽然Leila老师的话有着庞大的信息量,但那不过是对现状做出的解释而已,并没有实质对他们的认知造成影响。
——除了停电和停止供暖外,宿舍的结界应当还在,所以那里应当还安全。
“嗯。”Kuriki点了点头,“走吧。”
一直迟滞着的三人这才又迈开了脚步。
但是前行最终也没能持续太久。
指望着这种状况下的植物园可以让他们平平安安顺利无阻地回到宿舍本来就不是一件靠谱的事情,没过多久他们就理所当然地遇到了生长红色果实的藤蔓,几次战斗后他们又不得不再度停下来休整。
——难怪Leila老师说不要单独行动。
像这样的魔物,根本不是普通学生一个人能够应付得了的。
费伊停在路上略微喘着气。
他的体力一向不是很好,接连的战斗让他格外地疲倦。
Kuriki和East也都有些疲劳,只有West仍然不知疲倦似的帮他们警戒着四周。
“汪!”
“West?”
它的声响吸引了费伊的注意。
他走到它身边,低下身抚摸着West的脑袋,而后顺着它的目光看去——
“……!”
在附近藤蔓的掩盖下,远处的植物园里几个人影正在交错穿行,魔法的光芒正在不断闪烁流转,宛如他上个学期期末在操场边缘看见的幻象。
——在战斗着。
这个概念一瞬间刺过他的脑海。
“啧……!”
——谁?是谁在那里战斗?
是与他们相同的学生吗?那他们战斗的对象又是谁?……或者、是什么?
换生灵的感观一瞬间向四周展开,黑暗中无数的藤蔓正在蠢蠢欲动,他们战斗的地方绝不是什么好的地点。
可总有些什么让他们无暇去顾及这些,眼底的光影向上刺痛着额角。
……比这植物园里的其它东西都要糟糕的某种事物。
以他的认知来说那是浑浊并且异样的魔力,糟糕的感触如同弥漫在学校里的那些气息甚至更甚,余下的一切显得虚浮而不切实际,但却有着毋庸置疑的强大,若他单独对上这样的对手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避。
不过眼下与他战斗的也并非单独一人,在那里战斗的至少有五个人,攻击时带起的魔力波动犹如一场激光表演。
“唔、……”
集中……集中注意力!
他不是不能分辨出眼前的一切,只是换生灵的感观强行叠加在人类的感官上总会带来些许不适。
——最远处正在燃烧着烈火。
那些火焰他曾经与之战斗,就算不熟悉也带着熟悉的光华。
魔力的主人他也同样介于熟悉与陌生之间,他认得那人,西芙·米兰达,她手中的火焰一刹爆发,犹如莲花转瞬的绽放。
然而这朵莲花转瞬就被封在了坚冰中,那个陌生的魔力闪烁着流动的光芒。
“怎么了?”Kuriki走过来问道。
远处的火焰在冰中逐渐熄灭,尖锐的风刃随着冰封在半空生成向下俯冲直撞向那怪异魔力的拥有者。
哈。
费伊几乎可以听见轻笑的声音。
人形扬手向半空就是一挥,跃出的东西有魔力却并没有太多的魔力流动——是类似附魔一类的东西吗?
“啪”的一声伴随着空气的震颤,物理性的攻击竟然凭空击碎了魔法凝聚的风。
“不是吧……”他听见惊叹的声响,如果Kuriki看到这一幕一定会露出更加茫然的表情——Kuriki正扭头呼唤East,家妖精灵从他的肩头一下子跳到了费伊的肩头。
弦切在远处的半空划开一圈轮舞,漆黑的火焰伴随着交错的弦刃成为了攻击的随影,那种战斗方式他也同样认得,因为太过独特而让他印象深刻。
——是余弦……
那么前头那个挥舞着闪烁着魔力光芒的长枪的一定就是张青吧。
结论、结论、结论和认知。
拙仓濯的身影像是在暗中伺机而动的刺客,他熟悉的人、他不熟悉的人。
更远处。
那是另一个二年级学生吗?他好像记得他的名字,Elias,他很少见到的学弟。
“这是……”East发出轻喃。
他一定也与费伊看到了相同的光影,只有Kuriki没有任何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捕捉一切的感官。
“喂、发生什么了?”他有些焦急地问道,被蒙在鼓里的滋味他可不想一而再再而三地知道。
“这个……”
他的答案费伊一时半会儿听不到,远处魔力的光和影都仍在闪烁不断,他药住牙凝固住自己的意识在那怪异的魔力之上。
——冰。
无数的冰随着那里魔力的流动而生成。
余弦丢下几个燃烧瓶却被蛮横的魔法生生凝结,霸道的力量让人有一瞬的错愕。
西芙双手上两道火焰闪烁着不同颜色的魔力光芒,更远处有人正凝聚着木元素的力量。
“!”不行!
植物不能忍受那样的寒冰!
“……Argat!”
身后的Kuriki和肩头的East都吓了一跳。
无数尖刃在半空凝聚成形,坠落的剑刃瞬间切裂了冰封与植物间的间隙。
“切。”East的声音。
爱丽丝的粉末再度发挥效果,足有190cm的家妖精再度显出身影。
“这下只能参战了吗……!”
West已经确保了前头的道路,绕开一丛藤蔓后站在被围攻位置的是个黑发的男性,长着恶魔般的翅膀与尾巴,见到他们露出了冰冷的微笑。
Kuriki在反应过来眼前状况的一刹就开始吟诵咒文,进攻的人数上升至七。
“费伊!”对面的西芙叫了他的名字,“你怎么会在这里?!”
地面在烈火与冰封间相互转换。
“我才想问你。”费伊皱眉,鞭子抽在他身前的地上,被张青一枪挡下,“这家伙是……?!”
……说来在前面挡下鞭子的那一位,你真的是魔法师吗?
“是魔族的幻影。”——所以有着不切实的魔力,“不过以我们来说,能做到的也就只有对付这样的幻影了。”
长鞭裹携着冰霜呼啸而来,费伊一扬手身前无数风元素堆积起了厚实的墙体,却被长鞭划开的风瞬间击溃。
“唔……!”尖锐的、疼痛。
另一边的Kuriki已经被East护到了身后。
费伊·叶茨向后退一步,他的胸口因方才的攻击而冻伤了一片,Kuriki丢过来一个担忧的眼神,转手凝聚起火元素配合余弦的人。
……笨蛋,别在植物园里用火啊。
虽然现在这里长满了来自魔界的寄生植物但也不能这样吧?
张青和拙仓濯在前面挡住了大部分物理性的攻击。
咦……?
不对劲。
从刚刚开始视野就似乎格外的——
——澄澈。
他忽然发觉自己视野里的世界平静得不可思议,换生灵的感官让时间和空间的流动变得怪诞了起来。
East向这边看来一眼,他眼中的世界会与他相似吗?一定不会。
每个人的视野都独一无二。
他一把拽住了思绪末端飘浮的某些因子,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
所有答案之中一定有个最优解。
“……刻印。”





3040字。
VS 火球球
=======================
命运的流向 4
费伊·叶茨再度拉起了“弓”。
他的手指间凝聚着魔力,然而眼睛却没有睁开,全靠自己的感知校准。
——从这里走到Kuriki那边必须绕路才能避开那些藤蔓,但他的魔法能比他更快,在他之前就击中目标。
“West,你先走!”
水元素凝聚的箭矢射出的前一刻他听见了“汪呜”一声,任意门展开向着Kuriki的方向冲去。
水凝聚的箭径直穿过树木的间隙,远处有另外一阵魔力的波动一把把kuriki拉住掩在身后——是east——而他的箭矢猛地向那团燃烧着的火焰,却被对方一下子避开。
“啧……!”
火焰似乎相当得意地燃烧得越来越旺盛,它扭头转向这侧,一团凝聚着的魔力立刻向着费伊冲来!
——跑……跑起来!
他飞快地迈开脚步,视野中路线若隐若现,身后的火球没有转弯,落地的一刹那些蓝紫色的火焰点亮了方才一直为感受魔力而闭上的双眼。
……在那边。
突如其来的光亮却也同样暴露了他们的位置,黑暗中长着赤红色果子的植物张牙舞爪地伸出了爪牙。
费伊再度加快了脚步,赶在藤蔓出现前回避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他能把握住它们间的空隙。
几道冰箭冻住最近的几根藤蔓,留出的间隙刚好可以让他穿身而过。
West的声音一下子更近了。
它的身影一瞬间闪现在他面前冲着另外一侧吠叫,费伊转手凝聚起水球向那个方向砸去,动作流畅得没有丝毫迟滞。
——水球在不远处撞上了蓝紫色的火焰。
爆发的水蒸汽一下子把他向后冲开,费伊脚步一个踉跄险些又撞进了一丛植物之中。
“啧……!”
不能停下!
一旦停下脚步他就是个活靶子而已!
思绪即刻紧绷,他一瞥望见了视野另一段的Kuriki,擅长水与火魔法的魔法师一手正握着自己的魔杖——
“水元素听我的召唤——”
原本准备逃离的脚步立刻停顿,费伊站在原地同样念诵起咒文:“水元素听我的召唤——”
快两年没有使用的魔咒。
……太中二了。
两个水球同时砸了过去。
黑暗中传来一声不属于West的“汪”声,两道蓝紫色的火焰先后亮起,将两人的水球一一蒸发。
视野随着水球的蒸发再度暗了下去,但那一刹的火焰也足以让他们捕捉到黑暗中的身影,那是个蓝紫色的圆球形生物,长着同样颜色的翅膀和尾巴,看着他们露出小小的虎牙。
黑暗中传来得意洋洋的“汪”的一声。
“……”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对方着实令人有些……不爽。
费伊皱起眉,他看向黑暗的另外一侧,魔力的感官能够捕捉到Kuriki的身影,他再度向那一侧移动过去,West的身影不断在两人间奔跑着。
——East呢?
在奔跑途中他忽然意识到。
那妖精应该与他有着类似的感官,黑暗对他来说不是问题,方才在来这里的路上他明明还看见了那位家妖精的身影——
“喂,你这混蛋,这边。”
话语声忽地在不远处响起,有些陌生的声音让费伊猛地抬头看向声音的来向。
——那个是……
黑暗中一点魔力的光亮伴随着剧烈的闪光一瞬间炸开!
费伊不由得后退了半步。
剧烈的闪光让他的双眼被刺痛得想要流泪,然而这时来自另一端的声响拉住了他下意识的回避。
“趁现在!”
是Kuriki的声音。
……任何长年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都无法抵抗突如其来的强光。
意识到这点的瞬间水元素就已经在半空中凝聚,另一边的黑暗里传来了Kuriki念诵魔咒的声响。
那只不知名的生物因缺失的视野而发出了一声哀鸣。
与此同时半空中凝聚的水元素瞬间被引导成为下坠的箭矢,径直刺向了声音的来向!
“嗞啦”——如同水浇在了火上。
视野渐渐恢复了宁静。
黑暗中几个微弱的光球腾了起来,费伊向那里望去,带着面具的家妖精正站在植物园中的一片空地上,他手中握着光球——身高足有190cm。
“……”
变大粉的效果似乎有些太好了。
在他脚边,那个蓝紫色的球状生物“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蹦蹦跳跳地跃进了黑暗中。
……这年头连反派生物都会卖萌,还能不能好了?
East的面具似乎也变得有些微妙。
然而他很快镇定下来,他看了眼费伊,又把目光移向了Kuriki:“这边看来不会受到植物的攻击。”他说。
随着变大粉的效果他的声音也低沉了下来,那也正是之前那个有些陌生的话语声的源头。
West的吠叫从脚边传来。
费伊冲它点点头,两人一起走向east,不过家妖精的注意力显然更多地集中在Kuriki身上,战胜了方才敌人的魔法师似乎相当开心,他跑过去和East击了一掌才又转向费伊——
“Nice combo啊,费伊。”
击掌。
费伊看着自己还有些微痛的手掌,有些愣神。
“还不能掉以轻心。”这种情况下的East远比他要冷静。
“嗯……啊,说得也是。”经他这么一说费伊才多少回过神,“这个植物园……不,整个学院都已经变得有些奇怪。”
“我、我还是明白要小心谨慎的。”Kuriki也从方才的兴奋里回过了神,“话说回来,费伊你怎么在这里?”
“……因为发觉不对劲,所以我出来找你。”临时想借口已经来不及了,费伊索性说出了真实的理由。
“唔……”这个理由让kuriki沉默了下来——“费伊,你果然有点奇怪。”
“?”
“我总觉得,以前的你不是这么积极的人才对啊。”
“……”以前我在你心底到底是什么形象啊?——费伊忍不住想这样说。
然而他没有。
话语到了一半变成了叹息。
他叹了口气,在微亮的光线中揉乱了Kuriki的头发。
“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才对吧?”
“——”Kuriki没有说话。
关于他家里的事费伊从来没有主动询问,这句突如其来的话似乎让他受到了惊吓。
他看着费伊,蓝灰色的眼睛因为光线的灰暗而看不出什么情绪。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在East把话题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是啊。”费伊很快接上了话题,“宿舍里电也停了,照明用的魔法光球也不见了……”
他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迟滞。
——各种各样的迹象都在说,校长大概发生了什么。
他根本不愿去细想这样的可能,宁愿它沉没在黑夜之中。
但这是仔细考虑眼前的状况必然会得出的结论之一,这所学院的魔力全靠校长支持,如果说学院失去了魔力供给的话……
“总之现在的学院不同寻常。”他理了理自己的情绪,又说道。
……他比他自己想象得还要焦虑和担忧校长的状况,那种情绪之前一直被他强行压下,一经触发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校长他……怎么样了?
Kuriki和East都在看着他。
费伊强行收回了心绪,回应着另外两人的目光。
“不过宿舍应该是安全的——至少就我之前看到的情况来说。”他说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Kuriki问,“继续在这里等下去吗?”
“不……虽然现在这里是安全的,但我们不能确保那些植物是不是会蔓延到这里。”East说道。
他的面具现在一片严肃,在微弱的光亮下显得有些怪异。
“先回宿舍吧。”最后还是费伊建议道,“毕竟那里现在是安全的——稍微等一下,老师们一定会很快开应对措施的。”
应对措施比想象中来得还要快。
很快他们耳边就响起了Leila老师的声音,从植物园望去能隐隐看到远处礼堂亮起了光。
还在植物园里的三人互望了一眼,加快脚步离开这里也未尝不可,不过几次尝试后他们还是决定暂且按兵不动,等待几人完全恢复魔力。
——就在这时,Leila老师的声音响了起来。
那声音不大,似乎礼堂中扩音魔法的残余顺着风飘到了这里,才让他们能够听见。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不过先听我说完。”老师说。
礼堂内一定是嘈杂一片,又被用魔法放大过的声音强行压下。
Leila老师将现在的状况一一告知。
——魔族入侵什么的、危险的结界什么的、战斗的准备什么的。
他们的日常学院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呢?
是从入侵开始时?是从他们在学院里发现魔界蝙蝠时?还是、魔法什么的。
一开始就是一场“非日常”的梦境?
Leila老师的声音还在继续,在植物园的三人都暂时没了动作,虽然并不在礼堂,但他们也体验着在礼堂的学生一样的情绪。
——最后关于教师的问题……
其他老师都还在岗位。
恕老师失踪,达梓老师和哈茜老师都状态异常。
而校长……
“被囚禁在校长室中”。
这明明是个已经可以想见的成功,却始终不是一个好接受的答案。
学校的现状足以说明很多事,只是有人依然在固执地不肯去接受
“……”
Kuriki扭头去看身边的费伊。
后者凝视着礼堂方向的黑夜,沉默,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有手掌狠狠地握紧成拳,指节泛白、没有一丝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