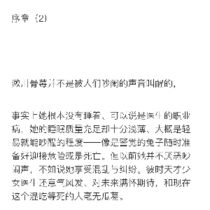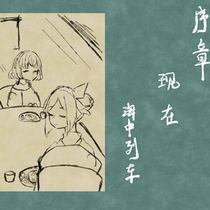
我讨厌麻烦的事情。
究竟是因为麻烦会带来麻烦而变得麻烦,还是麻烦本身就是个可恶的存在,要理清这之间的关系也太过于麻烦了。如果让这些东西都具象化成实物,然后摆在我面前叫我排序,那我一定会立即、毫不犹豫地打开窗户,连容器一起全部丢出去。
所以,在我听见对面的人自我介绍了“职业是魔方选手”后,我的视线在他与我之间游荡一个来回,然后迅速地做出了“把自己丢出这辆餐车”的选择。
“哎哎、你稍等一下…!”
是我起身太过迅速了吗,篠原一瞬因为讶异微微睁大了眼——尽管他马上就恢复了先前的模样,笑容满面地试图挽留。
真是耀眼的人呢,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选择与我这样明显冒着「生人勿近」的气场的家伙搭话。不过,若是直说出来我的疑惑,“既然被称作超高校级就一定有着耀眼之处吧”,总觉得会被这样的客套话打发过去。
不过,事实上,篠原向我搭话,多半就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因为看见你不断在平板上写着什么,心想也许与我一样是因为短期记忆障碍才总是记录日常”。只可惜,我只是单纯为了进行试睡员的工作而已,会早早来到餐车也是为此。
眼下,我正打算头也不回的迅速离席。预计的逃跑路线上却突然插入了障碍,一头乱发的健壮女性险些与我相撞。我本能地向后一退,于是就此错失了最好的离开的机会。
仅仅相隔几秒之差,篠原的追问紧接着就缠了上来:
“莫非小日花里……与魔方有什么过节吗?还是说,是对「玩魔方的人」有所不满?”
“……”
唉。原本倒也没有,现在却是有了。
“我说你啊——呃、你……”
说来先前自我介绍的时候,篠原似乎不多不少刚好比我高了一级。意识到这点,我瞬时收住了脱口而出的呵斥。……真是够麻烦的。
但规矩还是得尽量遵守。
“篠……唔,前、前辈?……前辈…嗯,前辈啊……”是这么念的来着吗?
不清楚呢,前辈这个音节,对于不常去学校、工作上也没有这类存在的我实在太过陌生了。就好比有夹心的硬糖一样,接触的分明是坚硬的面,咬下去却又软绵绵的,说不出是哪里不对劲。
于是,我忍不住多重复了几遍确认读音,细细回味这颗糖的残留在喉间的余韵。
“……篠原、前辈?”
“哈哈哈哈,对敬语苦手的话,不用为难自己也可以哦?小日花里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称呼我好了。”
“帮大忙了。那你也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吧。”
挤在胸腔里的不适感一扫而空,果然还是习惯这样的说话方式呢。一旁路过的服务生向我投来了奇怪的视线。给好好工作啊,如果还想在年末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的话。
“哈哈哈,还真是不客气呢小日花里…啊,不要再瞪我了。不喜欢被直接称呼名字是吧?我知道了、知道了,小柳沢。”
讨厌的杂音终于消失了,我向他丢去一个对他的理解表示感谢的眼神。至于他有没有领会到,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话在这里暂时划下了休止的记号。是离开的好机会。我正准备站起,却又有什么、好像是一团黑色的东西飞快地跳到了脚边,堵住了我的去路。
“……掉到下面去了。”衣着古怪的少女慢吞吞从地上爬起来,一手捧着一只柠檬,轻轻掸去灰尘,然后自顾自地向着出口的方向走掉了。
“那么,继续刚才的话题吧。”
篠原微笑着,又一次用言语将我绑回了座位上。不知是不是刚才柠檬少女的缘故,篠原有意无意地握紧了手中的魔方。
“自报家门之后是这种反应,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坦白说,有那么一点被打击到了呢……”
“我也只是尽量避免会招惹麻烦的人而已。”
——虽说现在也已经够麻烦的了。
大概是正式的用餐时间已经结束的关系,此时餐车内的乘客有愈来愈少的趋势,但留下的人、游荡的人却也不是少数。如果没记错的话,左后方的那位看画的大叔至少已经在这个车厢里踱了四个来回了……
“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引起你的不快,即使如此也要听下去吗?”
实在是不想重复「站起再坐下」这个过程第三次,我招手叫来服务生添了些茶水。举起茶杯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也不知道是哪一点逗乐了他,篠原的笑意比之前更甚了。
“啊呀,都到这种程度了才来问这种问题吗。小柳沢还真是奇怪呵……是我要问的,请不必顾虑地说下去吧。”
“……”
也罢。这样一来,如果生气了的话,也不会再找过来了吧。虽然多少有些失礼,但毕竟是对方要求的,我如他所愿表明了我真正的想法。
“魔方这种东西,在我看来是没事找事的存在。”
“……。”
预料之中的,篠原并没有像先前一样客套地应声、或是马上回话。我察觉到他的指腹轻轻摩挲着魔方的表面…嘛,也算是正常反应吧。
“打乱了色块,再花时间拼回来,这件事本身就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
我继续阐述着观点,将篠原的沉默当作容许,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着这位超高校级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想保留每一个面都是同色的模样的话,一开始不打乱不就行了。想要让颜色变得相同,比起花时间研究怎么转回来,直接用颜料重新刷一层不是更简便吗?——换做是我的话一定会这么做的。”
这是真的,小时候父亲曾经沉迷了一段时间的魔方。屡次想要推荐给我,却都被我因为嫌麻烦而毫不留情地用颜料强行完成了谜题。
“我是理解有觉得这样有趣、把它当成爱好的人,因此,也不会特意去向对方灌输强制让人赞同我的想法……诸如此类的。只是,以此为乐的人,多半是十分、特别、尤其擅长招惹麻烦的家伙,或者根本就是麻烦的本源……
“而你现在,已经完全证明了我的猜想。”
=====
混了个关于npc离开餐车的时间的线索……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参与了主线。(ノ)'ω`(ヾ)不算的话就纯当是跟魔方小哥聊个天吧(靠)谢谢fla借角色给我!!
hkr算是想的多说的少的类型,于是试着用了第一人称。后面让她说了这么多话感觉要累死了XXX
写得匆匆忙忙质量也比较差……能读完真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