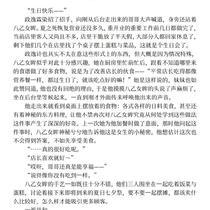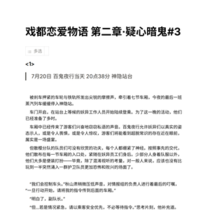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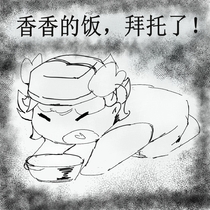








“一份刨冰,谢谢。”穿着深蓝色浴衣的男子走上前,站在刨冰摊点餐,“优奈小姐,你呢?”
“…点完自己那一份才想起我来吗?蜘下。”名为优奈的女子哼笑,踌躇过后也跟着点了一份,“付钱的事就麻烦你了~”
“来客人们,两位的一份蓝莓刨冰,一份草莓刨冰——。” 蜘下纪生付了钱,拿着刨冰朝着朝地优奈在的地方走去,这时的她站在祭典面具的售卖摊位前,指了指类似蜘蛛的面具问他:不觉得和你本人一模一样吗?蜘下纪生挑眉不语,只是把手里的刨冰递到人手里就大步往前走,朝地优奈就着吃上一口,酸酸的。
走在前面的蜘下纪生胡乱走着,手里的刚买到的蓝莓刨冰已经三两下就干净,换上了甜腻的苹果糖,拜托摊位老板切开来,放进口中咬的嘎嘣脆。实际上自己瞄了一眼优奈小姐所说的面具,第一反应是丑,真的原本长那样吗,蜘下纪生第一次对自己原貌犯难。第二口苹果切片糖咬下才发觉自己好像小孩子赌气把优奈小姐扔在了后头,犯错的小孩都知道会站在原地等家长,可他是叛逆小孩。第三口咬下时只感觉肩膀被人拍了拍,蜘下纪生注意到动静转头——后脑勺就被人来了一个爆栗。
“叛逆小孩真的只顾着往前走呢。”朝地优奈收回手,对着人笑笑,仿佛刚刚爆栗面前人不是她,上手帮忙捋捋被打得翘起的发。
“……对不起。”做错事的小孩闷声道歉着,解下了红色绑绳,上手随意梳梳,在人面前面无表情状快速绑好。朝地优奈鼓起掌,走上几步才出声夸赞道:“其实披发……还的确很适合你们妖异呢。”
「哎呀?你很适合披着长发呢,小蜘蛛。」
「……没兴趣。别打扰我。」
蜘下纪生眼皮跳动,过往的回忆犹如水流涌上,过了几秒迈步跟上她步伐,与她肩并肩才回应:“我不适合。我更喜欢现在这样。”朝地优奈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位男同事的头发解开了会如何呢?会不会像蜘蛛吐出白丝那般一样长,一样多?
蜘蛛手里的苹果糖最后由着和人类一起分食了,最后几块还是入了妖异口里,被以太甜了,你是怎么吃得下这种理由拒绝进食下去。两人之间渐渐开始没有任何的话题,就这么肩并肩走着,路过感兴趣的摊位上前玩玩,这自然是男同事付的钱。
“烟火大会要开始啦!”
“居然都快是这个时间了,我们快去山顶!”
过往的人察觉到什么,步伐都加快了不少,渐渐地两人从普通走路变成了快走,最后变成在人群里被推搡着走。蜘下纪生后悔认命闭眼,好麻烦,他进来之前本来看了地图的,没想到走的这条路居然是通山顶去的。后背被人大推一把,蜘下纪生咬牙稳住身形,烟火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值得你推我我推你吗!人类还真是力气都不收,只顾着烟火大会了根本不顾死活。
“优奈!抓紧我!”蜘下纪生对目前混乱情况咋舌,小声道了一句失礼,顾不上什么敬语了,他现在脑内只有一个想法——握紧她的手。察觉到她所处的位置长手一伸就握紧了,担心会不稳松开扯下发丝施法将其缠绕到两人手腕。朝地优奈对此感到惊奇,还没出声问就见自己被拉到人怀里,可见的浅色蛛丝围起两人周围,接着是眼前一片黑色,睫毛扇动,覆上的触感是冰冷的。朝地优奈很快想到——也许是蜘下纪生的手掌心。
光亮起来了,朝地优奈不适应地眨眼,妖异的法术不知何时结束了,浅色的蛛丝有少许掉落在她手心,风一吹就立马消失地无影无踪——连同刚才缠绕两人的蛛丝也是。朝地优奈张望,很宽阔的地,还有适宜的风,往前几步,山脚下灯火亮堂的夏日祭会都能够看完全貌。朝地优奈将吹乱的黑色发丝别至耳后:“怎么发现这里的?”
除去上面所说的,朝地优奈才发觉这里一个人影都没有,妖异的法术就是好用呢,遂看向一旁站着不语的男同事,男同事——蜘下纪生盯着山脚的夏日祭会很久了,朝地优奈观察到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保持这样,保持的手插进浴衣袖子里,仍由风吹起他的发,他的衣服,即便是被弄乱了也无动于衷。朝地优奈也是第一次观察起这位只在门口发传单男同事,那双眼眸似乎在思念什么,她发觉到:这位妖异男同事可能不是第一次来。一定没错,他深知脚下这处好位置——看烟火会特别漂亮,正如流沢山山顶。朝地优奈再次抬眸,却和蜘下纪生对上眼。
这时,烟花冲上了夜空,掩盖住他的声音。朝地优奈眯眼想识别他的唇语,但烟火的声音太大,朝地优奈放弃了,她可不是有这么专注力的家伙,反正都是同事,早晚都能问出来他在烟火前究竟说了什么。
现在不如和人好好的欣赏这片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