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昂先生曾經說過,對於妖力的感受性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只要時候到了就會明白了。
芽以為自己或許永遠都沒有機會體會這麼件事情--
與雪女那帶有清爽的寒意不同,那有如被某種生物盯著的強大魄力就那麼突然地刺進自己胸口,雪女半妖因為身體的不適而曲下身,下一秒卻感受到勁風擦過自己裸露的項頸後側。
鈴鐺聲,這是在那瞬間除了風聲之外,留在了芽耳中的聲音。
「甚麼?」強風吹得她重心不穩,芽幾乎是在同時跌坐在地上,直往眼前的道路上撞去的是一道黑白相參的影子,直到風停了,少女才終於看清楚眼前的人...或者該說是妖。
是妖,而不是半妖,擁有著與昂一般敏銳的感受力,芽幾乎可以這麼肯定。
那種強勁而霸道的妖力,跟半妖完全不一樣。
「嘖...原來不是剛剛那傢伙...」似乎在追著甚麼,眼前有著少年外表的妖,一頭銀白色的短髮,耳前的鬢髮留長直至胸前,左右各別上一顆黑灰色毛球,與髮同色的狐狸大耳在頭上輕顫著,「不過你的味道也好難聞...雪女半妖啊...」黃澄的圓眼盯著芽,看上去滿是不屑。
儘管如此,芽依舊沒有別開視線,她抱著剛從書店買回來的書,小心翼翼地重新站起身。
少年披著黑色袍子,胸前垂掛著一顆拳頭大的鈴鐺,看來剛剛聽到的聲音就來自於此。
讓芽忍不住一直留心的,是對方身後的數條狐狸尾巴,蓬鬆的樣子讓她老有種衝動想伸手去摸... 不過,現在這狀況,恐怕對方是怎麼樣都不會答應這件事情的吧。
深吸了口氣,芽小心翼翼地開口:「那個,請問,您是妖異吧?」
只距離幾步之遙的少年不知道在想些甚麼,冷哼了一聲之後露出了譏諷的笑容:「要不然?我看起來像是人類那種噁心的生物嗎?」
看來還是個對人類很有偏見的妖異先生...
「我想知道您是什麼妖異...您看,您也已經知道我是雪女半妖了,所以...告訴我吧?」她繼續謹慎地開口,內心的緊張感令芽忍不住捏緊了手中的包裹。
「妳眼睛是長著裝飾的嗎?而且知道了要做甚麼?反正妳等會就要死了。」
「不會死的。我會誠心的拜託您別殺我的。」
「妳說甚麼?憑甚麼本大爺要聽妳這小半妖的?」
不知道是否是刺激到了妖異,少年猛地逼近了芽,纖細卻十分有利的手扣住了芽的下巴,將其拉到自己面前,兩人身高差不多,少年的眼睛就這麼直勾勾地撞進芽的眼底。
「您不是聽,是完成我的請求...不過在那之前...我還是想知道您是甚麼樣的妖異...我對妖異一無所知,我真的很想知道...」芽的圓臉蛋被捏得堆起肉團來,一開口說話就像是魚嘴般開開闔闔,就連語調也變得奇怪起來。
「拜託您告訴我吧?」不是不害怕...但是就像現在自身的存在一般,如果不去面對,那她又該如何自處?
【TBC】
==========================
因為聯絡不上荔枝人,所以臨時自己動手幫打了這張卡,沒有詢問過任何詳細,有可能OOC,只能先說聲抱歉了(合掌)



一个吻,你就知道我所有沉默的心事。
-聂鲁达
深绿薄绿的小灌木丛半掩着门前的小木牌。木牌上的刻字因为年代久远,受风化影响已经变得有些过浅,几乎看不出上面原本写着“大森屋”的字样。也许是前代哪位主人随手写下插在庭院附近,字迹虽然颇有古趣,却明显漫不经心,被怠慢打理也显示了这并不是什么正经招牌。除了这三个字也不再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讯息,以至于大家也不再探寻究竟木牌出现的原因,只是由得它就那样留在原处,隐隐透露出年代久远。
森美月拿起放在一边的布巾,擦了擦手中因为茶水溅出变得有点微湿的托盘。她刚刚才为最后一桌进门的客人送上茶点,眼下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于是她脸上带着得意志满的表情靠在了柜台边,看着门外的小女儿折下了几朵小花蕾。飞鸟像是感应到母亲的视线,抬起头来,对母亲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美月忍不住笑意,对飞鸟扮了个鬼脸,天生有点往下长的眉毛此刻扬了起来,笑意在嘴角跳动,整个人显得轻松愉快,像是忙碌反而让她十分享受。
“卯三郎你看,如果每天都那么多客人,那该多好啊。”
被称呼为卯三郎的青年从账簿间抬起头来,瞥了一眼嫂嫂,又往店子里嗡嗡低语的客人们看了看,手中的计算并没有停下,只是敷衍地“嗯哼”了一声,就又低下头继续算账。
得不到让人满意的答案,美月用手中的托盘轻拍了他一下,用的力气比她想象中大了一些。森卯三郎捏着钢笔的手被她拍得一歪,笔下的字迹就那样斜飞了出去,在整洁账簿上留下了一条短短的划痕。
卯三郎放下了笔,抬头对她瞇了瞇眼。
“哎呀,”始作俑者却并没有悔意,她笑着对他合了合掌,说,“对不起。”
卯三郎作出要用尽全力怒瞪她的样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做出凶恶的表情。相反,他只是看着她良久,柔软的视线从头顶落到她眼角笑出来的细纹,到开怀的嘴边,最后回到眼睛。他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钢笔,说:“每天都那么多收入是不错。”
浅色的瞳仁定在了对方的脸上,美月看着那双眼睛里自己的身影,一时语塞。她很快移开了视线,伸手摸了摸耳鬓的发夹,把散落出来的头发别回耳后。手刚好刚好把他的视线挡开。美月不着痕迹地移开了一步,浅笑着转身看向茶屋的顾客。然后,像是要把什么话扼杀在喉咙里,她把一只手放在胸前,感受着手下因为叹气而来的轻微起伏。
“我们大森屋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客人了,”她轻声说,似乎并不在意卯三郎的回应,只有手指轻轻敲着手上的托盘,“这两年来一直都一团乱的,总算是重新振作了起来。”
“……是呀。”卯三郎看着她的侧面一阵,话里有种微妙的,如释重负的安心,他抿了抿嘴,重新拿起了放在桌上的笔,继续未完的计算,“我算了一下,最近生意慢慢重上轨道了,我们可以考虑多雇几个人帮忙。”
“如果白能更能干一点的话,可以少雇一个,”他的声音不算响,但是足以让站在不远处的小猫又听得清清楚楚。被点名的小姑娘吓得肩膀一缩,悄悄扭过头看了卯三郎一眼,晶亮深润的眼睛在他身上溜了一圈,几乎是马上就把求救的眼神投往美月。
“对不起………”白小小的呼声盛着深深的歉意,她举着手中茶盘子挡住脸庞,一张巴掌脸只露出一双大眼睛,尾巴和耳朵都忠实反映着主人的心情,丧气地垂了下来。卯三郎不为所动,并没有抬头,钢笔不断在纸面上划出沙沙的声音。美月斜睇了一眼,看着他低头漏出的小小笑意,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她咬着下唇止住笑意,往前走了几步,伸手摸了摸猫又低下的头,手指刚好拂过白色的耳朵。“小傻瓜。”耳朵的手感实在太好,本来打算收手的美月忍不住又摸了一下,继续说,“你只要慢慢学习就好,不过呀。”
她对白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打碎的杯子在你工资里扣。”
“呜哇老板娘——”白叫苦不迭,伸手按住了头顶的耳朵,有些委屈地噘起了嘴。“我会小心的啦……”
美月看着白,只觉她现在简直浑身都写着低落二字,摇摇头,好不容易继续摆着严肃的表情,继续说:“所以工作时要……?”
“小心……”对方有点尴尬地回答,但是小姑娘很快又振作起来,过分精神的尾巴在短裙後晃了晃,竖了起来,“放心吧老板娘,我不会再打破杯子的了!”
闪闪发亮的眼神似乎昭示着她的决心,为了强调,白还捏紧了拳头,耳朵尾巴都激动得动了动。美月抬起了一边眉毛,说:“真的吗?”
“真的!”
“那我就拭目——”她笑着点点头回答,话却无法说完。
“哎,晦气。”粗粝的男声在门边响起。森美月循着声音回过头,看着明亮阳光下的人。大森屋大多做附近居民的生意,来去都是差不多的几位客人。正如附近的居民对这里大多相当熟悉,几乎闭上眼就能描绘出它的模样一样,美月对客人的脸也记得相当清楚。眼前的确不是熟悉的客人,看起来是为了躲避午后最毒辣的太阳而来的生客。
她放下手中捏得久了的盘子,敛袖迎了上去。客人往她的方向皱起了脸,从鼻子哼出一句话:“我不要里面,外面。”
美月轻蹙起眉毛,她往后瞄了一眼,正好看见白晃动的长尾,心下了然。卯三郎放下了笔,站了起来,往柜台外走了几步,来到她的身边。他没有举起手,也没有做什么大动作,只是往美月侧了侧身,把那人和她稍微隔了开来。只是美月抬起头,往柜台看了一眼,示意他回到座位上。卯三郎有些迟疑地踏开一步,下巴紧绷的线条显得并不是很情愿。
她很快转过了身,脸上漾开一个微笑,伸出手往店外一指,把靠在门边的客人引向茶屋大开的门前。
现在正是帝都最好的时候。这里的晚春与别处远远不同,别处的樱花可能尚且留恋枝头,姹紫嫣红开成一片灿烂不绝的花海。这条小巷的花却都是些急性子,薄樱色的花瓣早早就已经谢满了一地。一簇簇的紫阳花蓄势待发,像是随时都要喷薄而出,在尚未来临的梅雨季节前展现自己的身姿。
他们掀起门前落下的布帘,走到屋前。阳光下的茶屋看起来有点像半途而废的长屋,低矮的平房前立着几把遮阳的大伞,下面是几张矮桌,让客人歇脚饮食。眼下就有好几位客人坐在深红色的座垫上,低声笑着喁喁细语。
美月快走几步,走到男人的身前,把他引领到伞下。她双手叠在身前,等待对方落座,然后才柔声开口:“请问您要点什么吗?”
“茶和厥饼。”等了一阵,对方才开口,粗硬的声音带点刺耳的沙声,嘴角往下拉出了深深的法令纹。他往室内看了一眼,继续说,“你送过来,里面那个,不能碰。”
“我明白了。”美月点点头,脸上挂着无懈可击的微笑。她对客人稍躬身致礼,踏着轻快麻利的脚步回到屋内开始倒茶准备。
卯三郎抬起了头,对她投来讯问的眼神。她看了白一眼,确认她正在忙别的地方才稍微举起一只手指,指了指猫又半妖,然后摆摆手示意。卯三郎难得摆出了不乐意的表情,摇摇头。她叹了口气,把茶和厥饼摆到托盘之上。
虽然曾经听说三十几年的百年法案让妖怪和人类的关系稍缓,但是就像搬家到别的地方,就算自己再努力,也不会摆脱曾经来自别的世界的标签。她的年龄让她无法经历两边明显角力的日子,但是她还记得小时候邻居先生总是被叫成“那个原来长翅膀的”的事情。结果虚伪的和平也维持不了多久,天狐暗杀事件就让人类和妖怪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她抿了抿嘴唇,把茶点放在客人的身旁。
就在她想转身离开的时候,却被一只手止住了脚步——那男人伸手捉住了她的衣袖。她一愣,轻轻抽回自己的羽织衣袖,问:“怎么了吗,客人?”
对方下巴往店里点了点,压低了声音,说:“你们被缠上了吗?”
“什么?”她有点疑惑。
“里面那个,你们是被缠上了吗?”男人又再说了一遍,大睁着眼睛。布满了血丝的眼白和不管不顾的劲头让他看起来有几分疯狂。
“你是说我们家的招待吗?”美月往后稍微退了一步,离对方远了一些,“也不算是。”
“我可以帮你们带走它,”男人把手伸进前襟,握住了什么,他收紧肩膀,继续说,“我是除魔师,还有门道可以把它们卖给政——”
“客人,”美月打断了他的话,她伸出了一只手,轻轻按着对方的手臂,“我们的茶更适合在温热的时候品尝,您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男人抬头看着她的微笑,眼神偏离了一下,说:“越来越多人表现出不像人类的特征了。这是会传染的。”
“迟早我们都会变成那种人不人鬼不——”他大力挥动着手臂比划。
美月还在微笑,眼睛却已经冷了下来,她背对屋内往前踏了一步,稍微弯腰,屋内看起来就只觉得她是在和对方交谈。她笑了笑,伸手握住男人的双手,那男人一愣,抬头看着她的嘴唇张张合合,柔声说话:“客人,小店经营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有很多事得烦心。”
“虽然小白是个不错的招待,我却也没有闲暇去管太多外面的传闻。”她放开了一只手,伸手拿起放在身侧的茶杯,轻轻放到对方的掌中,“要是打起来了,那可就伤脑筋极了。啊,我看您不是这边人,您要是喜欢,就请您喝着这杯茶,我来给您说说这周边合适游览的地方。”
“我对我们大森屋的茶可是有相当自信,巡捕所的先生们闲暇的时候也常来休息,喝杯茶之后回去继续办公呢。” 她站直了身体,继续说,“所以呀,要是您还喜欢,还请不要客气。”
那男人看了看手中的茶杯,又看了看她,脸上泛起似懂非懂的表情。他脸色一变,把手中的温茶一饮而尽。站起了身,似是想说什么。
“哦小美月,我回来了。”明朗的声音响起,高大的身影随后才在森美月的身旁落下。她抬起头,正好对上仓松野性难驯的脸孔。他对她咧嘴笑了笑,把她往旁边拉了拉,自顾自压低声音对她说话。
“这是?”他说,声音依旧如雷般隆隆作响。
“客人。”美月回答,她皱了皱眉,继续说,“仓松先生,请你去照看一下飞鸟,好吗?”
仓松一顿,又看了那男人一眼,咧嘴露出笑容,明显的犬齿让人有点心惊。他侧侧头,转身走向屋内。
那男人张目结舌看着他把甩到身前的长辫别回身后,举起颤抖的手指往美月指了指。
“客人?”她说,笑意依然没有从她的脸上离开。
对方没有说话,只是避忌地往仓松远去的方向看了一眼,从怀里摔下茶钱,就拂袖离去。
美月看着对方远去,哼了一声,扬声对屋内喊了一句:“小白,把我的扫帚拿来。”
白在门边应了一声,却是卯三郎很快就把扫帚拿到她手边。美月对他挥挥手,让他回去继续工作,然后低头把零钱扫到一边,不再理会。只是对方没有动,身上散着隐隐的怒意。
“刚刚那男人是怎么了?”他说,年轻的脸上有点不易见的焦急,说完之后就不再说话,只是全心全意地看着她,等待她的回答。
美月张了张嘴,没有说话。身边的客人哧了一声,她就像得到救兵一样扭头看向对方,只见是个看起来柔弱文雅的少爷,身边站着位管家。他的脸上带着过分快活的笑容,对他们两人眨眨眼。
“抱歉抱歉,”他比划一下,修长的手指在嘴前比了个安静的手势,“你们继续,别管我。”
趁着他一打岔,卯三郎似乎惊觉到什么,拉远了点距离,张了张嘴。
“我说美月,”仓松从屋后转出,“你说让我照看飞鸟,飞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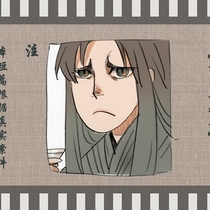

难产了蛮久的文总算发出来了,希望没有太OOC,如果有真的很抱歉;;
本来想了个聪明的逃脱方法,权衡一下放弃了,还是吃鳖吧x
字数大约4500
---------------------
常言有道: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鸡汤是激励人去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付诸实践的东西,除此之外,它也就只是个可望不可即的伟大愿想了。所以,绝不能仅仅把理想之言挂在嘴边,内心却依然惨遭禁锢,事实证明,这样做还不如一碗山参鸡汤来得更令人舒畅。
于是,在睡足整整一上午之后,江古田道尔被逼无奈,只好选择翘课:他睡意全无,顺带一想下午的授课,绝望,绝望,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事了。
江古田有个怪癖。他讨厌压抑,尤其是课堂和考试这样的气氛,这会让他坐立难安,就像幽闭恐惧症患者被关进狭小的黑暗洞穴中那样。睡过去便罢,倘若清醒着,那可以说是比一个人待在太平间还可怕——不过事实上他并不惧怕死人。总而言之,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他斟酌许久,最后毅然决然地踏上征途。
一般情况下,午休时间里很少有老师在走廊上巡视,并且这期间学生可以自由出入校门。换言之,只要一路上碰不到老师,或者更确切的说,碰不到佐仓凛这样好几次抓了他现行老师,“密室逃脱”就成功了。
——然后就是规划一下路线。 他在脑海里打开这座破旧教学楼的地图,想象着将所有教师和其他员工可能出现的场所进行标记,迅速找到了一条通往伊甸园之路。
江古田爬上铁丝网,从F班楼上的天台,校园中不起眼的肮脏角落,环视了一圈对面富丽堂皇的敞亮建筑群。
那种地方气氛会更压抑的。他趴在铁丝网上想着。
鬼才会去啦,这种悠闲又自由的生活放着不过才是笨蛋。
身后因年久失修而摇摇欲坠的天台门吱呀一声打开,来者快速踱步到天台边缘,用手一下子扣住铁丝网。
“哟,江古田同学也来这看风景吗?”
铁丝网的振动传到了江古田身上,他顿时有一种悬崖走钢丝般的不安全感,于是他便落回地上,回答道:“算是吧。那是那边的风景不属于我们,看着也觉得无趣。”
“我们可以抢过来啊!”
“免了吧,就算胜率有99%我也不会同意的,1%的补习也是会死人的,没错,会死人的。”江古田一脸不情愿地说道。他才不在意设施和同学们的生活状况如何,什么都不比自己快乐重要。
“也对,不管其他人怎么样,输了的话代表的分数一定会归零嘛……”对方挠头,笑了笑。
是啊,我可没有那么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江古田在心里牢骚。不过这个时间点星宿会来天台,不是上来吹风就是闲得无聊,那么……
“星宿,你下午打算翘课的吧?”他打量对方一会儿,唐突地说。
星宿立即露出“答对了”的表情,四下看了看周围,还好没有其他人。江古田同学也不像是会打小报告的人。他衡量了一下,说:“是这样的……为什么突然……?”
“来的正是时候。”江古田兴致高昂起来,拍了拍星宿,“我就觉得我们一定志同道合,走吧,一起去商业街那边打打小钢珠如何?”
“噢好好好——”
的确是中了他的下怀。
“那么逃课同盟现在开始行动——!!”
星宿兴奋得一跃而起,颇像踏上春游旅途的小孩子。逃课——在这之后可以做他感兴趣的事情,这样的人生才算洋溢着光辉。一上午的物化生加古典文学,见鬼去吧!
“喂喂,逃课同盟算什么啊……罢了,以后有人一起逃课一起玩有趣得多了,到处呼朋引伴还有招到不良小打一架的风险。”
跟单纯的人一起行动各种意义上也很方便。
脑海中浮现出麻烦到死的小说家的脸,江古田愤愤地咬了咬牙,抬手扣住铁丝网狠狠攥了攥。
“好像很顺利耶!”
"嘘——星宿你声音太大了。"
"抱歉!"
"都说了小点声——!!"
"明明江古田同学你很大声。"
"……抱歉。"
江古田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星宿不停地在一旁搭话,他的大脑总在随着话起话落有节奏地嗡嗡作响。不过这并不是责备,江古田现在很兴奋:现在终于有个喜欢闹腾的家伙和他一起意气相投地做事了。
虽然对方看上去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
不……人不可貌相。江古田告诫自己。就算初见面感觉一本正经的小说家,切开来竟然是那样不知好歹的搅事狂。
"听着星宿,你我都是开学被抓了好几次的常犯,想必那几个我们看着特眼熟的老师见我们这时候到处跑必定会起疑。"
江古田把星宿拽到角落,还不忘站在破旧走廊上唯一一个盆栽后以作掩护,贴近对方的耳朵小声说道。
"所以我们要像特务一样行动是吗?"星宿也依着神秘兮兮的气氛,拿手挡在嘴边,接着说。
"没错。你知道要躲谁吗?"
"不是背景板的有人设的老师。"
"正解。除此之外还有。"
"诶~谁啊,想不到了……"星宿认真地绞尽脑汁想了一会儿,最后耷下脑袋。
江古田揽着对方的肩膀,夸张地好像寻宝队发现宝藏却只想和朋友两人独吞的队员一般,认真地黑着脸小声说:"みな(这里想说源,みなもと)……"
"道尔,你在这干什么呢?充满谜团与浪漫的侦探游戏?"
后方传来清泠的女声,只不过是在搭话,却完全盖过了江古田窸窸窣窣的低语。同时一双手伸出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没干什么……等等星宿你叫什么啊!!"
只不过拍成了星宿。
"彼、彼方,要被你吓死了……"
已经被人发现,无奈,江古田拽着星宿从花盆后面走出来,站到走廊中间,回拍着自己的好友,天上彼方。
"不过星宿你刚才声音太……"
太大了。
江古田本来想这么说。他虽然刚刚的确慌了一下子,但姑且还是侥幸地蒙蔽自己,一定不会惊到其他人的。
这一层没有F班或E班的教室,运气好的话只有他们三个,运气不好的话……
距离江古田他们十米外的教室骚动了一下,好像一首优美乐曲的节拍被不合时宜的突兀鼓点扰乱。随后,教室的木门吱呀一声打开,更准确的说,似乎被不得了的气场所弹开——
"我就想谁在外面大吵大叫,果然是道尔。"
给学生补课中的物理老师,佐仓凛走了出来。她看上去没有生气,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也与素日不尽相同,然而周围的空气却莫名其妙地开始扭曲起来,好似达利的那副画儿。
"哈?!不是我啊,明明是……"
江古田开始反驳,像往常一样,而他这次没有耍嘴皮,说的是切切实实的真话。
"哦~是吗。"佐仓也像往常一样,把江古田充满“诚意”的辩驳当做耳旁风,“说起来道尔,还有一刻钟午休结束,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是又想逃学了吧?”
“哈哈,怎么会呢,我只是……”
“只是?”
“只是……”
江古田编不出来了。
来这做实验?开玩笑呢,他说想好好学习连笨蛋砂糖都不会信;想找老师?别了,肯定二话不说就要被拉进去开小灶;想随便逛逛?你为什么会在教学楼里散步啊!
如果对面不是佐仓,江古田眨眨眼睛就能把这事糊弄过去,可对方偏偏是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恶魔……
"道尔,就算你追我到这里,我也不能答应。"
"哈……?彼方你……?"
彼方将江古田搭在肩膀上的手拿下来,趁机冲他使了个颜色:总之先应付过去。
"就像怪盗和侦探一辈子都是宿敌,对我来说你也只是搭档和不懂得魔术的梦幻总是拆台的对手而已啊。"
虽然很感谢你但总觉得好不爽。江古田拉这脸压了压眉毛,气鼓鼓地用眼神回复道。
佐仓看着一唱一和简直可以搭台作戏的两人,摇头叹了口气。"我说道尔,自己是个废柴就不要高攀求得天鹅肉了,人家女孩子可是……"她顿了顿,似乎没有面前学生的印象,又换了种含糊不清的说法。"……总之看上去很中规中矩,你配不上的。"
"喂不记得人家就不要强行用这个损我啊!"
"佐仓老师说的很有道理。道尔虽然很聪明,但天天像社会青年一样游荡,将来是会被社会的浪潮吞没的。跟道尔交往就像是在悬崖边和恶魔跳舞,一不小心就会堕落呢。"
——彼方你也别借着这个黑我啊!!
江古田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多说一句被佐仓发现逃学就遭了。补课地狱,绝对不要。他看着彼方背后才真正藏着小恶魔的笑脸,哼了一声将手狠狠插进衣兜。
"好了好了,你们快回去准备上课吧。就算是青春也别太荒废时间。"
佐仓恢复到平常讲课的声调,摆摆手返回教室。
见到瘟神终于走了,江古田后退几步,靠在墙上深深地抒了一口气,释然到快要将前胸贴向后背。
"真过分啊,彼方。"
"我可是帮了你啊。只要能到达阳光普照的大地,乘坐什么交通工具都无所谓,不是吗?"
面对友人的抱怨,彼方不以为意,反而愉快地笑了。
"净占我便宜,罢了。时间不多了,我们走吧星宿?"
没有人回答。江古田看了看彼方,后者摊手表示同样不明所以。
"…………星宿——?!"
"佐仓老师,刚刚外面发生了什么吗?"
佐仓回到教室,在铺着榻榻米的教室中席地而坐的源青海问道。
"没什么,道尔在向哪个女生告白失败了吧。"
"道尔?向别人告白?"源嗅到了把柄的味道,摊开摆在手边的记事本,"那女生是谁……啊……佐仓老师可能不记得……她的外貌是怎样的?"
"粉色长发,戴着圆眼镜的孩子。"
"佐仓老师,您被他们骗了。我打赌他们只是在演戏。"听罢,他严肃地斩钉截铁道。
"此话怎讲?"
"以我对道尔的了解……他们只是在制造事端上狼狈为奸的同伙而已,告白的离奇程度不亚于地球反转。"源把笔记向前翻了几页,默读一遍后,把道尔和彼方极力掩盖的东西毫不留情地宣告出来:
"您现在去校门比较好,道尔只是想逃学罢了。"
还有五分钟。
江古田在楼梯上疯狂跑着,扶住油漆已经斑驳的扶手一路向下冲。
他刚刚以最快的速度跑遍了楼上所有没有教师的屋子,同样也绕着天台仔细查看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哪里都不见星宿的踪影。
该死,关键时刻这家伙跑到哪里去了。
星宿不是无义之徒,他自己跑掉了这个选项可以排除,那么只可能去了这栋教学楼一层的某处。
话说他为什么突然跑掉啊!真的去躲凛姐姐了?不……在我跟彼方说话的时候他就已经不见了,我没有告诉过他需要躲学生…………
等下。
道尔突然想到了什么,风一般地朝着同一层的储物室飞奔。
——这个笨蛋!!绝对是把みな(源的前两个音)听成了みんな(大家)!!
——能在那么短时间内从走廊消失,结合这一层的房间布局以及星宿的速度,只能是躲在楼梯旁边还不上锁的那里了。
江古田仿佛要崩溃一般拉开储物室的门,在那里他看到了星宿,后者正举着扫把,仿佛时刻警戒着的士兵,还挂着颇为认真的神情。
"大哥!外面安全了吗!"
江古田不忍心戳破星宿的这份迷之纯真,只是淡淡地说:"外面安全了,时间不安全了。接下来的一百二十秒,往死里跑。"
说罢,他便拉起星宿拼尽全力用最大速率迈开脚步,后者被吓了一跳,直到被拉出储物室才后知后觉地一个全垒打把扫把扔进屋子。
江古田觉得自己这学期都没这么拼命过,虽然这学期才刚刚开始。什么障碍,什么源青海,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事只有一个——不要上课,要自由!
"江古田同学……等等……我快跟不上了。"
速度差了一大截,又被对方拼命拉着,星宿忍住手腕快要脱臼的疼痛气喘吁吁地说着。
"离校门只有二十米了,最后十秒也不要放弃啊!"
"可是……前面好像有人……"
"嗯?"一直在扭头跟星宿说话,江古田没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前方。待他看清前方的人影,慌张地刹住了步子。
惯性没有让星宿的速度减下去,而是拉着他狠狠撞在已经稳妥停下的江古田身上。江古田重心一偏,两个人一起扑倒在距校门十米远的地方。
"既然你们那么心急地趴下拜师,那么恭敬不如从命了。"校门前,真正的恶魔已静候多时,她仰起脸笑道,"江古田道尔同学,星宿五玉同学,物理的地狱欢迎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