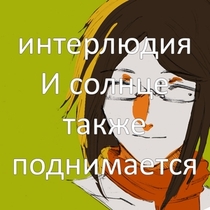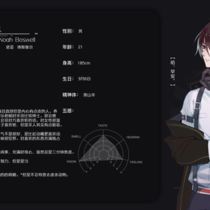我来复建了!手好生啊……总之先这么着吧(你等等)
回忆剧情,ZZ和熊熊介于20~21岁的时候,还没有正式成为搭档之前的故事,其余设定会慢慢补完,写一点是一点吧~
=============================================
“我的意思就是,我喜欢你,想和你交往试试。”
泽万认得眼前的这名黑皮肤的哨兵,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对他进行精神疏导。“三次”这个数字有点尴尬,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哨兵有权利选择自己偏好或者适应性高的向导,但在多数前提下,向导却没有权利拒绝哨兵。泽万见过不少对自己有兴趣的哨兵,他在抚慰哨兵们的时候,总会尝试悄悄进入他们的思想。不用多深,甚至只是浅层次的,就能让他明白他们的企图,他向来对此乐此不疲。而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知道阿伯拉德这个人的。站在自己面前的木讷男性身上有着灰尘、伤痕与血迹,看上去才从某次任务中解脱出来,此刻正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向导R08与哨兵Q02,你们可以使用疏导室了,时间不要超过两小时。”
教官如是说着,不等自己话音落下就匆匆离去,这次的任务出了点状况,还有好几名哨兵需要额外帮助,他要处理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能总是像老母鸡一样带着这群长不大的孩子。
阿伯拉德一言不发地目送着教官离去,在对方走过转角消失不见的同时,帮泽万推开了疏导室的门。泽万看了一眼将目光锁定在自己脸上的阿伯拉德,不由分说地径直走了进去。
“坐,”泽万率先选了自己喜欢的椅子,他大大咧咧地给自己调整好舒服的姿势,翘起了二郎腿,“想说说你的遭遇吗?”
摇了摇头,阿伯拉德拽过剩下的椅子,坐在泽万的对面。
“你知道你应该配合我的,不为别的,因为在优秀的向导面前,哨兵的‘不配合’没有任何意义。”抱着胸的泽万让自己的嘴角扬起优雅的弧度,他喜欢看别人因为自己不知所措的样子,也喜欢看到事情按照自己计划那般发展。
“我……”将双手相握并搭在双腿之上,阿伯拉德弓着身子低着头,“我犯了错。”
“什么样的错?”
“我又发怒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同行向导负伤,我看到血就晕了头。”
“保护向导是哨兵的天性,这很正常。”
“但是因为我的暴怒使得任务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又更多的人因此受伤。”
泽万撇撇嘴,至少这个哨兵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嘿——听我说,大个子。”
听到这话的阿伯拉德反而又把自己往椅子里缩了缩,简直好像极度想要和椅子融为一体。
“哨兵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哨兵才需要向导,你才需要我。为什么要对‘理应如此’的事情如此介怀?”
苍白的、除了两把椅子就别无他物的疏导室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潺潺的水流声作响。泽万平静地等待着,他大可以像对别人,甚至是最开始对阿伯拉德那样,直接清除不利的记忆,让疏导变得轻松便捷,但他这一次却没有这么做。
“我想,成为更好的人,”阿伯拉德抬起头,这是自从进入疏导室,泽万第一次看清他的脸,“不只是有用的哨兵,我也想成为有用的人。”
说完阿伯拉德又低下了头,用左手的大拇指蹭右手的指头。
“我想成为温柔又强大的人。”
泽万偏了偏脑袋,在多次的接触疏导中,他曾无意被展示过这方面的记忆。彼时的阿伯拉德能力才刚刚分化,无法自控的他因此做了很多在自己看来“不可饶恕”的事,并且一直在为此自责着。
“我要进入你的思维了,可以开始了吗?”
难得地,泽万在自己记忆中第一次征求了哨兵的意见,虽然他依旧没有等对方回复就打开了思维共享。经历过像是快速坠落的感觉后,他侵入了阿伯拉德的脑子里,某些记忆像是破碎的玻璃,悬浮在这个毫无时间与空间概念的地方。它们一边向泽万展示着自己,一边又愧于见人。泽万开始找寻着最新的一次记忆,他也听说了这次任务,校方选择参与的都是测试前几名的哨兵与向导,因为其中另外有个对他太热情的哨兵也在,泽万不想因为吊桥效应将日后的关系变得更麻烦,就推脱自己身体不适没有参加。
【别抗拒我。】
泽万对阿伯拉德说,他的声音像是柔风、像是春水,像是世界上任何温暖柔情的东西,那声音径直回响在阿伯拉德的头脑中,使他无法拒绝。
【展现给我。】
现实中处于迷茫状态的阿伯拉德瞳孔失了焦距,他瘫直了身子靠在椅子里,这才显现出他的身材高大。浅色的蓝环章鱼不知何时被呼唤显现出来,却用与它所持有的剧毒相反的温柔缠绕着阿伯拉德的身体。
自责,这是泽万在阅读过那段记忆后,率先浮现在他脑海中的情感。他充分感受到了阿伯拉德的自我苛责,那份感情在天性与过往的结合下变得更加排山倒海,令人窒息。泽万忍不住在心里叹气,这个人怎么看上去傻乎乎,实际比看上去的更傻呢?但这一次他却不想采用以往的一贯做法,他开始认为,对待阿伯拉德一定还有更好的疏导方式。
【醒来吧。】
宛如刚浮出水面,阿伯拉德猛地深呼吸一口气,终于坐直了身体,蓝环章鱼依旧缠在他的身上,他也没有丝毫抱怨的意思。
“今天的疏导结束了,”泽万平静地说,“你现在感觉如何?如实说,我能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
听到这个词眼,阿伯拉德很明显地蹙起了眉头:“没感觉和之前有什么变化。”
“这就对了,”泽万打了一个响指,放下自己的二郎腿,“因为我什么也没做。”
见阿伯拉德眉头隆起的更深了,泽万忍不住笑了起来:“Q02,你说你想成为温柔又强大的人吧,想成为有用的哨兵和有用的人。作为哨兵你可以寻求向导的帮助,但实际上,作为‘人’,你的这些烦恼他们也有,并且他们都是自己解决的。所以不如这次试试自己走出困境如何?”
“你没有对我疏导?”阿伯拉德平静地问,看不出多余的表情,蓝环章鱼的一只触手搭在了他的脖子上,像是恋人一般抚摸着他的下颌。
“没有,我觉得没有必要。”
“什么意思?”
“你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自己想做什么,只是你错误地以为自己势单力薄,一个人做不到才需要向导的帮助。实际上你不仅可以自己做到,还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我并不是嘲笑哨兵都是意志力薄弱的莽夫——抱歉,我笑了吗?——总之,这是你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做到的事情,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可以随时来问我,若是后期实在无法解决,我继续为你疏导也没问题,毕竟这是我的工作。”
阿伯拉德沉默着,看上去一时半会儿无法理解泽万的话,章鱼的主体正趴在他的肩头,八只触手全部都缠在他的身上了。
“时间还有剩余,如果你想继续在这里呆到时间结束,我也乐得清闲。你的意见呢,Q02?”
“阿伯拉德。”
泽万唇角边的笑意更明显了,他从刚才起就听见了眼前人的其他心声,在纷杂的记忆中唯有这个想法清晰明确。
“我的名字是阿伯拉德•阿伯特。”
“哎呀,被告诉名字了,虽然我早就知道了,不过现在说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我喜欢你,想和你交往试试。”
【喜欢你。】
T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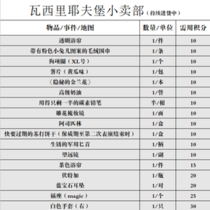
计字3097,滑铲准备
-----------
景箫又头痛了。
他最近总是做些乱七八糟的梦,梦见景慰晴和那个影子,梦见夏芝,梦见吉安和优娜,梦见加西亚和弗朗西斯。他们全身鲜血地在他的梦里呼唤景箫,对他说那边很黑很冷,他们离不开那个地方,而最后景箫总是被他们拉扯着落入深渊,接着就蓦地睁开眼睛,看到头顶被暗暗的火光映红的房梁。
少年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和刚刚成为友人不久的大男孩睡在一起,每次这样惊醒时,他身边归海青均匀而安稳的呼吸声总是会娓娓地告诉他“名为景箫的人还活着”这样的事实,而他渐渐变得在那规律的呼吸声中才能沉沉睡去,才能不再做那些撕裂他神经的噩梦。
他没对归海青说这些,然而习惯已经这么根深蒂固地种下了。
他们在这些天里陆陆续续又清理了些倒塌的民房,好歹找出了几件能够替换的衣物,还找到了趁手的打磨工具——景箫的刀已经钝了,甚至还有那么几处出现了卷刃的征兆,在打磨好它之前如果不是必要,他不太想用自己的铁搭档再去砍什么东西。
虽然粗心,他也是会心疼东西的。
好在学习现在用的这种大开大阖的刀法之前他还用过短剑和匕首,毕竟一个十岁的孩子力气有限,景箫现在这柄刀大概比那时候他自己的体重轻不了多少。当他久违地试图从那堆匕首和短剑中找出趁手的武器时,有那么一瞬间竟然后悔起没把加西亚的剑也带来。
然后少年突然觉得背后发凉,仿佛那些同伴的幻影就站在他背后对他说话,用他们腐烂的怨毒的眼睛看着他,冰冷的黑色的粘液从他们发白的伤口里滴落下来。他战栗着猛地回头,背后只有正在默默收拾柴火的归海青。
可他总觉得自己听到了幽灵的耳语。
「有……吗……」
景箫确认,一定是有什么人——或者什么鬼,正在他耳朵边上断续的窃窃私语。
「有……得到吗……?」
少年能分辨出,那声音属于一个陌生的男人,带着种奇怪的失真感,让他忍不住去想象那些诗人们口中所述的“来自深渊的呓语”。
“归海青,你听见什么声音了么?”景箫忍不住对着男孩发问。
大男孩带着一丝迷茫抬头,四顾之后摇了摇头。
“没什么声音啊。”他耸了耸肩,继续把从倒塌的房子里捡出的木料劈成小块。
少年烦躁地挠起头来,他的幻听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出现过了,现在出现的声音他从没听过,但也无法确认是不是他自己的幻想,毕竟那个总在他脑中响起的声音他也没听过。
“谁啊?”景箫试着去回应那个声音,毕竟那个幻听从来没有回应过他,这次如果有了回应,大概就不是他自己的幻想,而是某个飘荡在废墟里的幽灵了。
“喂?喂……有……听见吗?”声音提高了嗓门,景箫能更清晰的分辨出来这声音属于一个年轻人——从语调来判断,这个“幽灵”比他自己大不了几岁,还处于心高气傲的年纪吧,大概——听起来现在有那么些气急败坏,随后还咋着舌头嘟囔了句什么,少年没听清楚。
“所以你谁啊,幽灵吗?”景箫噌的站了起来,判断出那声音不是从自己脑袋里发出来的时候他的胆子一下就壮了,在少年看来就算声音的本体是幽灵也不过是和空气差不多的东西,只不过比空气要烦人一些。归海青好像也听到了什么动静,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狐疑地四处扫视。
“这小子怎么跟人说话的?”那声音毫不客气地反问,带着股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神气。
“嘿你还上劲了哈?”少年无名火重新冒了上来,两下把袖子捋起来做出要打架的动作,“个什么玩儿还装神弄鬼的,信不信老子给你蛋黄打出来?”
“什么东西?”归海青歪着头皱眉,似乎也听到了这奇怪的声音。
“总之有人就……,快……图……你们……民!”清晰了几十秒的声音重新变得模糊起来,只是听这谜之声音的口气都能听出里里外外的不耐烦,而从断断续续的音节中分辨出来的字词显然表示着它已经无视了景箫的挑衅,说了件什么事情想要听到声音的他们去做。
——听都听不明白,谁会去做啊?
景箫的火气一下被憋下去了,只好用鼻子出了口气,朝着归海青耸肩膀。大男孩表现得像只受了惊的小狗,探头探脑地四处看着。
“别听了,不管它。”他伸手揉归海青凉而柔软的黑发,“白天弗洛斯缇要我明天去树林帮忙挖水源,你一起来么?”
归海青偏了偏视线:“不想去。”
“最近有候鸟停在树林子里休息了,说不定就有肉吃哦。”景箫锲而不舍地继续引诱。
大男孩眼睛突然亮了:“我去抓鸟。”
人类肉食动物的秉性当真可怕,归海青一晚上修整好了全部能用的装备,还把他们上次从仓库拿来的黄豆耐心地切成小块装进袋子,甚至连从镇子里倒塌的民房里刨出的铲子锄头和箩筐都被他修整得像模像样了。拿着短剑和匕首对着空气熟悉武器重量的景箫看着搭档高涨的行动力感受到一阵凉意,如果第二天抓不到鸟吃不到肉,大概这家伙会消沉很长一段时间吧。
第二天早上归海青像是要出远门的小孩那样天不亮就把景箫给晃了起来,他们出门的时候弗洛斯缇已经带着那只多嘴的鹩哥静静地站在他们房子的不远处等着了。狗妖精话很少,偏偏归海青也是个话不多的主儿,三人一路几乎无言,憋得景箫从胃里尴尬。
这一次他们走的方向和上一次采集蘑菇的时候有微妙的不同,从某个地方开始他们走了一条更加湿润的道路,有新鲜的泥土粘在景箫的鞋子和裤子上,弗洛斯缇循着景箫看不出的痕迹轻车熟路地疾走,少年有那么一瞬间对妖精竟然生出了羡慕的感情。
“你们妖精的体型真的很轻巧,像我这样的人类永远都做不到这样。”他没话找话地跟狗妖精这么说。
“轻巧归轻巧,我们也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比如清理大块的石头和木头,比如今天找你们来帮的忙。”弗洛斯缇没回头,“你们带的铲子就快有我那么高了,像我是绝对挥不动它的,如果不找你们这样的人来帮忙的话,大概我永远也挖不出那块水源吧。”
“说得对,”景箫拍掉一块粘在他裤腿上的泥,“不过我也就做些这种粗活,再细致的事情是真的做不来的。”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弗洛斯缇文绉绉地说了这么一句,少年闭着嘴想了半天这句话的意思。
他们到达那个水源地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天顶了。这片树林的枝叶比起他们上次达到的地方来更加稀疏,而所谓的水源现在也就只是一片泥沼而已,大概两个世界的撞击对这里的地势也产生了影响。柔软的泥土里横七竖八地印着某种食草动物的蹄子印记,景箫不太能确认那是羊还是马,而这两种动物似乎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
“是鹿。”弗洛斯缇似乎看出了他在思考什么,“那是鹿的脚印,他们应该在这附近喝水觅食。这个地方如果挖开,应该会有泉水涌出来……虽然也不太一定。”
景箫还在思考的时候,归海青已经扛起了铲子。
“挖开它吧。”大男孩说话言简意赅。
看起来很简单的任务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如果穿着鞋踏入泥浆,他们就会白白地损失一双鞋子,而光着脚踩进去,如果被隐藏在泥沼里的毒虫咬到就更加得不偿失了。思虑再三后景箫一咬牙穿着他那双脏靴子踏进了泥里,瞬间黄黑的泥水就漫过了他的脚面。他用锄头把泥沼周围那些土地翻开——这不是件轻松的工作,如果动作太大泥土就会没筋没骨地落回它们原来的地方,如果动作太小只能在原地留下一点痕迹。少年皱着眉一点一点翻动周围的泥土,把它们慢慢变成可以下脚的硬地。归海青跟在他背后将泥土踩实,用那个对于他们的身材而言不算大的铲子一铲一铲地将那些黑泥从浑浊的泥浆里起出来,扔在那道泥土构成的小小堤坝另一侧。
这件工作是繁杂又枯燥的,挖了一半的少年们很快失去了兴趣,仅仅凭着在这个年纪的孩子中少见的耐心和言出必行的自尊心在机械地重复着劳动。他们一直挖到太阳开始向着树林的另一边沉下去,稀稀落落的候鸟开始陆续归巢,有一半以上的泥沼都已经被他们挖开,浑浊的水从地下缓缓渗出来。
“这样就行了,过上一段时间它自然会变得清澈。”狗妖精用手掬起一捧水来闻了闻,她身边是个看起来相当精巧的套索陷阱。
归海青没理会弗洛斯缇的动作,他眼睛里闪着光看不远处枝头上站着的鸟儿,从包袱里摸出了那个箩筐。
“我们今晚有鸟肉吃了。”景箫看着搭档的动作,忍不住笑出了声。
3133
——
《无人时代》
这些东西应该被称为历史,但毫不客观,故而只不过是一个缺失理智的人类——也许不是人类的自言自语。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料想到它们的未来:随着尸体、遗迹和现存的一切努力一起沉入土地深处,在这样的时代,历史和艺术都不比一抔肥沃的黄土来得有意义。
要说这是世界末日也并不恰当,因为严格说来,世界并没有毁灭。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些时间中,世界比想象中更复杂也更轻松的方式活了下来。真正毁灭的只有我们本身。
我们在文明的遗骸之上苟延残喘,现在也在认真的思考是不是要用人类的遗骸堆肥。
有的时候,世界是比我们想得更多的谎言聚集而成的。
——
最终,兰尼德尔并没有收集到合适的材料去编织渔网。水比他想得要急而宽阔,至少渡河一事总是无功而返。天气还没有暖到生命增长最疯狂的时候,连能用来编织或直接当作绳索的水草也不多,所以暂时也就搁置了,只是随便做了些饵和钩子。
每次往返镇子上都要花去过多的时间,所以兰尼德尔选择在这里建一个临时居所。不比在镇上那里土地坚实土层很厚,河边的泥土分为湿漉漉、爬满了植物的烂泥和泥沙混合的湿滩子,所以再那样住在地下已经不是什么好选择了。
在过去的——大概是半个月——中吧,他一直一边诅咒着牛、马和骡子之类历史上向来为人类与类人生物忍辱负重的动物,一边把没有办法用附近的材料替代的东西拆掉搬走,分批运到河边;路上的每一株树都被伐得只剩下一时间够不着、也细得没法用的树顶小枝,把长而笔直的加工木板劈成条状,深深砸进泥土里,然后以不复杂但很繁琐以至于懒于被描述的方式搭成临时的窝棚,用泥土和沙子的混合物涂抹墙壁和屋顶,再用草皮和碎布保证它们不会在一场暴雨之中被洞穿。
它勉强经受住了前几天的雨。这场春季的雨以一夜遥远滚落的闷雷开始,湿润温暖的气息从土地内部往外蒸腾,又引发了兰尼德尔长篇大论毫不重复的咒骂。他不得不在窝棚下面与小小的火堆蜷缩在一起,那热源大大侵占了他能放腿的地方,所以得时不时转身让火烤一烤被洇湿的背脊。
一卷厚而黄的纸张从外面飞进来,差点就砸进了火堆里,兰尼德尔不得不空手把它挑得更远一些。她带着一身湿润的水汽站在窝棚外面,相比起而言,兰尼德尔确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细雨落在她的身上、也许还没有落上,就被蒸发成些许水雾,这些雾气像固体一样堵在兰尼德尔临时居所的门口,他不禁又往黑暗的深处收了收双腿。
她无声地笑了笑,坐在了雨中。
“就算你把写好的东西丢给我,我也看不懂。”兰尼德尔无聊地拨弄着火里明亮的炭。对于他而言,这些东西的价值只在于在它们干燥的时候是很不错的引火物——比不上炭化绳和极端干燥的苔藓,但比草屑好用不少。他眯起眼睛借着火光看着纸上面的文字,反正看不懂,也无从评判是好是坏,连文字是否端正也判断不了。
“原本是想叫你帮我把它们保存下来,在这些方面你可比我懂得多。但是仔细一想,其实也没这个必要。”她抱着膝盖,把下巴搁在膝头,“历史是写给别人看的,墓碑是立给自己的。”
“如果我像你一样整天想这些的话,早就饿死了。”
“从现在的状况来看,也许早点饿死反而是比较幸运的选择。”
兰尼德尔耸了耸肩:“如果老想这些过去将来,如果大概的事情,也是早就饿死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
“等雨小一点,就去钓会儿鱼。”
“我是说以后的打算。”
“……把鱼处理一下然后晒成干。”
“……再以后一点?”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没有,真的没有。”兰尼德尔用脚尖把冷掉的碳灰拨进火堆里,“等活到那个时候再说吧。”
然后他们都没再说话。兰尼德尔透过火焰看着她,看着她周身的雨水不再蒸发,额发和红裙都湿透了黏在身上。她抱着膝盖,越过臂弯和脚尖看着那些木柴燃烧之后黑灰相间的炭火灰。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沉默已经是他们彼此之间都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兰尼德尔也从未想过要问她冷不冷之类没什么意义的问话,毕竟说到底关心自己的幻想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外面的天色稍微亮了一些,但只是云层没有那样灰而厚了。兰尼德尔决定按照计划去钓鱼——这样的天气可以遮掩人的动作和脚步声,鱼通常会更愿意吃食。
说是鱼竿,其实也不过是一截弄弯了的钉子系着捶打过的长草茎。他把虫子、以前所捉到的鱼的下水混在一起,捏成剂子,挂在鱼钩上,系上水鸟的羽毛。空勾的损失并不大,但最怕的是鱼线被水泡酥了之后断裂,毕竟现在其他的都能再造,金属却暂时不可产生,所以他额外用布条做了个粗糙的网兜。现如今鱼钩和其他农具都堪比精致等重的铁箭头,兰尼德尔不觉得自己会锻造,也不觉得其他幸存者会锻造。
她不在,这是很罕见的事情。自从他们知道现在是这样的时境,就常常陪伴对方——毕竟自言自语好过发疯,虽然在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两者没有很大的区别。他能感觉到棚子里的火堆仍然在散发热量,胜过在雨中干坐着几百倍,但相比起来,食物永远是更重要更优先的事项。
实际上,他情愿让自己忙于食物、建造和其他所谓的更紧迫的事情,而这样就不必去想过多的事情。虽然以往他也经常在林中或荒野独自生活,但那与现在的情况还有些许不同:知道同类存在的孤独和几乎无同类的孤独依然不同,这是个无人的时代,就像树木无根、动物无巢,有的时候他甚至会怀疑曾经的繁荣和历史,曾在人类的村庄和城市生活的时间是否都是幻觉——他原本对那些生活就没什么实感。
钓鱼比其他的选择要差,因为这会有大段大段空白思考的时间。它不是一项很需要精力和思索的工作,只需要分出有限的一点余光观察浮标就可以。钓鱼和小雨都一直延续到夜里,饵食换成了气味更强的肉泥和内脏,那些鱼更加肆无忌惮地吃食咬钩,大约没过半夜就捉到了不少鱼。
终于兰尼德尔没有熬过这场小雨,他躲回了自己的窝棚里。少年脱掉也已经湿透了的上衣,把它们铺在一边烘干,赤裸着上身处理今天钓上的鱼——这比裹着湿漉漉的破布要暖和太多。
他对于这项工作已经很熟稔了。剖肚,去鳍,把整片的鱼肉从刺上面剃下来,留下今天要吃的部分烤熟,其他的挂在细枝子上,晾在阴暗通风处。鱼肉在逐渐干制的过程中逐渐变红而透亮,泛着一种死去的光,有一些因为最近潮湿的天气而长出了其他勉强能吃的东西,便都用小刀削下来,放在石头上烤熟。
白色的蛆沾着鱼的油,不一会儿就不动了,只在滚烫的石头上面发出咝咝的热气。贴着石头的那一面焦糊了,兰尼德尔不得不用树枝去拨弄它们,肥嫩的白肉破裂的时候也发出咝咝的声音。他已经习惯了。
用鱼油煎出来的东西总有股鱼味儿,所以兰尼德尔也不是很在意这些,四舍五入都是肉,但她肯定受不了。他一边心不在焉地吃着,一边惦记着快要到来的夏天。一到了夏天,住在这样的水边也会因为温度和高湿度而难受,但大量干净、可靠的饮用水又让人犹豫不决,再者,一旦入了夏,必定会有大量的食物无法储存,苍蝇、甲虫和让肉液化的其他玩意儿都会疯狂滋生。
他知道镇里的人们在尝试种植和养殖,但不知道到了夏天,灌溉植物的水够不够用。毕竟要靠井水供给人、动物和植物,毕竟是有些困难……吧?
兰尼德尔吃掉了半条鱼,把骨头和内脏收集在一起。一如既往,鱼肠被洗干净挂在架起的枝条上,苦胆埋进炽热的灰里,其他红呼呼乱糟糟的东西被团在一起,留待下次钓鱼的时候当作饵食使用。
在这个时候,她又站在了窝棚外面,半弯着腰往里瞅着。
“你都弄完了吗?”
“不如直接说有什么事情吧。”
她叹了口气,活动了一下肩膀:“我猜你是忘记了,或者没看到,毕竟现在除了与食物直接相关的事情你都不怎么在意。上次我们——你往下游走了一小段路想找水草的那次,我们看到人工的石头来着?”
“所以呢?”兰尼德尔敲了敲他因为长久低头工作而僵硬的肩膀,“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我的确不记得了。”
“那里大概是水渠的遗迹吧。”
“……其实我一个人在这里活得很不错的,虽然偶尔要去翻垃圾。”他把鱼刺小心地埋进土里,免得不小心踩到划破脚掌,“水渠不弄也没什么不行。”
“仔细想想你比我要冷血。”
“只是自私而已,我又不关心‘全人类’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