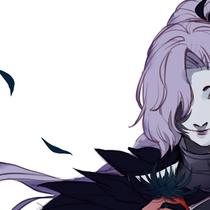字数:1549
---------------
“我们到了。”
传送门中的三人缓缓走出,开始环视四周。
“乱石滩...除了这些灌木之外实在看不到什么称得上是补给的东西。”
“...真是寂静的可怕,空气连一点流动的迹象都没有。”子裕用自己的能力确认了一下周围,却只能感觉到他们三人的呼吸。
“等一下,那里...是座城吗?”
其余二人一齐向着秦颂所指的方向望去,一幢幢高楼在远处依稀可见。
“该不会是海市蜃楼吧?”
“应该不会,这一带丝毫没有敌方生物的踪影。考虑到协会的安排,敌人和补给点应该都在那座城里。”
“问题是这距离,是要走一整天?”
“故意削弱我们的体力再遇敌吗...异协的那帮人真是有够恶趣味。”
“快走吧,夜晚呆在这种这种没有掩体的地方不安全,我们要尽可能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那里。”
-------------------
“咕——”
面对两个人的目光,秦颂的神情有点羞涩。
“哈哈,没关系的。再忍耐一下,我们就快到城里了。”
“抱歉打断你一下维泽,我们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合适的庇护所。秦颂,麻烦你进城之前提前挑几根大一点的树枝点上火,天就快黑了。”
“哦...好的。”
“你啊...”
------------------------------
“该说果然是这样吗...本来就没抱什么期待...”
“看来完全是座空城,应该废弃了有一段时间了。”
三人举着灌木做的简易火把,谨慎地在城中穿行。原本的道路早已被土块和瓦砾占据,放眼望去,尽是残垣断壁。
子裕在城中央的一个广场停下了脚步,“现在我去找庇护所,维泽,你和秦颂一起去寻找补给,30分钟后在这集合。”
“欸?你不一起来吗?”
“分头行动能节约不少时间,还有...”子裕笑着指了指秦颂。
-------------------------------
“咕——”
一阵闷响打破了夜空的静寂,秦颂羞的直捂肚子。
“怎么,你们没发现补给吗?还有维泽,你怀里抱的是什么?”
“全是鲱鱼罐头,异协那帮崽子在货架子上放的东西就这些还能吃。”
子裕的眼角稍微抽动了一下,“算了,有总比没有强。对了,你们那边有任何敌人的迹象吗?”
“完全没有,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的,让我们在这空城吃完罐头之后出去找怪?”
“好了好了,先不提那帮人是怎么想的了。我在离这不远的地方找到了间位置不错的房子,已经提前用异能打扫过了。今天晚上我们至少不用睡水泥地了。”
“哈啊~”,维泽打了个哈欠,“好歹能休息一下了。”说完就迈开大步向广场外走去。
“等一下...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秦颂一脸不安的说。
“哇,这罐头这么厉害的吗?没开封就有味道的?”维泽慌忙检查起手中的罐头来,毕竟这东西只要漏了一滴就够要人命的了。
“不,不是罐头。”,子裕的额头冒出了冷汗,“这来源...更像是在地下。”
他的感知范围里,原本应该死寂的空城,突然有了异样的颤动。
“小心!”
话音刚落,一束苍白色的雷柱就在维泽身后迸裂开来。
维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吓了个趔趄,差点倒在身后的焦尸上。
“啊啊...这就是那股味道的来源吗...”虽然靠战斗本能放出了闪电,秦颂对眼前的一幕还是在禁不住干呕。
“多亏你到现在还没吃饭,不然肯定都要吐出来了。”维泽苦笑了一下,从他的脸色来看,他自己也是半斤八两。
“抱歉,但还请你们忍耐一下,现在有大量个体朝我们的方向来了,做好撤退准备。”
“谢谢啦,”维泽搭了子裕一把手,在站起来前回头撇了一眼那具尸体,但尽可能不去看那张面目全非的脸。
“竟然会从地底冒出来,为什么之前一点迹象也没有?”
“应该是人为的控制了活动时间吧...等下,这是什么数量!”
数以万计的僵尸,将整个城市中心围的水泻不通。
“可恶...只能硬闯了吗?”
“看来没办法按原定计划前进了,先突围出去要紧,我负责中间和两翼,秦颂,你负责殿后,维泽,务必拿好光源。”
“明白。”
“欸等一下,罐头怎么办?”
“要什么罐头,逃命要紧!”










字数:5670
*有ooc介意慎看
*每一个人都有病
第二章
在上一次大战后,人委、妖委和异协组织了集体加强的训练,就这样消失了一年,这样安心放松的日子真是难得,对于逍遥游来说。
真的么?
这一天肖还在家里面变成小狐狸晒太阳,魅鸦就很冲进肖的房间,满脸微笑的对肖说:“要不要搞事?”“搞!”都快因为悠闲而僵硬的肖瞬间兴奋的跳了起来,然后愉快的跟着魅鸦去了总部。
到了总部只见一个大概16岁的白发少女拿着大镰刀十分随意的坐在桌子上,正在与旁边一身字的男人斗嘴,这竟是逍遥游的上层干部的总参谋和代BOSS。
“早哦,光年,二老大!”魅鸦随意的对着他们打了声招呼,对着他们的争吵是完全无视,毕竟,在逍遥游这早已是见怪不怪的事了。“光年,肖也一起来哦。”魅鸦拍拍身边的肖,光年比了一个GOOD的手势并扔给肖一套衣服,“快换上吧,肖,哼哼~这可是潜伏的装备哦!”肖似懂不懂的点了点头,看着手上这深色的而且有些眼熟的衣服,去换衣间换上了它。
在肖换衣服的时候,其他几个人也慢慢的走了过来。一身整齐的女仆装,显得这几位少女十分的可爱。看着其中一个白毛走前来,魅鸦十分兴奋的点了点头,拍着少女的肩愉快的说“来吧喵喵!”松尾喵喵看了看还是身着原来的衣服的魅鸦摇了摇头,“你要知道,我的能力使用了你会立刻变成男人的,你的衣服……”
“噗噗!”站在后面的缘和瓷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魅鸦你那样真的好让人期待啊。”“不对,变成男人应该会把衣服撑爆吧。”“哈哈哈,刚变成男人就让我们看裸体,魅鸦真是恶趣味hhhh”瓷和缘在一旁笑的前仰后合,并故意摆出期待的眼神望着魅鸦。
“啊喂……你们够啦!!别这么看我我我不是变态!!我只是刚刚没想到,喂别笑啦!!!光光年,衣服有没有我先去换一下!”魅鸦瞬间手忙脚乱,原来那幽魅淡然完全消失。
光年突然一脸失望的看着魅鸦,并敲敲身边的祀,“切,二老大快给魅鸦造身衣服。”在一旁观望很久的祀突然爆起来,“臭小鬼!你看我是那么随便的代BOSS么!”“那你想看魅鸦爆衣么。”光年饶有趣味的笑着看祀。“喂光年你别这么笑好可怕!!你才是最想看的吧!”魅鸦冒着冷汗不禁往后退了一步。“没有没有你想多啦……呵。”光年甩了甩手。
那个“呵”是什么!!!!好可怕!!!
看光年不行,魅鸦双眼散发着小星星似的可怜巴巴的望着祀,“爸爸~”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滚。”祀撇开脸完美躲过星星眼攻击。
看着一旁尴尬的魅鸦,光年笑着从身后拿出一套衣服,“哈哈哈哈哈哈哈好了好了不逗你了,我这么聪明当然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接过衣服的魅鸦一脸懵逼,恨不得跳起来揍光年一顿,可就在这是,在他们身后一人大声的叫住了光年。
“光光光年……!!!为什么,这裤子这么短??!!”这时,穿着超短裤的肖红着脸从换衣间走了过来,“这是裤子么?!是小裤衩吧??!!”
“哇哦~”光年磕着桌子比了一个大大的GOOD的姿势,并且自满的笑着。
“光年干的好。”刚刚还在起纷争的几个人这时一起赞扬光年。
“嗯~别这么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光年笑着擦擦鼻子,“都说了我智商有500。”
“什么啊你们这群家伙……”肖晃晃悠悠的走上前,“原来你们都这么想,果然还是狼狼好!!狼狼都不这么想看小短裤!”说完跳起来扑向吃骨头不明真相的祀的狼。
“嗷?”
砰!
肖揉着自己的鼻子看着自己扑了个空,一脸幽怨的望向瞬间将狼抱起来的祀,“狼是我的!”
“二老大你是要狼还是要我。”肖把脸鼓的像个包子。
“狼。”
“二老大我突然想起来我远方还有个干女儿我要去妖委了拜拜。”语罢肖就准备抬腿走人,被光年拉走了。
“肖你把头发放下来,你那样太明显了,再短点,嗯,再短点……好对就这样。”光年打量着肖直到自己满意,这时魅鸦也穿着松散的衣服走了出来,喵喵拍了拍魅鸦,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容貌魅惑的男人。
“果然就算魅鸦变成了男人,你的气质也没有变嘛。”缘笑着看向高自己一头的魅鸦。
“喂,你说的是帅的意思吧~”魅鸦俯下身,眯着眼看着缘,因为魅鸦本来就很魅惑,更何况现在变成了男人。
“不,是欠打的气质。”
魅鸦顿了一下,连连往后退。
这时一直盯着魅鸦的肖轻轻发了声赞叹,用特别小的声音嘟囔,“鸦鸦这样还是很帅么……非常符合我的审美啊……”这时光年拍了一下肖,用无奈的语气教育道“我知道你是花痴,可你不能对谁都犯吧。”然后看见了肖十分认真的点了下头,光年也无语了。
终于,准备好了的6人终于要出发了,出发前光年还是不忘与祀斗下嘴。
“祀你这么闲是要度过老年生活么!”
“啰嗦!你去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祀不耐烦的摆摆手想轰光年走。
“嘿你胆子肥了啊!我看还是送你去扫厕所吧!又锻炼体力又美化环境还可以帮总管减轻负担,这不是一举三得么。嗯嗯~”光年架着镰刀,一只脚踩在桌子上,与祀四目相对。
“嗯好啊,但我先送你一程!!”说着二老大就开始聚力,一副要打光年的样子。
“啊不好不好,快跑快跑!”见状光年先冲了出去,顺便带着其他无人也冲了出去,“拜拜了您嘞!”
看见光年一行人跑了出去,祀沉重的揉了揉太阳穴,又长长叹了口气,“终于可以清净一段时间了……天天被他们折腾,我感觉我老了1000岁。”然后抚摸着狼说,“要不,咱们去度假吧。”
逍遥游这一行人,装扮成异协的样子,被光年叮嘱不要暴露身份,这次行动主要是来手集情报的,进入了一个碎片。
“这个碎片好空旷啊。”魅鸦四处望望,看见的只有尽收眼底的土坡和稀疏的杂草。
“什么嘛,异协为了作这个还是下了一番功夫么。”光年上下打量这片地方,“果然有钱就是任性。”
在远处的异协会长哭着打了一个喷嚏。
“喂喂光年,”肖背对着他们,对着他们打招呼过去,“你看那边那个白毛是不是特别像炽啊。”
语罢大家都挤过去看,“是啊这个好像炽啊。”光年磨磋这下巴打量着远方在与龙打斗的狐狸。
“这个肯定是炽炽,我有炽炽感应器的。”魅鸦一脸坚定的说。
“喂,你这个是什么危险的能力啊!”瓷在一旁抹了把汗。
“炽这个家伙,敢被着我先来潜伏?看我不教训教训他。”光年坏笑着看炽和另一个人打完龙,走上前去指着炽笑着说“想过我这关,就把身上钱全交出来!尤其是这只狐狸!”
突然闯过来的光年把炽吓一跳,〖什么玩意!你这故意刁难我呢吧!逍遥游为什么要为难逍遥游啊!〗炽嘴部抽搐的看着伸手要钱的光年和在光年背后偷笑的魅鸦,亚尼塔刚要冲上前去就被炽以百米赛跑的速度揪走了。
看着跑远的炽和亚尼塔,光年不屑的“切”了一声,“什么东西,我都是怎么教他的,竟然一分钱都不给!?竟然敢这么对上司!回去跟二老大一起扫厕所吧!”
原来你是真的想要打劫的啊!!!!
魅鸦看着远去的炽的身影,叫住了身旁的喵喵,“喵喵,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很久了。”“什么事啊?”“下次在遇到炽,你再对我俩一起用能力,这样我就可以随意****炽了!”喵喵翻了个白眼,虽然早就知道魅鸦叫住他没有好事,可是自己真的十分想吐槽一句,“这样的话我怕你还没****炽就先被他打飞了,炽可是规则级啊。”
“emmmmmm那还是平常好啊,炽是不会打女生的。女生真好。”魅鸦留着冷汗恍然大悟的说。
谢谢你炽,让魅鸦认识到自己还是个女人的好处。
就这样过去了很久,肖这样碰上了老熟人。
在茂密的森林里,有那么一行人穿梭在其中,里面最明显的也就是那穿着白制服的高个子。
这时肖正好与其他人走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看见了那个最明显的人。
“喂——白——喂!”大声的呼喊着眼前的名字,肖是完全不在意的,反正就认识他一个自己还打扮成异协。
听见了熟悉的声音,白应声往远处望去,但看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人影,直到看见不远处树丛里一对呼扇的耳朵和一根若隐若现的角。
〖肖不要在这么远喊啊,你们逍遥游为什么来了我先不吐槽,在我的方向看你真的很尴尬,既然你讨厌别人说自己矮,那就不能站在这么高的树丛下面啊……〗白眉毛抽搐了一下,跟旁边的队友打了声招呼就快速前进走到肖身边。
“你为什么在这里。”白用冷漠的口气 看着穿着异协制服的肖。
“我在哪里不用你管,但是现在有很紧急的事。”肖摆了摆手,“我跟其他人走失了。”
〖所以说逍遥游的还不止你一个还有一堆??!难道这里也危险了么?可是最近没有听到有逍遥游的人入侵啊。〗白还在思考敌我上的事,随眼低了下头,就看见了草丛中和上衣下若隐若现的,小短裤。
〖卧槽!这是什么?!为什么感觉杀伤力好强??!!〗白瞬间断开了思考,注意力全在这条小短裤上。
“肖,你为什么穿着裤衩出来啊?”话音未落,白就中了一记飞踢。
“混蛋!!!你连短裤和裤衩都分不清!!你是多没见识!!”肖红着脸用头发比了一个竖中指的动作,冲着白大吼。
白捂着脸,被击中的鼻子还在冒血,然后颤抖着手比了一个GOOD的手势。
为什么所有人看见小短裤都这样??!!
〖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肖的大白腿……这次算是值了。等等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白还在疑惑途中,一根小树枝悄咪咪的绕到肖身边,快速缠上去,把肖扥走直到消失在树丛中。
“唔哦哦哦哦!!!!!”被拽到大伙身边的肖还带着一丝懵逼,虽然自己的能力也会经常这么拽人,但是被拽还是头一次,原来,这么刺激啊。
树枝慢慢抽走,回到绿发女孩身后。“肖,没有找路能好好跟着走,你这样万一又被骗了我们也很头疼。”缘摇摇头对着还坐在地上的肖说。
逍遥游资金万一-100000-100000的怎么办。
肖摸摸头,呆呆的回话,“嗯,好,没问题。”
在这个碎片的另一头。
“肖!你被拐到哪了!?”白一个人在没有声音的大森林里呐喊,跟在后面的其他三个人一脸不明。
“毒萧,白怎么了?”
“不知道,八成情绪压抑太久疯了吧。”
“莲莲,我们这么悠闲真的好么?”躺在地上仰望星空的炎生突然问身边的莲歆。
“emmmmm挺好的啊,雪地这么漂亮,炎哥还这么暖和。天上的星星也这么美。”莲歆摆出少女崇拜式动作,痴迷的望着星星。
“话说,我们为什么又到雪地了?雪地是不是爱我们?”炎生翻了个身,看着莲歆说。
“说不定是炎哥太暖和了,特别吸引雪地。”莲歆眯着眼笑了起来。
虽然不是一个地形,但他们所处的地方依旧的雪白一篇,夜晚的天空因为雪的反射显得不那么黑暗,这个地方正是观景的好去处。
正在一片祥和之际,二人正要昏昏欲睡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怪物吼叫的声音。
“怎么办炎哥!!有怪物!”因为技能是被动技的莲歆十分慌张的朝身边的炎生说。
“不想打怪呢……要不找个洞钻进去?”炎生挠挠头,随手扑了扑了身边的积雪。
刚要逃跑的二人还没有确定怪物的位置,就看看天上垂下来长长的,如同刀板一样的头发,随后则听到了怪的一声闷叫,就再无声音了。
【这个技能是……】
“好烦啊....虽然这次单独行动但为什么是雪地啊....”一个身着异协服装,垂着两个大爪子的人慢慢走到二人视线。
“叔叔!”“肖!?”
二人同时喊出来,这时还在东张西望的肖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唔啊!?炎生??还有.....莲歆。”肖的声音从惊讶中带着写幸奋变成了淡淡的回答。
莲歆忙忙跑过去,抓住肖的手臂,“叔叔还在生气么?叔叔是不要莲歆了么?”略带可怜的撒娇,尽管肖始终努力保持断绝的态度,但毕竟是自己养了十年的如同自己女儿般存在的孩子,自己也不是无情之人,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如同曾经一样的用头发把莲歆举起来,而且嘴边还略带娇宠的微笑了一下。
“哦哦!!叔叔飞高高!!!”莲歆在半空中幸福的笑着,一旁的炎生见状没有问题,也走上前打招呼。
“哟,肖,好久不见!你果然还是这么宠着莲歆。”
“哼,那是,怎么说她也是我养大的~啊不对!!哎!!为什么炎生会和莲歆在一起啊?”肖惊讶的看着身边的炎生。
“组队啦组队~难道你放心把莲莲交给别人?”
“嘛....说的也是,以后莲歆就拜托你了!还有莲歆犯错了不要打她虽然她还是小孩子!!”肖一脸任重而道远的表情看着炎生,炎生尴尬的笑了笑。〖不行这个人怎么这么宠自己家的孩子,而且我也不会打莲莲的呀。〗
“对啦,”肖把莲歆放了下来,“你们有没有见到黯驹呀。”
“没有,怎么了?”炎生和莲歆有点惊讶为什么肖会认识黯驹。
“没事没事,只是有点闲想骑会儿飞马。”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看着别的方向。
“????!!!!”
突然远方出现了一团黑并闪烁着红色光芒的的人影,肖像是看见猎物的狐狸,健步如飞的跑了过去。
“老王八蛋!!!!”
背对着肖的黯驹还没有回头,就被一记飞踢击倒在地。
在远处观望着二人扭打的炎生和莲歆不禁留下冷汗。
“莲莲,那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不知道,不过我也不想知道”
终于长达几个月的侦查结束了,逍遥游六人也带着略显疲惫的身体回了逍遥游总部。
“真是好久不见啊。”在办公室悠闲的看着书的祀冲他们打了个招呼,“嘛,虽然我们很随便,但是毕竟你们去了那么久,咱们就正式一回,你们说说这几个月侦查到了什么吧。来光年,你第一个。”
“果然还是抢点钱比较好。尤其是炽的。”一脸正经的回答着祀的问题,先是让祀有些惊讶光年会这么乖的回答自己的问题。
“啊?你们不是侦查去了么???算了,魅鸦你说吧。”
“果然我还是适合女人。”瞬间答出了毫不相干的内容。
“什么鬼!!嗯??魅鸦你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么??等等这也不是侦查内容啊!喵喵你来。”
“呃……”喵喵突然皱起眉头,“史莱姆,再也不想遇到了...”
“不知道怎么去吐槽才好,嘛...这也算学到了什么....肖你呢?”
“我想好好的骑一次飞马。”肖略带失望的回答,“二老大,逍遥游有圈养飞马的么?”
“没有滚。唉....我为什么要问你们这些....缘呢?”
“我真的不会长果子。”缘恐怖的微笑着,除了祀之外的人暗暗的冒了冷汗。
“啊?什么???这跟你们行动有什么关系么???最后,瓷你怎么样?”
“我没什么,就是,真的挺好玩的。”瓷轻松的笑着。
突然祀站起来,把手上的书甩在桌子上。
“你们是去侦查的么!!!???喂!!!你们是去郊游的吧!!!”
随着祀站起来,众人的视线不禁朝向...祀的下半身。
“说我们....祀~你可以先给我解释解释你的沙滩裤是怎么回事~”光年突然奸笑的看着祀的沙滩裤。
“!!!?”被惊吓的祀也看向自己的裤子。〖卧槽,我怎么忘了换回来!!??可恶他们回来怎么这么急??!!〗“嘛...休息日不行么?”
“我们这么辛苦您老人家在这里享受?肖,缘,瓷,魅鸦,喵喵!上来帮忙!!把二老大丢厕所去!!!”
“哦!!”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