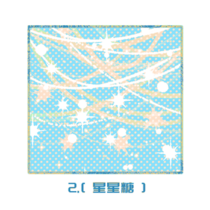*企划:口力口女子高校企划二期→打卡-磨合;
*故事承接上两篇,两三周后;
*没有磨合,只有我高强度乱磕!
*中森系准备的煎茶-预知梦
*感谢两位老师被我揪过来串场,擅自捏造了互动,如有不满意可以拒绝响应或者狂殴我私信改一万次(土下座(反复磕头))
——
每次缝针穿过布料,我总会用手指试探它的位置是否正确。
一点一点按着裁剪边缘以气消笔留下的痕迹,不敢有半点差错。
最终做出来的小熊,虽然很可爱,但毕竟第一次制作,那张脸还是难免有些搞笑。
我想到它被你抱在怀里的样子,脸上也不由得洋溢出独属于自己的幸福。
可惜我没能送出去…
——
-我正在你眼前-
中心地带入夏显然比北海道快,树上盘绕枝桠的嫩叶逐渐浓郁,这让如月莲实想起先前校方带着女孩儿们出外修学旅行时路途京都一带开放参观的茶叶园。只要到了季节,就会见到茶农到温室或田野采摘,过程大约是有晒干一类,可惜她并没有专门学习过茶道,了解过其中任何学问,自然是不知道它们都是如何变成现在中森系递来的煎茶的。
就学两年以来,如月莲实就没有少往医务室与心理咨询室两边跑:一是她手上的绷带出于特殊原因常需要更换缠绕的纱布,二则是在新学期起似乎总能碰上经常到医务室串门的中森系老师。这还确实是帮了个大忙,若是负责管理药物或医用品的稻见老师不在,就可直接往不远的心理咨询室挪几步直接找到与医务老师关系最近的新人教师寻求帮助。
一连串的缘分妙不可言,前两年原本只是经常边换纱布边和稻见空老师唠嗑,也在今年这个春天得到了改变,出于一些原因,如月莲实开始常常以除这之外的原因课后来到咨询室或医务室。
“结论来说,小如月还是没有把那个交出去?”
话到中途,用热开水烫开茶叶的中森系开始探寻地询问着在同僚的监督下更换包扎物的女学生。如月莲实真的对这个话题敏感过度,几乎马上对她这些字节反应起来,手滑没拿稳纱布卷,差点要因为浪费医务用品而被训一顿,霎时间教师二人脑里几乎同时响起“踩到猫了”的童谣旋律。
或许是某种八卦的天性,两个成年人对这关系还算良好的女同学在这学期那段极具喜感的故事相当好奇——也就是时隔八年,对如月莲实来说音讯全无的那个旧识戏剧性地和她入读了同一所高校,甚至在开学第十八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跟这个学姐结为姐妹关系的俗套小说剧场。稻见空望见双手包扎的动作完全没在进行了,赶紧嚷着身旁同事把那别有心裁的假天然开启话题的攻势收敛着点。而中森系似乎早就料到了女学生的反应,慢悠悠地提起茶壶将其移动到茶几上,为三个小杯盛满茶水才开始补充后续。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之前听小如月提这件事情时,你好像有些不开心。就会想到是不是有什么不太好说的内情,没太好提。”
话音刚落,在稻见空的帮助下如月莲实还是成功地结束了包扎工作,终于闲下来回到了茶桌旁边开始继续话题。
“并不是不开心。”
成熟而音色特别的声线在热茶润喉后稍显出一阵郁闷,两名教师如临大敌地坐直了身子,准备开始认真听取如月莲实的阐述。
“老师,呃……倒也,不是那么的大事…您们不用紧张…”
“这,这可是小如月的人生大事!!”
如月莲实看见暖洋洋的向日葵颤巍巍地握起双拳。
“啊…不,就是…那个……”
“不论发生什么,我和小系老师都会站在你这边的,如月同学不用担心。”
又见到了和善的古都狐狸虽然稍显沉稳但不多。
为了赶紧解开她们以为自己和对方吵架了的误解,如月莲实只好开始整理语言。
——
不知道是基因突变或者是遗传,如月莲实自幼起似乎一直是易留疤体质。她总是很倒霉,旧的疤痕没去,又因为奇怪的原因为双手带来新伤。最后它们都跟胎记一样难以消除,为了不要吓到身边的同学,女孩子开始学会为双手包扎做个掩饰,只不过即便如此自己也总是得到新的伤害。
家住小樽,父亲继承老一辈靠海吃海的工作成为了她的好借口。如月莲实总会说自己的伤其实都是拉扯渔网弄来的,摔伤弄肿的,总比单薄的纯粹倒霉听起来更有话题性,更能让别人闭嘴不再多提——哪怕实际上确实是倒霉到头了。除了这样的不悯属性,也另有其因。
过去那纯粹又深沉至极的心意驱动了她为心爱的人缝纫过一只小熊。
……呃,当然不是手上这一只,毕竟按照如月莲实微妙的尊严来看,让她抱着一个黑历史产物七八年还是有点太为难了,现在被收纳于某个精致的礼物包装袋中藏在即将要搬到峠宫家里的行李里头,在办理了退宿手续后会直接一起运送过去。
至于为什么之前没有送出去,这段理由有些繁杂,简单来说就是完成的那天,在海边长大的女孩就没有见过从城市里来到这里乘凉的那个朋友。自那一天起这个满载心意的小熊除了会被定期拿出来清洗干净以外,都没再与和如月莲实面对面过了。
万事都是开头难,就跟现在她没法直面峠宫薰那炽热的情感一样,在开始缝纫这只小熊的时候如月莲实的手工技术也正和她擅长掩饰欺瞒的水平呈反比那样,完全对等的不熟练。以至现在拿出来和手上的熊碳…熊碳二世相比,那张脸可能还有点歪。还有不同在于,熊碳一世脖子上的丝带则是浅黄色的,上面用有点歪歪扭扭的线缝着一串字符——实际上是女孩子的名字,莲实的罗马音字。
幼时还尚存纯真稚气的女孩子听见了电视的娱乐新闻,那时候流行将手工物交给心倾那方,表白就会成功的传闻。这不正好!小熊做好了就是还没送出去,现在紧急加一条缎带似乎也不错,有了想法就动手的如月莲实当天就裁剪了合适长度的绸缎,耐心缝了一个下午。只可惜决心要带过去,为花火大会的事情做回应的那天,在蝉声与即将远去的夏日吹息之间已经找不到那一颗炽热的心了。
总不可能再也见不到吧,于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拭去泪水生活下去。一年,二年,四年…甚至在第六年,下了血本赌最后这一次,如月莲实花时间捣鼓了一番她的学业,攒了点费用,直接考到了现在在读的高校,想着能在关东地区的哪个角落碰到峠宫薰。曾一度几乎要因为幻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差点放弃了寻找对方的念头,而如今竹枝捅破窗户纸直接贴到了自己脸上。
这时起反而让自己开始难以接受和面对了,伴着煎青绿茶的香气,如月莲实沉声叹道。那一刻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毒素慢慢钻到每个角落,那个深色中长发,有一对颜色清澈深邃,橄榄石般的双眼,长得和自己一般高的女孩总是见缝插针地出现在自己脑海里。心被挖空大半数年,好不容易终于习惯了,这时候忽然又将全新的内容狠狠塞进来,别人不知道,她可要为此心悸或者苦恼——以至于课程走神被老师的粉笔砸到额头上。
“但是她也等着要来找小如月很久吧?”
教师中森系的声音就跟早就心有所想的答案重合在一起,敲打着蜷缩在记忆里自己那间狭小房间的衣柜中,躲藏着所有流动情感的如月莲实。如梦初醒般她点点头,但还是那样愁眉苦脸,哪怕眼睛是眯起一条线。
“不…呃,我时常在想她是不是在被我说了那番话后甚至憎恶我。”
“那反应,我倒看不出那孩子对你有什么负面情绪。”
说罢稻见空把玩着自己红枫色的长发,手指灵巧地将起分成三股,逐渐编成麻花状。见到空空如也的茶杯,她身旁那位心理教师殷勤地拿起茶壶注入新的热茶,紧跟随后继续回应着苦恼的女学生。
“有倒是可能有。”
“呃,那果然还是……”
女教师竖起食指,跟着头两边摇的动作左右倾斜继续说道。
“比较可能是在埋怨你为什么还不愿意坦白也说不定哦。”
“说不出的事情就是…有点难说。”
“小如月真是个容易想多的人,不说说怎么知道呢?”
“我……”
话题被铃声打断,午休时间结束了。如月莲实从座位上起身,躬身感激了二位愿意倾听自己心声的教师。望着她没有继续作答离开了医务室,稻见空和中森系相视彼此考量着。
“会不会说太过了?”
“我觉得刚好。”
“……说起来,这个煎茶不会喝出什么奇怪的效果吧,比如突然好运然后倒霉一周。”
听到这个疑惑,中森系咯咯笑着,朝发问方比了个保密的手势。随之她双眼看着刚给如月莲实倒的那一杯煎茶,水面直立起的茶叶杆让女子加紧叫上了稻见空一起看过去。
——
周末的午后,如月莲实终于把眼前的地狱绘图收拾干净了。在之前期间时不时会传出敲门声,门外那个年下的女孩几乎隔了十几二十分钟都会来问需不需要帮忙——当然坚持自己的东西一定要自己收拾好的她一律回绝了…毕竟万一收拾的时候被看见了自己保守那么久的秘密就不好了。终于在应允声后,恭候多时的峠宫薰推开竹制的日式障子门,带着一盘茶水跟和菓子一起走到她的身侧,很快放下来殷勤地为其倒茶。
说起来好像在来这里之前断断续续地做了梦,如月莲实看着这杯绿茶,暗暗回忆着梦里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她也清楚自己不应该为了那点纠结心情撒先前那个根本没有必要的谎,去编织这数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由生疏到熟悉,充满了私人仪式感的走近,磨合的过程。她们分离与再遇间相隔甚久,这段没有任何交集的时间让本就缺乏安全感的女高中生有些情绪无法流通到正确那处,分不清这会儿应该欢呼悦雀还是平淡对待。且不用说再见面让她是否开心了,抱着绿色缎带小熊这人心里最优先到位的竟是尴尬和不习惯。
短暂沉默间峠宫薰发现眼前那位开始分散注意力,这让容易吃醋的女孩开始十分在意地凑近,甚至一直到她几乎鼻尖要和对方碰到一起了,才终于把人从幻想里拉了回来。当然,是一副惊恐往后倾倒的样子,这更让后辈在意被自己吓得睁开颤抖双眸看过来的如月莲实在想什么事情。是有什么顾虑?或是,心中另有其人?那视线无意识露出了威胁与侵略性,把年长一方毫不留情地抓进青绿色的牢笼之中。
每到休闲时间如月莲实都会将白银色的长发简单地扎成高马尾,发质松软但微卷,背朝地倒下散在青色竹炭芯榻榻米上,脸颊泛红难为情的样子真是十分引人遐想——这差点让本在不悦中的峠宫薰也被脑里延伸出来的映像勾走了。骗子小姐撑起不安挪动的身体,提醒对方这行为的不妥,很快她们尴尬地挪开身子,再度重新远离开始保持礼貌的半米距离,在彼此身侧正坐着。
峠宫家的大小姐家教良好又懂事,马上清楚这些事情不能强求,更不能逼迫。当然也自然明白阔别已久的幼相识为什么会这样反应,或者做出了那个选择。于是峠宫薰即便心急如焚地希望拥抱如月莲实,最后也还是再三思考地变更为耐心等待她的心结解开,再把自己心中缺陷那部分慢慢弥补上。接着为了缓解彼此之间让人不安稳的距离,大小姐选择率先开口。
“您累了吧,一个人收拾了那么久,真的辛苦了。”
“收拾一下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
说罢如月莲实拿起茶杯轻嘬一口。
“床铺的话,家里还有多的,待会我为您拿过来。”
“接下来一段时间要劳烦你照顾了。”
这话说得听上去她几乎要转身过去给峠宫薰磕一个,太拘谨了,让年下一方心里听得痒痒的。在简单交谈过后双方又再次落入了尴尬的沉默,斟酌了半晌,后辈还是没有将心里那句话问出去,果然想要迈出一步对彼此来说都很难。另一边如月莲实虽然正坐着,压在臀后的脚趾却在不安分地相互摩挲,像个不好意思的小孩对着手指。当下明明有空调吹出的凉气降温,空气的焦灼程度却在逐步攀升,两人都几乎要把汗闷出来了。
“那个。”
那个——尴尬氛围下同时吐出这一句提起话题的语气词,如月莲实那张脸本就够红了这一下更是把她干得变成一个红苹果。这下坏了,沉默再次笼罩到她们之间。
“如月前辈,您可以先说。”
峠宫薰尽量压平自己的语调说道。
“不,不,你,你你先吧,我是你前辈,让着你是理所当然…”
跟所有人都一个乐天派兜兜转转玩闹样的如月莲实就这样口吃了,甚至在这话语刚落期间整整停顿了五秒上下。令人想不到的是,平日不苟言笑的峠宫薰反倒先禁不住笑了出来。她眼前沉静平和那人产生极大反差带来的信息量太大,望着这几乎笑岔气的样子,年长一方恼羞成怒地拍到了地面上。也笑得太过了吧!她既心急又憋不出几个字。十数秒后被笑意充满的后辈勉强睁开眼睛,差点又因对方紧紧抿着双唇极为可爱的模样,再度陷入比唐突爆笑更难调理的急促呼吸中。
这下倒也缓和了先前蒸炉一样的氛围,逐渐从笑声中爬出来的峠宫薰自然地前凑去,贴到那热乎柔软的脸颊边。这相较于自己稍凉的体温俘获了怕热的雪国人,她的身体诚实地响应对方,很快两个人没有意识地就贴近到了一起,哪怕刚才火大的心情也马上褪去了。
这就和以前一样…这一瞬让如月莲实那天谎称已经不记得此事的事情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她几乎要沉溺到对方清新的香气中。伪装成亲近友好姐妹关系时,骗子小姐总会相当提防发生这些事情,如今却正像打开了水库阀门那般难以关闭——好香,好难分开,不久前出于奇怪的距离感撒的谎不允许,可这样柔和的气息顺利安抚了那股不安,最终还是顺从了这般行为。
终于,她做了先开口的那一个人。
“那…那个。”
“请说。”
“……我有东西要给你。”
接着,如月莲实从行李箱中取出最后没有拿出来的包装袋,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自己跟前。一些家教修养让峠宫薰不会在对方有要说的话的时候开口,以免截断思绪,不过瞥见眼前女性用手指轻触纸袋引起自己注意的样子,她才回忆起喜欢的人是不愿主动说话的类型。
“请问我可以打开么?”
“都说了是给你的,开吧。”
“那请容我恭敬不如从命。”
沙沙。此举带来听见包装袋逐渐敞开的声响,这让不敢直视和面对身旁那人的如月莲实更加难以动弹,在这段杂音中还有一声峠宫薰在倒吸气的声音。百般飘动的视线追寻过去,看见的是那人双眼中饱含爱与喜悦的笑意,就是那样幸福的样子。
她想见到的样子。
“真的可以收下吗?”
“我不愿说第三次这是送你的。”
“您说了。”
“烦,烦死了啊!不要的话可以丢了!”
即刻眼前一本正经的人把小熊贴到自己脸边,相当有意地露出可怜的样子。
是啊,是如月莲实那个夏天没能完成的缝纫熊偶,专门为自己制作饱含心意的可爱小东西。峠宫薰不可能不收,不可能弄丢或者嫌弃。就像她没有拒绝成为自己的“姐姐大人”一样,应那个夏夜之约而前来的女孩更是愿望着与对方紧紧相依。
“莲实一心一意缝出来的小熊,我怎么可能不收呢?”
称谓的变化让如月莲实才终于注意到了如今已经暴露出自己记得那一个约定的事情,百般尴尬上涌而又开始难以调理自身,她应激地向后退,向后退,甚至开始找借口要离开这个房间。然而身后实际上已经是这个房间最深处的墙边,此时被逼到绝路的女性发着抖将视线转回到跟前…
完了。
“莲实,我想撤回前言。”
“哈…?”
“其实我家没有被子了。”
“演的吧!!”
“如果再见面的时候我还抱着那时候的心情,您就会答应我一切事情,对吗?”
“话…话虽如此…”
“请和我睡一张床。”
峠宫薰丝毫没有打算放跑自己,早已紧逼到跟前。
这场攻防战看来是如月莲实完败了,她后脑贴在墙边,认命地低下了头,没有明确答应,更没有拒绝自己心爱的人。这一段情景,似乎也都在那弥漫煎茶香味,破碎的梦中出现过,一股宿命感油然而生。意识到断续内容接起来了,那么接下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情节,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那个才是。至少在下一个瞬间峠宫薰再度凑到与自己近在咫尺的位置,双唇紧贴在一起之前,都是这样想的。就好像等这一刻等了好久好久,此时此刻展露出来的点点滴滴,皆为解开她内心宿命剧本的钥匙。
那只看起来有些可笑的小熊,当初缝纫它的心境似乎此时又再次浮现在了如月莲实的脑海里。她希望收到这孩子的人能为此心生幸福,哪怕不是自己所向的答案,只求那个人喜欢,这便就是独一无二的幸福。随后浓郁的煎茶味逐渐散去,取而代之以清新柔和,如风一样爽快的雨后竹林的气息。
“能再见到您,真是太好了。”
峠宫薰松开腕上的珠串,将其与如月莲实的手一同和自己缠绕紧扣一起,这下继续维持那似有似无的姐妹关系,似乎也都有些不合时宜了。若说给圣母大人听,必然会降下触犯禁忌的天罚吧——
当然这无法撼动本就不忠于天的有毒巨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