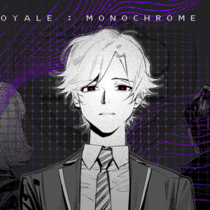雨。
其实还没下,只是浓云滚墨,氛围潮湿压抑,黏稠的水汽凝成一片蒙雾附着在所有人身上,宛若已经下过一场淅淅沥沥的雨。
无风,无声,只有草木寂寥,青山环绕。
段伍沉默地看着面前的人。
还是记忆中的身高,足足八尺有余,隔了些距离还是得略微仰着些头看。虽然看似是随意站着,但是也能从对方站立的姿势、两腿之间的距离、膝盖的承力看得出此刻他的重心微微下沉,典型的不知道蹲了多少年的马步的职业病。整体看去,对方的身形修长,体格壮硕却不突兀,应是经历过系统的训练。但偏偏那人此刻又是一副青绿色粗布外罩衣襟大开,内里白衣随意裹挟的模样。细细看去,便可看出此人身上的服饰布料的边缘早就因为因为长期没好好清洗而泛黄,完全就是把不修边幅几个字写在身上。好吧甚至不仅仅是身上。只要稍微把视线往上抬抬就能看出对方的胡子拉碴不知道多久没剃,被油垢粘成缕状的长发凌乱遮住半边面庞叫人看不清面容,然而即便如此,这人的存在也是极为不可忽视的。一双持刀的手满是老茧与风霜。袖袍之下,三寸寒光利利,骇然便是一把威风凛凛的金背九环刀。
对方没有动作,段伍自然也没动。
他不是蠢的。虽然他觉得自己掺和这事真的很对不起天天在家里念念叨叨的段师傅。但是来都来了,若不把事情的真相解明,他估计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觉的。眼下,他仔仔细细分析了一番现在的局势。矿洞事发,左呈梧第一个带来消息,旋即之前一起下矿的原班人马便快速集结,然后就是洞口被炸掉的事。
“我就知道矿洞有问题!”左呈梧随手把刚拆下来的机关丢得老远。机关术是他的老本行,难得出门一趟采风顺带找人,谁知道这边塞城市的矿洞里还真能给他碰着机关。大部分机关的构思精巧却也算不得高超,他来这地方跟回老家逛菜场似的。
“来都来了。”子奕连声劝道,剑身下压再旋,无形之中已然悄悄化解傀儡的劈砍,再一套熟练的借力打力削飞了傀儡的一只手臂。所谓剑舞空灵、刀行沉重,金身傀儡力道虽大,但却受制于动作迟钝,正好被他的剑法克制得死死的。
段伍段四没说话,地上的蛇有点多,饶是段伍提前准备的雄黄也有些不够。空间狭窄地方闭塞,也不能用烟熏之法驱蛇。松石和剑来早已躲进段伍的背篓,露出个小脑袋大声叫着努力声援。四人边打边退。不知进了哪个窟窿哪扇门,蛇虫倒是不追了,意识却骤然模糊,视线的最后仅是铺天盖地的符咒。再睁眼时,映入眼帘的已经是这方天地。
寻常人或许会疑惑,这场景切换的速度过于快速,饶是话本也不敢写这世间有瞬移的法门。如此便极容易推断是自己或许是身处幻境。但有时人又会自我怀疑,譬如,现在的自己是否是在梦中,还是其实现在才是现实,出山之后、在陇玉城的经历才是做过的一场梦?这问题倒没难住段伍。他心里早已有了明了。松石不在,这里肯定是假的。他一向很是清醒。
现在对方没动,他也不做主动。
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应当抢占先机。敌我双方实力不明的情况下,以静制动也是一种稳妥做法。
他行事向来稳妥为上。
两人就这么僵持了一会儿,对方终于忍不住了,率先开了口:“你其实已经知道我是假的了吧?”
段伍点头:“确实。”
“怎么发现的?”对方好奇问。
段伍沉默了一下,说,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你长什么样了。
一道恰到好处的微风拂过,浓郁的墨色额发之下,露出的是一张没有明晰五官的脸。
“我草。”那人登时骂道,“段伍你个小没良心的。”
“你不会连我的名字都没想起来吧?”
段伍移开了视线。
这不能怪段伍。他们认识的时间总共也没有超过十五日。又早在四年前,那会儿段伍才十二岁。
他一个人去山上找素材,按着规矩本来是要赶在日落前回家的。谁料在山里上蹿下跳打算回村的时候,只是走在山路上就不小心踢出一个人来。
这人浑身是血,样貌凄凄,衣着倒是华丽,一把大刀看上去威武帅气,可惜人的面色看上去是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段伍犯了难,想起听别人常念叨的话本子,这种人大概就是传说中被追杀沦落至此的,擅自叫人反而可能惹事。于是他在山上寻来草药,给对方简单包扎了下。也没通知外人,就把人拖到洞穴里养着。
头一天这人没醒,第二第三天还是没醒。高烧连着四五天,好几次段伍都觉得这人要嗝屁了,结果对方眼睛都没睁开浑浑噩噩就开始开口问候人名,上至天皇老子,下至江湖地痞,有名都没名的都问候了个遍,在山洞里形成回荡不停的折音。虽然荒谬,但这高热居然应是给他扛了过去。
第七日的时候,这人总算是醒了。两人都是直性子,交流了几句,便已经互相有个基本了解。果然是熟人背刺、仇家追杀,那人骂骂咧咧念叨了许多,段伍一个字都没记进去。最后,他看了看段伍,说:“我现在浑身上下没什么东西,就这看家的刀还是块好料子。这把刀给你,你拿去熔了,去铸你的剑。”
段伍摇头:“这刀沾过太多血,不好使。”
“啧,哪来这么多讲究?那你就做成菜刀去。到时候拿回来给我用。我已经决定金盆洗手了,这刀不必再出现在江湖。”
现在那三把菜刀正躺在段伍的背篓里,所以段伍更能确定眼前这人更加是幻境的了。
两人都没打算先手,于是他俩就这么大眼瞪小眼。
对方说要不你来打我吧,段伍说不行,如果幻境内外的动作同步,会伤着其他人。
对方说那咱俩干站着?段伍说也不行,说不定会被其他人打。
对方气笑了,说那咋整,我自己自尽了?
段伍说这最好了,你赶紧的。
对方沉默了片刻,说,你在试探,你在验证这里是否是根据你的记忆映照出来的幻境,依据便是这里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心里幻想得出来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段伍说,”那我就不会死在这里。“
“因为你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滋味?”那人放声大笑,“那我来提醒你,你分明经历过。”
于是声未至而刀锋已至,段伍拔剑格挡的动作与对方出刀劈砍的动作几乎是同时进行。金属碰撞发出尖锐刺耳响声,昭示着此番并非演练与教学,而是实实在在的刀与剑。
对方反应极快,在刀身被阻挡之际登时翻腕侧刀令刀身与剑身擦过,借着第一劈的顺势换腿往前大踏一步劈砍出第二刀。段伍自然不会硬接,他直接连步后撤同时左脚震地,右脚却是轻柔缓点,绵延接下汹涌来势又不会拉远距离,在近身的片刻便可反手执剑而令出单手振拳直击对方面门。这是太极的巧劲,这两天他跟城里头的武馆现学的。姿势不咋地,但所谓狗急了也能跳墙,临危之际也被逼着用上了两招。
几番招式交错,电光火石之间,两人的身形已经打成一处。
剑走奇门,刀踏中宫。
拳风阵阵,金石铿锵,身影交错之际,隐隐约约却荡起一些往昔的回忆。
乃是一大一小两道声音,年龄差听着就极大,一来一去插科打诨,彼此间的语气熟稔得却像是多年老友。
“等我恢复了,我教你刀法。”
“不学,我要学剑的。”
“哎你这小子,你知不知道我的刀很多人想学?”
“关我什么事?我就想学剑。”
……
“锵——”
长刀直直没入树干两寸入无物阻拦,力道之下震下一树枯黄叶片骤然洒落。与此同时,段伍感觉到一股猩红热流顺着自己的额角蜿蜒而下。眉际是钻了心的疼痛,竟是仅凭刀风就生生削下一小块肉来。
“你是工匠,因此你总会下意识不敢太过发力,怕把手震坏。”对方笑,“这个习惯你还是没改。”
段伍没有接话,他有些恍惚。
那一日也是这样,这是他们唯一一次对打。天寒料峭,对方病情骤然加重,身体虚弱,弱得连他这个十二岁的孩童都能接上几招,然而姜毕竟是老道,他终究是没能打过。九环佩刀就这样钉在他的身侧,环扣相碰叮当作响。像是遥远的铜铃,也是催命的厉鬼,浓郁的杀气迫得他喘不上气,对方是真的想要杀他,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离“死”如此之近。
他不明白对方要杀他的理由。他们之间差了整整二十岁,彼此没有任何冤仇,甚至他算是对对方有恩,延续了对方十五日的性命。他在后来的日子花了一些时间去理解,去探究,但没有一个人能给他正确的答案。是因为不甘自己的生命就此折损,还是想要这刀再沾上一次鲜血?是觉得一个人走黄泉路太寂寞,还是说……只是单纯的,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一辈子之后,如今,仍是想要死在交锋之中。
哪怕现在身边的对手只有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
……
“那一天,你没有杀成我。”段伍的声音很平静,沉稳但有力,如同讲述每一次他所认定的既定事实,“所以现在,你也杀不了我。”
刀客不作答,一柄剔骨刀不知何时穿透了他的胸腔,直直刺入他的心脏,刀确实利,切人骨若葱白豆腐,是那三把厨刀中的一把。他想要开口,却从喉呕出一口血来,他想挣扎,伤口因此被扯开,堵不住的鲜血汩汩往外流。
那看不清五官的面庞上,终于在此刻清晰刻出了一张带着无奈和欣赏的笑脸。
“怎么做到的?”那人问道,“我分明已经避开了你的剑。”
段伍说:“可能因为我用的是刀法。”
对方满是不可置信:“弃剑习刀?你?怎么可能?谁教你的?”
段伍语塞。其实他不是故意要学的,但是是个人被连着揍三天也能揍出点什么啊。这念头在段伍脑子里一闪而过,他很快斩钉截铁道:“不关你的事。”
“……这样吗。”对方愣了愣,或许是感觉到生命流逝,所谓人之将死其念也淡,他很快释然,整个身子都随着力道的卸去软了下去,重重地倒在地上,“你已经往前走了啊。”
段伍没回答。他收拾东西,觉得再不出去其他人就要等急了。
就在他打算走出幻境时,身后忽然传来悠悠的声响,带着一丝怅然:“后会有期?”
段伍回头,远山与人皆已不见,留下的仅是一片空落落的黑芒。
“……后会无期。”他说。




*与连衡交换了银奢靡与铜奢靡
*构了对赤梁作战的主要部门
连衡得了令,要往中军大营处议事,于是驾上那匹通体棕红、赤铜鞍辔的河西马上了路。
近了中军大营,见得士卒装备齐整,操练整队,甲胄上粼粼地泛着日光,连衡暗暗点头,知晓镇守此处的确实是精锐的甲士。大营正中扎着一处旗杆,旗杆的顶端却不是什么令旗,而是一柄巨大的伞盖,金赤的丝绢随着谷地吹来的秋风猎猎作响,便是指示着皇帝所在的龙纛。龙纛之下又有连成一片、井然有序的营帐,那传令兵便引着连衡来到一处系着赤色丝绦的大帐处,想来这便是议事之所了。
掀开大帐的门帘,连衡只觉视野暗了一暗:这营帐不比长安的官衙,未有什么开窗,秋日夹杂着枯草气息的微风与阳光便被隔绝在了外边。帐内点着碗口粗的御用烛灯,放着影壁似的屏风,及座椅五张。一处圈椅面朝大帐门帘处,背靠屏风,雕着各路纹饰,坐北朝南,底下还铺着张赤色的毛毯;另四张座椅背对门帘,未有什么装饰,两前两后,整整齐齐地面对居中的座椅摆放。
靠近圈椅的一侧,有一黑发红袍之人落座。此人神色淡漠,只对连衡点了点头,乃是右威卫大将军,三皇子晁承祐。以他的地位,按理来说不该这么早入得营帐的,但此人向来便对这般礼节事物不甚在意,便在此等候了起来。
在晁承祐之身后,另一处座椅上坐着红衣披甲之人,羽林军将军花既白。见着连衡前来,也不做言语,只微微闭着双眼养精蓄锐。连衡只对着二人拱一拱手,于花将军身侧落座。他并非什么好言论的性子,只默默地盘算起行军后勤一事。
帐中的三人如此各自落座,一言不发。帐外不时有士卒巡逻路过,帐中便回响起甲胄敲击的声响。又过了不久,有马蹄声传来,营帐的门帘“哗啦”一声掀起,镇军大将军、武安公主晁允夏走了进来。此人身披全甲,也不对帐中三人行礼,只径直走向那处仅剩的空座椅,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
按照大烨的官场规矩,开会前的时刻,向来是为参会的众人结党营私、打听各自机密事宜准备的。哪怕非是互相勾搭,仅是互行个里,说两句天气或是健康之类的寒暄也是十分正常的。只是在座这四人,各有各的一番心思,对开口寒暄之类并不上心,也让这议事的营帐安静异常了。
帐中气氛凝重,四人却不以为意,依旧一言不发、各想各的。然而营帐后门的门帘一转,未曾有人听闻靠近的脚步声,一个白发白衣、人树间杂的诡异身影便转了出来,自顾自地坐到了主位的那处圈椅上。
“陛下……”“父皇!”
见此人落座,下位的四人这才各自起身,对着上位处的身影一拱手。行军时,为示自己对打仗的重视,披甲之人无需行全礼,而是以简化过的拱手礼为军礼。上座那人在圈椅上调了调位置,使穿胸而过的桃花枝不至于碍着视线,才受了这礼,摆了摆手:“诸爱卿请坐。”
“我们谈的是灭国之战,也无需那些繁文缛节了。”大烨皇帝、太玄子挂着众人读不懂的笑意开口了:“赤梁兵马众多,各位爱卿可有什么方略?”
这不合议事流程,但今夏的几番灾变以来,朝中众人也未必讲究什么流程了。三皇子晁承祐起身拱手:“愿领军镇守中军,宿卫大营!”
晁承祐在京中便是领了禁军守卫京城的,而今请愿镇守中军,更是挑不出什么错来。此人不好名声功绩,对他来说,镇守中军确实是一个相当适宜的选择了
只是晁允夏皱了皱眉:“入了战场,还在想护着身家安危么?自古有请愿当前锋的,未曾听闻甘愿做中军的。”
“公主这话哪里说得,右威卫大将军这些年率禁军护卫京城,功绩有目共睹,众人皆知,宿卫中军有何不可?”连衡反驳道。
花既白微微摇头,似是不愿牵扯进这番争执,只叹了口气。
晁允夏也不顾连衡的反驳,起身对着太玄子一拱手:“某愿为前锋,为父皇犁庭扫穴!”
“将军行事这般鲁莽,可小心中了赤梁人诱敌深入的计策。”连衡反驳道。
花既白又一叹气,也不知是为了什么。
“若父皇有意亲率大军,又何必居于中军大帐呢?”晁允夏高声说道,“以父皇之能,与我共为前锋,定叫赤梁人有来无回!”
“如此将陛下至于先锋军中,公主将陛下的安危置于何处?”连衡反驳道。
花既白用力闭上了眼,似是不愿再听这般可笑的军议。
“连尚书!有空在这里批驳,倒不如请缨做些什么。”晁允夏皱起了眉头,对连衡怒道。
“在下身为兵部尚书,自然要负责补给线的完备。”连衡反驳道,“难道公主要让大军饿着肚子进攻不成?”
花既白撇了撇嘴角,又叹一口浊气。
“花将军几番叹气,可是对我的布阵有何意见?何必在底下这般气馁,不如说来与大家听听。”晁允夏又将矛头对准了花既白。而花将军只一如既往地以忧愁的表情回之。
“花将军在思考战略,又何必打断思路?”连衡反驳道。
“三哥!”晁允夏转过身,对着身侧的晁承祐,“你当真不自请做前锋?”
“我……我?”三皇子愕然,好似一场神游终于醒来,“有我的事了么?”
太玄子挂着莫名的笑意看着下方的争执,额头上长出的桃花枝也一抖一抖的。眼看素来脾气直爽的武安公主几番握拳,终于在这一场军议演变成武斗前开口:“坐镇前锋……倒也合我的胃口。仍需设置中军大营么?我看倒不必了。四方拱卫只在堂堂正正的对垒中管用,至于这次……”他仰着头,嘎吱嘎吱地将视线扫过一圈:“此战也非是寻常战役,我看承祐就任左卫吧。”
“……”晁承祐眨了眨眼,“……是,臣领命。”晁承祐得知了自己的任务,于是安下心来,又坐回椅子上神游起来了。
“父皇说得是,此非是寻常战役,还请几位专心议事,共同进退!”晁允夏为太玄子做了总结,又向着众人一挥手:“我看也不必有什么前后军的区别,我们率众一同冲上一波……”
“还请公主多多考虑后勤之事!”连衡反驳道,“常言道,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难道公主不屑做这等袭扰之事?”
花既白似是不屑地叹了口气。
“既然连尚书这般积极,不若将袭扰之职一并承担了便是。”晁允夏偏过头去。
“在下的兵线已布置在了后方的补给线上,若是这般摊薄兵力,被赤梁寻见了弱点,又是谁的责任呢?”连衡反驳道。
花既白偏了偏视线,一言不发。
“这也不能那也不能,我看干脆不要袭扰算了!”晁允夏怒道。
“有机会却不去削弱敌人,哪里有这样打仗的呢?”连衡反驳道,“花将军常常奔袭作战,我看切断赤梁的补给线就交给花将军好了!”
“我……唉!”花既白又深深地叹了口气,“唉,臣领命!”
-
“会开完了?没通知我呀。”
晁承祐后人一步从营帐里走了出来。天色已晚,士卒已点上了照明用的火堆。又有士卒捧着军令立在人群聚集之处宣读今日军议做出的决定:
以镇军大将军晁允夏为先锋,镇守战场正中,迎敌回击。负责一应战事。
以右威卫大将军晁承祐为左卫,攻敌侧翼,迂回作战。
以兵部尚书连衡为右卫,负责营地防备及粮草供给。
以羽林将军花既白为奇兵,绕后袭扰,断赤梁粮草及其他一应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