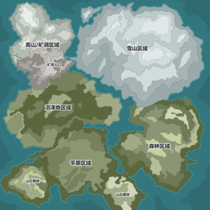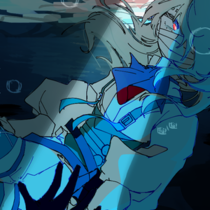各位秘宝猎人,舞台3已公布。具体请移步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5025/




感谢玩家【本不是喵】的一章言弹整理!
地图/死者档案:
非日常: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3435/manga/#manga1
地图: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1742/manga/
巡逻鲨鱼放置室:
【巡逻鲨鱼排班表】by 才波 朝阳、彩泽 弦乐
每个鲨鱼每隔20分钟交接一次(需要进行充电)
每一只鲨鱼充电15分钟,巡航20分钟,充电完毕的鲨鱼会在一旁进行5分钟的睡眠待机,睡眠时间结束则会再次开启巡航。
【巡逻鲨鱼使用说明书】by 才波 朝阳、彩泽 弦乐
巡逻鲨鱼是鲨ki社畅销的产品。仿真的外观,冰冷坚硬的内心。只会执行程序的死脑筋和从不插队补充能量的好品质,以及配备咬合力超强的上下颚,则是本产品的最大卖点。这么完美的巡逻保安鲨鱼产品在这里可找不到第二个!顺便一提娇小可人的嘴是鲨ki社长别出心裁的设计!
【近几天的巡逻鲨鱼巡航显示器】by 才波 朝阳、彩泽 弦乐
鲨鱼巡航的记录会被保存在时刻表上
第一天的巡航时间记录
00:00-00:20 01:00-01:20 23:00-23:20
00:20-00:40 01:20-01:40 ~~ 23:20-23:40
00:40-01:00 01:40-02:00 23:40-00:00
案发当天凌晨的排班表:
00:00-00:20 01:00-01:20 (无显示)
00:20-00:40 01:20-01:40 (无显示)
00:40-01:15 (无显示) (无显示)
【鲨鱼充电装置】by 羽海野 奥罗
装置在距离出水口非常近的地方,很明显是巡逻鲨鱼用来进行充电的地方。只要想象成自动扫地机器人充电的地方就很好理解了。充电完毕的巡逻鲨鱼会从这里出发巡逻。每次充电的时候只能容纳一只巡逻鲨鱼。
【废弃的充电装置】by 羽海野 奥罗
干净的和对面充电装置一样。
【备用鲨鱼待机位】by 羽海野 奥罗
放置了许多备用机械鲨鱼的地方,每一只的背鳍上都写着数字。分别是一号备用,二号备用,三号备用,并没有被启动过的痕迹。
巡逻鲨鱼附近:
【三号巡逻鲨鱼】by 须弥山 尸罗、伊佐木 欣弥、飞鸟井 白哉
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巡逻鲨鱼,发现的时候嘴部呈张开状,看起来是因为电源耗尽,将死者的头部拿出来时,可以发现机械鲨鱼嘴里有着类似充电接口的装置。
【三号巡逻鲨鱼身上的痕迹】by 伊佐木 欣弥、飞鸟井 白哉
表皮上的有一个很浅的孔。
【三号巡逻鲨鱼嘴部】by 须弥山 尸罗、三千院露利
发现的时候嘴里含着死者的头部,尖牙上有着肉屑和鲜血的残留。
【三号巡逻鲨鱼充电口】by 三千院露利
位于上颚,已被肉屑堵塞。
【一号和二号巡逻鲨鱼】by 须弥山 尸罗、狮子原 清隆
由于被三号堵住充电口而挡在外面的两只巡逻鲨鱼,均电源消耗完毕并丧失了行动能力,身上没什么特别的,嘴部有着和三号一样的充电装置,发现时嘴部紧闭,稍微用一点力就可以打开。
海滩:
【尸体情报】by 黑田 梦、師走 坂鳥
死亡原因为颈部断裂,失血过多。衣服已经被海水浸湿,身体和衣服完整,并没有挣扎的痕迹,皮肤有些泡出褶皱来。
死者档案上写的时间为清晨,尸体颈部血肉模糊。 除了颈部,身体上没有其他伤口。
虽然有一些血肉模糊,但脖子断面的血管呈现的样子,确实是被锋利的东西一下子切断的。
检查胃部残留着一些面食,肠道的情况是食物刚进入食道。死亡时间不超过六个小时。
胃部没有其他明显残留同时也没有积水。
【海滩上的模糊讯息】by 秋田 阿卜杜拉
在刚到海滩上的时候,第一眼看到沙滩上有字“xxxxx”,只能依稀辨认出笔划看不太清楚了。
【残留的灰烬】by秋田 阿卜杜拉
在燃烧殆尽的灰烬里用手去触碰,似乎有一根未烧尽的线头
【捕鱼装置】by秋田 阿卜杜拉
位于巡逻鲨鱼放置室最近的装置里的鱼叉少了四根,其他的装置鱼叉数量正常。
【建筑物上残留的痕迹】by秋田 阿卜杜拉
有一些细小的荆棘被折断了,落在了地上,朝上面看,有一些残留的线挂在那里。
其他(塔内):
【厨房记录】 by 黑田 梦
八千代 绢色
花山院 香绪里
黑田梦
山鹿 伊织
三千院 露利
湖湖
叶山 根子天
羽海野 奥罗
黑田梦
【犬伏伸司】个人房间的言弹及额外信息 by 新谷 蓝市
【一份报纸】:知名探险队雪山遇难,十九人丧生,超高校级的探险家,是否名不副实。
全篇内容均在批判这位探险家所做出的抉择害死了一个团队
【犬伏伸司的日记】:
1. x月x日x年 考试日
考试,虽说是疗养院的常规目的
但自身并不是为此而进入的疗养院。
必定无法通过的考试……不过院长会在意这个吗?
完全不了解治疗师,火鸟同学能通过吗,她已经完全是个合格的治疗师了吧?
。
黑板上的字改变了,变成了超常规的离奇的内容。
还冒出一个玩偶鲨鱼,说什么自相残杀,意义不明。但以这个鲨鱼的灵活性看来,制作者应该很不了得,为何会绑架一群人做这种无聊游戏。
教室确实是考试场地,但其他房间却不是。
建筑物没有出口,周围的房间看上去也是普通的建筑。
这样的大工程,有官方参与的可能性吗……?
八千代的茶会……或许能安抚大家的心情
。
有自动贩卖机,至少基本的饮食在这几日内能够保障。
虽然这么想有些糟糕,但专程绑架一群人过来,大概率不是为了让人饿死。
2.x月x日x年
大脑有些混乱
想比起前一日的鲨鱼玩偶,今天的内容着实有些夸张。
海天逆转……
怎么想都不是现实能存在的场景!物理上都不会允许,总不会是被外星人绑架了吧。
这里的生活设施很齐备,看来需要长期生活。
……
又是杀人游戏
(一行小字)鲨鱼玩偶有了制衡玩家的手段,看来游戏的进行是必然了。
作为被“外星人”观赏的“斗兽”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境地吗?
(一行小字)无论是外星人还是虚拟空间或是梦境,这超现实场景……常理来看无法逃离吧?
破坏鲨鱼玩偶的手下也许是个办法。
【温泉混浴】by 叶山 根子天
在温泉有过洗浴痕迹,但没发现衣物,厕所无异常。
追加询问鲨ki清洗频率和清洁剂用量的答复:厕所一天一次,浴室三天一次,清洗剂鲨ki说它每天都有在用,消耗状态是鲨ki一早就在用,用量无法分辨
【死者包内物品】by 火鸟 歌桂
小型氧气瓶,应急食物(含自热袋),水瓶带水200ml,防滑手套,安全带*1,锁扣*4,绳子少许(有被切割过的痕迹),滑轮*2,纸笔,液体创可贴。
【绳子长短】by 火鸟 歌桂
绳子比之前短了许多。
突发事件相关言弹
【突发事件-预备计划】 by 须弥山 尸罗
预备计划附近的沙滩上放置着大块生肉·、金枪鱼等
【海滩上的讯息】by 安乐城 他祭【陈述3】
在你们来到海滩上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字“如果能够成功,我希望你们逃出去”
作品链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4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