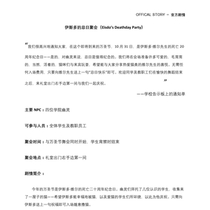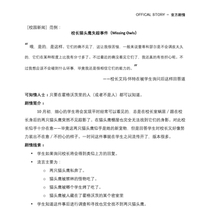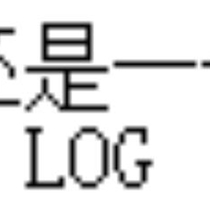


*字数6075,因为大部分还是9月的事情所以想了想投第一章吧
*本文为纯文字版,图文版走这边,手机观看效果最佳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9974/
*大量关于梦的胡扯,求不深究设定问题
希尔达•库珀陷在拉文克劳公共休息室的扶手椅里,壁炉的温暖让她昏昏欲睡,事实上她几乎是睡着了,意识仿佛被挤压进一条曲折的管道。如果不是对面的男生开口叫她的名字,她大概会完全进入梦乡也说不定。
她猛然睁开眼睛,试图装作刚刚什么都没发生。对面的密斯托•文有点担忧地询问她:“是昨天没睡好吗?”
“只是有些热了。”她揉了揉眼睛,像是在做祛除睡意的仪式,“抱歉……我不该睡着的。”
“毕竟很安静。”密斯托轻声说。公共休息室里只坐了几个正在看书的高年级生,只偶尔能听到翻动书页的声音。
“我看过你最近的梦了。仅仅是知道梦的内容还远远不够,可供解读的方向很多,按照惯例,我还需要问你一些问题。”
“嗯。”希尔达点头表示明白。她找到这位高年级生,是因为偶然得知他的家人是《周公解梦新说》的著作者,而他本人也很擅长占卜的缘故。希尔达从以前开始就执着于探索梦的秘密,将自己做过的梦记下来加以解读也是她的必做功课之一。只是自学学到的东西着实有限,书中无法理解的部分太多,而霍格沃茨要在三年级才开放选修课程,这个事实还让她消沉了一阵子。
困扰她的是,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梦。每本书上所说的都不尽相同,一个特定事物的出现往往有着几十种解读方式,至于书中说的冥想,灵感,水晶球之类的方案,她都尝试过,最终只出现一系列更加难以解读的东西。她鲜少向人寻求帮助,但在明白自己已经没有解决的能力之后,依旧如此固执,这就显得有些愚蠢了。
思前想后,她把做梦日记放在了密斯托面前,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答案。
“按照常理来说,预言性质的梦是很罕见的,并且通常都难以甄别。当然也不排除那些有特殊血统的人能够清晰地了解预知梦与普通梦的区别。所以,一般解梦的时候,我通常会尽可能地着眼于过去与现在。如果仅仅是想要知道未来,纸牌占卜或者水晶球也许是更有效的做法,”密斯托抬起头来,“但你明显对梦更感兴趣。”
“是的。”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梦开始吧。”
密斯托把本子摊开,平放在桌面上。
9月7日
她在楼梯上走着。这条楼梯像极了通向霍格沃茨地下室的路,狭窄阴暗,因为梦境的缘故显得更加模糊不清。她向下走,不断地向下走,但螺旋的道路似乎并没有尽头。
不,也许是有的——楼梯消失了,眼前是充满着诡异植物的丛林,遮天蔽日的绿意并不友善,她甚至听到了低低的咆哮声。她向前踏出一步——
她坐在一只猫头鹰身上。耳边的风声告诉她自己在天空中翱翔,先前的不安一扫而空,这时她发现自己又回到地面,松软的雪地上有动物杂乱无章的脚印。
“从表面上看,这个梦显示出你的一些不安。没有尽头的楼梯通常是一个人焦虑的表现,在做这个梦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吗?”
“唔……我想……也许是魔药课。”她之前就注意到,那段楼梯正是通往魔药课教室的必经之路。她不太喜欢魔药课,这种极度要求精准操作的课程让她很犯难,稍不留神就会让魔药失败。她在这个学年的第一堂课上就不幸造成了小事故,虽然没有爆炸,但她让之前的辛苦全部化作泡影。
“我想也许之后的丛林也代表着你对魔药课的不安,我可以充分理解这种感受,因为我也不擅长魔药学。”密斯托安慰道。
“猫头鹰……我原本以为是代表着寄来的信。但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信寄来,我不是很明白。”
“可供解读的方向有很多种。在梦中飞行可能代表你对于突破束缚的渴望,或者是对危险事物的追求,也许只是想打魁地奇……都有可能。”
“也许是与魁地奇有关……”希尔达沉默片刻,“我有了一把新的扫帚。但没什么机会用,学院队的选拔也没有开始。”
“你可能在潜意识中忧心之后的选拔结果,是这样吗?”
“也许。但猫头鹰……究竟代表什么呢?”
“它可能代表很多东西,也可能什么都不代表。并不是每个在梦中出现的东西都必然有其指导意义,”密斯托伸手指了指壁炉的方向,红色的火苗温和地吞噬着木柴。“假如我今晚的梦中出现了壁炉,多半并不象征着我渴望温暖与安全感,而仅仅是因为今天我与你在壁炉旁聊天而已。如果你能完全解开梦境的秘密,那么梦还会像现在这样有诱惑力吗?”
希尔达与密斯托蓝色的眼睛对视片刻,摇了摇头:“我想不会。”
“虽然种种迹象都表明,正确的解梦方法能够让我们拨开迷雾看未来,不过谁又敢说自己是正确的那一个呢,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无限接近那个正确答案而已。所以你也不要太拘泥于正确了。”
“我记住了。”她轻轻点头,又问,“那怎样才能无限接近正确呢?”
“经验,也许还需要一点灵感。有的人天生就有这种天分,他们总能靠近正确的结果,或者说……被真相所吸引。”密斯托停顿了一下。他的眼睛映出炉火的颜色,红发被火光衬托得更加鲜明,希尔达总觉得有些诡异,但这也许是她的错觉。密斯托深吸一口气,又继续说他没有讲完的话:“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件好事,也许无知比全知要更加幸福吧。”
但我想知道,希尔达想。
“雪地和脚印一般来说也许代表了‘留下痕迹’的愿望,如果是动物的脚印,则根据动物的不同也有所区别。不过你还无法分辨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吧?”
“是这样没错。”
“梦就是这样,充满了无法解释的部分,不要过多在意了。”密斯托摇摇头,翻到下一页。
“接下来看看你的第二个梦吧。这个梦相对更直观一些。”
9月20日
她坐在一把崭新的扫帚上,手握着光滑的木头柄。她正在赛场上,所有的人都在雷雨交加的天气里狼狈地飞行。她本该握着球棒,但她没有,她不是什么击球手了,因为她被赋予了最重要的任务。
金色飞贼从她眼前一闪而过,伴随着一道凄厉的闪电划破铅灰色的天空,她飞快地俯冲,挤进一条狭窄的黑色管道,也许是通风口。在那里她失去了扫帚,只能不停地向前爬行。这里狭窄得令人不愉快,她要拼命挪动身体才能前进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金色飞贼嘲讽似的停在她眼前,与她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
下一秒包裹着她的便不是什么坚硬的管道了,而是柔软的靠垫,温暖舒适的感觉让她感到安心,于是她放任自己的意识向更深的地方沉下去。
“试着分析一下吧,在听过我说完上一个梦之后,我想这个对你来说不是很难。”
“唔……雨天……魁地奇球场上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的情况。金色飞贼……应该是……”她悄悄瞄了一眼密斯托的表情,其实她不怎么想说下去了。想追求一个自己都不知道为何物的目标这件事,她不是很想与面前这位还不太熟悉的前辈分享。但对方应该能够解读到这一步,自己无论是否说出口,对方都已经知道了。
“你已经有答案了,不说出来也没关系。”密斯托温和地笑笑,伸手指向其中一段文字,“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找球手这个位置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梦里你会成为找球手?”
“我……我不知道。”她摇摇头。她是绝对不想成为找球手的。被他人注视,被他人期待,成为胜负的关键,这些事情对她而言都太可怕了。
“也对……”密斯托摇摇头,“你毕竟年纪还小。有些事情不去经历是不会明白的,即使是成年人,认识自己也是非常艰难的事……不过这个梦最后似乎平静下来了,这应该意味着你的身边有支持你的力量。也许……是现实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也说不定。”
“?”
希尔达不解地看着他。
“比如梦魇的成因之一只是什么东西压在了胸口导致了呼吸不畅,梦里拼命叫喊的声音只是闹钟在梦境里的投影之类的。所以我想会不会是与你入睡时发生的事有关。”
“……”
希尔达沉默了。他说得对,的确有关。
这一短暂的梦境并不是产生在她的四柱床上。
9月20日,她如同往常一样来到了图书馆。为了应对草药学的报告,她需要找到一本名为《食人植物饲养法》的书。她费了一番工夫,最终还是找到了那本书,只不过不是在书架上,而是在另一个人手中。
白发的高个子男生友好地为她让出位置,并且同意了她借书的请求。她那时还不知道他叫卡洛•福克斯,也绝对不会想到他只是个一年级生,毕竟他的身高太抢眼了。她如同往常一样奋笔疾书,完成了关键部分后便哈欠连天,本来只想趴在桌子上闭目养神,却没想到自己真的睡着了。
密斯托说的没错,寒冷,糟糕的睡姿,压迫感大概就是这个梦的主要成因,至于最后那个令人感到安心的结尾,大概是来源于醒来后自己身上披着的那件外套。她不太敢直视外套的主人,自己给人家添了大麻烦,有些丢脸,可是不道谢不行。她摘下还残留着温暖气息的外套,递交到那人手上,小声道谢。她没察觉到自己涨红了脸。
卡洛则是温柔地微笑着。
“没关系,我想你可能会冷。”
如今她想起这个梦的始末,当天的场景重现在眼前,总让她有点不好意思。她还是不太适应接受陌生人的好意,大概如此。她不便与密斯托多说,便含糊地应了几句,把梦日记翻到下一页。
“这个梦……就有几分预知梦的意味了。”
密斯托饶有兴趣地注视着纸页。
9月30日
起先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她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道自己将往何处去。
渐渐地,面前出现了交叉的路口。动物的足迹出现在其中一条路上,于是她沿着那条路向前走去。远方钟塔的轮廓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她发现她已经来到了钟塔之上,眼前出现了满天星斗,但这星空很快变得扭曲起来,仿佛被什么东西吞噬了一般。
“这个梦也许预示着你正处于人生的交叉路口上。在这个时间点上,你的选择变得尤其重要。你在梦里选择一条路之后,看到了钟塔和星空。钟塔与时间直接相关,代表了一种紧迫感,钟响的时候正是日期变更之时,也同样预示着改变。而星空同样也与命运相关……你看到的是一个从有序到混乱的过程,可能预示着一些不祥的结果。”
密斯托面色严肃,希尔达不禁稍稍有些畏惧。不祥……会是真的吗?
“我该怎么办?”
“试着走另一条路。我注意到是动物的足迹把你引向这条路的,你能分辨出那是什么动物吗?”
“也许是小型动物吧……猫,或者是狗……”
“这与你之前的梦里出现的足迹相同吗?”
“我不清楚……也许是吧。”
“那么最近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联想到这些动物,你就要留心了。不过……即使未来有其预兆,梦中暗示的也不一定是全部,究竟做怎样的选择,还是由你自己来做主。”
希尔达点了点头。密斯托已经将三个梦境解释完毕,她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她打心底里感谢这位前辈。
“这是……谢礼。”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牛皮纸袋,里面装了不少糖果零食,“是家里寄来的,我吃不完……”
密斯托显然没料到会收到礼物,在希尔达的坚持之下最终还是收下了。希尔达松了口气,如果密斯托执意不收,她也不知如何是好。
很快便到了宵禁时间,希尔达取回自己的日记本,与密斯托告别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她开始思考自己9月30日那天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她给密斯托的三个梦境里,前两个都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少许关联,只有第三个梦像是凭空捏造似的,平白无故地出现了那样的景象。
9月30日那天她在做什么?
她记得自己从扫帚棚里取出了自己的扫帚,和卡洛来到庭院,帮他进行飞行课的训练。由于总是能在图书馆碰面,她与卡洛也算熟悉了起来。希尔达为自己糟糕的解梦技巧苦恼时,曾经与卡洛聊起关于天赋的事情。
“家人说我有打魁地奇的天赋,但我……我是说之前,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运动。但占卜学……无论我看多少书也搞不明白,这种感觉真糟。”
“嗯……虽然有人说我的画技很糟糕,不过我觉得自己还挺擅长绘画的。”卡洛拿出自己的涂鸦本,风格鲜明的涂鸦让希尔达吃了一惊。
“酷。”希尔达喜欢这种风格,因为看起来超酷。
“比起这个我更担心飞行课。其实我不是很擅长飞行,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几乎从扫帚上掉下来了。教授说我这样下去也许没办法通过考试。”卡洛平静地说。
“我想我可以帮忙。我有一把扫帚,几乎是全新的,也许能派得上用场。”
“好啊。”
于是他们来到庭院,希尔达站在一旁,帮忙纠正卡洛的动作,学着教授的样子发号施令。
“我数到三,试着腾空,准备好了吗?1,2,3——”
卡洛腾空而起,扫帚摇摇晃晃升到半空,不时轻微地晃动几下。
“试着慢慢降落!”
卡洛握紧扫帚柄,但扫帚突然发疯似的摇晃起来。希尔达慌乱起来,卡洛已经摇摇欲坠,随时可能从扫帚上掉下来,但他似乎并不怎么惊慌,只是短促地“哦”了一声。
“不要松手!”希尔达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寄希望于扫帚能够自己停下来,但卡洛明显已经到了极限,随着扫帚的摇晃,他没能抓牢扫帚柄,直直地向下坠落。
“Arresto Momentum(减震止速)!”
希尔达飞快地抽出魔杖,对着卡洛念了减震咒。卡洛下坠的速度慢了下来,她松了口气,跑到卡洛身边。卡洛跌落在地上,减震咒起了效果,他又正好落在一堆落叶中间,看样子没有大碍。他柔软的白色长发在红褐色的叶子上铺开,像四处流淌的河。卡洛躺在那里,对希尔达露出一个微笑:“能拉我起来吗?”
“啊……”希尔达愣了愣神,伸手抓住卡洛的手,等他站起来之后,又帮他拿掉身上的叶子。她还不太会用清洁咒。
扫帚已经回到希尔达手中,她尝试骑上扫帚,它像往常一样听话。所以并不是扫帚出了故障,是卡洛的飞行技术真的十分糟糕。
“还想再试一次吗?”她问。
“我想可以。”卡洛似乎完全没有把失败放在眼里,他重新调整好姿势,双脚蹬地,升空,不知为何,这次扫帚竟然异乎寻常的安静,卡洛稳稳地升高,在空中盘旋了几圈,颇有种想俯冲下来的架势。
希尔达仰头看他,拿着魔杖随时准备施减震咒,但卡洛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在盘旋几圈后便慢慢下落,还笑着冲希尔达挥了挥手。
希尔达总算是松了口气,也举起手挥了挥。为什么卡洛突然变成了一个如此优秀的飞行高手?她只是稍微疑惑了一下,就把这个问题抛在脑后,跑到卡洛降落的地方去了。
“我想你的飞行课可以得到一个O。”
“太好了,希望下节课我也能像今天这样飞。”卡洛微笑着注视她。
他们把扫帚放回扫帚棚,一起去礼堂吃了晚饭,余下的时间便在公共休息室里继续复习功课。希尔达没有从这段回忆里找到任何能与梦对应的元素,越是思考,越觉得糊涂。
但很快睡意席卷而来,思考成为了无法继续的任务,黑暗拉着她向梦中走去。
10月3日
她向前走,脚下是一条石板铺成的道路。道两旁是开满玫瑰花的篱墙,散发出怡人的香味。
她停下脚步,面前是似曾相识的岔路。一团灯火指引着她,让她向另一条道路走去。
道路的尽头有什么东西在发光,走近后她才看清,那是火光,是什么东西烧了起来。
热浪袭来,她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影背对着她站在那里,那人回头,眼睛里闪着疯狂的光,让她不由自主地后退两步。
她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她知道他在笑。她曾见过这个笑容,也见过与这个笑容相似的其他东西,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她不能后退,只能向前走。在她即将走入火中之时,火焰凝聚起来,变成了一只银白色的狐狸。它在空中盘旋片刻便消失了。
最后,她发现,道路的尽头空无一物。
希尔达在莫名的空虚感中醒来。她觉得胸口有些闷,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她不知道这种情绪从何而来,睁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天花板,才走出情绪的泥沼。
时间还早。她花了点时间记下整个梦境,留待以后分析,她今天有一整天的课程,还要继续做魔咒学的功课,这个梦在她看来并没有那么重要,只是她众多古怪梦境的成员之一,虽然梦对现实世界有指导意义,但重要性绝对不会凌驾于功课之上。
她起床穿衣,下楼用餐。
学院长桌上已经有了不少学生,她随意找了位置坐下,旁边的布莱恩正缓慢地喝着浓汤。
“早上好,库珀。”他笑着向希尔达挥了挥手。
“……”
她本该说早上好的,但看到那个笑容的时候,脑海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不知道为什么,她也学着布莱恩的样子微笑起来:“早上好。”
是他。希尔达咬下一块南瓜派。
那个笑容的主人,正是布莱恩。
TBC
有关希尔达的梦的解析:
9月7日
无尽的螺旋楼梯:对于魔药课的担忧
丛林:紧张感,无特殊含义
猫头鹰和飞行:魁地奇
动物脚印:实为狐狸脚印,对应卡洛和布莱恩
9月20日
风雨交加的魁地奇比赛:预示着未来无法上场
担任找球手:对于承担责任的恐惧,梦想与现实的差距
柔软的靠垫:卡洛给希尔达披上了衣服
9月30日
分岔路口:命运的分歧点
动物足迹:卡洛
时计塔:与卡洛可能的结局之一
10月3日
玫瑰花:与凯莉重逢
火光,狐狸,笑容:布莱恩的妒意
空虚的结尾:如果选择自我封闭后,希尔达面临的未来


分数结算(截止至4.1):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0528/
—
第二章主线剧情说明: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0529/
支线系统: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0530/
—
[官方剧情汇总]
*如有疑问请联系负责该剧情的NPC。
决斗俱乐部: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0531/
校长猫头鹰失踪事件: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0533/
“秋后算账”: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0536/
忌日聚会&万圣节舞会开场剧情: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0537/
—
[非官方剧情汇总]
合唱团: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0563/
MOCKINGBIRDs: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0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