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铲产物
评论随意
我熟练的把小马扎打开,坐在上面,放下鱼竿杆,打窝,带耳机刷抖音,一气呵成。
过了好久好久,我手机抖音都刷的没电了,发现鱼竿还是没有动静。
我呆呆的看了一会,决定把充电宝拿出来继续刷抖音。
就在我准备拿充电宝的时候,发现杆子猛的动了一下,我当下立马去拉杆,本想着这肯定是一条大鱼,终于可以发个朋友圈时,我才发现手感不对,应该是个杂物。
不过本着不空军的想法,我硬是拉了上来,准备看看是什么东西,可是一拉上来我就反悔了。
一个手提箱,外表被黑色发臭的泥沙所包围。
我不自觉的屏住呼吸,准备给手提箱来一脚,送它离开千里之外。
可就在这时,手提箱说话了。
“别别,我是徐鑫,好久不见啊,啊涛!”
我的下巴快被吓掉了!
徐鑫我的大学室友,一个已经成了传说的男人。(remake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昨天网吧包夜的原因,以至于我出现了幻觉。
我的脚又一次的瞄准了手提箱,准备用射门来给自己清醒清醒。
“啊涛,你暗恋欣欣同学!你上厕所小便不冲,每天晚上上厕所要很长时间!”
“胡说,我明明喜欢zz同学,还有你上完厕所小便也不冲,最后我晚上上厕所时间长只是因为我~嗯~因为我便秘,对我便秘!”
“那你应该去看看医生有没有痔疮,而不是每天晚上躲在厕所里。”
“我没有痔疮!”
“那你现在相信我了吗?”
“相信什么?”
“我是徐鑫啊”
“不信”
“为啥”
“因为你是一个手提箱”
“嗯!因为这个,在因为那个,米西米西,话不拉叽,我就变成了手提箱”
“嗯!非常合理。所以我还是要把你送回快乐老家!”
“别!我现在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当然不能违法犯罪,我是良好公民)”
“好,我现在就要许愿,我想要一个肤白貌美,腿长波大的女朋友!”
“好!没问题,安排。”
3分钟之后
“艹,为什么这么慢,三分钟都够我来一发了!”
“有时候太快了,未必是好事。”
“草草草(一种植物),你在玩我!我要你不得好死!”
说完我把口袋里一块钱一个的打火机拿出来了
“嗨嗨嗨!”
“你不要过来啊!”
名为徐鑫的手提箱,疯狂大叫。
只不过正当我拿着打火机一步一步靠近手提箱时,我感觉有人在向我靠近。
我回头看了一下,立马呆住,说不出话。
只能痴痴的挥了挥手 。
来人正是欣欣同学,啊涛和徐鑫的大学同学。
她看啊涛的呆样,不自觉的笑了一下,也挥手示意了一下。
170的个子,大长腿穿着白色长靴,每走一步都踩在啊涛的xp上。
啊涛看着欣欣同学越走越近,并且她身上的香味还随着风飘了过来。
啊涛用力吸了吸清香的空气,慢慢的把身子弓起来,坐在了小马扎上。
在正准备和欣欣同学说话时,欣欣同学因为穿的白色大长靴,走路不方便,被小路上的一个石子给绊到了,身体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衣服变的脏乱不堪,并且发出来一声惨叫。
啊涛此时顾不得生理反应,一下子冲了出去。
“周欣欣,感觉怎么样?”
“~嘶~脚好疼”
说着想把白色长靴给脱了下来。
徐鑫聚精会神,心脏磅磅跳动!
可欣欣同学坐在地上,发现鞋子脱不下来。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啊涛,意思显而易见。
啊涛看了看欣欣,得到了肯定的眼神后,吞了吞口水,手颤颤巍巍的移动到欣欣同学的白色长靴上。
那厚实的靴底让啊涛意识到这并不是幻想,鞋子在往外拉的过程中啊涛随意的把手放在了欣欣的小腿上,紧实且富有弹性。
脱掉靴子,露出黑色船袜,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脚趾的轮廓,啊涛觉得自己的心跳的越来越厉害了!
可就在这时沉寂许久的徐鑫手提箱跳了出来。
“啊!磅臭!呸呸呸!”
啊涛和欣欣同学都惊呆了!
啊涛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后,直接站起身一脚把徐鑫手提箱给踢飞了。
看着手提箱在空中划出了优美的弧线,啊涛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
想着旁边还有美人,立马扭头露出自认为非常英俊的笑脸。
却突然发现人不见了,刚刚还在地上躺着的个大活人,突然就不见了。
啊涛想着想着,发现自己周围的一切已经变了,向雾气散去一样。
在一次微小的眨眼后,啊涛突然发现了一件事,自己大概是已经死了。
在这个夏天里,因为刷抖音,刷的睡着了,沉入了水里,而后自己被水草缠住,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眼看到的就是沉在湖底的手提箱,还想起了那个已经remake的大学室友徐鑫。
作者:狐獴
免责Mode:随便评
猎杀女娲
part.1 旧神已死
简多在冲今天下午第三十三杯起名过长的饮料时,一个提着淡蓝复古手提箱,把自己包的严严实实的女士走了进来。
她扫了一下自己的身份手环,绿色的光闪了一下,绿色腕标意味着来者身份是新人类,罕有但有力的存在。
“赞颂母神!”简多和其他店员忙不迭地齐声大喊,这位女士无动于衷,随便指了个饮料后就坐到了最靠里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手提箱放到了腿上。简多偷偷多看了两眼,那箱子一望便知价格不菲,乳白色的皮革似乎散发朦胧的光晕,箱角的五金暗示了它坚实的一面。可随着那位女士一层层去掉披肩,丝巾,墨镜时,这个箱子便再也不引人注目——她像是童话书里走出来的人物,毫无瑕疵的艺术品。不过简多无心欣赏那么多。
“她刚才为什么不回应?我们之中有谁没张嘴吗?”简多悄悄和负责点单的小姐妹咬耳朵。她们身处严格信奉娲神教的教区,作为普通人,遇到每个新人类都需要向他们赞颂母神的伟大,若否,会被新人类举报登记进虔诚簿里,要花上一笔不菲的请恕费才能消除。
逾越造物的“新人类”产生于一百三十年前,是人为推动基因进化的结果,相较普通人类,他们在基因上被编辑地完美无缺。新人类的诞生对立于达尔文学渐变学说,无论从人口还是社群地位都呈现出爆破性发展,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裂变,“新人类”占到了全球人口数的2%,攻陷了绝大多数重要岗位,社会发展和资源分配有史以来第一次落后于生物进化,由此产生的畸变是无法在此一一论述的,外面一月一度的颂神游行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新人类少有地与普通人类混在一起的时刻。人们集结完毕,努力排得稍稍整齐一点,列队摇着代表各个社区颜色的旗子大喊,人如洪流踏过滚烫的柏油路面,声浪滚滚冲刷人心,队伍走地并不快,却像是模糊的幻影,掠过城市每一个角落。这场盛大的穷极无聊发生在一切网织就的城市里,铺满了渺小的陆地,而在洪流之上3500公里的高空里,七颗“金乌”卫星沉默地计算,注视着人类每一道腕标,每一次脉动。
简多把饮料端了过去,那位女士轻轻说了声谢谢,简多借此机会抬眼仔细看了她一下,可能因为血统不纯的缘故,相比于其他新人类,她美的并无攻击性,美的温和,没那么令人心生畏惧。
她大概不会举报我们,也许是她并不怎么信奉娲神教。简多结合她并未参加颂神游行的行为,大逆不道地推测。店外队伍喊完常用的赞颂,便开始用各种奇怪的话语赞颂母神,凌乱的歌颂砰碎一地,被各色明晃晃的服饰搅成粉末,沦为毫无意义的喧哗。简多在这摊杂碎中只能捡到那个字眼——娲神!娲神!这二字足以点燃荒野与城市,她是新人类诞生的源头,是基因学的盗火者,是屠杀旧神、创造新人类灵魂的人,在她的技术授权下,一百年间各大人口工厂得以稳定产出新人类,她居功至伟,最终被奉为神明,她的生平有诸多神化成分,连真名都不可考,最终变得云里雾里,是个高不可攀的生育神像。
娲神、母神,简多在碌碌人群中被迫信仰她,但她的存在对简多无益。外面吵闹不休,她神经衰弱地摁了摁额角,如果“娲神”真的存在,想必也会因这荒谬的演绎皱眉冷笑。而最可笑的是“娲”的历史原型大概是某位杰出的女基因学家与她的团队,她以科学推动人类发展,人类却把她变成了玄学——在这点上,高低贵贱,新旧人类并无差别。
那位女士大概也不喜欢这样的氛围,她把手提箱立了起来挡在外侧,隔绝了她与外面的视线,这样的举动赢得了简多的喜爱,她悄悄地欣赏了一会那位女士,直到口袋轻微震动,店外人群的游行也将告一段落,凌乱的声音又重新聚拢,汇集成公认的口号。
“旧神已死!娲神永生!”简多在震耳欲聋的吼声中艰难地接起家里打来的电话。
“旧神已死!娲神永生!”同样的口号更为整齐地响在特种作战指挥部,汇集在此的少数精英声如钢铁炮火、信仰坚如磐石,震得空气一窒。而后他们立刻散归各自操作台前,凝神当前作战计划。
“‘基因夺还’计划欧亚分支第079926次行动,本次行动由八个分支队进行,抹除对应八个嫌疑人,本作战部负责六支队行动,目标锁定……”通讯官话语一滞,大厅显示青蓝靛紫的屏上突然跳出了红色的巨大闪动光点,伴随着大大的93.5%——历时七年,经历了将近八万次失败,“金乌”俯瞰大地,又一次向他们发出了醒目的讯息。
“红色高级预警!”指挥官一把抢过通讯器,“娲神教区全体高级武装,评级绿色及以上军官立即出动,目标锁定娲神教区新未来茶饮店!”
当她听到柜台里一直偷看自己的小姑娘对着电话说出“妈妈”二字时,便是心头一紧。她一路躲避这个词语,想在这小店里摘了伪装歇息片刻,还是被‘巧合’撞个满怀——她不该在有监控的地方露出脸来。
她参与“金乌”系统研发测试时,将自己的真实姓名、代号、声纹、面部识别、基因信息通通抹去了,但当时的她过于年轻——狂妄地留下了个最普遍的词语作为自己的身份——“妈妈”。
“金乌”无法将她从亿万呼唤母亲的声音中剥离出来,但模糊的面部、体型特征与这个“巧合”词语相结合,足以引起“金乌”系统的警醒。
还有……这个箱子,这个最致命箱子。她看向她从不离身的手提箱,它是人类的贪欲、是桎梏她的锁链、是对造物最大的亵渎。它虽然被伪装成纯洁无害的样子,但却是潘多拉的魔盒,开启之后,永无宁日。
她一旦被“金乌”锁定,这个箱子就会变成她最可疑的特征。她迅速披上披肩,起身欲离开此地,就见外面游行队伍一阵骚乱,一个荷枪实弹的作战小队踢开茶饮店门冲了进来。
“身份手环。”小队长举着检验器,简洁有力地冲她下命令。
她抬起了手腕。
简多要被吓死了,她接了个老妈让她下班买鱼回家的电话,一挂电话就看见新人类炯炯的目光看着她,她还在犹豫要不要去问一下她需要什么帮助,就见一队特种卫队杀了进来。
小队长捏住她的手腕扫了一下,属于普通“新人类”的绿标。他怔住了,“金乌”系统几乎不会出错,眼前此人被突然判定为“‘基因夺还’目标90%以上嫌疑”肯定是有原因的。
小队长松了指头——这个姿势就算是拉着犯罪嫌疑人也不太礼貌,可当他再瞥向检验器时,他立马把对方抽回一半的手拉住了。
“目标锁定!锁定!”他扔开检验器去抽枪,迭声大吼,“是……”
检验器砸到了柜台,简多看见识别界面不断闪动,明显是出了错误。
可“她”更快,在被重新攥住的那刻便用足以瞬间摧毁金属的力量,反手捏碎了小队长的指骨,她像只黑色的乌鸦突然展翼跃起,精准地踢向小队长战头盔与防弹服脖颈处细微的空隙,击碎了他的颈骨。
小队长软绵绵倒地一瞬,枪声四起,特种卫队所配备的高频射枪,激光切割枪,自动步枪齐开,硝烟如网罩向目标。此番配置足以一瞬摧毁二十人以上的普通军队,却没能奈何那个手提箱,那个女人。
她一眨眼已跃上了墙壁,踩着店内茶饮装饰牌如履平地跨足飞奔,手提箱挡在身前,子弹、光波触之便会改变弹道,向周围散去。她试图窜出茶饮店,可门口又有一队武装搡开人群冲来,火力不管屋内人死活地压制着正门。“旧神已死”的口号早已停了,游行人群惊恐踩踏逃生。
她叹了口气,再次像只象征死亡的乌鸦一样腾飞扑来,用箱子护着,腾挪转闪之间,又是三名队员气绝倒下,她停在柜台上,血顺着她指尖装饰用的陶瓷碎片滴下,融进满地
的血污中。
黑压压的特种卫队成群挤了进来,这次他们没轻易开火,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地站在台阶下,射程包围了柜台每一寸。
她今天除了说“谢谢”之外,又一次开了口。
“没错,我是你们要杀的娲,”丝巾与墨镜盖住了她的脸,看不清任何表情,“基因在我手上这个箱子里,你们最好专心来追我。”
一声巨响,柜台后的玻璃幕墙应声而碎,娲藏在手套里的微冲电磁炮常常大材小用,但无往不利,她在枪响之前翻身撞向如瀑的玻璃碎片中,这些尖锐的匕首已无法伤害任何活人,千疮百孔的柜台后,身穿浅绿色工作服的普通人店员早已无活口。
跳出去的那一霎,娲看到了简多被激光削掉一半的头颅,那试探的目光仍黏在她身上。
火力擦身而过,娲其实很想听她再对着电话喊声妈妈。
ect.
作者:阿苔
评论要求:随意
在热热闹闹的海边都市凯那市里,生活着一个非常害羞又胆小的小女孩桂枝。我们可以叫她小桂。小桂很害怕与陌生人或是宝可梦相处,比起和同龄人聚在一起玩乐或是对战,她更喜欢独自看看书,养养花,或是在森林里散步。不过她也有自己的宝可梦,那是父母在十岁生日时送她的生日礼物——一只刚出生不久的伊布。刚出生的伊布看起来很弱小,毛茸茸软趴趴的,在她战战兢兢打开礼物盒子的盖子时抬起自己埋在蓬松尾巴毛发里的小鼻子迷茫地看着她。‘独自来到陌生的环境里很害怕吧。’她和伊布对视着,在那清澈的棕色眼眸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于是这只名字叫“不怕人”的伊布正式成为了她唯一且最最要好的伙伴。
有了伙伴后的生活变得多彩了很多。实际上不怕人是一只有些瘦弱的伊布,它比同等年龄的伊布要小一圈,娇小的样子甚至被她的训练师妹妹柚怀疑营养不良。但小桂一点也不在乎,她们一起研究园艺,一起在森林里散步,或是小桂给玩耍的它画速写。在一起的她们非常快乐。
一次睡觉前,小桂把不怕人抱在怀里看画册,不怕人毛茸茸的尾巴在胸前不断摇晃,“好痒。”小桂笑着把它抱得更紧了些。“伊布有很多进化型呢……每种看着都很可爱。”小桂的手指在画册上有规律的移动着,给不怕人介绍着每一种可能,“不怕人你有想进化的类型吗?”
“布伊……”怀中的小脑袋不断的来回摆动着,最后扭过头来看向了小桂。“布!”它眯起眼睛抬头蹭了蹭桂的脸颊。
“我来选吗?”桂惊喜的睁大了眼睛,“谢谢你,不怕人!”
“我好喜欢草精灵!就这样约好了哦,进化成草精灵!”
不怕人抬头看了看正欣喜诉说着草精灵可爱之处的小桂,“布!”也兴奋了起来,摇着尾巴舔了舔主人的下巴。
从那天以后,森林里的苔藓巨石就成为了她们的固定速写地点。阳光穿透浓密的绿色屋顶投下一束束暖色光柱,蝶粉般的闪烁粒子没有规律的浮动着,让小桂觉得自己就像躺着水草丛中睡觉的鱼。不怕人在苔藓石周围跑跳着玩耍,玩累了就回到小桂身边趴着休息,顺便享受主人的抚摸。有时它抬起头看到小桂在画草精灵,小小画师的表情分外柔和,翘起的嘴角就像在做一个无比美好的梦。
随着一人一宝可梦的相处时间逐渐变长,家人们开始越加担心桂枝的社交。一次秘密家庭会议后,刚刚写生回来的小桂被告知了自己将要参加华丽大赛这件事。“你的妹妹都拿了好几个道馆徽章了,桂枝你也是很聪明的孩子,努力一下拿到缎带不是问题!”父母笑着按着她的肩膀鼓励到。小桂紧紧抓着自己的裙子低下了头,感受到不怕人担忧的目光,她挤出一丝微笑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会努力的。”她抱起不怕人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参加华丽大赛的事情已成定局,小桂不得不大幅度压缩自己的写生时间练习那天要表演的内容。一天,母亲委托小桂去集市采购日用品,心情低落的小桂紧紧抱着不怕人挤入了集市。她不喜欢这样人多的地方,她觉得自己的胃拧在了一起,细小的沙粒填塞碾压这胃壁,涌上了喉口。‘我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她把帽檐向下压了压,加快了脚步。
意外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青色的耀眼光芒本应是希望与喜悦的代表,但在这时,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伙伴逐渐发生变化,发生自己不希望的陌生变化。
不怕人进化成了水精灵。
她的梦想破碎了。
从进化的那天起,不怕人钻进了院子的小池塘里,再也没有出来过。
她也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哪里都不去。
小桂不知道自己在生什么气,如果自己只是想要草精灵,就该在柚让给她自己培育的伊布时开开心心的收下,重新开始培育起来。但她也只是推回了精灵球,继续在自己的屋子里闷着。
她的房间窗户正对着池塘。她有时可以看到水精灵浮出了水面,远远的望着森林方向,一段时间后再一个甩尾消失在荷叶下。她只是静静的看着,什么也没有做。
今天吃完饭,她再一次习惯性的看向池塘方向,只是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她们对上了视线。
随后水精灵再一次沉入了水中。
失望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她,眼睛好涩,在不断眨眼的过程中苦涩的海水即将溢出。
……随着巨大的水声,有物体炮弹一般飞入空中。
强劲的鱼尾带来了极强的推动力,水精灵在空中自如的扭转着身体,珍珠白的鱼鳍划出优美的弧线。同时使用的水枪技能在空中转了一个圈,小水珠散布于空气中,在阳光的照耀蒸发下闪闪发光着化为了彩虹。
这是桂和不怕人练习了好久的华丽大赛招式。
“再使用高速星星!”桂激动的探出了身子,仍沾着泪水的脸上洋溢着未曾有过的笑容。
作者:关节
Mode:随意
是同人复健,原作是漫画《DOUBLE》,很冷门,没看过原作可能会有一定阅读障碍……但还是非常欢迎写作方面的指导(如果有的话),本人心脏很强不怕被批评。
宝田多家良,三十岁出头的新生代演员,长期借住在邻居家中以至自己的房间疏于清理,变得拥挤而凌乱,只勉强留有铺榻榻米的小片空地,其他空间则随意地堆放着长期积存的各种杂物,给搬家收拾行李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多家良从来都不擅长整理打包,幸亏还有好邻居鸭岛友仁帮忙。房间不大,多家良环视一圈,把风扇旋钮调大一档。
“这个箱子你还留着啊?”友仁大汗淋漓地起身,从房间角落高高的一垛Jump周刊底下拖出一个黑色手提箱。“拉链好像有点坏了,”他把箱子表面的落灰擦拭干净,试着开关几次,“你还要吗?还是要我帮你丢掉?”
全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多家良立马举手:“不要丢!我还要!”
友仁回头看他一眼,随后见怪不怪地把箱子递过来:“行,小心被拉链夹到手。”
虽然翻出这个箱子纯属意外,但多家良几乎瞬间就想好了要在里面放什么东西。第一次站在这栋低矮公寓楼前时,他手中提着的正是这个手提箱。那时的宝田多家良的所有财产除了箱子就只剩一个装得半满的双肩包。头发被漂成浅金色的鸭岛友仁招手:“我来帮你搬东西吧!”说着接过箱子,掂一掂,“很轻的,没关系!”
二十岁的多家良着急地比划几下,想表达谢意。箱子当然很轻,里面装着几件当季的换洗衣物和两块毛巾,除此之外大概只剩一腔少见的勇气与固执。回望过去,仅因几句写在记事簿上的请求就把从没有表演经验的他收入剧团的水野英雄可谓相当草率,更何况多家良那时还饱受失声症之苦。鸭岛友仁则更是一副完全没把新同事的病症放在心上的样子,很兴奋地给多家良介绍剧团前辈,带他一起喝酒,听说他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又热心地给他介绍房东,帮他搬家。友仁指指二楼某个房间门牌上的“宝田”对他说:“你以后就住这里。”又指指隔壁房门上的“鸭岛”:“我在你旁边,无论是生活还是表演,有问题都可以来敲门。”
从此多家良果真常常去敲门。好邻居鸭岛友仁给他做饭,教他演戏,陪他读剧本,为他打点生活中的一切。他的失声症大概在搬进公寓的一周后痊愈,然后就和任何一个新人演员一样,从龙套演起,渐渐可以出演戏份少的配角,再然后可以和鸭岛友仁同台演出,时至今日,他已经可以承担剧团中诸多保留剧目中重要的配角角色,甚至比友仁扮演的角色戏份更多。对于他的飞速成长,友仁似乎毫无怨言,十年如一日地陪他钻研剧本,设计角色动作,在他有其他电视剧龙套要拍摄时代替他排练。写满笔记的剧本越垒越高,多家良就这么一步步出演晨间剧,客串电影,主演商业广告。友仁在他背后,永远一副高兴的模样,好像事情只要有关多家良他就无所不能:多家良,做得好!多家良,出门记得带手机,去剧组坐车不要坐过站!
这次搬家是冷田小姐的意思,出乎多家良意料的是友仁竟然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决定,并且看上去不打算和他一起住进新家。他试探着问:要不还住在这里,换一扇能遮光的窗帘就行了吧?反正房间也小,拉上窗帘外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铁面无私的冷田小姐解释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他的住址被暴露,不搬走以后会有无尽的麻烦找上门。他求救似的看向友仁。友仁正色:小心为上。经纪人小姐在旁边点头:小心为上。
小心为上,多家良把这四个字在嘴里翻来覆去咀嚼几遍。总之搬家就这样不容拒绝地定下来了,演员本人在其中并没有太大发言权。深夜他躺在地上盯着天花板,心中不免有些埋怨:连遭到狗仔跟踪的自己都还没有说什么,友仁凭什么擅自决定让他搬走一个人住,凭什么丢下他不管!可这点不满很快就被愧疚如海潮一般掩盖过去。对于友仁的无私帮助,他之前都习以为常地全盘照收,可最近几个月,准确地说是确认出演黑津导演的电影以来的几个月,他越发频繁地如此刻一样感觉羞愧、自责、无以为报。黑津导演对他的责骂他没敢告诉友仁,因为怕友仁伤心;好不容易拍出令导演满意的片段,他又忍不住担
心友仁将来看到这一段会作何感想,会觉得他演得好吗?如此这般,他总是担惊受怕,冷田小姐有天被他的脸色吓了一跳。那天冷田小姐来给他送剧本,最后竟演变成了带他在咖啡馆喝咖啡。冷田小姐对于处理情绪不稳定的多家良已然经验十足,边拿出手机给友仁打电话边问:你还好吗?是又被黑津先生批评了吗?
多家良摇摇头:不是。先别给友仁打电话——
冷田放下手机:怎么了?
多家良低下头,不敢与冷田对视:打电话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他现在应该在便利店打工吧,还是不要麻烦他了……
就是这样。多家良知道与同龄人相比自己也许显得单纯甚至幼稚,他总希望友仁永远和他在一起,可无论是信赖的经纪人还是崇拜的导演,抑或关系匪浅的同僚,甚至包括友仁自己,好像都希望他能一个人独立地做出点什么。具体要他做什么呢?多家良不知道,也无从得知。想到明天的搬家,他辗转反侧,眼前总浮现出友仁靠在他新家阳台边的背影。友仁以后只会偶尔在他家过夜了。
红灯亮起,川上先生借给他们的面包车摇晃着停在斑马线后,后座上的箱子柜子随惯性向前,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多家良回头检查:自己的那个黑色手提箱好好地待在车厢左侧,摞在友仁去年新买的大箱子上面。友仁说他以后不免要跟随剧组去全球各地拍摄取景,所以给他换了个据店员说“用十年都不会坏”的高级行李箱。他重新坐好,正对前方,余光还瞄着友仁。友仁正摸着下巴盘算,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可多家良还是听清了:等会要再开车跑一趟,把停车场里社长送的健身器搬过来,不然继续在露天淋雨早晚会生锈,多家良你一个人住要记得锻炼身体,保持身材……
“记住我说的了吧?”友仁再三确认。
多家良郑重地点点头。
“对了,你之前那些剧本都收在哪里了?如果落在书架上我等会顺路帮你带过来。”友仁说。
“我收在箱子里了。”多家良看向窗外。远处大楼的电子广告屏上正播放着NEKE新商品的广告。
作者:贩卖机
那是发生在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的我还只是个除了学校,对一切都分外感兴趣的小学生。嗯……硬要说的话,就是那种连路上的石子都得研究半天的小孩子吧。
那时我去学校所走的,是一条在居民区中绕来绕去的小路。比起走出小区,规规矩矩沿着柏油马路一直走,这条小路实际是要绕远一些的。但由于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周围又有许多小伙伴居住,可以结伴在道路上毫无顾忌地玩耍。我便一直经由这条路来回。
那条路经过一大片空旷的荒地。虽然以现在成年人的角度去看,恐怕不过是块只有足球场大小,一眼便能看完的杂草地罢了。但在小学时代的我眼里,大约有一整个公园那么大的面积。
在我对童年时代所剩不多的记忆中,一间荒废的铁皮屋,半截红砖墙,还有齐腰深的杂草中的各种昆虫,是我消磨时间的好去处。
我想那应该是春天开始不久的事情,草还没有长到可以掩盖地面的长度。那一天,在砖墙下,杂草之中,我发现了一个手提箱。那个箱子很新,外壳是银白色的,看上去与电视剧里的劫匪交易时会用来装纸钞的箱子一摸一样。它在太阳下反射着银色的光,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我被它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不由得停了下来。
毫无缘由地,我有一种想要触碰它,想将它打开的冲动。
我在手提箱前蹲下身子,手慢慢地伸向它,就在这时——
“嘭、嘭、嘭”手提箱中传来三声短促的敲击声。
我吓了一跳,手指僵直地停在仅仅一个指尖的距离。
“咚。咚。咚”又是三次敲击声,不过这次的间隔略长。
手提箱里有什么东西在敲打着箱体,对未知的好奇使我兴奋起来,但同时也让我对这个箱子产生了一些害怕的情绪。
万一——那箱子里面的东西跳出来攻击我怎么办?
我默默地与手提箱对峙。
“嘭、嘭、嘭”仿佛是察觉到我的迟疑,箱中之物再次敲击起箱壁。
“喂——你在那里做什么?快走了!”这份沉默很快就被不远处小伙伴的招呼化解了。
“来了,来了!”我赶忙小跑着离开。
但我的好奇心并不会因此停止,第二天经过荒地,我鬼使神差般地走向前一天发现手提箱的位置,那个箱子还在。
我停了下来。箱子仿佛察觉到有人在旁边一般地,动了一下。
对,没错,它,动了。似乎是内容物急着从手提箱内逃脱出来一样的,动了。
而后,箱内传出急切的拍击声和抓挠声。
那东西急切的想要从箱子里出来,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抓挠箱壁的声响越来越急切,越来越用力,甚至像极了指甲刮在黑板上的声音,刺耳而令人恐惧。我心生退意,再一次地,从它的面前,逃跑了。
之后的几天,我都选择走无趣的大路,只为避开那个奇怪的手提箱。
直到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心不在焉的走在放学路上。天空阴沉的厉害,似乎快要下雨了。正当我边走边想着无关紧要的小事的时候,我的脚边传来嘈杂的人声,其间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哭声与怪异的笑声。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居然不知不觉中又走到了那片荒地,而那些奇怪的声响,正是从我脚边的手提箱中发出来的。
我再一次的燃起了打开它的冲动。
这冲动不断地催促着我,我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树枝,慢慢地、慢慢地向手提箱伸去。
我屏住呼吸,树枝的尖端一点一点地接近手提箱,各种各样的声音从手提箱中一齐发出来,机器轰鸣声、蜂鸣声、尖叫声、咆哮声、笑声……它仿佛为即将被打开而雀跃不已。而在这嘈杂声中,我紧张的仿佛听得到自己的心跳。
树枝更加的靠近了。
“喀嚓!”
与闪电同时发出的突如其来的惊雷使我丢下了手中的树枝。手提箱突然沉默了,它安静地看着我,我看着它,那种无法退散的莫名其妙的冲动促使着我再次伸出手去,“喀嚓!”又是一声雷鸣,伴随着这一声雷,黄豆般大小的雨点哔哩啪啦地砸向地面,同时也砸掉了我打开箱子的冲动。
我顶着狂风暴雨跑回了家,身后是依旧不断的雷声和细密不绝的雨。
这场雨一直下,直到第二天。那一天是周末,窗外的雨已经变成淅淅沥沥的小雨。
不知为何,我居然迫切的想知道手提箱在雨中怎样了,于是我随便编了一个什么理由,跑出门去。
手提箱还在原地,只是已经在一夜的风雨中完全湿透,变得破破烂烂。周围一圈的草与它的外壳都仿佛被烧过一般的焦黑。手提箱打开着,里面空空如也,除了存留的雨水之外什么都没有。
备注:就这样吧。电脑卡的我不想写备注。
_(:3」∠)_虽然说真的只是个普通的都市怪谈。但是似乎由于最近在听一些up讲鬼故事的缘故不知不觉写了个这种风格的玩意。
_(:3」∠)_写到一半感觉。啊。好像有种放了个【期待许久的东西结果打开之后啥玩意都没有】的核的感觉。
_(:3」∠)_但真的一开始没有这样的意图啦。
_(:3」∠)_只是普通的怪谈故事啦总之。
_(:3」∠)_这个月也在艰难努力的不咕咕。
评论要求:笑语/求知
作者:月溪明
评论要求:笑语
慕年坐在公园长椅上,下午的阳光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热意似乎传进了心底。
慕年静静坐着,一动不动,眼睛却一直注视着不远处。
那里有一排树。
现在是春天,万物开始萌发,光秃秃的树枝上也开始冒出点点青绿色的小芽,柔柔软软,看起来虽然弱不禁风,却饱含生机。
树的后方是一片沙滩,沙滩上有一群孩子们开心地玩耍着。
那些孩子年龄最小的只有一两岁,最大的有十岁左右,他们兴高采烈拿着塑料小铲子和小桶在沙滩上挖来挖去,一会挖出一个坑并往里面倒水,一会双脚踩进坑中,用沙子把自己的脚埋起来,玩得不亦乐乎。
沙滩上又来了一个小孩,他带了一架大约两个篮球大的玩具挖土机,操纵这挖土机行驶在坑坑洼洼又崎岖不平的沙地,嘴里发出轰隆隆的配音,显得气势十足。小孩时不时转动着挖土机上自带的铲斗,这里铲一下,那里铲一下,虽然挖沙子的效率并不高,但是跟其他小孩手中的塑料铲子相比,显得更高级一些。
别的小孩看着眼热,纷纷围在玩具挖土机周围,想要过一把玩挖土机的瘾,那小孩犹豫着,不太愿意分享帅气的挖土机,其他小孩便七嘴八舌说可以把自己当玩具借他玩,还可以帮他建造他想要的东西,于是那小孩点头答应了。
这群原本互不认识的小孩迅速打成了一片,准备齐心协力在沙滩上打造一片城堡群,他们忙得热火朝天,欢笑的声音回荡在公园上空。
慕年一直坐在长椅上,看着小孩们从无到有在沙滩上堆砌简陋的城堡群,还挖出连接一座座城堡的沟槽,把从人工湖里舀来的水倒入其中,形成连通的河道。
小孩们摩拳擦掌,准备再接再厉地在城堡群外围挖一条护城河,但工程刚刚开始,他们的父母便招呼他们准备回家了。于是他们依依惜别,约定第二天继续一起挖沙子。
该回去了,慕年想着,不然等会天色变暗,眼睛看不清,会更容易摔跤。
他拿过放在一旁的拐杖,吃力地依靠它撑起自己的身体站立,然后慢慢地往公园出口走。
公园外面也有很多人,他们大概十二三岁,穿着相同的衣服,沿着相同的方向走着。慕年知道,他们是公园附近那所初中的学生,现在是他们放学的时间。
学生们叽叽喳喳,分享着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讨论着同学和老师的八卦,商量着回家后一起开黑。他们行走在路上,就像在一条湍急的河流,河水流淌间发出激昂的声响,生气勃勃地前进前进在前进,在道路的尽头分道扬镳,奔向各自的远方。
但这只是暂时的分别,因为再过两天,等到周一,不,等到周日晚上,他们又会再见。
慕年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环绕周身的电影荧幕中间,看着周围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充满着人间烟火气,可这一切的热闹,都与他无关。
他就像一个透明人。
慕年站在一旁,等学生们走得差不多了才继续向前走。
慕年走得很慢。他准备离开公园的时候,天空非常明亮,阳光也很温暖,但当他走到离公园不远的小区门口时,太阳已经西下到了接近地平线的地方,黄昏的光芒落在他身上,却没有像之前那样给他带来热量。
慕年感觉有点冷。
现在是初春,气温才刚刚开始回升,但并没有脱离寒冬的冷意。
慕年正准备走进楼道口,突然有个小小的身影从他身边一溜烟窜了过去,差点将他撞倒,幸好慕年习惯性靠着墙走路,这才避免倒地不起的结局。
“彤彤,你跑那么快干嘛,差点撞到这位爷爷了,快点过来道歉!”
随着一声大吼,身后走来一对夫妇,他们露出歉意的表情,带着跑回来的孩子给慕年道歉。
慕年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什么大碍,那对夫妇才放下心。
慕年目送他们进入电梯,隔着电梯门,听到他们训斥孩子的声音。随着电梯显示楼层的变化,声音也渐渐消失。
慕年原地站了会,再次抬脚,慢慢走到自己位于一楼的家门前,摸索着掏出钥匙开了门。
门内一片黑暗,他在墙上摸索了一阵,找到开关,啪的一声,客厅灯光亮起,映入眼帘的是他的老伴带着笑容的脸,只是,是在墙上,是黑白色的。
“我回来了。”慕年轻声说。房间很安静,他的声音非常清晰。
他回身关门,黑色的木门缓缓靠近门框,砰的一声关上,暖黄色的光线被门阻隔在房间内,只剩下漆黑,就像盖上棺盖的棺材。
(想写出随着年龄的增大,社会关系逐渐死亡的感觉,但是好像失败了┭┮﹏┭┮)

作者:原殊
免责Mode:笑语
我在火车上注意到了那个人。
这并非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之处,单纯是因为我喜欢观察别人的习惯罢了。为了不让他们觉得冒犯,我一向将那种目光掩饰得很好。虽然这次停留的时间长了些,但没想到的是他已经直直向我走了过来。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在想视线会不会也是某种实体,然后准备好解释的话术。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把手提箱放在中间横亘的桌子上——我的视线又不由自主地转了过去,要知道对于一个这方面的强迫症而言,一个圆角的手提箱是怎样的能够扰乱我的心情。我发誓没有什么比四角方方的东西更好了。
但他并没有再说多余的话,只是靠在椅子上低下头,被竖立起来的手提箱遮挡住面庞。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或许是他的座位,因为以前的购票习惯让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要不是手机不能用我也不会来现场买票,要不是现场买四张票太过奇怪而我又不习惯于特立独行,我也不会和别人坐在一起。
我有些烦躁地抓了抓脑袋,一只手按压着另一只手的指节。彼此都处于视线死角,我便放肆地打量起眼前的手提箱来。这并不是常见的造型,手提箱的转角都相当圆滑,外面用真皮包裹着,几乎不见一丝褶皱,反射着列车内有些惨白的灯光;而把手却又棱角分明,如果装着什么重物提起来,想必能把手掌磨出青紫的痕迹。
车站的广播适时响起温馨的提醒,列车再过十分钟就要发车了。
“先生,需要帮您把手提箱放上架子吗?”路过这里的服务员客客气气地询问,我松了一口气,虽然盯着这个手提箱看了很久,但也并不与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让它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相冲突。
他抬起头,伸手将手提箱抱进怀里然后摇了摇头:“不必了,我拿着就好。”服务员没有多做表示,于是绕过他,然后帮我把沉甸甸的行李箱摆上了架子。
看来我只能与这该死的手提箱共度两天的旅程了,我叹了口气。但是总不能在这种事情上干涉别人。我只能靠在椅子上半闭眼睛,实施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战略,虽然这样需要牺牲的就是我的好奇心,但人的欲望总是难以两全,两害相较取其轻便已是上策。
这个故事到现在都还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小小牢骚。我先对愿意忍受我絮絮叨叨废话的人表示感谢,是这些人让我多了两百块的稿费。
那么转回正题,真正让我记住那个手提箱,是在晚上我模模糊糊醒来的时候。我本来打算很快又睡过去,但是此时我的对面传来了断续的低语,那些声音并没有传到我的脑海里变成可以理解的词句,却足以吸引我的注意力。他低头看着手提箱喃喃自语,当时他脸上的表情——不夸张地说,就像情人的缱绻。
许是终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他有些歉意地看向我,为了消除奇怪的误解向我解释:“这是我的挚爱。”
当然我并不觉得这能消除误解,不如说向那种常见的恐怖情节更进一步。而看着我震惊的表情,他哑然失笑,语调也带上一些调侃的意味:“怎么,你以为里面装着的是一个尸体?对一个手提箱来说这有些过于为难了,哪怕是四肢扭曲的婴儿也不能放下。”
我勉强点了点头,不得不接上话茬:“那这里面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恋物癖,我并不礼貌地想着。
他打开手提箱的锁扣,将里面的东西完整地展示在我面前——那是一个人偶,做工精细而考量,脸上绘制着淡淡的红晕,人偶闭着双眼躺在手提箱里面,周围铺着柔软的缎面,宛如一位刚陷入沉睡的少女。
“她叫莎曼缇菈。”他用手指轻轻触碰着人偶的面颊,眼神无比温柔。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尚还只是高中。您知道的,所有的高中都大同小异,总会有那么一条堕落街。而我的高中正好处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附近还开了一家手工的人偶专卖店。
“我偶然地隔着橱窗看着她。
“偶然,纯粹的偶然。说实话我上学的时候并非一个好学生,数学和物理,在我看来只是枯燥无味的数字和符号而已。然而,在那一瞬间,我理解了那些纯粹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的感受,公式的简洁,宇宙的浩瀚,为一瞬的灵感耗尽终生,何等幸福。
“只那一瞥便让我停下脚步。啊,怎么描述呢——她的发丝如瀑布般垂泻,她的双手优雅地交叠,她的笑容是恰到好处的温暖,她的眼眸如湖海般宁静深邃。
“我以前经常听到关于那家人偶店的闲谈,他们说那里的人偶栩栩如生,封印着纯洁少女的灵魂。咳,您知道中二的少年有多么热爱幻想,而还有一种中二是对这种幻想嗤之以鼻,比如说我。
“事实上看到她的时候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那些人实在是大错特错。灵魂并不是什么高贵之物,那样的人偶怎么可能活着呢?只有死寂与冰冷才能构造出那样的疏离的美丽,将之与人类作比简直是对她那双无机质的眼瞳的玷污。
“当然……我当时并不觉得这会影响到我的现实生活,只是为找到了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而兴奋不已。简直就像触类旁通一样,我还爱上了数学、物理、包括生物,每个老师都为我的转变欣喜不已。每当推导着那些公式,剖析着动物的机理,我都会想到那个人偶…那份幸福感让我近乎哭泣。
“然后我考上了还不错的大学,拿着用成绩换来的奖金去人偶店买下来那个人偶。店员们说她是最昂贵的,也还好我提前预订,不然定会被某些收藏家给带走。我给她取名叫莎曼缇菈。
“大学的生活相当平静,虽然只是按部就班的生活却令我心满意足。我也交到了女朋友,忘了是谁主动,或许是我先约她一起做课题的?总之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还是室友拿我们两个做调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的。
“你的表情怎么这么古怪?不,我并没有欺骗她的感情。我想我确实是爱她的,我可不是那种每天对着人偶想入非非的变态——那大概是一种极端的向往吧——自然也会有正常的恋情。她不爱笑,但笑起来必定很好看。她是一个性子有些冷淡的人,这刚刚好,她的锁骨上有着蝴蝶的纹身,她能沉默一天不开口,但相处的时候,她有问必答。
“她是完美的……有段时间我这么想。和莎曼缇菈不同,那是另一种完美的形式。而我同时拥有着它们,似乎也能助我的灵魂脱离泥沼,升向高空。哪怕付出生命,又算什么代价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我再想想。大概是她第一次质问我为什么晚归开始吧。那天晚上我到底做了什么我也忘了,但是她愤怒而脆弱的表情却是如此清晰。而我,感到的却是无比的恐慌,那样的表情与她太不相称,像一个虽然微小却无法忽视的瑕疵。
“而有一天,她在我面前哭着向莎曼缇菈砸向地面——她没有坏,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但我仍清晰地感到了那种几欲令人作呕的厌恶感。我清晰地明白,如果我不做点什么,我会同时失去我所有的。
“从那以后我再难以去爱,她总控诉着我的背弃,可她的愤怒是如此丑陋可鄙,致使她的呼吸也令我厌恶。有几天我甚至觉得,莎曼缇菈也会用那双眼谴责我,谴责我寻求另一个灵魂的荒谬做法。那并不需要不是吗,第一次面对莎曼缇菈的澎湃激情又在我的心中回荡。我可爱的女朋友,害她变成那样的是我,我无比怀念她淡漠的神情。我明白这是我的错,我有责任让她变回一开始完美的时候。
“当然,我做到了,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我又迷恋上了爱情。莎曼缇菈…又不只是她,无论我经历过多少旅程,我的挚爱都将与我相伴。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先生,先生,你还在听吗?”
那一晚我没有听完整个故事,因为待他讲述到一半我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我甚至难以分辨后面的故事是从他嘴里讲述出来的,还是我的大脑自动编造出的合理理由。我其实并不及得那个男人的脸了,然而那个手提箱令我印象深刻。是的,一个圆角的手提箱让我难以容忍,而当那个男人下车与我分别之后我才想起来,我到底为什么无法从那个手提箱上移开视线。正是在那个圆角处,有着无比美丽,仿佛要振翅欲飞的蝴蝶花纹。
但起码我与他还是有共同之处的,看来我们都些有强迫症。因此我决定不对这个故事进行更深的探究。这只是一篇旅途之中的平常见闻,或者是用于大家围在一起讲述鬼故事时的小小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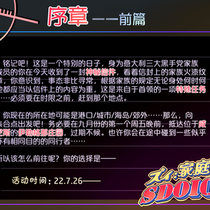

评论要求:笑语
“那是很久以前人类的文明。”
由纪子插下一朵兰花,这只花篮终于完成。接着她熟练地剪下丝带,素白的手指翻飞间,梅特迪安能看见那些柔软鲜艳的飘带温柔地缠绕上竹筐,就像蛛丝裹上猎物的身体。
川雪如同幼猫一样腻在梅特迪安的颈窝处不肯下来,明明屋子里暖气烧的很旺,梅特迪安还专门把被炉开到了最大,但是从纸门缝里透过来的寒风依然带来了几丝寒意。
“拜托你了,梅特迪安。”
川雪在他耳边不满地大声嚷嚷,被他一把丢给母亲。梅特迪安取下自己的皮袄,转身看见化身黑色圆团的剥皮行者在被柔柔摸了两圈后软乎乎地化成一滩,摊在女人的膝盖上哼哼。
“妈妈,我出门了。”
此时正值冬季,山谷间的小镇比山下还要冷上几分。梅特迪安出门时,今年的第一场雪堪堪落下,万幸雪势不大,梅特迪安把兜帽往头上一甩,捧着花篮走在安静的街道上。
很少会有阿拉克涅喜欢冬天,在旧时这不光意味着猎物的稀少,更代表着迟钝僵硬的关节和愚钝的反应速度。饥饿与迟钝,对于所有猎手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偶尔有几户人家的门敞开着,孩子蹲在门口玩,大人就在身后看着。年幼的阿拉克涅不知道怎么收起爪子和眼睛,两只明晃晃的眼睛在额头上四处张望,和孩童体型相符的纤细勾爪七扭八棱地堆在背上。蜘蛛对震动和声音敏感,孩子抬起头,看见梅特迪安,咧着嘴就笑起来,颊肉肥嘟嘟的,连额头上的两只眼睛都弯成月牙。
看着孩子的女人对梅特迪安挥了挥手,招呼孩子进屋吃饭去了。被裹得圆滚滚的孩子咿呀笑着,像个圆滚滚的小雪球一样。
“师傅,师傅!”
梅特迪安站在道场外面喊着,寂静的街道上他的声音散开来。
“下次告诉由纪子,不要再送了。”二楼的木窗推开,一个小老头倚在窗户口。
“孩子都来了,说什么呢。”道场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和蔼的胖妇人一边迎梅特迪安进屋,一边对着老头喊道,“正好也要到午饭时间了,留下来吃一顿再走吧。”
屋里的暖气直接烘上脸颊,梅特迪安觉得身体都软了。师母盛情难却,梅特迪安也就恭敬不如从命。
今日的道场并未开放,只有师傅和师娘两人。锅子在火上暖烘烘地炖着食物,热气蒸腾开,散发出野鸡和野菜的香气。
"前几天去的山上采菜,正好打了一只野鸡。"师娘盛出一碗放在梅特迪安身前,又从壁炉里拿出一个罐子,捞了点萝卜咸菜放在小碟子里,"为了好吃,又喂了几天,肥了不少。"
"你师娘就知道多事。"师傅没好气哼了一声,捧起碗默不作声地吃着。
梅特迪安轻轻闻了一下,鸡汤鲜美,野菜清新,并没有油腻的感觉。
饭后师娘还想留他吃点小点心,梅特迪安见是在不能留了,只好推脱,借口下午还要诶母亲练习新的曲子,不走可能要来不及了,这才被师娘放过。
回程的时候雪已经停了,几个孩子溜出来打雪仗,小小的爪子背在身后,一晃一晃的,在雪球上乱挠。有的人家趁着这个时候出来扫雪,丈夫用爪子抓住铁锨,铲得飞快。梅特迪安念着要和母亲下午练习,加快了脚步。
每年他再回到这里时都会想起这些。
村子早就不在了,连建筑都在那场火中全部化作灰烬,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墓碑。几十年风吹日晒下,墓碑的边缘已经风化,爬上了青苔,连上面的刻字也有些模糊不清。
如今除了自己,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来到这里。父亲以前还会因为悼念母亲前来,但是在他阵亡牺牲后,这里就再无人悼念。
梅特迪安在墓前放下花束,眼前飘过一个白点,他下意识抬头,只看到雪花簌簌飘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