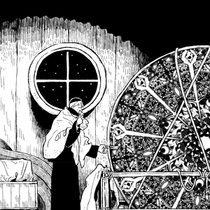12月13日,周五。晴。
养狗的中年人的一天从湿漉漉的狗鼻子开始。Molly今天也准时上楼,大摇大摆地走进Collins夫妇的卧室并爬到床上,要求Davis带她出去散步。儿子搬出去后的几年间虽然还是经常回家,但Collins太太还是觉得寂寞,便有了Molly——今年5岁的金毛犬。提出养狗的是Collins太太,但Davis多年来晨练的习惯让Collins太太理所因当地把遛狗的任务交给了他。
Davis撸了两把Molly的脑袋,转身给了还在睡梦中的太太一个早安吻,然后起床下楼放Molly去院子里。待他穿戴整齐,就牵上Molly走向离家不远的Morgue公园。Morgue公园中央的大湖周围都是步道,正好可以成为Davis遛狗顺带晨练的路线。Davis每天早上带着Molly绕大湖跑一圈再回家准备上班,除了有紧急工作时外风雨无阻。偶尔Collins太太也会加入,两人一狗就会沿着湖岸慢慢散步到公园的另一头吃早餐。
Collins夫妇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结婚也有20多年了。Collins太太从小身体就不好,两人结婚后医生也建议,以她的身体条件最好不要勉强她生孩子,儿子是后来领养的。收养那孩子之前的几年Collins夫妇一直持续着幸福的二人世界,Davis也没感觉到孩子的必要性,结果后来儿子搬出去和恋人同居的时候夫妻俩倒是觉得寂寞得不得了。Collins太太隔三差五要不是自己跑去儿子的公寓,就是打电话强迫儿子过去吃晚饭,偶尔还逼着Davis带着儿子会喜欢的杂七杂八的小东西去上班好交给儿子。
“Dave工作的时候还能见到那孩子,可我每天在家里没有他陪我还是很寂寞的啊!”Collins太太如是说。
Davis表面上嫌妻子对儿子过度保护,实际上偶尔会在午休的时候偷偷溜去儿子的办公室看他两眼。
说起来那孩子最近好像胖了,带着黑眼圈上班的情况也少了不少…看来是有在好好吃饭睡觉。Davis在心里不情愿地夸了两句儿子擅长做甜点的恋人,不得不承认,在烘焙方面Collins太太确实并不是非常成功——虽然她做的饭真的很好吃。
Davis回到家时早餐已经在桌上等着他了。
“今天是周五呢,下班之后要是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们去看电影吧?”Collins太太笑眯眯地看着Davis切他的煎蛋卷。
“可以啊,你有什么想看的么?”
“嗯,最近有些想看的…今天我会查一下场次的。”
“那我下班回家后回家接你?”
“我去警察局等你吧。”
“好,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提前给你打电话的。”Davis起身准备餐具,Collins太太早他一步把盘子放进水槽,把Davis的公文包递给了他。
“路上小心。”
“我爱你。”
“我也是。”
每次和下属的Sean说起家里的时,这位单身青年总是一脸不满的样子,“Collins先生你又跟我秀恩爱!和没有女朋友的人说这种事情真的好过分诶。” 而Davis总会用嘲笑的语气说让他赶紧去找个女朋友。Sean只比自家儿子大个几岁,Davis觉得自己可能下意识把这个总是傻笑着的小子当成自己另一个儿子了。…才没可能呢,我家儿子比他聪明多了,哼。Davis立刻否定。
“说起来啊…Collins先生和Sokolov先生是同期吧?”Sean突然问。
“是啊,所以我和你这愣头青可不一样。”
“但是Collins先生到现在都没升职呢。”
“…你什么意思。”
Sean明显觉得到自己被Davis的眼神捅了好几刀,立刻补充道:“所、所以我在想…是、是不是有什么理由…比如说升职了就会调到别的城市,离夫人很远什么的…?”
“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带她一起不就好了。”
“啊…但不是还有…”
“闭嘴,上司的事轮得到你多嘴?”
“是…”
看着讪讪地低下头处理文书的Sean,Davis皱了皱眉头,“其实没什么特殊的原因。我不想升职,所以拒绝了提拔而已。”
“诶诶——为什么啊!”
“跟你说了和你没关系啊蠢蛋。”
“…好嘛。”
Davis叹了口气,“我出去抽根烟。”
“不是说要戒烟么?当心我告诉…”看到Davis的眼神,Sean立即改口,“您随意。”
Davis皱着眉头,像是逃离办公室一样去了吸烟室。那个臭小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Davis最初当上警察,只是单纯觉得警察很厉害。20多年前的Davis比现在的Sean还要单纯得多,顶着一张比当初想还不是Collins太太的Collins太太告白时还要红的脸,说着要保护喜欢的人和她喜欢的城市,报名了警校。当上刑警后的Davis也一直是个正义感爆棚的热血警察,几年间也破获过不少大案,要升职是绰绰有余的。
啊…说起来那年,也差不多是这时候。Davis吐出一口灰白的烟雾,隔着同样灰蒙蒙的窗玻璃看着外面的晴朗得不合时宜的天空。前几天的积雪还没完全融化,大约是这些积雪的缘故,鲜明的街景显得格外刺眼。
12年前的冬天,N市警察局接到报警,一个孩子颤颤巍巍地告诉接线员,他的父母被杀害了。Davis和当时的搭档赶到现场,发现那个孩子跌坐在一片血泊之中,而暗红的中央已经不成人形的,恐怕就是男孩的父母。犯罪现场小组仔细检查了现场,法医翻来覆去地审查两具尸体,Davis和搭档严密盘查,却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而那个孩子当时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什么也说不出来。Collins太太去警察局给他送换洗衣物的时候,在被布置成临时卧室的会议室里见到了那个孩子。Davis当时的搭档不顾Davis的反对让Collins太太去安抚那个孩子,虽然成效明显,但那孩子只是回家时发现双亲已经被害,对于加害者没有任何头绪。
因为太久没有新的线索,警察局要求Davis放弃搜查,将这桩谋杀记录为悬案。但当时坐在血泊里的孩子眼神久久停留在Davis的脑海中,让他无法原谅没能为那孩子找到凶手的无力的自己。父母双双过世后,也没有其他亲戚愿意收养那个孩子,Davis便和太太商量,领养了那个孩子。
“我向你发誓,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一定会找到杀害你父母的凶手,让他为他对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那个孩子搬进Collins家空着的小卧室的那天,Davis在那孩子面前蹲下,笃定地对他说。
Davis坚信,只要自己还留在这座城市,还能直接接触到这座城市里的犯罪,就一定能发现那个罪犯的蛛丝马迹。十多年过去,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年轻气盛的热血刑警了,甚至被安排了现在这样的闲职,但他还没有放弃。
“说起来…就是下周了吧?忌日。”Collins太太突然说。电影散场后天空已经完全是深紫色,可能是因为太冷,夜空中连星星都寥寥无几。Davis牵着妻子的手突然僵了一下。
“啊…嗯。”
“今年也不会去吧,那孩子。”
“为什么突然…”
“只是突然想起来了嘛。”Collins太太叹了口气,“都十多年了,他一次都没去过呢。扫墓。”
“他只是还没想通吧。”Davis伸手把妻子揽入怀中。明明早已不年轻的夫妻俩却还总是做些热恋中的小情侣才做的亲昵的动作,Collins太太的友人们总是酸酸地夸他们感情好,让她半高兴半害羞。
“到时候叫他来吃晚饭吧,我会做他喜欢吃的面。”
“别太宠着他了。”
“是是是,最最宠儿子的Dave爸爸。”
“…”
“Dave害羞的表情好可爱w”
“…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