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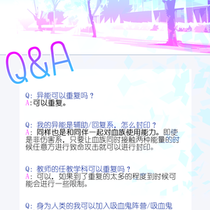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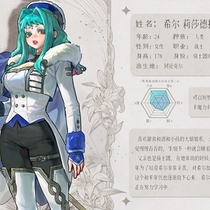


这次终于写了主线φ(゜▽゜*)♪
字数:3200
+++
一足鸟站在厕所外,心不在焉地听着里头的人交流刚看见的事儿。他胳膊上搭着周一的外套。除开兜帽里有满满一兜的彩虹糖而不是爆米花以外,一切就像任何一次电影散场后那样。
而如果要给在那个冰冷、阴暗的停尸房里发生的一切打分级,那无疑是pg-17——毫无疑问是恐怖片,但混有少量喜剧(或者说地狱笑话)元素。
首先,主角们理应是具备职业素养的、来自中国的、会功夫的道士。可他们一开场就被困在停尸房的冷柜里,生死不知,变成了没那么多戏份的特邀嘉宾。那些冷柜,在残肢断体拼凑的肉山怪物面前就像是一台台的冰箱。他逐个打开变形的柜门,像是穿山甲在找蚂蚁,不费吹灰之力。有时他会从柜中拽出什么,也有时会因柜内空空如也而敲瘪更多柜门。
而其他人呢?
手无寸铁、围在停尸房外的长廊,拿着可笑的武器和防具,像一帮发现主演罢工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上的群演。包括他,也包括周一。
通常这种情况下该有一位世外高人伸出援手,可他们能指望的“帮手”只有时在时不在的Ymir。安排这样的混乱中立外挂,导演大概是铁了心要拍全灭结局。不甘认命的群演在公共频道拼命刷屏,寻找带了符、能掐会算的道士和看起来三拳能打死老虎的功夫人。可那两个账号像是掉线了,始终没发言。
到了这种局面仍算“pg”而非“x”,是因为在任何一部,呃,更古典的邪典片里都不会有人在想呕吐时呕出大量彩虹糖。它们铺满地面,像盛满巧克力豆的容器被打破,遮掩了满地的黑红血迹。当一足鸟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倒是想过如果发生这种事该有多酷多快乐。可他现在已经25岁了,只觉得这部游戏里的设计实在是混乱得够可以。
公屏叮叮当当的提示声和停尸房里的声音混在一起,古怪得要命。这里的隔音有时特别好,有时又像完全没有衰减——至少咀嚼的声音毫无掩饰地钻过铁门到了一足鸟耳朵里。他被迫在骨骼被清脆地咬碎、骨髓被珍惜地吸出、并且从关节被用力扯断的声响里分辨出气息奄奄的求救和哀嚎。
这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他不得不绝望地反复确认口罩是否戴好了、甚至紧紧用手指按着它,尽管理论上那是一片不会掉落的贴图。
门开着一道缝,他站得不近,但或许还不够远,也许他的视力在万灵所得到了加强,否则怎么能清晰窥见怪物捏在手里的断臂断腿呢?理论上它们不会喊疼……但那就更糟糕了。人体的断肢面滴着血,人们喷涌的呕吐物却是彩虹糖。彩虹糖是真的,那么感官生出的食欲或许也是。一足鸟必须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这是vr游戏,你看到的只是没有实际气味和口感的贴图”……老实说,收效甚微。
在看见腐坏的露骨肢体时,他也看见焦红如被高温炙烤过的断面边缘;他嗅到腐臭的气味,也闻到滴落的肉汁;他看见怪物发黄的犬齿撕扯人体,也看见去除皮肤后的饱满脂肪与肌理。他的血管里似乎正生出羽毛,喙和爪也似乎又要回到身上。而他的咽喉和口腔在万灵所就已被腐肉征服,固定成了一只游隼或秃鹫,听见进食、看见“类人之物”被吞吃的场面,尽管属于人类的胃部隐隐痉挛、将胃液上逼,但冷汗似乎都向口腔汇聚,叫他口舌生津。
幸好被恐怖与美味同时拉扯神经致使两厢矛盾的大脑最后指挥身体——你大吐特吐吧!
做得还不错。喉头被颗粒物撑开时,一足鸟拉过周一的兜帽,在对方的抗议里把肝胆和食欲都吐了个一干二净。很神秘——没有血迹,没有唾液,只有 光洁的糖——他看着这些东西竟没有生出多少抵触心理,甚至神差鬼使地捻了一颗放在舌尖。东京湾已经这么做过了,但吃不知谁的代码构成的糖果,就好像吃掉了对方意识或身体的一部分。这是需要额外警醒的事情。
甜的。
咀嚼,咀嚼。和平时一样没很喜欢,真不知道谦人哥为什么会吃到得蛀牙的程度。
血肉也好彩虹糖也罢都是由代码构成,为什么其中之一变得明显更有吸引力?一足鸟试着回忆在万灵所发生的:人类,动物,几乎所有在场的生命都收到抽屉中血肉的吸引。可那样的东西难道不是圣餐吗,怎么反而带来无可救药的欲望?
……不,动物们自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食,积蓄足够的能量而繁衍。只有“人”会为“无可抑制的食欲忧心。
大师们还是毫无动静。
一些人决定逃跑,另一些决定声东击西创造救援机会。理所当然周一是后一派,他往怪物的方向丢杂物想吸引它的注意力,而一足鸟把他拉扯到房门边的走道,用CD机的一角猛敲墙面制造更多噪音。
怪物要冲到他们面前也就是20秒的事,一足鸟平时不会掺和进这种混乱局面——就算在逃生游戏里,他也是更倾向于独自逃跑的一派。周一会说“等等兄弟我来捞你”,而他说得更多的是“See You”——他的道德只到看见““英雄”被“暴徒”暴揍不会笑着录像发到社交平台。柯蒂说“你们是英雄”,一定是有哪里搞错了。
只有一小撮人真的不假思索在做勇者。年龄越小的越这样,中二病和勇者只有一线之隔。也有些人不那么小了但天生有颗侠义心肠,遇事不决搭把手。
中国似乎特别流行这个。
一足鸟望向周一。后者向他投来一个“好兄弟够义气!”的眼神,砸得更卖力了。
……有点抱歉。
一足鸟转而去看其它地方。
很难和周一解释他只是由于已经处于被兽性入侵的状态,唯恐再不多做点“人性所致”的壮举恐怕会被同化得更快,故而为不沦落到四足爬行而在努力。
看看那个以人的形体扯了肉吃的程序维修员吧!他的眼睛根本要黏在怪物身上了!
有人冒险关上了停尸间的门。过了片刻,恬静微笑着的“前台管理员”从里头走了出来,朝躲躲藏藏的群演们浅浅鞠躬。公屏消息慢下来几秒,随即刷得更快了:
【她不是在简的背包里吗?】
【在的,ZIP格式】
【现在出来的是什么?】
【她就是刚才那个怪物吗??】
没人敢拦着她问是发生了什么事,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像抱换洗被褥一样抱着一堆血肉进入了卫生间,又两手空空回到“工作岗位”。再过了会儿,停尸间里又伸出四只手,齐齐把两扇大铁门掰得更开——黑白中国人一左一右闪亮登场。
“摆摊!宵拐!你俩没事啊!”欢呼的人们迎上前去,而公屏消息中突然刷出好些发送时间为数分钟前的图像。
——肉山怪物翻找停尸柜胡吃海喝。
——肉山怪物从自己身上撕下多余的手脚。
——嶙峋的怪物吞吃从自身扯下的部分。
——它剔除几乎所有的多余,变成“她”。
——前台小姐抱着多余的血肉离开停尸间。
一足鸟猜想这可能是某种自洁型杀毒程序,只是它的呈现形式过于直接……不过玩家曾用过的载体居然也是病毒的一部分吗?幸好分开送的第二具尸体并不在这里。它在他和周一的房间安睡,不日便要被他们送进奇观所的集体墓地——只要他们没有因其它原因死于非命。
群演们也很快接受了这件事。在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带领下,人们浩浩荡荡地挤进厕所型谜象的内部开始探险,人们的惊呼声和谜象的赞颂声此起彼伏。同样不容忽视地还有快要从厕所最末的隔间喷薄而出的血肉。女高中生们在和谜象谦虚,周一在和谜象互夸,白川奈奈的哽咽夹杂在大笑间。还有人在气急败坏地喊““别说啦!”。
明明有那么多纷纷扰扰的声音,一足鸟却痛苦地发现占据自身最多注意力的是卫生间里飘出的香味。他只看了一眼就缩回脑袋——有些人正捧着血肉往隔间内塞——像个拒绝陪孩子登上儿童小火车的家长。
他往嘴里又丢了几颗彩虹糖,飞快地 机械地咀嚼。
甜的。甜的。酸的。甜的。
有个人弓着背走出厕所。一足鸟注意到,那是同样在万灵所吃了肉的维修工。他的喉结在频繁地上下挪移,像正被使用的粘毛滚筒。
“想抽烟……”他因一足鸟投去的视线含糊地解释了半句,又在看到他的黑色口罩后戛然而止,转而身体贴着墙往下滑,叹息着像只大狗一样蹲坐在地。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不住搓动,像那儿夹着根看不见的烟。
一足鸟垂着眼看他:”你怎么样了?“
”我吃了一块分开送。“维修员牛头不对马嘴地说,“很香,口感像生牛肉。那台料理机真的不错……你那天是不是没留下?很可惜啊。”
一足鸟闭紧嘴。
或许他该规劝对方别做这些出格事。但这是“游戏”而非“现实”。
“我好饿啊~你也是吧,不想填饱肚子吗?”维修员是个大个子,无论何时喊饿都合情合理。一足鸟看见他健康的牙龈和牙齿,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似乎是在笑。并不泛黄反而森白的牙齿嵌在粉色的肉里,让他看起来像只追猎失败的野兽。他的肚皮还是空瘪,但野性得以释放。
他们都知道这种饥饿要如何缓解,但一足鸟只是掏了把糖,分给他。
他往自己嘴里也又顺手丢了一颗。
……是绿色的,好酸。

